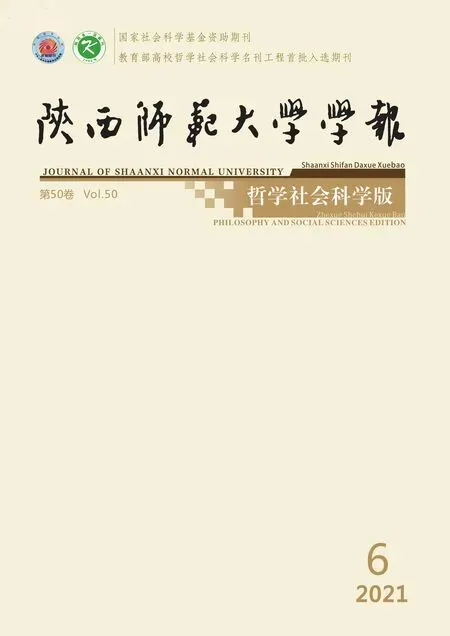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姜 涌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1)
“共同体”概念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一个颇具影响的概念。实际上,共同体思想从古至今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含义和学术含义都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这一哲学“运动”兴起,高举“复兴共同体”的大旗。美国社会学家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西方世界正处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冰冷时代,因而期盼共同体的温暖和人性关系的复苏(1)相关论述参见Amitai Etzioni, ed., New Communitarian Thinking: Persons, Virtues,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ie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5; Amitai Etzioni,ed., 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Amitai Etzioni, Political Unification Revisited: On Building Supranational Communities, Lexington Books, 2001; Amitai Etzioni, The New Normal: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Common Goo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4。。传统共同体失去之后的社会不能实现“幸福生活”,人们对各谋其利、貌合神离的现代生活不满,所以渴望新的开端和社会新变,渴望共同体精神和价值,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对共同体的渴望成为一个时兴现象。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falsche Gemeinschaft)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诠释当代社会共同体的尺度。“虚幻共同体”一般翻译为“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错误的共同体”等,用于指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虚幻共同体”的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wirkliche Gemeinschaft)(2)Wirklich一词的本意是真实的、现实的,实际的、确实的。真正共同体也可以称之为现实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也可以翻译为“现实的共同体”“真实的共同体”“实际的共同体”。。因此,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提供了人们进行社会生活的“平台”,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而非其政治哲学的尺度。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应以“实践”为基础,基于其政治目标和社会原则去诠释,建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意识。从马克思研究的商品形式和商品关系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主要研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政治权力关系;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是内在于资本或货币关系中的,因此价值要素只可能在剩余价值中保存和发展,而剩余价值只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得以保存和增殖。这才是马克思关注共同体概念的利益选择和思想关系的定位所在。
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共同体的寻求在20世纪形成潮流,而在21世纪则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人们对共同体的渴望体现出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结构所造成的错位,人们对共同体的寻求反映了人们的权利需要完备的保障。对于自然共同体的讨论也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对共同体思想的诠释反映出权力在社会中位于何处以及如何分配权力才能呈现制度的正义,进而保障一个有意义共同体的存在。
一、 人类解放的现实价值: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
基于哲学家的思想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探讨了人类社会“理想的共同体”中有关人类解放的现实价值。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政治哲学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将其视为“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因为这种“共同体”表面上代表所谓的普遍利益,实际上它是为特殊利益——资产阶级利益代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未获得什么自由,相反,人们在异化的处境中失去了自己宝贵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幻共同体”的批判立场:劳动分工和异化是市民社会的标识。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私的个体为什么要组成共同体?共同体是自私的个体的集合体?组成的共同体是放大了个体的自私,还是规范和限制了个体的自私?共同体的性质是维护和保障组成共同体的个体利益,还是仅仅维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都生活在城邦共同体中,离开了共同体的人,非神即兽。马克思步入社会工作以后,把哲学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也为个体的社会属性增添了新的内容,然而这也使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共同体中利益选择的排他性和个体自私性的集合现象。
同样,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一样的关系。在前国家时代,个体独自存在于自然的生活中,可以说个体的存在是共同体产生的前提和根据。因此可以说,个体对于共同体的逻辑先在性使个体对于任何共同体之要求皆具有一种道德的先在性。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个体的自然先在性呈现为个体自我保存的生命样式、财产的权利保障以及自我的自由存在样态。个体的权利保障基础是无需证明的、先在的。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个体是构成共同体的“原子”和“因素”,是共同体的起源和目的;同时,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规制着共同体的权力界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同意和权利转让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在个体与共同体当中,共同体的存在在于保障个体的存在性和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被国家的“守夜人”“打更者”角色所规定。可以说,如何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
“虚幻的共同体”是与有个性的个人相对立的存在。作为“虚幻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从属于自己的创造物,实际上是从属于人的生活桎梏。“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形式,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愈加激烈,“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想脱离的独立形式”[1]536。“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1]576避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使个人不再沦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成为历史中生成的具有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个人,从而使个人在分工过程中实现自由的联合,在共同体劳动中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决拒斥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实际奉行的是“知识的等级制”,普通个体由于缺乏全局知识而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政治缺少监督和主动变革的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国家是徒有“理性”虚名的僭政;对于统治者而言,国家则是他们个人自主性的俘获物,是“私有财产”。观念论声称普遍理性(知识)创造、支配现实世界,其政治纲领只能通过少数优选者的统治贯彻,这使它无法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关系。“它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抉择意志的统一主体,进而据此作出行动,只是因为包含在它之内的自然人将其中的多数达成的一致肯定或一致否定设想、虚构为此主体的抉择意志。”[2]341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将目光转向了唯物主义,转向了市民社会中的现实个人。马克思最初的“民主”思想源于相信社会是个人发挥自主性的产物,所以对社会的整体调控也应反映个人自由的原则和目标,这也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通过实质性的联系,通过个人的基本特质而同个人联结在一起。它们是个人的基本特质的自然行动”;“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3]29可见,正是因为相信个人的自主行动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所以青年马克思才将建立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民主制”视为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最终出路。
现代社会共同体与古代社会共同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是身份等级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则是以身份平等为基础的自由契约决定着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诸如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言论权、结社权和选举权等皆是现代人的权利,它们是人们通过反抗传统社会体制争取来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希腊人的权力观是与城邦的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是城邦创造了公民权利,而不是公民权利创造了城邦。也就是说,是先有共同体,后有个体,而不是相反。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共同体的博弈不是权力与自由的对立,或者是特权者与人民的对立,而是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的对立,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对立。在传统的共同体的几千年嬗变中,人们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并未终结人性化的存在,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社会特征并未撕裂传统共同体所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诸如当代中国依然保留着家族式的祠堂文化、祭拜祖先、保有家谱,而且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带,传统文化也依然赓续着。那些生活于全球各地的华人同样保有着传统共同体的根系文化。
即便是当代社会面对着现代化共同体的冲击和激荡,传统共同体依然歌颂着人际关系的美好,赞扬忠诚、孝顺的美德,并用这样一种美德去反衬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淡。尽管存在着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但是并未排除共同体当中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它为各种真实的交流留下了位置,传统共同体的血脉依然流淌在全球华人的心际。
二、 共同体与自由辩证: 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实质
“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从西方传来,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绵延几千年的政治体制而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闯入者,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之市民阶级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4]338。他者的缘起势必对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双重的冲突,不同的共同体碰撞,也势必产生新的融合。因为“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资产阶级的国家中,等等。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157-158。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的教谕。马克思认为洛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5]393
也就是说,在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的变化过程中,马克思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的颠倒,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物化”呈现出资本主义共同体所有权的特征。正是看到这样的共同体特征的变化,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共同体中的个人的独立自由在“物化”主导中失去了主体性而使共同体变成“虚幻”的。劳动成为了“异化劳动”,成为“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经济学家眼里,利己主义和追逐利润是每个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建立在以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划分之上”[6]16。在工业生产的成果分配方面,两个阶级处于根深蒂固的斗争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对象化和异化是一回事,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一切劳动所具有的必然特性,并将劳动力置换到它所创造出来的对象上去。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的形式,工人“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虚幻的共同体表现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受阶级身份的限制,“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571;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受“物的力量”奴役,“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1]572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527人们也是为了生存而保持人的社会性,也使人的社会性复归于人的自然性。政治解放“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这势必会造成“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1]568从而使作为个人共同体的“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1]570。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人是抽象性存在,个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1]46。这样,根据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根据整体观念构想国家”[7]228,这样建构的共同体只能是“虚幻共同体”“冒充共同体”,而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共同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205。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是孤立性、敌对性存在。资本作为主体实现了对劳动的宰制,实现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资本的本质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关系,而资本的真相呈现的是“物的人格化”,对人的统治实现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1]152资本作为无生命的外在物质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劳动占有,实现了对劳动人格化的工人的统治。资本“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财产。”[8]45-46这就势必造成了劳动“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1]123,实际上资本家也被抽去了人的主体本质,被注入作为外在物的资本的逻辑,成为资本统治世界的提线木偶,“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1]130。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蒲鲁东在这个意义上指出“所有权就是盗窃”[9]38。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1]177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而劳动条件作为资本与活劳动相对立,因为“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8]43。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10]226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8]37。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万恶之源”[11]174。因为“货币在它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规定上,使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货币在它单纯是同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形式的财富时,使吝啬得到实现。”[11]174也就是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11]174-175。然而,由于没有使交换价值充分发展,同时也没有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这样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同体”的原文是Gemeinwesen,俄文版将其翻译为“社会联系”(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注释①。。共同体自然保有每个个体,同时共同体内蕴个体的“排斥”,共同体和共同体内的个体之间的联系物“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存在。所以,“占有货币像对古代人的共同体起的作用那样,对他起瓦解的作用”[11]176。瓦解个人所从事的社会生产的意义,使个人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单纯的发财致富,而“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11]176。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货币共同体的积极作用在于:“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11]176。
马克思认为:“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在货币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第三种规定上的发展,破坏了古代共同体。”(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货币的第3种规定是指作为离开了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因为“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11]178-179正是因为“价值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剥削之社会角色的一部分”[12]47,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是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加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12]101。奈格里指出:“这一价值规律通过对主体反抗的极端强调开始形成剩余价值规律。但是,只有当劳动的过程被包含在资本中的时候,才能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因此,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引出了剥削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上,所有停留在价值理论上的幻想都不见了。”[11]101
三、 共同利益与个人权利: 马克思真实的共同体的理想
“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536共同体是一种利益呈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同体是一种完全“物化”的利益反映,即使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536,以便获取更大的阶级利益,因此伤害利益比伤害人的灵魂还要痛苦。所以,“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12]101。这也是获取利益的最根本的方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86共同体一定是一种利益载体,反映着利益共同体所承载的社会利益的分配。然而,共同体中的利益主体是谁?共同体的利益又是如何具体分配的?“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537
马克思指出:“在国家的层面上树立起一个假冒的由‘平等’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掩盖着市民社会中不平等的成员之间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竞争活动……公民被赋予的权利强化了市民社会以自我为中心和对抗的倾向。”[13]134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自由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个人自主性得到了极端发展,“将一个人形容为完全拒绝任何负担的、完全即兴的自我,与社群、历史、传统或公民责任都切断了联系。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将自由本身看成目的,而主张自由需要秩序和约束的观点受到排斥。这种不要任何限制的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有权‘不让任何人来打扰,不考虑其他人的价值观,不考虑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限制,不受工作、家庭或政治生活中任何专断权威的支配’”[14]12-13。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认识正是当代社会和共同体价值观焦虑的“元凶”,这样一种自由至上主义极力主张所谓的个人自由,置个人的责任和社会的限制于不顾,只是把个人视为不断增加的法定权利的持有者,以及把个人视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上的消费者。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田园传统,“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34。一切社会关系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8]34。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8]34。因此,在自由至上主义者那里,公共政策和社会约束就是侵犯个人自主权,是对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干预,完全没有个人应受到义务的约束去服务于我们所称的社会。这种理论的践行者眼中只有自我个体。
然而,“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435。任何社会的权利都是由其所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制约着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而在其中最能反映社会根本利益趋势的就是阶级构成的利益走向,所以我们说个人权利的历史局限性在于阶级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非常清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8]31也因此,马克思以“阶级解放原则”改写“个人权利原则”。
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只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才会“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过程,从而把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他们把可变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与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过程混同起来”[15]489。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并不是简单的买者和简单的卖者彼此对立,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在市场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15]495这种生产过程的核心是“现在,全部产品就是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存在的形式,而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则重新作为资本家的财产,作为独立的力量和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所以,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前,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15]543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统治和被统治构成了政治关系的两极,这可以被视为是马克思阶级解放原则的第一个原则:“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8]31。革命意味着颠覆和彻底的改变,所以个人权利只是历史诠释中的特殊性原则,每个个体都只有融于个体所属的共同体中,个体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8]51。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个人权利最终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马克思的阶级解放原则的第二个原则就在于阶级解放原则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内在性超越路径,克服个人权利的历史局限性。人的解放的实现须经由阶级解放完成,“这里涉及到的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6]10。《资本论》被视为《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的学理性证明,人们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判决书,其内容有三:《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灭亡以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可期待的分析、批判与论证。
《资本论》现实的政治意义是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内在破坏性过程,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人合理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以及由利润驱动的生产加速发展和技术的盲目发展给人类的内在主观性和生理条件的破坏。《资本论》首要的贡献,不是对历史必然逻辑的论证,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片面性和否定性的诊断学以及寻找抵制和驯服资本主义盲目破坏性的思想资源。《资本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义的权力的“构成性”与法律意义的权利“被构成性”的生成转化逻辑的政治哲学。“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67“资本逻辑”是对社会矛盾的真正遮蔽,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让资本回归真正属人的世界和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历史承诺。《资本论》证明了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证实和证伪才成为可能。而这恰恰证明马克思的“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1]167科学判断的正确性。也就是说,阶级解放归宿于阶级的消亡和人的解放,因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7]106。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7]106“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167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是辩证统一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成为“虚幻共同体”的变体;这种“虚幻共同体”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这其中蕴含着对现代性批判的基因,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被资本的批判所代替。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所呈现的虚幻共同体的现象,诸如道德疏离、敌视世界、恐惧自由、非理性的侵犯冲动、没有应对任何困难的无助感,等等。与此同时,社会组织承担制度功能,而个人的异化感缘于这种制度功能组织出现了问题,不再整合人们的目的感。“在我们制度化的互助、救济、教育、娱乐及经济生产和分配体系中,家庭、地方社群、教会以及整个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再拥有决定性的作用。”[14]49其所造成的危害在于社会错位、道德混乱、价值冲突,其冲突的性质在于“以宗教、个人权威、传统义务为基础的东方体系和以理性、非人格的法律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西方体系之间的冲突”[14]49。正是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中,资本主义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应该是一个同时代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而已。即使是“家庭远远不是一种以相爱或道德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而是我们都无法脱离的一种机制。”[14]52其权力现象学的标识就是王权、神权和人权。
在现代化社会,原子式的存在、碎片化的生活无法满足个人共同体归属感,这只会使共同体的“剥离”感趋强。而日益增长的疏离感使人们对共同体的需求沉迷,现代化的技术进步解决不了人们对共同体的渴望。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正在终结,而人们的忧虑和挫折感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长而强化。诸如每年的中国春运使生活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们意识到:怀乡症会始终萦绕在人们的想法中,然而曾经给予我们的道德确定性和传统固有身份的古老事物的消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从前旧有的“制度”,追寻过去就如同追寻未来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毕竟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的潮涌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