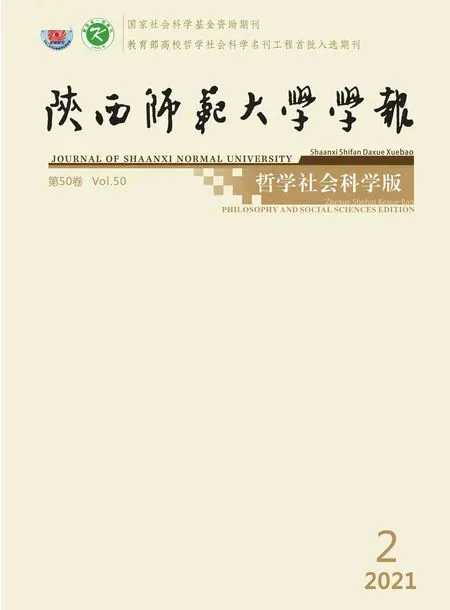“不言之教”是什么教?
——兼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的原创性特质
李 忠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不言之教”是先秦道家学派的教育理念。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老子》第2章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1]《老子》第47章庄子亦说:“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2]《庄子·德充符》,“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2]《庄子·知北游》。但是,“不言之教”并未受到后世中国教育学者的重视(1)有学者将中国教育史缺乏对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 其一,先秦道家学者著作中专门讨论教育的篇章较少,有限的教育论述也因哲学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被误读为反对教育和反文化创新的表述而受到批判。其二,先秦道家思想与长期处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存在重大差异而受到抑制,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颁布实施后,包括道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受到严厉的抑制。见王凌浩、王睿《先秦道家的原创性教育思想探赜》,《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有限关注“不言之教”的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教育方法,具象为“身教”,对应于“言教”,表述为“身教重于言教”。[3]228-235这种解读可以理解,但却与“不言之教”本旨相去甚远。在老庄看来,“不言之教”由“道”的性质所决定:“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庄子·知北游》。对不可言之“道”的教育,只能是“不言之教”。此其一; 其二,“道”的“自然无为”属性,要求教师辅助学生成长却不能干扰学生的自主。在老子看来,理想的教师是辅助学生成长而学生却“不知其有”的教师;那些被学生“亲而誉之”的教师,已经干扰了学生的自主、自动,与“道”的自然无为属性相悖;至于侮辱学生人格、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的教师,与“道”的自然无为属性相对立,不适合从事教育工作。“太上,不知其有。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1]《老子》第17章因此,“不言之教”不是通常所言之“身教”,亦非仅指教育方法,而是有独特内涵与价值的教育思想体系。道家的“不言之教”与儒家的“言教”与“身教”形成显著差异,成为先秦时期带有原创性教育思想体系,虽未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却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教育学术研究现象。
一、 “不言之教”的目的: 培养具有“天道”品格的“有道者”
“道”是先秦儒家和道家共同关注的对象,但其内涵与指向却大为不同。儒家重“仁道”,道家尊“天道”。仁道讲“仁义”,“要在仁义”;天道重“道德”,“以道德为主”。[2]《庄子·天道》仁道强调人为,“仁者人也”[4]《四书章句集注·中庸》;天道尊崇自然,“道法自然”[1]《老子》第25章。仁道指向世俗,“仁者爱人”[4]《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下》;天道趋向超脱,“生而不有”[1]《老子》第2章。仁道讲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颜渊》;天道倡平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庄子·秋水》。仁道可言,且“言必信”《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子路》;天道不可言,“道可道,非常道”[1]《老子》第1章。仁道有限,天道无边。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老子》第42章天道是包含人道在内的“天之道”。所谓“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2]《庄子·天道》。依照道家学者的观点,道—德—仁—义—礼是天道的逐步蜕化过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老子》第38章。当孔子向老子强调“要在仁义”时,老子却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2]《庄子·天道》。在道家学者看来,仁义礼虽有价值,却是失道与失德之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存在先天缺陷,常被用于颠倒是非,违背天道,忤逆人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2]《庄子·祛筴》因此,重仁义而轻道德,是一种过失,“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2]《庄子·马蹄》。
道不同,教有别。道、儒两家的教育,因道不同而相异。虽然儒家学派重视“道”以及“道”的教育,强调“志于道”[4]《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里仁》“以身殉道”[4]《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上》,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4]《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里仁》,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4]《四书章句集注·论语·述而》,但是儒家之“道”是“仁道”,属人道范畴,侧重人伦关系与人生理想。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以“仁道”关照“人道”的“仁者”,内容集中于仁义礼智等世俗道德规范,成为“言教”与“身教”的典范。道家学派则重“天道”,范畴大于“仁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老子》第25章在道家学者视域中,“道”是宇宙的本源、世界的本体、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趋势,是包含人道在内的“天之道”。所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2]《庄子·田子方》,道家教育是“不言之教”,目的在于培养以“天道”烛照“人道”的“有道者”。
不言之教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懂得天道并具有天道品格的“有道者”。在道家学者看来,天道范围虽广,最终却要落实到人间,即以天道关照人道。“有天道,有人道……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2]《庄子·在宥》“有道者”是以天道关照人道的人。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老子》第77章有道者以天道关照人道,需要具备基本条件。首先,知晓“道”理,明晰权界,不为外物所役,“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2]《庄子·秋水》。其次,具备天道之品格。其一,平等性、公平性与正义性,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以补不足”。其二,利他性与超脱性,“利而不害”[1]《老子》第81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老子》第51章,“功成而弗居”[1]《老子》第2章。其三,“无为”性与效能性,即依天道行事,可获至最大功效,“无为也而无不为”[2]《庄子·至乐》。其四,不争不言、便于应对,即“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1]《老子》第73章。知晓道理、具备天道品格的人,才可能以天道关照人道,此之谓“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以天道关照人道,需要条件,更要行动。依照天道行事,是有道者将天道品格落实于人道的关键。“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2]《庄子·天地》“德”就是将天道落实到人道的中间环节,依照“天道”品格行事的观念与行为就是德,“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老子》第51章。韩非在《解老》中说:“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5]《韩非子》“无为”“无欲”“不思”是有道者的养成方式,也是有道者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即“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老子》第51章。“不言之教”就是要让学习者信仰并实践天道,道不离身,“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1]《老子》第23章。如果说知晓“道”理、具备“天道”品格是有道者的素质,依道行事、将天道落实于人道就是有道者的规格,即“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2]《庄子·知北游》。在道家学者看来,依“天道”品格行事,既可成就自我,亦可达成理想社会,“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2]《庄子·秋水》。道家学者希望通过教育,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具有平等、公平、正义、利他、超脱等观念并能践行这些观念的人,使人与社会得到健康和谐发展。
二、 “不言之教”的内容: 反思之“意”与实践之“意”
“道”的非言语性,决定了“教”的非言语性,有道者主要依靠非言语的“意”来培养。“意”是主观作用于客观后形成的意识与能力,是“不言之教”的主要内容,表述为“得意而忘言”。在道家学者视域中,道与言相悖相依:相悖为主,相依为辅,因而有“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庄子·知北游》之表述。然而,正因有此表述,使道与言相存相依。“道不可言”的意思,正是通过“言”得以表明。因此,道虽不可言,老庄依然以言言道,形成道与言的相悖相依关系,《老子》与《庄子》则是道与言相悖相依之典范。老子关于“道”与“言”的表述,让后来者充满困惑。白居易专门做《读老子》的诗句慨叹:“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对此问题,老子有清晰认知。他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1]《老子》第77章在老子看来,道与言性质不同,言不及道,把握道主要靠意而非言。鉴于此,老子主张“希言”(希言自然)、“善言”(善言无暇谪)、“不言”(不言之教),庄子则提出“寓言”“重言”“卮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2]《庄子·寓言》。因此,老庄不否认“言”之作用,却将言限定在表“意”上。换句话说,“言”要表“意”,“意”要通“道”,以此实现“言”“意”“道”的联系。
“意”是得“道”的载体,是“不言之教”的主要内容。老庄所言,多为表意。老子虽未明确界定“意”,《道德经》却为表“意”之作。举凡“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老子》第5章,“功遂身退,天之道”[1]《老子》第9章等,皆为“意”之表达。庄子则以“言”与“意”对列的方式表“意”,并对“言”之限度做出分析。他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2]《庄子·秋水》他还借用载“言”之书对此做进一步说明:“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2]《庄子·天道》“意之所随者”即为“道”,可以意会却“不可以言传”,可以感受却不能被表达。在庄子看来,不可言之“道”,只能通过“意”来把握,因而主张“得意忘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庄子·外物》。
道家学者视域中的“意”,至少有两种类型:反思之“意”与实践之“意”。所谓反思之“意”,是对理所当然的观念与行为反思之所获得的“意识”。在这方面,作为周王室“守藏史”的老子有诸多表述。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老子》第12章。在老子看来,这些常人追逐的感官享受,与“道”相违,与“德”相悖;相反,对于水之特性,老子给予高度认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老子》第8章,并据此得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1]《老子》第78章之论断。这种与常识相悖的观点,显然是老子反思与批判的结果,也是“意”之形式。可以说,《道德经》就是一部反思之“意”的结晶。庄子继承老子的做法,《庄子》中“意”的反思成分同样鲜明。但是,庄子对另一种“意”——实践之“意”——给予了高度重视,“轮扁议书”与“庖丁解牛”可谓典型事例。《庄子·天道》载: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2]《庄子·天道》
实践之“意”是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意”。其实质是能力——行动或实践能力——明智解决事务的能力。能力只能培养却无法教授,即便是遗传素质相近之父子,也无法教授,以至“轮扁”“行年七十”,依然为轮匠。庄子借“轮扁”之口,说齐桓公所读“圣人之言”乃“古人之糟粕”,原因在于其精华(即“意”)只能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获得,并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庄子的实践之“意”,被当代英国学者欧克肖特称为“实践知识”。这种知识不规则、不确定,口不能言,只属于活着的个体且不能传授,它只能通过亲身实践来获得,并与实践和领悟程度成正比。[6]9《庖丁解牛》给这种实践之“意”以生动描述: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2]《庄子·养生主》。以至文惠君发出“善哉!技盖至此乎”之惊叹。庄子借庖丁之口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2]《庄子·养生主》在庄子看来,这种通过实践获得的“意”(技),是得“道”的媒介,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因此,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客观事物,是获得“意”的最佳途径,所谓“善弓者,师弓不师弈;善舟者,师舟不师奡;善心者,师心不师圣”[7]《关尹子·五鉴篇》,《庄子》中有诸多此类表述,如“痀偻丈人之承蜩”[2]《庄子·达生》,“津人之操舟若神”[2]《庄子·达生》,“大马之捶钩者”[2]《庄子·知北游》等等,都是通过实践活动向事物学习而获得“意”的例证。因此,获得实践之“意”,显然不能依靠他人之言、书本或身教,而必须是依靠个人的实践活动,即“道行之而成”[2]《庄子·齐物论》。正因如此,实践之“意”是持续实践的结果,是“意”的另一种形式。
反思之“意”与实践之“意”,构成“不言之教”的主要内容。其中,反思之“意”培养人的反省意识,关涉价值观形成,指向人的完善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旨在形成符合“天道自然”的教育价值观;实践之“意”提升人的行动能力或实践能力,是践行“天道自然”价值观的教育。两者差别在于:反思之“意”是通过反思指向价值诉求,实践之“意”是通过实践指向能力提升。两者共同特点是:非语言性、不确定性和默会性,能够感受却不能被教授,能够意会却不能被言传,只能通过个人默会性地反思或实践才能获得。需要说明的是,道家“得意忘言”的不言之教,不是绝对地排斥“言”以及“言教”。老子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1]《老子》第42章如果所教之“言”能表“意”,所表之“意”符合“天道”,则要在反思与实践的基础上予以继承。这样做的益处是: 一则验证言之真伪,深化认识,去伪存真; 二则活化言之内容,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三则提高人的反省意识与实践能力,能够创造新思想、新价值。这就如同《老子》与《庄子》,是老庄在反思与实践基础上继承以往之“言”而创造的结果,由此达成以“言”表“意”、以“意”传“道”之效果,并使它们成为与当时一切所存之言都不相同的言说,道家学派由此形成,道家教育得以出现。
三、 “不言之教”的方法: “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
“有道者”主要靠“自为”“自化”的方式培养。“道”的特点与“意”的性质决定,“不言之教”主要不是言教,亦非身教,而是“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因为“道”虽真实,却以“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老子》第14章的不确定方式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老子》第21章。对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1]《老子》第14章的“道”,要通过“意”而非“言”来把握。如上文所述,“意”是主观作用于客观后形成的意识与能力,这种意识与能力无法传授,即便在遗传素质极为接近的父子之间也是如此,“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2]《庄子·天道》。换句话说,“意”的获得只能通过个人的反思或实践。如同庄子所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2]《庄子·大宗师》因此,无论是反思之“意”,还是实践之“意”,都主要依靠自己而非他人。在道家学者看来,教育只有激活人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人作为自己发展的主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自为”“自化”是“不言之教”的主要方式。所谓“自为”,是按照“天道”品格积极作为;所谓“自化”,是依照“天道”的特性,结合自身特点的自我发展。因此,“自为”“自化”的效果是自我努力的成效而非外在教化的结果。老子相信人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强调“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1]《老子》第57章;主张充分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积极反思,获得“天道”的品格,向有道者靠拢。庄子亦强调“自化”,并从“道”的无限性阐释“自化”的必然性,“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2]《庄子·秋水》。但是庄子更强调“自为”。他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2]《庄子·天道》人是自己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自己做了什么、如何做的以及做到何种程度。在庄子看来,受教育者能够做到“自为”,教育的功效也就达成,“行言自为而天下化”[2]《庄子·天地》。
首先,“自为”“自化”是让人成为人的教育方法。道家学者认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其共同本性,即人的“自然”,实施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教育,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2]《庄子·庚桑楚》。教育要顺应人的本性而为,使人成为人。相反,如果教育违背人本性进而扭曲或戕害人的本性,人就会被异化、驯化甚至物化,这样的教育就会演化成反教育的妄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2]《庄子·缮性》。作为自我教育的主体,受教育者同样需要自律,不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而肆意妄为,“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义,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1]《老子》第24章。鉴于此,庄子对违背并戕害人性的教育给予尖锐批判:“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庄子·骈拇》。因此,老庄提倡“自化”“自为”的自我教育,是将其作为使人成为人、维护人类“自然”共性的方法。
其次,“自为”“自化”还是让人成为自己的教育方法。人不仅有共性,还有个性。庄子指出,只有个体自身才最了解自己的个性,“自为”“自化”是让人成为自己、完善自己、成就自我的方法。他说:“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2]《庄子·骈拇》那种不是通过亲自反思与实践而获得的见闻,是无原则适应他人而放弃自我的做法,其结果是让人丧失自我,“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2]《庄子·骈拇》。在庄子看来,“自为”“自化”作为让人成为自己、成就自我的方法,至少包含以下含义:其一,受教育者以完善自身、成就自我作为接受教育的目的,突出实践与反思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其二,教育活动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展开,为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实践条件与反思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不是不要教师的教,而是对教师的教有更高要求。它要求教师不能无视学生的特点以强教,更不能放任学生以自流,而是以自然无为的方式,积极创设条件与机会,唤起学生对“天道”品格的信仰与对“有道者”的认同,激活学生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使学生按照“天道”的品格思考和行为,身处其中却“不知其有”,“大人之教……处乎无响。行乎无方。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2]《庄子·在宥》。如同庄子所言:“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2]《庄子·天地》就此而言,“自为”“自化”的“不言之教”,是“面向人自身”,唤醒或点燃人成长的内在愿望与激情,激活人的内在发展动力的教育方式;是充分实现学习者主体性和主动性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自己得出结论的教育方法,也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方法。
四、 “不言之教”的原则: 以“自然”“无为”方式治理和实施
“自然”“无为”是“天道”的存在形式与行为方式,是“不言之教”的原则。从这个层面看,“不言之教”是“自然”“无为”之教。其中,“自然”是“不言之教”的根本性原则,“无为”是“不言之教”的治理原则和施教原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老子》第25章“自”是自己,“然”是样子;“自然”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引申为自己这样、原本如此之意,“道法自然”是指“道”按照自己本来样子存在和运行。道如此,天、地、人莫不如此。“无为”是“道”的行为方式,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1]《老子》第2章。因此,“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按照事物本来样子“为”,而且要积极地“为”。(2)美国学者森舸澜将“无为”解释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如的涉身行为,颇有新意。他说:无为最好的翻译是“自如地作为”或者“自发地作为”,“无为是指那种动态的、自如的、无意识的心智,拥有这种心智的人更积极,更有效。无为的人感到他们仿佛没有做什么,但其实他们可能在构建一部伟大的艺术品,轻轻松松地化解了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使全世界走入和谐的秩序。”森舸澜《为与无为:当代科学遇上中国智慧》,史国强译,现代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正因如此,庄子将“为无为”视为“天”,“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2]《庄子·天地》。“自然”针对的是“人为”,“无为”则针对“妄为”、强作为。就“自然”与“无为”的关系而言,“自然”是一种状态、观念,也是一种价值和效果;“无为”是落实“自然”的方式与行为,是实现“自然”的手段。“自然”的状态、观念,要求“无为”的方式;实现“自然”的价值与效果,是检验“无为”的准则。[8]88培养“有道者”的“不言之教”,需要在“自然”“无为”的原则下进行。
“自然”是“不言之教”的根本性原则。在道家学者看来,包括“道”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有其本性、内在法则与运行逻辑,即“自然”。人与教育也有自己的“自然”。人的本性与内在法则就是人的“自然”,教育的本性及其内在逻辑即教育的“自然”。在“自然”状态下,人与教育能够保持其本性,发挥出最佳状态。人与教育的“自然”需要努力实现,却不可扭曲;一旦被扭曲,就会被异化,变成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东西。因此,敬畏人的“自然”是教育的第一原则,“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老子》第51章。任何违背人的“自然”原则的教育,都会事倍功半,甚至遭到抵制与惩罚。[9]159正因如此,老庄对培养人的教育活动充满敬畏。老子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1]《老子》第69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老子》第64章。庄子亦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2]《庄子·骈拇》“不敢为”是要依照“自然”原则谨慎而“为”,不敢肆意妄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灾难多是因违背“自然”的妄为造成,教育灾难同样如此。因此,维护人与教育的“自然”本性不被异化,是教育要遵循的根本性原则。
“无为”是“不言之教”的施教原则。“无为”不是袖手旁观的“不作为”,而是按照人的“自然”与教育的“自然”积极作为,即让人按照自己本来样子和内在法则得到充分发展,使教育按照自己本来的样子与内在逻辑得到健康运行。它至少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教育必须维护人之“自然”,保证人之本性不会被扭曲;其二,教育必须发展并完善人之“自然”,以便更好地成就人。这种做法,使人与教育都按照自己的本性得到发展。在老子看来,“道”滋长并成就万物,就在于其“无为”。他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1]《老子》第67章“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原因就在于它虽创生万物,却不干扰、限制、主宰万物,而是辅助万物顺其自然的自我化育、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庄子甚至将“无为”视为“天道”与“人道”的差异所在:“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2]《庄子·在宥》因此,“无为”是“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得以实现的保障。
“无为”还是“不言之教”的治理原则,表述为“无为而治”。在老庄看来,依照“无为”原则治理教育,才能充分释放人与教育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目的。首先,“无为而治”能够预防并避免因妄为而造成教育失误和失败。“无为”对立于妄为,妄为是背离人与教育的“自然”本性而为,因而只能招致失误和失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1]《老子》第64章。其次,“无为而治”为人与教育的自治提供保障,服务人的自我教育。老庄认为,“无为而治”是让人形成自治意识并具备自治能力的基本保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老子》第57章。自治不是依靠外在压力或诱导,而是借助内部觉醒与觉悟的自我管理,“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老子》第17章。最后,“无为而治”为人与教育的活力释放提供保障。“无为而无不为”[1]《老子》第48章,“无为也而无不为也”[2]《庄子·至乐》。“无为而治”就是为人的成长与完善积极创造条件,却不干扰、不主宰人的成长与完善的治理方式。正因如此,老庄将“无为而治”视为教育治理的最佳原则,“为无为,则无不治”[1]《老子》第3章,“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2]《庄子·在宥》。
五、 余论: 先秦道家“不言之教”的原创性特质与持久生命力
以培养“有道者”为目的,以反思之“意”和实践之“意”为内容,以“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为方法,以“自然无为”为原则的“不言之教”,是先秦道家教育的主要特色。“不言之教”内容的非语言性,越出“言”与有字之书之范畴,让人在反思与实践过程中成为自己、成就自我。“不言之教”强调“为无为”,以达“无不为”之效果,将人的成长与自然、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以便从容应对变动不定的世界,使其成为具有穿透力并带有原创性的中国教育智慧。
其一,先秦道家的“不言之教”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关于默会知识的教育主张。默会知识是可以感受却无法表达、可以意会却不可言传的知识,是应用知识的知识,只能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或反省活动来获得。老子与庄子以其独特的观察和体悟,依据“道”的默会性与不确定性提出知识的默会性与不确定性,将不确定的默会知识区分为反思之“意”和实践之“意”,并将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道家学者主张教育要为学习者创造条件与机会,帮助学习者通过反思与实践的方式获得默会性的反思之“意”和实践之“意”,并将反思之“意”与实践之“意”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外部世界的武器。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关于不确定的默会知识并将默会知识作为教育内容的教育主张,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对人类教育的重要贡献。伴随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来:“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只有不确定性本身才是确定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混沌科学、复杂性科学和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得到了蓬勃发展”[10]81。不确定性的默会知识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举凡“个人知识”“软知识”“暗默知识”等等,都是学者对默会知识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默会知识被认为是应用与创造知识的知识,与人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人格完善密切相关,不仅受到研究性大学的重视,而且受到创新型企业的重视。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等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将默会知识作为创造新知识进而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内容予以重视,认为日本企业能够屹立于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默会知识的重视。(3)默会知识是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其1958年《个体知识》中提出。他将知识分为明晰知识(即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和记忆而获得的知识)与默会知识(即通过一定实践、经验并从中领悟得来的知识,虽然可以获得和积累,却要通过特殊的路径才能实现),前者是社会性知识,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服务于社会的稳定;后者是个体性知识,有助于个人的完善和发展。见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 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波兰尼提出默会知识概念后,引起西方学者广泛关注,举凡“软知识”“隐性知识”“暗默知识”等等,都是默会知识的另外表达形式。默会知识对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成长意义重大,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以“知识运动之父”著称的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指出,“知识创造一直是这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源泉”,“暗默知识却是日本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序》,李萌、高飞译,世界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其二,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提出“无为而治”的教育治理理念,即所谓“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2]《庄子·至乐》。如前所述,“无为”不是不为,而是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为。在老子与庄子看来,包括人在内容的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本性。只有以“无为”的方式,才能实现人与教育的“自然”本性,即“无为而才自然”[2]《庄子·田子方》;只有辅助人与教育的“自然”而为,才能使人与教育的本性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即“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2]《庄子·在宥》。老子与庄子依据道的自然无为属性,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1]《老子》第3章的教育治理理念,是关于“无为而治”(4)老子的“为无为,则无不治”观点,被孔子概括为“无为而治”,作为理想的治理方式。《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最早表达,强调按照人与教育的“自然”本性治理教育。但是,按照人与教育的“自然”本性治理教育,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对人与教育的“自然”做深入探究和了解,即能够充分地认识人与教育的“自然”,这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前提; 二是要对人与教育的“自然”保持足够的尊重与敬畏,能够维护人与教育的“自然”,即“无为为之”。在此基础上,按照人的本性及其内在成长秩序与教育的本性及其内在逻辑治理教育,即“无为而治”。这种做法,是避免由于不了解人与教育的本性及其内在发展逻辑而产生的妄为式或折腾式治理的有效方式,是任何教育得以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道家的“无为而治”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并具有中国智慧的教育治理理念,至今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5)教育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严重问题,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成果多从国外汲取经验而鲜有从中国教育历史汲取思想资源的做法,这一问题依然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严重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石中英教授研究指出,作为教育治理重要内容的教育评价中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最为主要的原因: 一是对不科学教育评价体系危害认识不足,即对“妄为”式与“折腾”式评价的危害认识不足。二是对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即缺乏对人的“自然”、教育的“自然”以及教育的内在逻辑认识不足,以致教育评价成为折腾式的形式评价。详见石中英《回顾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教育研究》 2020年第9期。
其三,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师资”概念和“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理念。老子与庄子根据天道的品格,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平等性、正义性、利他性、无为性和效用性。老庄倡导的“不言之教”,将人与天、地、道并列,作为“域中四大”[1]《老子》第25章之一,尊重人、相信人,认为人人可以成为有道者。他们主张,在“道”面前,人人平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1]《老子》第49章。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师资”概念,“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1]《老子》第27章。老子与庄子依据道的特性,推演出教的方法,强调“自为”“自化”的自我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主张以反思与实践方式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观点,不仅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中熠熠生辉,即便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也毫不逊色。
先秦道家的“不言之教”虽未受到后世中国教育学者的重视,却被国外学者密切关注,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教育学术现象。牛津大学教授大卫·帕尔菲曼在《高等教育何以为“高”》中,将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等量齐观,认为这是促进人的成长与完善的重要方式。[11]22哲学家、教育家马丁·布伯将老子的“无为”解释为“解放”(6)马丁·布伯对“无为”作如下解读:对生命中的事物施加干预,意味着同时伤害他们和自己……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微小且显著的力量,不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强大且神秘的力量……完美的人……不会干涉生命中的个体,他不会将自己强加于其上,但是他会“帮助所有生命获得自由 ”。通过他的合一(unity),他也带领大家达到合一,他解放了万事万物的本性和命运,也将其中的“道”解放。转引自卡尔·罗杰斯《论人的成长》,石孟磊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2页。,对心理学家罗杰斯产生深刻影响;罗杰斯说:“我对人民所做的努力,也是越来越朝向解放‘他们的本性和命运’这个目标”[12]32。科技史家李约瑟将道家“不言之教”视为儒家的“礼教”、法家的“以法为教”的对立面,并将其作为道家反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革命性。[13]118政治哲学学者欧克肖特将庄子的实践之“意”视为不确定的实践知识,并以“轮匠”与齐桓公的对话为例说:“实践知识既不能教,也不能学,而只能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唯一获得它的方式就是给一个师傅当徒弟——不是因为师傅能教它(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才能习得它。在各门艺术和自然科学中,正常发生的是,学生在被师傅教和从师傅那里学技术时,发现他自己也习得了另一种不是纯粹技术知识的知识,它从未被人明确地传授,也常常不能精确地说它是什么”[6]10-11。欧克肖特显然将“不言之教”视为是不确定性默会知识的教育。复杂理论的倡导者埃德加·莫兰在其著名的“方法五书”《总序》中,不仅以《老子》中“谷神”表达“道”的精神,而且认为复杂方法的两个基本原则——两重性逻辑的原则和回归环路原则,可以在道家学说中找到类似表述。[14]1对于不确定性世界中的知识与教育,莫兰充满期待。他说:“今后人类征途的不可知的特点应该促使我们培养准备应付不测事件而处理它们的头脑。所有身负教育之责的人们应该走向迎击我们时代的不确定的最前沿。”[15]9道家的“不言之教”主张通过掌握不确定的反思之“意”与实践之“意”,以应对不确定世界的做法,为人类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