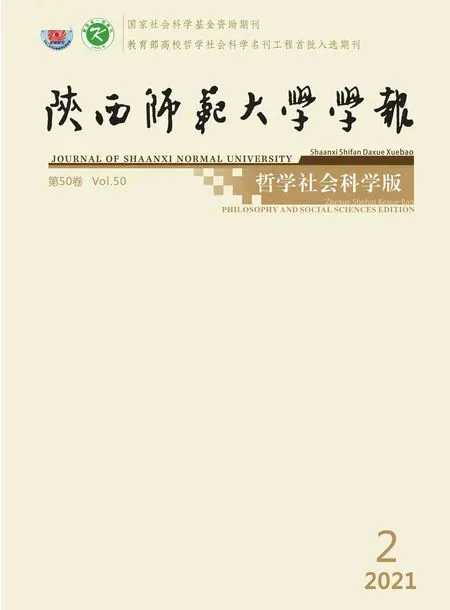国际东南亚研究的演变
——以东南亚史研究为重点
包 茂 红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作为区域研究的东南亚研究即将走过一个世纪,正在经历兴旺之后反思和寻找新方向的阵痛,似乎也在经历格局变化的调整。东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学术名词,是欧美的创造,东南亚研究也同样是欧美学术界的发明,在欧美形成的研究范式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逐渐成为主导范式。然而,这并不是说世界其他地区不存在东南亚研究,或即使存在但不重要。相反,在东亚,东南亚研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生和发展,正与东南亚的东南亚研究一起形成巨大合力,改变着东南亚研究知识生产的内容和面貌。
本文将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重点,简要梳理欧美、东南亚、东亚的东南亚研究,并在前人提出的可能发展方向基础上提出一孔之见,强调指出,实现文理交叉,推动环境史研究或许可以成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一、 东南亚概念的谱系
东南亚这个名词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的出现是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早在殖民时代,英国殖民者把自己在现在东南亚的属地视之为英印帝国在东部的扩展,也是通向中国的海道上的重要据点,因而称之为“远印度”(Further or Farther India)或“大印度”(Greater India)。[1]227荷兰殖民者把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占领地称之为“东印度”(East India),法国殖民者把自己的殖民地称之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尽管德奥两国在这个地区没有殖民地,然而唯独德奥学者在19世纪末相继在著作中称其为“东南亚”(Südostasien),其中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冯·海涅—盖尔登(Robert von Heine-Geldern)[2]8。在美国,虽然牧师霍华德·马尔科姆早在1839年就在波士顿出版了一本名为《游历东南亚》的书,使用了东南亚(South-eastern Asia)这个词[3],但却是来自德奥的学者从文化和历史方面阐释了东南亚不同于印度和中国的特性,促进了东南亚概念在美国的演进[4]9-11。显然,这一时期在欧美世界出现的东南亚概念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灵光一现,并没有形成系统性论述。
一战后,欧美学术界和军事界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英国国力下降,不得不在英帝国实施开发计划。东南亚因为战略资源丰富而成为重点开发区域之一,英国甚至想把这一区域变成自己的内湖(British lake)。同时,对研究这一区域的官方资助增多,一些在缅甸仰光大学和海峡殖民地莱佛士学院任职的学者相继回到英国。形势的变化加上在地观察和研究的经验促使这些学者跨越大陆东南亚和海岛东南亚的自然区隔,进而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与印度和中国切割的整体来看待。标志这一变化的事件,是1932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设置了东南亚和群岛系(Department of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Islands),[1]12这是在欧美学术界第一次正式建制性地、明确定义地提出了东南亚这个概念。
二战爆发后,东南亚地区几乎全部被日本占领。在日占区,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打出的旗号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这些口号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它要把东南亚地区与欧洲殖民者切割; 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属于本地区人。显然,日本殖民者用这些口号来为自己的侵略开脱和装点,但对欧美殖民者来说,却启发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东南亚不仅是英国和其他宗主国的东南亚,还是东南亚人的东南亚。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商议确定,由蒙巴顿勋爵设立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这意味着东南亚一词正式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单位(其中不包括由华盛顿负责的菲律宾)。在美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再像以前那样使用“中国及其周边”的说法已不合时宜,于是,“东南亚”一词被广泛用于替代中国的“周边”。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南亚”这个概念就是冷战的产物,是发明出来的,用以支撑美国对亚洲战略的“概念装置”,[5]149这一重大政治和战略认识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根本性影响[6]44。此后,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都相继设立了东南亚研究计划,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1)1947年,耶鲁大学设立了东南亚研究计划,这是美国从多学科研究东南亚的第一个计划。1950年,康奈尔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计划,这是美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东南亚研究计划。
在东亚,东南亚概念的形成却是另一番景象。早在汉代,现在的东南亚和印度在中国典籍中被称为“南海”。到了宋代,有时也把这一地区称为“南洋”。但因为这一区域面积广大,于是划分为“东南洋”和“西南洋”。从元末到清初,逐渐简称为“东洋”和“西洋”。吕宋岛、苏禄群岛、摩鲁加群岛和其他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属于东洋,而越南、暹罗等属于西洋,下南洋的航线也分为东洋针路和西洋针路两支。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指东西洋分界线以西区域,包括印度洋地区。到了清代,南洋又成为普遍使用的名词。辛亥革命后,部分回到中国的华侨学者组建南洋研究机构,发行南洋研究杂志和出版南洋研究系列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采用了来自欧美世界的东南亚概念。如果说南洋是从中国中心或中国的天下观来观察现在的东南亚及其临近区域的话,那么解放初采用的东南亚概念就是从主权国家和区域独立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居,部分地区也深受中国文化和中国移民的影响,但从欧美世界借用过来的东南亚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南洋概念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日本虽然在江户时代末期从中国借鉴了南洋概念,但其内涵并不相同,主要包含了现在的海岛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两部分,大体上反映了作为岛国的日本和作为陆地国家的中国的不同关注点。明治维新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和一战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的部分殖民地,获得了对密克罗尼西亚的托管权,并称之为“内南洋”或“后南洋”,现在的海岛东南亚就被对应地称为“外南洋”或“前南洋”。[7]7“内”和“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日本南进这两个区域的距离远近。1919年,日本中小学的地理教科书采用了欧美学术界已经使用的东南亚概念,对接的是“外南洋”或“前南洋”概念,从而强化了南进论的思想和政策,尤其是从日本南下冲绳、中国台湾和马来半岛的军事企图。[8]1-27自然,这个概念在二战后占领时期一度被禁止使用。但是,战后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寻找可以代替中国市场的目的地的考虑,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宣布与美国共同开发东南亚,在资金、技术、服务和双边关系等方面与东南亚国家全面合作。政府的宣示使东南亚概念逐渐在日本社会流行开来,并成为热点词汇。学术界的响应是京都大学在1965年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随后成立了日本东南亚史研究会。这说明,日本的东南亚概念经历了从战前的蕴含军事企图向战后的注重市场开发的转变。
总之,东南亚这个概念是欧美人的创造,是东南亚区域和其宗主国关系变化的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衬的结果。东亚国家紧邻东南亚区域,双方关系历史悠久,但中日在战前都是从自己的需要来看待这个区域的。对中国来说,东南亚区域是需要教化的边缘;对日本来说,东南亚是剑锋所指之地。但是,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变使东亚国家都接受了欧美国家的东南亚概念,但也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略需要出发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因此,东南亚概念是多元的,是不同文化和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建构。
二、 欧美的东南亚研究
近代以来,东南亚先后变成了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这种历史渊源使欧美的东南亚研究独具特色。由于不同宗主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位置、面积、文化等不同,加之宗主国开始研究的时间及其学术传统不同,致使欧美不同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各自的样貌。由于篇幅所限,本节以英国和美国的东南研究为重点来说明。
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东南亚研究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二战前,在伦敦形成了以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组成的英国东南亚研究的核心力量。1962—1963年在哈尔(Hull)大学、1978年在肯特大学建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1969年,英国建立了东南亚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K),在学术上团结东南亚研究学人,推动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同时,联合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共同组织东南亚研究的学术会议和研究项目。1992年,成立了欧洲东南亚研究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但是好景不长,英国的东南亚研究和区域研究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陷入低谷。1991年,肯特大学关闭了它的东南亚研究中心,2002—2005年,哈尔大学终止了它的东南亚研究计划。英国的东南亚研究形势继续恶化,不过,到2009年,英国东南亚研究会仍有100多位注册会员在从事与东南亚教学和研究相关的工作。
在英联邦的东南亚研究鼎盛时期,诞生了3部对东南亚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第一部是丹尼尔·G.E.霍尔的《东南亚史》。在这本书里,作者力图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力图写出以东南亚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史,改变先前把东南亚史看成是印度史或中国史、英国殖民史的延伸的认识。可以说,这本书是东南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但在第一版中,菲律宾史并没有被包括在内。第二部是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瑞德出生于新西兰,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工作。该书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分析方法,力图刻画出近代早期东南亚的整体史。它改变了先前的东南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宫廷史的传统,转而关注农民和小商人的生活史,给从整体上看待东南亚史提供了新的内聚力和结构。但该书的结论主要建基于海岛东南亚的历史,未能有效地把大陆东南亚史整合进来。[9]10第三部书是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作为著名的“剑桥史”系列丛书的一种,塔林邀集了世界著名的22位东南亚史专家共襄盛举,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在1992年完成了这部集大成之作。该书采用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和结构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不同专题分析了东南亚自古至今的历史,在比较中突出了东南亚史的整体性。但是,过于突出专题研究导致无意中对历时性的忽视,造成不同专题在历史分期上的不统一甚至冲突。[10-11]从英联邦的东南亚史研究来看,除了强调整体性研究之外,还注重从不同时段和因素来建构东南亚史。
为什么英国和英联邦的东南亚研究会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呢?关键是政府公布的两份报告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份是1947年的《斯卡伯勒报告》(ScarbroughReport)。该报告是由来自多个政府部门的16位资深人士组成的“跨部门调查委员会”,通过深入调查和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后完成的,提出了加强英国的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对策建议。报告认为,英国在这些方面的现有研究机构和力量既不能满足战后英国人了解这些地区的需要,也与战后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不相适应。英国政府需要设立奖学金和研究基金,支持这些地区研究和相关人才培养;相关机构不但要提供相关地区的语言培训,还要开展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促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尤其要更加关注对这些地区现实问题的研究;增强与这些地区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向他们传递和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12]28-35,69-77虽然这个报告是个整体规划,却对作为东方一部分的东南亚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英国东南亚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建立、人才培养计划的出台等都是执行这个报告的直接结果。可以说,这个报告是英国东南亚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份报告是1961年5月公布的《海特报告》(HayterReport)。由于战后经济处于恢复时期,能够给学术研究提供的资助有限,加之美国的区域研究快速发展,英国的大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评估自《斯卡伯勒报告》公布以来英国的区域研究的发展情况。与任何调查报告一样,《海特报告》先表达了对《斯卡伯勒报告》在促进多学科研究方面的失望,指出英国的区域研究不适应世界重心已从西欧转移的新趋势,建议设立非语言类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现实问题,另外还提出了设立大学教职、研究生奖学金、海外实地调查基金、多学科区域研究中心的具体数目。[13]应该说,《海特报告》比《斯卡伯勒报告》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报告中的对策的落实使英国的东南亚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
正如《海特报告》所说,战后东南亚研究在美国快速发展,迅速超过了传统宗主国的东南亚研究。从1943年开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提出,必须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即整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域外所有地区进行研究,以满足正在成为世界霸权的美国需要全面理解世界的要求,弥补对(欧洲以外)当代世界陌生的缺陷,并为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识支撑。这个构想在来自政府各部门(主要是国务院、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基金会(主要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在大学变成了现实,成立了多个区域研究中心或计划。就东南亚研究而言,从二战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总共建立了8个研究中心(分布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马诺阿夏威夷大学、密西根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俄亥俄大学、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其中5个得到了联邦政府基金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向东南亚研究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和语言课程培训资金,反战运动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研究和学习东南亚的兴趣,几乎所有大学都产生了开设有关东南亚课程的需求。
相较于欧洲先前的和正在开展的东南亚研究,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独特性。新设立的机构都有若干个正式的教授席位,附设图书馆、语言培训课程、田野调查基金等基础设施。研究者不再是具有殖民管理经历的研究者,而是接受了或正在接受正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并以求知为己任的教授和研究生。受美国政府需要和缺乏历史档案资料的客观基础的影响,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注重研究当代问题,参与的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现代史,对文学和艺术、考古等几乎不感兴趣。学生的培养和教授的研究都贯彻了在地化、跨学科和跨国家的原则。在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每个研究生和教授都必须学习所研究国家的语言甚至是所研究地方的方言,都要去当地做持续的实地调查。每个研究生在学期间都要参加至少两个“对象国研讨班”,每个年轻教授不但要讲授自己研究国家的专题课,还要讲授自己学科的基础课。通过落实这些规定,学生和教授学会了自觉使用跨学科和比较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对东南亚地区及其不同国家和专题的整体认识。另外,大量邀请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和政要到美国讲学,同时大量招收来自东南亚的研究生,给学者们创造近距离观察和理解东南亚学者及其学术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密切交流和相互砥砺,在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逐渐形成了内聚力很强的学术共同体,被戏称为“康奈尔小集团”(Cornell Mafia)。(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57页。在伯克利也形成了类似的小团体,戏称为“伯克利小集团”(Berkeley Mafia)。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也形成了类似的学科交叉与当代问题研究结合的机制,从而激发创新活力和形成更大影响力,参见克利福德·戈尔茨《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林经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与欧洲东南亚研究注重档案资料和基础理论醇厚相比,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显现出学科交叉渗透和活跃创新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初,哈里·奔达(Harm Benda)和约翰·斯迈尔(John R.W.Smail)分别发表论文,倡议撰写既不同于殖民史学又区别于民族主义史学的东南亚自主史学(autonomous history)。[14-15]它从分析地方资料出发,发掘东南亚人的历史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东南亚史。在此框架下,新概念、新视角、新观点层出不穷。例如,斯金纳的 “泰国华人同化论”,戈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和“剧场国家”理论,斯考特的“理解农村抗议运动的道德和理性视角”,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安达亚的“中心/边缘分析模式”,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解释的“文化转向”,或者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戈尔茨等人类学家的“文化阐释”理论的深刻影响。[16]29
但是,随着冷战的缓和以及最终结束,欧美的东南亚研究至少从表面上看已不像从前那么繁荣,部分研究中心被关闭,教授席位缩编,资助大幅度减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研究的概念基础和有效性都遭到质疑,区域研究难以适应把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整合进而生产综合性知识的时代需要。广泛的质疑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欧美的区域研究处于“危机”状态。[17]1然而,如前所述,推动东南亚研究兴旺的因素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还有探索和理解未知世界的知识创新冲动。换句话说,虽然时代需求发生了变化,但求知东南亚的冲动并未根本改变。基于探求和传播知识的核心理念,尽管区域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制度模式正在重塑,但作为我们学会如何去观察、思考和生存于这个世界的研究领域,区域研究依然至关重要。东南亚研究也不例外。[18]19
三、 东南亚的东南亚研究
如前所述,东南亚这个概念是欧美人的创造,东南亚虽然是东南亚研究的后来者,但不是缺席者。早在殖民时代,宗主国就在殖民地设立了研究机构,出版学术刊物。1878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在新加坡出版了《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部杂志》(JournaloftheStraits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1923年改为马来分部。在法属印度支那,1898年在西贡设立了法国远东研究所(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01年迁到河内,编辑出版有《法国远东研究所简报》(l’ÉBulletindel’É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1904年,英国成立暹罗学会,出版《暹罗学会杂志》(JournaloftheSiamSociety)。1910年3月29日,英国在缅甸成立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翌年出版《缅甸研究会杂志》(JournaloftheBurmaResearchSociety)。这些机构和杂志虽是殖民者所办、主要为殖民服务,但客观上为后来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在人才培养、资料积累、学术组织经验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
东南亚国家独立后,殖民时代的大学、科研机构和期刊相继民族主义化。在宗主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东南亚人相继回到国内的大学任职。例如,王赓武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主政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招募了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安东尼·瑞德讲授全新的课程——近代早期东南亚史,这为他以后的科研选定了主攻方向和选题。[9]7在设立作为整体的东南亚的课程之外,还建立了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例如,马来亚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设立了多学科参与的东南亚研究项目,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也在大学相继设立了东南亚研究机构。有趣的是,越南1973年在越南社会科学院创立了东南亚研究所。与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东南亚研究有所不同,越南强调在反帝、反封和反新殖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研究东南亚国家内外的发展战略,同时把越南置于东南亚区域内研究,进而使东南亚研究本地化和民族化(localizing and indigeniz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6年实行革新政策后,越南的东南亚研究进一步发展,1996年成立了越南东南亚研究会,注册会员超过2 500人。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之所以有较快发展,除了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之外,寻求区域认同也是一个重要动力。另外,东盟在1976年的《曼谷宣言》中提出要“促进本地区东南亚研究发展”,倡议和推动了的东南亚研究的本地化。2015年,东盟宣布在年底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发布了愿景文件——《东盟2025:携手前行》。这个行动对东盟国家内部的东南亚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在当年访问菲律宾的雅典耀大学并与其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小阿吉纳尔(Jr. Filomeno V. Aguilar)教授交谈时,深刻感受到他们希望在共同体框架内改造教学和研究体系的迫切愿望。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东盟共同体建设把该地区的东南亚研究推向了新高潮。
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具有世界影响。1960年,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创办了《东南亚史杂志》(JournalofSoutheastAsianHistory),为发表从本土出发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成果提供了学术平台。1961年,在国际亚洲历史学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的支持下,新加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东南亚历史学家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这两个重要事件昭示出: 新加坡想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雄心。[1]1741962年,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63年创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旨在整合不同学科,推动对东南亚进行多学科研究,培养从交叉学科研究东南亚的研究生。1968年,该研究中心获得编制和稳定资金支持,升级为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东南亚史杂志》也在1970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杂志》(The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以体现交叉学科研究的特色。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作为东西方交通要冲的地域和学术特点。东南亚研究所的所长和教授都是从世界各地择优聘请,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大多来自于新加坡之外,其学术影响也完全超出了新加坡和东南亚。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欧美东南亚研究陆续萎缩的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专家人数反而持续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1993年80人,1997年112人,2009年107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是世界和东南亚区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之一,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无疑具有世界级的学术影响。
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族主义史学阶段;第二阶段是全球化时代更为自主的史学阶段。独立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逐渐摆脱了他们的老师从事的殖民史学和所谓“自主的东南亚史学”的影响,探索以东南亚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史学,意在彰显东南亚人的历史能动性和创造力。例如,缅甸历史学家貌丁昂(Maung Htin Aung)、泰国历史学家禅威·格塞希利(Charnvit Kasetsiri)、马来西亚历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菲律宾历史学家提奥多罗·阿贡西留(Teodoro Agoncillo)等。他们的历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战色彩,表现出强烈的、从本民族出发、修正西方学者已经建构的东南亚历史的企图和行动。他们都深度参与本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历史研究几乎都遭到了西方学者诟病,被视作至少不是严肃、科学的历史研究,他们甚至被认为是文创历史学家(literary historian)。貌丁昂的老师D.G.E.霍尔(被誉为“东南亚史之父”)曾直言,貌丁昂的研究是“糟糕的缅甸民族主义学术”(bad Burmese nationalist scholarship),并警告自己的学生不要学习貌丁昂,因为他接受的是文学创作训练,而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训练。(3)这两个例子都来自里纳尔多·伊莱托教授于2013年10月底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讲座,题目是《东南亚史教学:在我研究领域中发生的 “好事”和“坏事”》(Teach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tories about the “Good” and the “Bad” in my Field of Study)。作为霍尔的学生,奥利佛·W.沃尔特斯在1967年也警告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里纳尔多·伊莱托(Reynaldo C. Ileto)不要向自己祖国的当红历史学家阿贡西留学习,“你将来不要像他那样写历史,因为他是和貌丁昂一样的糟糕的历史学家”[19][20]151。美国历史学家格兰·梅也批评阿贡西留在历史著述中存在不严谨、不客观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21]635-636显然,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史学家和前宗主国历史学家的争议不仅仅是学术规范之争,也是两个阵营争夺话语权的复杂斗争。
东南亚国家第二代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和全球意识更强,他们寻求在研究东南亚自己历史的基础上重塑世界历史,或者是把东南亚融入世界的新历史。欧美的东南亚研究尽管试图从殖民主义立场转变为东南亚的自主历史,但是塑造东南亚区域研究的概念基础和学科(人文学科,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规范仍然是欧美的,是从欧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换句话说,与先前批判、反思欧美东南亚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和欧美中心论不同,第二代东南亚的学者对欧美关于东南亚的知识生产的学科基础进行否思(unthinking),同时希望能从本地区的制度环境中寻找独特的学科和认识潜力,进而克服欧美区域研究中出现的危机,为东南亚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否思不是通过突破“欧美中心论”走向从东南亚出发的“亚洲中心论”,也不是改变从外部观察东南亚走向从内部观察东南亚,更不是从殖民主义视角走向民族主义视角,而是通过将地方经验理论化、突破传统学科分野以及关注移民史等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来达到东南亚研究去中心化、流动化和多元化的目标,最终实现知识生产的转型。[17]1-44
四、 东亚的东南亚研究
日本虽然没有与东南亚直接接壤,但对东南亚的兴趣不输欧美宗主国。中国与东南亚是近邻,东南亚历史上的许多王国曾经是中华帝国的朝贡国,在中国正史和民间记载中有不少关于东南亚的史地信息。因此,就正式的东南亚研究而言,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从汉学传统出发,着重考证汉籍中的东南亚地名和史迹。在中国有向达、冯承钧、张星琅等学者,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提振民族自豪感的考虑。[22]在日本有藤田丰八等从东洋史视角出发研究东西关系史和南海史。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南进探路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日的东南亚研究开始脱离汉学的研究路径,逐渐走上不同道路。在中国,由于受到列强侵略以及应民族解放和抗战的需要,中国革命者关注东南亚革命形势和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华侨华人,上海的暨南大学在1928年组建了南洋文化事业部,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东南亚开展有计划的研究。1942年,由侨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创立的中国南洋学会迁到重庆,继续从事华侨史和南洋研究与宣传工作。这两个机构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走向现代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23]34-351928年日本人创立的“台北帝国大学”设置南洋史学系,意在向南洋传播日本文化。系主任岩生成一主要研究南洋的日本人市町,台北由此成为日本研究南洋的桥头堡。在日本本土,东京帝国大学、广岛教育大学、庆应大学也有学者开展东南亚研究,并相继形成了南部史研究会、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印度支那研究会等机构。显然,这时的日本东南亚研究具有明显的为掠夺资源和为即将开始的征服战争服务的特点。
二战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中日的东南亚研究进一步分化。1949—1978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发展的政治气氛影响下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与南洋具有历史联系的东南沿海和毗邻东南亚的西南地区的高校和社科院,纷纷建立研究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出版学术刊物,翻译和编写著作。最能反映当时特点、也比较极端的是,成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写作小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编写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别简史。[24]日本在美国安排的战后“亚太秩序”中给予东南亚足够的重视,同时视东南亚为其实施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福田主义”发表之后,东南亚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1958年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后来并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1965年在京都大学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后来升级为东南亚研究所。该中心成立时,在资金上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在学术基础上,既立足于京都学派的传统,又借鉴美国区域研究的模式,在曼谷和雅加达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全面服务,最终形成在注重语言能力和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融和生态学、农学、地理学、医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文理综合的方法论开展东南亚整体研究的特色。(4)早在1959年,京都大学的学者就组织了每月一期的东南亚文化与社会研讨班。1961年组成设立正式研究机构筹委会,其中包括绝大部分西方研究机构忽略的、来自自然科学系的专家。1963年成立了虚体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协调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1965年中心获得4个正式编制,成为实体研究机构。这是日本大学中成立的第一家研究东南亚的正式机构。参见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World: CSEAS 50th Anniversary,Kyoto University Press,2015,p.9。1966年,在原来的南部史研究会基础上组建了日本东南亚史学会,出版会刊,1971年开始编辑出版学术杂志《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后来,日本东南亚史学会扩容,改名为日本东南亚学会,下设关西例会和关东例会。另外,还建立了日本马来西亚学会、日本印度尼西亚学会、日本柬埔寨学会等国别研究会,以及日本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研究会、日本东南亚论坛等专题研究平台。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无论从业学者数量、参与学科类别,还是学术组织机构和发表园地建设,都蓬勃开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势。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学术上与国际交流增多,另一方面引进外资需要海外华侨的帮助。于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华侨华人研究受到异常重视,二是对东南亚的经济研究增多。从体制变化来看,不少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纷纷改为国际关系学院。相关学术刊物虽然没有改名,但大都改版,增加国家关系和经济研究的内容,压缩历史学、文学等内容。(5)关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20与21世纪之交已经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进行总结,出版了多部学术论文集,在此不再赘述。可参见黄朝翰主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教育部推动在大学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和培育备案基地,目的是打造新型智库。可想而知,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南亚研究已经形成的国际关系化的倾向,短期考察(field trip,不是fieldwork)和学术交流增多,呈现出遍地开花、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就东南亚史研究而言,多位专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整体研究方面,以梁志明为首的课题组出版了系列东南亚史著作,如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梁英明、梁志明等著《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册(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等。梁志明长期从事世界现当代史教学研究,还主持了“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和“东亚现代化进程”等重要研究项目,同时专攻越南史,因此,他的东南亚史研究视野广阔、点面结合、持论公允,在东南亚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
与此同时,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扎实稳步推进。就东南亚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言,甚至提出了近代文明或资本主义是从海洋亚洲发端的观点。[25]132-146;[26]就东南亚史研究而言,出版了由池端雪浦等总主编的10卷本《岩波讲座东南亚史》。(6)这10卷分别是:山本达郎责任编集『原史東南アジア世界』(第1卷),桜井由躬雄执笔,岩波书店2001年版;石泽良昭责任编集『東南アジア古代国家の成立と展開』(第2卷),岩波书店2001年版;石井米雄责任编集『東南アジア近世の成立』(第3卷),岩波书店2001年版;桜井由躬雄责任编集『東南アジア近世国家群の展開』(第4卷),岩波书店2001年版;斋藤照子责任编集『東南アジア世界の再編』(第5卷),岩波书店 2001年版;加纳启良责任编集『植民地経済の繁栄と凋落』(第6卷),岩波书店2001年版;池端雪浦责任编集『植民地抵抗運動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第7卷),岩波书店2002年版;后藤乾一责任编集『国民国家形成の時代』(第8卷),岩波书店2002年版;末广昭责任编集『「開発」の時代と「模索」の時代』(第9卷),岩波书店2002年版;早濑晋三、桃木至朗编集协力『東南アジア史研究案内』(别卷),岩波书店2003年版。就学术范式转换而言,如果以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为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范式、两次转型。第一个范式是1965—1988年进行的联合研究(joint studies),主要是联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对重点研究地区进行多学科研究,在积累资料的同时,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个范式是1988—2004年进行的综合的区域研究(integrated area studies),重在发现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同一性。(7)综合的区域研究主要探讨区域认同形成的理论、区域开发的内部理论、区域内部联系的理论等。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矢野畅编『地域研究の手法』,弘文堂 1993年版;矢野畅编『地域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弘文堂 1993年版;立本成文『地域研究の問題と方法——社会文化生態力学の試み』,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版;高谷好一编『地域間研究の試み(上)——世界の中で地域をとらえる』,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9年版;高谷好一编『地域間研究の試み(下)——世界の中で地域をとらえる』,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9年版;坪内良博编『総合的地域研究を求めて——東南アジア像を手がかりに』,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9年版;坪内良博编『地域形成の論理』,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0年版。第三个范式是从2004年开始进行的多层面、全球的区域研究(multi-lateral and global area studies),通过把东南亚置于全球化进程中研究它与世界的不同层面的联系和影响。(8)全球区域研究主要是在地球圈、生命圈和人类圈的3层框架下探讨东南亚与其他热带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杉原薫、胁村孝平、藤田幸一、田辺明生编『歴史のなかの熱帯生存圏——温帯パラダイムを超えて』讲座生存基盘论(第1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柳泽雅之、河野泰之、甲山治、神崎护编『地球圏·生命圏の潜在力——熱帯地域社会の生存基盤』讲座生存基盘论(第2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速水洋子、西真如、木村周平编『人間圏の再構築——熱帯社会の潜在力』讲座生存基盘论(第3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川井秀一、水野広祐、藤田素子编『熱帯バイオマス社会の再生——インドネシアの泥炭湿地から』讲座生存基盘论(第4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佐藤孝宏、和田泰三、杉原薫、峰阳一编『生存基盤指数——人間開発指数を超えて』讲座生存基盘论(第5卷),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参见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World: CSEAS 50th Anniversary,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15,pp.12-24。促成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范式转型的项目分别是:1993—1996年实施的“通向全球区域研究的综合路径:探寻区域和世界和谐关系的范式”(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Global Area Studies: In Search of a Paradigm for a Harmon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d Its Area)和2007—2011年实施的“探寻亚非可持续的人类圈”(In Search of Sustainable Humanosphere in Asia and Africa)。与此同时,京都大学设立了亚非区域研究研究生院,授予相关的学位。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队伍国际化,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科研人员占到了一定比例。研究成果也用多语种发表,包括日语、英语和对象国语言,有自己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学术杂志和系列丛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机构,它主要进行中长期的研究,为国家的战略制定提供基础理论支撑。而短期的、应急的对策研究主要由政府各部委的研究机构来提出,因为他们掌握的情报更新速度快,来源更直接,对政府的需求也更了解,有条件提出应急对策。
正是在欧美的东南亚研究陷入危机和亚洲的东南亚研究欣欣向荣之时,由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国台湾“中研院”东南亚研究计划、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发起,于2015年在京都成立了亚洲东南亚研究机构联盟(Consortiu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并在京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规模宏大的亚洲的东南亚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曼谷举行,主题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不合常规的东南亚”,第三届在台北举行,主题是“变革和抵抗:东南亚未来的发展方向”。(9)3次会议的情况可参考SEASIA 2015 Conferenc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 (Kyoto, Japan, 12—13 December, 2015),https:∥seasia-consortium.org/conference-2015/ ;SEASIA 2017Conference “Unity in Diversity: Transgressive Southeast Asia”?(Bangkok, Thailand, 16—17 December, 2015), http:∥www.seasia2017.arts.chula.ac.th/ ;SEASIA 2019 Conference “Change and Resistance: Future Directions of Southeast Asia” (Taipei, Taiwan, 5—7 December, 2019),http:∥www.seasiaconsortium.org/seasia-2019/。虽然这个机构是亚洲的,但参加会议的学者却来自全世界。这说明,东亚和东南亚正在成为世界东南亚研究的中心之一,或许还可以说,国际东南亚研究的重心正在向东亚和东南亚转移。
五、 环境史研究与东南亚研究
作为知识生产的东南亚研究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所有关注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在20与21世纪之交不同学者和机构都对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加强或探索的领域,但是从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和亚洲的东南亚研究经验两方面来看,东南亚研究需要进行文理交叉的研究,而环境史研究正是一个实现文理交叉的抓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只是我自己的认识,或许只是井底之蛙之论。如果能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吾愿足矣!
众所周知,当今科学正朝着两个趋势发展: 一是跨越学科边界,进行整合研究; 二是学科内部分化出更加细微的新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这两个趋势貌似相反,其实都在尝试进行学科交叉,只是着力点的规模不同而已。自然科学因为存在概念的先后次序和现象的还原而易于合作,而人文和社会科学虽然没有类似机制但都有兼并主义倾向,从而使各学科成为可以互相沟通的开放学科。环境就是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环境史就是跨越不同学科、联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和纽带。
区域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的多样性和同一性,把握区域与外部世界或全球的联系与互动。但是,在现有学科的行政和学术分野框架下,就区域的某个专题可以进行学科内的深入研究,形成深刻的知识生产,但是显而易见,也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导致“瞎子摸象”式的后果。在现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人只是社会的人,其生物性被忽略,环境或自然最多只是人类历史上演的舞台或背景,人与环境的互动并未能得到重视和展示,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影响对区域的整体认识。如前所述,欧美的东南亚研究表现出对整体史的追求,但并没有像年鉴学派那样重视地理环境在长时段发挥的结构性作用,尽管在年鉴学派的认识中环境(milieu)是静止不变的。相反,日本的东南亚研究融合文理的独特路径不但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东南亚,而且表现出新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它的东南亚研究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并发挥出示范效应。两相对比,似乎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昭示出未来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走向。
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承认环境具有历史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与人及其社会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超级史”(superhistory)。这种超级史不但包括传统史学中缺乏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部分,更重要的是通过与环境联系而重新构建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心灵的关系,最终形成新型的历史。另外,与传统史学重视文字资料、考古资料、口述资料等不同,超级史在使用这些资料的同时,也注重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方法,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而获得的历史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超级史是自然科学化的历史,是把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进而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统一的新历史。[27]19-43
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开展起来了。[28]127-136;[29]333-340;[30]156-171然而,现在的东南亚环境史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狭义环境史的层面上,弥补了先前研究中缺乏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部分。从广义环境史来看,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路要走,东南亚研究要形成超级史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东南亚研究机构和从业人员要有意识地从人员配置、课题设计、成果形成和发布等方面考虑学科分布的平衡和全面,改变目前重视社会科学、轻视人文学科、缺位自然科学的失衡结构。这就需要对不同学科持有开放和尊重的心态,对不同的研究成果抱有包容的胸襟。其前提是对自己学科的弱点和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具有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长处来生产新知识的气度和能力。
第二,用问题意识来引导能把区域研究及其内外关联整合起来的整体研究。区域研究的目的是加深认识和指导实践。深化认识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现在常用的、从不同学科出发进行具体研究,另一条就是现在不常用的、对关键问题进行集体攻关。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两次学术范式转型其实就是利用大项目推动完成的。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大项目不但具有研究问题的功能,还承担着为高校输送具有从事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的任务。当然,这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的提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通过对国际学术史的认真梳理和对现实世界变化的深刻洞察而得出的,研究工作也是由具有国际学术声誉的著名学者来支持完成的,其学术成果也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10)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为根本问题导向,通过组织各种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来探索相关的概念、理论、和机制。另外,根据相关规定,各课题组必须由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而且专家来源必须国际化。可参见https:∥www.chikyu.ac.jp/rihn_e/about.html。
第三,站在全球高度上理解作为独特整体的东南亚。在地球村意识日益高涨的时代,作为认识主体的学者都应该具备3种认同和3种关怀,分别是自己的国家、所研究的区域和地球,并且要在这三者之间达到统一。没有地球关怀的区域研究是孤立的、碎片化的,没有自己国家的视角也是不可能的,但只有自己国家的视角而没有所研究区域的内部视角也是外在的。这就需要在所研究区域建立学术工作站,从事连续的、长期的、实地的跟踪观察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支国际化的、多学科的研究队伍,生产出对全球、所研究区域以及自己国家都有益的研究成果,进而增进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助。
六、 结 语
区域和国别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但这不是在平地上起高楼。就东南亚研究而言,欧美世界率先启动,经历了繁荣之后现在进入调整时期,气势不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势头良好,似乎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优势。之所以形成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原因很多,包括冷战的结束、欧美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欧美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等固有弊端、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域外研究投入减少等,但其中还有一个似乎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那就是学科分野造成东南亚研究不适合地球村时代的需要。战后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文理交叉研究,走出了一条既借鉴欧美区域研究模式又建基于自己学术传统的独特道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东南亚区域进行整体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众多需要改进和探索的领域中,环境史研究能够为东南亚区域研究提供新的思维和路径,以此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建构出超级的东南亚研究。或许这样的知识生产经验和构想会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