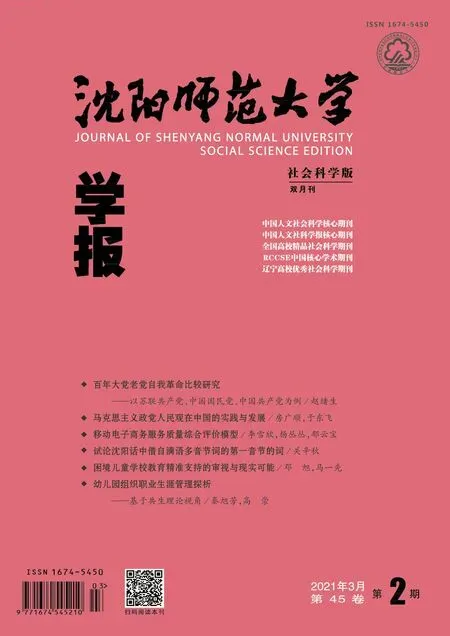试论沈阳话中借自满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词①
关辛秋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1)
一、问题提出
沈阳话中有一些单音词,写出来的话,有的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汉字,如女童游戏“嘎拉哈”(嘎拉哈源自满语gacuha。其意为背式骨,是猪、羊等后腿的胫骨,可做游戏时使用。游戏时使用羊嘎拉哈居多。嘎拉哈共有四个面,以四个为一副,配之以沙包,能提高孩童的敏捷力。)中羊膝盖骨四面中的其中一面(形状似花边瓦)叫做[tʂ33],有珍儿/砧儿/真儿等不同写法。有的词虽然大家勉强接受写作某个汉字,但这个字的读音和语义与实际的情况都不同。如我们称玩嘎拉哈时的一个典型动作叫[tʂhua213],在介绍这种游戏的文字材料上多写作“歘”[tʂhua55]。“歘”发第一声,是拟声词,“形容短促迅速的声音”[1]。但实际语言中[tʂhua213]发上声,是动词,它的意思不是“玩儿”,是指快速伸出手,迅速抓住目标中的嘎拉哈。“歘”与[tʂhua213]词义上有重叠,但是声调和词性都不同。有的词作为普通话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比如,“瘆”(shèn,词典中“瘆”词条的释义为,动使人害怕;可怕:瘆人夜里一个人走山路有点儿瘆得慌。)[1]1215。还有的词成为现在的流量流行词,比如,“怼”(duǐ)。
这些词是音译词,但不是整体音译,是把满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和语义,加上一个汉语的声调,借入到汉语。这是满语借词进入汉语的一种借入方式,也可能是他语言的多音节词汇借入到像汉语这样单音节语言的一种方式。
笔者的母语为沈阳话,因而文章标题将借词的使用范围划定为沈阳话。事实上,这四个单音词的使用范围不局限在沈阳。
二、沈阳话中“tʂ33”“tʂhua213”“瘆”“怼”四个词的来源
(一)“tʂ33”的来源
“嘎拉哈”一共有四面,其中的三面沈阳人把它们叫做“坑儿”“轮儿”“背儿”,全部都有儿化音尾,写成汉字也没有疑义,因为它们和所描述的实物很一致。一面的中间洼下去,像个小坑儿,故叫做“坑儿”。“坑儿”这一面被视作正面,相对的另一面叫做“背儿”,其样子也有点像人的后背。也有的地方依据其形状像肚子,把我们称作“背儿”的这一面叫作“肚儿”。嘎拉哈立起来,有一面看起来像两个轮子,因而把它叫做“轮儿”。与“轮儿”相对的那一面形状像花边瓦,叫做[tʂ33],声调属阴平,调值为33,低于普通话的第一声55调,也是儿音尾。“坑儿”“背儿”“[tʂ33]”“轮儿”,四个儿化音的词,非常整齐,成为一套,作为嘎拉哈四面的称呼。
满语词jerin[tʂərin]名词,意为边,折边,卷边。其形容词形式为jeringge[tʂəriŋŋə],有花边的;有折边的;有卷边的。例如:jeringge wase[tʂəriŋŋəwɑsə]花边瓦;卷边瓦[2]885。这个词的第一音节[tʂə]加上儿化音尾与沈阳话的[tʂ]音节发音一样,其语义和实物的形状也一致。
综上,推想可能是沈阳话借入了满语jerin或jeringge的第一音节,加上了阴平调,用来称说嘎拉哈形状似花边瓦的那一面。
(二)“tʂhua213”的来源
[tʂhua213]的声调是上声。发音时,韵尾a发的不完整,伴随着舌尖向上翘起,有儿化音,但不足以记作[tʂhua]。调值为213,属上声字,比普通话的第二声214的尾音略低。前述在文字材料上这个动作记作阴平字“欻”(chuā),但它的实际读音是上声[tʂhua213]。笔者问到在北京城区长大的、童年玩儿过嘎拉哈的人,将这个动作也发上声。不过,他们习惯把嘎拉哈叫做拐或羊拐,玩这个游戏叫“chuǎ拐”或“chuǎ羊拐”。长春也发上声。例如,2017年发表在长春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欻嘎拉哈太有意思了》特别注明了它读第三声。“原来,这里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欻嘎拉哈【注:欻(chuā)本是象声词,口语中变成动词,而且音也有了变化,变成(chuǎ)】比赛,那位哭着走出活动室的小朋友,是因为练不会欻嘎拉哈急哭的。”[6]因而,这个动作发成上声应该不是因为沈阳方音把它发成了上声。
[tʂhua213]是嘎拉哈游戏中重要的、代表性的动作。具体的动程为:面对桌子上或炕上的嘎拉哈,一只手(绝大多数人用右手)向上扔出沙包,这时腾出的这只手伸向嘎拉哈。[tʂhua213]的动作开始,快触到嘎拉哈时,手腕先有一个自然的略微向外、向上的动作(可能是为了发力),然后向下,触到嘎拉哈前,手开始收拢,渐呈半圆状,这时迅速将嘎拉哈拢起来,抓住目标中(比如搬成同一面)的嘎拉哈的同时,快速扫起。有人用“欻”字来记录,也体现出了这个动作“短促、迅速”的特点。汉语普通话里找不到另一个确切的动词或汉字与之对应。笔者童年时,沈阳的男童游戏玩具有玻璃球儿、啪叽([phia53ʨi])、冰车,称说它们时前面都可以加“玩儿”,但通行的叫法是在这些词前面加上一个典型的动作,弹球儿或弹玻璃球儿、扇啪叽(北京话叫拍洋画儿)、滑冰车。[tʂhua213]就是玩儿嘎拉哈时的典型动作,因而玩这个游戏叫做[tʂhua213]嘎拉哈。
沈阳话中还有一个词的发音与[tʂhua213]相同,就是一种民间的打击乐器“镲”,汉字写作“镲”,普通话或北京话发作chǎ[tʂha214]。沈阳话发作[tʂhua213],发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和[tʂhua213]嘎拉哈的[tʂhua213]一样,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儿音尾。有时会加一个明显的儿音尾,如“锣鼓[tʂhua]”。“镲”与动词“打”搭配,“打镲”。
在沈阳话中,“打镲”这个动作中的名词“镲”和[tʂhua213]嘎拉哈这个动作除了发音相同,在语义上两者之间有关联吗?打镲时的典型动作是,拿着镲的两只手也是先有一个向外、向上的动作,然后向下收回,左右两个镲发生碰撞发出声音,伴着声音,两只手迅速散开,向上。也可以一只手中的镲相对不动,另一只手中的镲去找那面不动的镲,碰撞、摩擦之后,动态中的镲向上,仿佛画出一道弧线。气氛热烈时,伴着锣鼓点儿,只见镲左右快速碰撞,胳膊在空中划弧,镲上的红绸在空中飘动。结尾处,两个镲同时快速碰撞后,打镲人的胳膊舒展地向上分开,定格。
从打镲和[tʂhua213]嘎拉哈的动作过程来看,这两个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相同的,都是伸出手后,先做一个向外、向上的[tʂhua213]的预备动作,然后迅速地与一个物体触碰后,扫起,完成动作。上述从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感受到了沈阳话中嘎拉哈游戏的典型动作[tʂhua213]和“打镲”的典型动作的契合点。在词典中,笔者找到了“打镲”在满语中对应的词。
根据《满汉大辞典》,满语中镲叫carki[tʂhɑrkhi],打镲的动作叫carkidambi[tʂhɑrkhitɑmpi],辞典对carki的释义为:“[名]①拍板;檀板;鼓板。②镲。”从释义看,carki指两种物件。carki的动词形式均译为“打”,“carkidambi[及]①打拍板;打檀板;打鼓板。②打镲。”[2]829都是在名词的后面加上了[tampi],其中[mpi]是满语动词的词尾。在满语中carki和carkidambi是两个词,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在汉语中“镲”和“打镲”,一个是名词,另一个则是动宾词组。满语这两个词的第一音节都是[tʂhɑr],辅音[r]在元音后面可以发成完整的舌尖中颤音,也可以发成儿化音。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满语词的第一音节借入到汉语,语音上名词和动词都可以发作[tʂhɑr]或[tʂhɑ]。如果汉语中名词“镲”和动词[tʂhua213]是同一个来源,它们在满语语义上的共同点也应该是站得住的。
carki[tʂhɑrkhi]和carkidambi[tʂhɑrkhitɑmpi]是满语的固有词,两个词均收于清代满语的第一部官修词典《御制清文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和其增订本《御制增订清文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御制清文鉴》是一部单语词典,只有满文。在它的卷三礼部·祭祀器用类和乐部·乐器类都收入了carki,祭祀器用类的释义为:“像个牌子,表面光滑的、窄的,木质而成,有三片或者五片,用皮条串联起来,把这个经击打而发声、与太平鼓相合的东西叫carki。祭祀时使用,唱歌、吹、弹乐器时也使用。”[7](笔者译)乐器类的释义为:“略窄、类似木牌、表面光滑,若干个用皮条串联起来,把这种经击打发出响声的东西叫carki。”[7]卷三乐部(笔者译)《御制增订清文鉴》为满汉合璧本,每个满文词目后,不仅有汉文对译,还用满文对该词的汉文对译注了音。carki仍被收入礼部和乐部两部,礼部的满文释义相较《御制清文鉴》少了“祭祀时使用,唱歌、吹、弹乐器时也使用”(笔者译)一句。乐部的满文释义使用的是“窄的”一词,而《御制清文鉴》用的是“略窄的”形容词的比较级。汉文对译上,礼部译为“札板”,乐部译为“楂板”,两者的满文注音相同,都是jaban[tʂɑpan][8]。把“打札板”的动作叫carkidambi[8]卷七乐部。
《御制清文鉴》及其增订本虽然对“札板”的样貌进行了描述,《御制增订清文鉴》选用了汉字“打”来对译它的动词,遗憾的是没有介绍演奏“札板”或“檀板”时怎样“打”。笔者在网上查找打檀板的视频、有檀板伴奏的歌舞表演,咨询见过萨满仪式、汉军旗香艺术、满族家族说古的满族历史、民俗专家,查看清代满洲世谱式样图,均没能得到与《御制清文鉴》的描述相一致的答案。形若木牌,略窄,数量上是“三片或五片”或“若干个”,用“皮条串起来”,击打发出声音,这些信息汇集到一起,“札板”的演奏方法可能和快板中节子板的打法类似。打节子板时,手腕先向外、向上转动用力的动程和[tʂhua213]很相似,转回,击打,扫起。若“札板”的打法果真如快板中的节子板,那么“打札板”“打镲”“[tʂhua213]嘎拉哈”三个动作就都有了共同点。
汉文中的“镲”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据已掌握的、现有的汉字字源文献来看,汉字“镲”出现的时期较晚,可能要在《辞源》初版的1915年之后,旧版《辞海》刊行的1936年之前。东汉的《说文解字》、清康熙年的《康熙字典》均没有收入“镲”。《辞源》初版于1915年,2015年修订第三版,三版均未收入“镲”。“镲”收在《辞海》语词分册下册,而非《语词增补本》,应在1936年旧版时就已经收入。“镲”的释义非常简单,没有例句。“镲[鑔](chǎ)小钹,打击乐器。”[9]《现代汉语词典》也收了“镲”,“镲(鑔)chǎ名钹(bó),一种打击乐器。”[1]144《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均用“钹”来释“镲”。《说文》虽然没有收“钹”字,但《康熙字典》已经收了“钹”,为一种打击乐器。《康熙字典》的释义为:“《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並蒲拨切。音跋。《玉篇》:铃也。《集韵》:铃属。《韵会》《乐书》: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圆数寸,大者出於扶南、高昌、疎勒之国,其圆数尺,隐起如浮沤,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唐燕乐、法曲有铜钹相和之乐。《正字通》:亦谓之铜盘,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大罗天曲有铙钹,盖其小者,今亦用之以节乐。或谓之草子,或谓之铺钹。”[10]这段文字记载了钹的制造者是南齐(479年—502年)的穆士素,制造原料是铜,形状为圆形,用来和乐,古时大的钹在东南亚的扶南国、西域的高昌国、疏勒国都有使用,钹有大有小。镲是小钹。
从“镲”字的语义、读音和它在汉语词典中出现的时间来判断,汉语普通话的“镲”可能是一个非汉语固有词。但目前还不能十分确定它来自满语。约成书于清乾隆末年(1795)的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御制五体清文鉴》,在满语carki[11]词条下,汉文对译为“札板”,对应的蒙古文、维吾尔文第一音节的读音都与满文接近。蒙文发作ɑrɡil[tʃhærɡIl],ɑrɡil的发音依据《蒙汉词典》(增订本)标注[12]。维吾尔文发作cakildak[tʃhɑkhil tɑqh],维吾尔文的发音依据《五体清文鉴》中的满文注音转写[11]663。因而“镲”可能来源于满语,也可能来源于蒙古语或维吾尔语,“镲”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同源词。
主要聚居在内蒙古和东北的蒙古族也有玩嘎拉哈的游戏。据介绍,玩儿法和笔者童年时相似,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包连锁先生介绍说,也有的地方将看嘎拉哈的四面用于占卜。他们用绵羊、山羊、牛和马(或骆驼)四种动物称嘎拉哈的四面。蒙古语的嘎拉哈叫[ʃɑ]或[ʃɑɡɑi],玩嘎拉哈叫[ʃɑnɑ:tɑx]【意为玩儿游戏】。中央民族大学2018级蒙汉双语专业的毕力格同学说她在市场上听到过汉族叫它羊拐骨。口语中类似于沈阳话[tʂhua213]的动作蒙古语叫[ʃu:rx]。蒙古语的“镲”叫ɑrɡil[tʃhærɡIl]“打镲”发作ɑrɡildaxu[tʃhærɡIldǎx][12]1236,其构词思路与满语相同,在名词后面加上动词词尾,两个词的第一音节[tʃhær]也与[tʂhua213]相近,但是[ʃu:rx]与[tʃhær]的发音差异显著,因而蒙古语的动词ɑrɡildaxu[tʃhærɡIldǎx]的第一音节应该不是沈阳话里嘎拉哈游戏中动作的来源。
为什么“镲”的读音在沈阳话中和[tʂhua213]相同,在普通话或北京话中却发作[tʂha214],没有u介音?这可能和满语自身的语音变化有关。
满语辅音字母c的发音一直有争议,有[tʂh][tʃh]两种观点,国内的满语词典和教材均记作[tʂh]。关辛秋依据清代英语、朝鲜语、蒙古语对满语的记音文献,满文特定字母的创制,与满语同语族语言的辅音分布,现代满语和锡伯语的辅音分布,得出清代满语标准语的辅音字母c应该发作[tʃh],而不是[tʂh][13]。满文字母c发作[tʂh]是后来语音变化的结果。推想沈阳话在将满语的[tʃh]音位借入的时候,用[tʂh]音位加上一个元音[u]介音来模仿[tʃh]音位。普通话或北京话“镲”发作chǎ[tʂha214]的语音材料或许能对满语辅音字母c的音变研究提出一个佐证。
综上,沈阳话中[tʂhua213]嘎拉哈的动词[tʂhua213]来自满语动词carkidambi[tʂhɑrkhitɑmpi](打札板)的第一音节,发音时,发作上声,带有不明显的儿音尾。汉语普通话或北京话中打击乐器“镲”的发音,沈阳话中锣鼓[tʂhua213]的[t ʂhua213]可能也来自满语,是名词的carki[tʂhɑrkhi](札板,它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同源词)的第一音节。沈阳话中的名词[tʂhua213]发音时多数情况下带有不明显的儿音尾,有时说成[tʂhua]。
(三)“瘆”的来源
“瘆”在普通话里发作shèn[ʂən51],沈阳话中不发成卷舌的[ʂən53]而是平舌的[sən53]。去声,调值为53。其语义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相同,“使人害怕;可怕”,词典中的两个例子“瘆人|夜里一个人走山路有点儿瘆得慌。”在沈阳话中均适用。
汉文文献中“瘆”的声母多读[s]。据已掌握的汉字文献,《说文解字》未收该字。《康熙字典》收录,其释义为:“《集韵》楚锦切。音墋。骇恐貌。又《广韵》疎锦切。《集韵》所锦切。並参上声。义同。又《玉篇》寒病也。又《集韵》所禁切。音渗。义同。”[10]733《康熙字典》汇总了“瘆”的两个语义,一个记录在《集韵》,一个在《玉篇》;共有四处反切注音,楚锦切、疎锦切、所锦切、所禁切。这四个反切上字,两个是“所”字,其现代汉语的声母为[s]。“疎”字现在读作shū[ʂu55],但是在《广韵》中也用“所”做它的反切上字来标音,“(广)所葅切山鱼开三平遇ʃǐo”[14]可以认为“所”与“疎”的声母曾经相同。“楚”的声母现代读作ch[tʂh],从其古代声母拟音为[tʃh]来看[14]97,“楚”的声母与“所”不同。如果把“所”和“疎”归为一类的话,用现代汉语来读“瘆”的声母,有s[s]和ch[tʂh]两个读音,s[s]占3/4,没有sh[ʂ]音。
“瘆”的反切下字,有“锦”“禁”两字,从中古汉语的拟音和现代汉语的读音来看,两者的韵母相同,中古为[kǐěm],现在同为[in],但是声调不同,“锦”为上声,“禁”为去声[14]236-237。其现代汉语的韵母均是[in],加上“瘆”的声母[s],现代汉语当拟音为[sin],很显然汉语中没有这个音节。
依据汉文文献,“瘆”的同音字“墋”“渗”的韵母为[ən]。《康熙字典》列了两个“瘆”的同音字,作“骇恐貌”同“墋”。据《康熙字典》记载,“墋”在《广韵》记初朕切。《集韵》《韵会》《正韵》楚锦切,並音碜[10]170。按“碜”的现代读音,当读chěn[tʂhən214],韵母为[ən]。作“寒病”意音同“渗”。按“渗”的普通话读音,它与“瘆”是同音字,都读shèn[ʂən51]。但是《广韵》中“渗”的反切上字是“所”字。“(广)所禁切生沁开三去深”[14]231,《广韵》中记载的“渗”是个去声、平舌的[s]而非翘舌的[ʂ]。结合上述文献,“瘆”“渗”同音,北宋时期(《广韵》成书于此时)它们的读音可拟为[sən51],这与沈阳话中“瘆”“渗”的情形相同,都是平舌、韵母为[ən]、去声,沈阳话拟为[sən53]。
“瘆”表达“骇恐貌”的语义应该是后起的,记载“害怕”义的文献出现在明清之际。“瘆”属疒部,《康熙字典》汇集其语义两分,“寒病”和“骇恐貌”。从造字的角度来看,“寒病”意应该早于“骇恐貌”。收入“骇恐貌”的《集韵》成书于宋代,收入“寒病”意的《玉篇》完成于南朝梁大同九年(543),南朝下启隋朝,也就是说《玉篇》早于《集韵》问世。从这两部文献来看,“寒病”义确实早于“骇恐貌”。《汉语大字典》收了“瘆”(shèn)字,语义仍为这两分。“骇恐貌”的援例来自距清最近的明代,为明汤显祖《牡丹亭·魂游》中的一句“一霎价心儿瘆,原来是弄风铃台殿冬丁。”这个“瘆”虽然表示害怕,但是没有使动义,和《现代汉语词典》中所示语义“使人害怕”不完全相同。“寒病”意所引两个例子都来自唐代。一是刘禹锡在《述病》中言:“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瘆如覆癏于躬。”二是柳宗元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15]从这三则文献所记载的使用过该字的年代来看,“寒病”义也早于“骇恐貌”。《牡丹亭》成书于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也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天命二年,也就是说,“瘆”作“害怕”义的文献出现在明清之际,而不是在《集韵》成书的宋代。虽然《集韵》说“瘆”的意思是“骇恐貌”,但目前尚未见文献中的实用援例。
不知何故,《辞海》(语词分册)和《辞源》都未收“瘆”字。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从其1978年的第一版就收了“瘆”字,却未收“寒病”义(或许口语中已经找不到表“寒病”的例子),也未收“骇恐貌”,而是收了与“骇恐貌”相关的语义,“瘆(瘮)shèn使人害怕;可怕:~人|~得慌”[16]。延至现在的第七版,该词条的读音和释义一直未变。从现有材料还很难得出“骇恐貌”“使人害怕”的语义是由“寒病”义引申发展而来的。
“瘆”字所承载的信息可谓细腻而复杂,兼有害怕和使动两个语义。这与满语中表使役的动词sengguwebumbi[səŋkuwəpumpi](使人害怕)的语义完全相同,发音上与其第一音节相近,与沈阳话的发音更接近。sengguwembi[səŋkuw əmpi]是满语的基本动词,意为:害怕;惧怕;畏惧;恐惧;发怵。与该动词相关的派生动词有sengguwebumbi(动词,使恐惧,使可怕;附加bu音节),sengguwecembi(动词,一直在恐惧,时常在恐惧,总是畏难;附加ce音节),sengguwenumbi(动词,一起畏惧,一起畏难;附加nu音节),sengguwecuke(形容词,恐惧的,担心的)sengguwecun(名词,恐惧,畏惧)[17]。
sengguwembi是满语的固有词。《御制清文鉴》在卷八人部四·怕惧类收入该词,有两义:“把内心畏惧叫做sengguwembi。把倦怠也叫做sengguwembi。”[7]卷八人部(笔者译)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将该词分收在第十三卷人部四·怕惧类和第十七卷人部八·懒惰类两处,怕惧类中保留了《御制清文鉴》满文释义的前一句“把内心畏惧叫做sengguwembi。”汉文对译为“惧”。在懒惰类的释义是:“把对事情倦怠(发懒、心灰意懒),不愿上前叫sengguwembi。”[8]卷十三、十七人部(笔者译)汉文对译为“发怵”。乾隆朝辞典将sengguwembi修订为两义:“惧”和“发怵”。两处、两个意思的汉文注音相同,都是“塞鞥沽倭穆毕”。第一音节由“塞鞥”两个汉字拼合而成。“塞”的中古拟音为[sək],入声[14]22。“塞”+“鞥(ēng)”的读音按北方明清音系拟为去声[sə+əŋ],合为[səŋ]。这个拟音符合满文seng guwembi第一音节的字母读音[səŋ]。
如果汉语中“使人害怕”的语义是借自满语sengguwebumbi[səŋkuwəpumpi](使人害怕)的第一音节,为什么不选择一个音节发音为seng的汉字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普通话中,seng音节四个声调只有一个第一声的汉字“僧”,其余声调无字。也就是说,找不到一个音节读音与seng相同,语义上与“使人害怕”有关联的汉字。现有的汉字“瘆”在语义上与“使人害怕”有关联,语音上sengguwebumbi的第一音节与沈阳话更接近,从上述古音构拟的文献看,也与沈阳话更接近。也许最早用“瘆”字来记“使人害怕”的意思是从东北的满族地区开始的。
综上,沈阳话中的“瘆”,发音为[sən53],意为“使人害怕”,有使动和“害怕”两重语义,因表达这一细腻语义的需要,推想可能早在明代人们就在口语中将满语表示“内心畏惧”的动词sengguwembi[səŋkuwəmpi]的第一音节借入汉语,再后来也许是同时(缺少援例)将表使动义的动词sengguwebumbi[səŋkuwəpumpi]使人害怕)的第一音节借进汉语。早期借入时,由于汉语中找不到与seng[səŋ]语音和语义相匹配的汉字,就选择了语音相近,语义有关联的汉字“瘆”。这个借入过程在“怼”字上正在发生。
(四)“怼”的来源
沈阳话中[tui]为上声,调值为213,发作[tui213]。[tui213]为动词,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争执时用拳推对方,一般是身体的上半部分,前胸、靠近肩膀的部位或者腹部,有时是后背。比如,两个孩子打架,辩理时一方说:“他先[tui213]我,我才打他的。”“他[tui213]了我三下儿,我才还手的。”孩子在外面被人[tui213]了,回家诉委屈,妈妈劝孩子:“算了,[tui213]两下儿,[tui213]两下儿吧,咱让着他。”二是往前或向里推进,有硬塞意。例如,停车时说:“前边还有地儿,还可以往前[tui213]一点儿。”盖红酒瓶的瓶塞时说:“劲儿小了不行,得使劲儿往里[tui213]。”三是由于对方先在言语上冲撞自己而被迫地反驳或质问。比如:“我没客气,当时就[tui213]了他几句。”“他这么说你,你就干听着,你不能[tui213]他两句啊?”据张明辉等对北京、东北、洛阳、广州、厦门等方言词典的统计,“怼”在各地都有捶、杵、推搡、捅、用拳头直打等用法。汉字写作“”“”“搥”[18],选用“”字居多。现在人们一般写作“怼”。沈阳话里所有的反驳或质问的语义,在哈尔滨方言里也存在。据《哈尔滨方言词典》记载,哈尔滨方言中也有“斥责”“责骂”的语义,用“”字来记,使用时为双音节词,“咕”“搭/嗒”“搡”[19]。同样的句子,在沈阳话中可以用“”一个单字来完成。
2017年“怼”被《咬文嚼字》杂志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人们用它来表示故意找茬、反抗、反对等意思。后来其义扩大,进一步衍生出‘比拼’‘竞争’等含义。”[20]巩建文通过收集“怼”的使用实例,得出“怼”有三个语义,1.反驳、指责。重在用语言驳斥、指责对方;2.对抗、攻击。有用愤怒语言攻击之意,程度较深;严重语言攻击。3.打、干、撞等行为动作[21]。前两个语义可以合为一个,意为反驳或用言语反击,程度上有轻重之分。“怼”的流行义在反驳或用言语反击,对“怼”来源的研究关注点也是这一语义。打、撞等义多用于方言。
关于“怼”作“反驳或用言语反击”义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依据《说文解字》有“怼,怨也”的记载,认为“言语攻击”义是由“怼”发展而来,为旧词新义[22][23]。作“怨怼”义时读作去声duì。依据[tui213]在方言中的广泛使用,认为应写作方言字“”,“直接源于其方言词义,而非‘怼’的文言词义。”[24]若是旧词新义,有两点理据上的不足。其一,[tui213]与“怼”的声调不同。其二,由“怨”到“言语攻击”,语义上虽然有关联,但从所发表的论文所援引的例子来看,看不到两者之间语义的演变轨迹。若是来自方言词“”,“”又是来自哪里?
满语中有一个动词duilembi[tuiləmpi],《满汉大辞典》对译为:质对、勘断[2]735。它的第一音节[tui]与“”和“怼”的发音相同。duilembi也是满语的固有词汇,在《御制清文鉴》中已收录。属政部·词讼类词条。“把凡事验实、审理叫做duilembi。”[7]卷二政部(笔者译)《御制增订清文鉴》则保留了该词条的满语释义,增加了汉文对译“勘断”,汉文对满文的注音是“都衣勒穆毕”[8]卷五政部。第一音节当发作[tui]。
成书于嘉庆七年(1802)的《庸言知旨》,是清代最重要的满汉合璧会话书之一。其第十章中有一句使用duilembi含有“质问”义的语料。“cananggi ucaraha de,(前日遇着了)inde duileki seme,(要与他较正较证,意即想怼他几句。)gisun femen de isinjifi,(话到了嘴边上)dere de eterakū,(脸上待着没法见,意即可是拉不下脸来)ainara sefi nakaha(那上头打住了,意即也就放弃了没说)”[25]duileki seme是动词duilembi的祈愿式,动词词根duile加上表意愿的成分ki seme,意为想要去质问。当时的汉语将duilembi对译为“较正较证”。可见嘉庆年间还没有用汉字“怼”或“”来对译duilembi。《新满汉大词典》也援引此例,将duilembi的汉语对译为“校正,校对,核对”[17]200。现在的满汉词典中也没有使用汉字“怼”或“”来对译duilembi。虽然作“质问”义的“怼”已成为流行词,它在东北方言的日常口语中使用频繁,但似乎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普通话词语来替代它。
《现代汉语词典》只收了“怼”的“怨恨”义,标为第四声(duì)。直至第七版表“质问”义,第三声的duǐ也未收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dui音节第三声没有对应的汉字。和“瘆”的情况一样,现在的流行义选用已有的汉字,与duǐ的语义有关联的“怼”字来记录。
综上,沈阳话借用满语表“质问”“勘断”义的动词duilembi的第一音节,表达“用言语来反击对方”的语义。方言字记作“”,现在流行记作“怼”,发作第三声。“怼”(duǐ)所承载的感情色彩和细腻语义有不可替代性。表“怨恨”义,发作第四声的“怼”与“怼”(duǐ)在语义上有关联,但“怼”(duǐ)不是“怼”的引申义。沈阳话中[tui213]表示“击打”和“硬塞”意的来源尚没有找到与满文相关的语料。
三、结语
(一)这些满语多音节词应该不是早期借自汉语的
满语的这些多音节词会是早期满语从汉语借去的吗?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没有找到佐证。从清代官方和民间对满洲外词汇的语言态度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前述清代第一部满文词典《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列一万二千余词条。63年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其增订版《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增加了五千余词条,扩展了近三分之一的容量。除增加满语的固有词外,增订版中将“新乐府”这样的汉文化特有词,满语人已经习惯用汉语称说的词,都放入专门介绍来自清语外的词条集《续入新语》,“新定国语增入者尤为详备,于以昭示来兹,为万万世同文之准云。”[8]序
雍正八年,1730年刊行的汉文注音满语教科书《清文启蒙》对后世影响极大,更有英文版行世。它最早为作者舞格先生家庭自用,“此本庭训小子”[26]。在其第一卷作者专辟“满洲外联字”,列出33个来自满语之外的词语,这些词经过辨识可知,有的来自蒙古语,如sain[sain](吉、善、好);有的来自汉语,如toombi[thuompi](骂,可能借自汉语“唾骂”的“唾”);多数词于今已辨别不出它的来源。在长白人舞格先生看来,满洲内和满洲外的词汇在满语的学习之初就要划分清楚。
这些满语借词进入汉语的时期不同。从文献来看,“瘆”可能早在明代就进入汉语了。“怼”正走在由方言进入普通话的路上。最初这些词都是以单音词进入汉语的。
(二)这些满源词(借自满语词首音节)的共同特点
语义上,它们所承载的信息细腻、传神,有的词不仅有词汇义还有语法意义,如“瘆”有使动义。读音上,有的音节现代汉语中没有对应的字,如chuǎ和duǐ;从已经选用的汉字来看,其《说文》释义或早期文献释义与本文所讨论的词义有关联,但缺少两者之间有强烈关联的文献证据。比如,怼,怨也(《说文》)与“用言语反击”;“瘆”,寒病与“使人害怕”。《辞源》中“瘆(shèn)”“怼(duǐ)”都没有收入,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在外观上,它们具有隐蔽性,以至于不被认为它们是借词。在使用范围上,它们在日常口语中十分常用。
(三)汉语中的第一音节音译词的构词原则
在汉语中选用语义上有关联、发音相近的汉字来记录这些音译词。比如:“欻”“瘆”“怼”。也有找不到语义有关联的汉字的情况,例如“珍儿”“砧儿”“真儿”。有的汉字《说文》中没有的或为其造新字,如“瘆”;有的字一直有两种写法,如用“怼”和“”来记“duǐ”。
这种类型的满语借词不是几个词,可能是一批词。例如汉语普通话中的“赖”“怂/”,方言词“捯”,对应的满语词是laidamb[ilɑitɑmbi]【意为:诬赖(无中生有)】、撒赖(小孩哭闹、撒赖)和赖(把别人的占为己有,把别人的好争为自己的),songgotu[soŋkothu](意为:爱哭的、好哭的),dorimbi[torimpi]【意为:(向上)窜、跳、爬、扒】。受篇幅所限,文献语料不能详尽展示。
除了从满语中借来的这些第一音节词,有一些英语词也在以这种方式借入到汉语中。例如,网络上看到用汉字“趴”来记录英语party[phɑ:thI](聚会,“开个单身趴”),用“掰”来记录battle[bæthl](战斗、较量),用“劈”来记录英文缩写“PK”(与对方决胜负)的第一个字母P[phi:]。将某一种语言某个多音节词中的语义和它的第一音节加上一个声调借入到汉语中,进而变身为与某个语义上有些许关联的汉字,这是汉语音译借词的一种借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