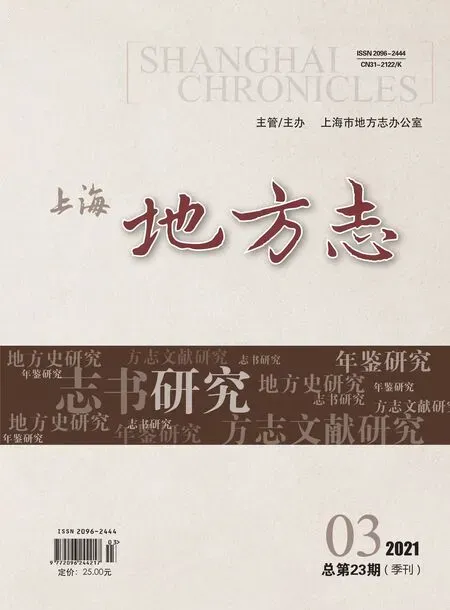嘉庆《四川通志》述评
张保见
嘉庆《四川通志》二百零四卷,首二十二卷,常明修,杨芳灿、谭光祜纂,开局于嘉庆十七年,蒇事于二十一年,历时五年,是现存部头最大、体例最为完备,也是最后一部王朝时期修纂的四川通志,被公认为存世明清七部省志中价值最高的一部。然学界对其至今没有专论,所见者仅为提要性或附带介绍性成果(1)参看张秀熟《重印清嘉庆<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书首,巴蜀书社1984年;何金文:《四川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印1985年,第82—83页;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21—28页;张学君:《四川通志考》,《国学》第二集,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2015年12月。,故兹联缀数语,予以述说。
一
巴蜀大地,文明悠久, 自汉以来,向有纂修地方史志的传统。惜宋以前诸书,除《华阳国志》外,大都失传。今人刘纬毅辑录有《云阳记》《巴郡图经》《巴蜀异物志》《巴蜀志》等,近五十种(2)参看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引巴蜀地志,据笔者考证,尚有扬雄《蜀王本记》、来敏《本蜀论》、谯周《巴志》、段氏《游蜀记》、李膺《益州记》等,凡三十余种(3)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0—268、388—391、401页。。张国淦研究,仅地方志,巴蜀地区,元以前可考的,共得二百九十种,其中通志为五十四种(4)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641—711页。。元代,四川省正式定名,然无通志出现。
明清地方志编修与一统志关系密切,修志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成就巨大,今存古方志,大多成于这一时期,尤以清代为多。 这一时期也是四川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期。何金文认为现存四川方志约有六百余种(5)何文金:《四川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印1985年,第8页。,《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收书792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671种。笔者认为综括各类志书,以及近些年重新发现的志书,应当不低于九百种。所存志书以明清,特别是清代,又以乾隆后方志为主,张秀熟统计清代共纂修方志四百六十种(6)张秀熟:《重印清嘉庆<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书首,巴蜀书社1984年,第3页。,是目前四川存世方志的主体部分。
明代,以“四川”命名的省志出现。今存最早的为正德《四川志》,三十七卷。书首附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川巡按御史卢雍序:“正德丁丑,同官瑞阳熊君尚弼,以清戎命与雍同事此方。君按治暇,阅旧志,病其记注多遗错,乃更为裁定。”熊尚弼,名相,江西高安人,历官有能名,时任四川清军御史。据熊相序例所言:“四川旧志,天顺庚辰布政马君显聘提学佥事眉山黄君明善所纂也。”表明四川省志的编修,在天顺间已经开始,但未成定本,或未加刊刻。此志的编修,是在寻绎黄明善旧稿的基础上而成,熊相称“余特正其文与误耳”,改动不大,故用时较短。全志结构先区分地域,后横排门类,虽大体覆盖四川行省基本事类,然篇幅较小,遗留问题仍多。
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川巡抚刘大谟聘用王三溪、杨升庵、杨芳洲三人重修,两月余即成初稿,是为嘉靖《四川总志》,八十卷,今存。前十六卷为志,后六十四卷为艺文。编排大体遵循正德志,而体例精严过之,略有增补订正。是志艺文收录所占篇幅过大,虽有保存文献之功,然于志体有碍,“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地理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
万历初,在虞怀忠、王廷瞻等人支持下,郭棐等再纂《四川总志》,并于九年(1581年)刊行,今称万历九年志。全书三十四卷,对于旧志错误之处,有所订正。然成书仓促,部头较小,缺漏仍多。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刊行吴之皞修、杜应芳纂《四川通志》,即万历四十七年志。志凡二十七卷,另收录杨慎《四川总志》艺文六十四卷,续补艺文五十六卷。
明修四志,在存史方面,有一定功用。但对于地域辽阔的四川来讲,明修志书部头较小,枝干虽备,而书写局促,或于志体不符,“未能悉中体要”(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四川通志四十七卷”条,中华书局1965年。,且漏略不足处较多。
二
清康熙初,巡抚张德地、罗森等有鉴于四川通志“兵烬之后,仅有存者,类多阙文”(9)【清】蔡毓荣:《四川通志序》,康熙《四川通志》卷首,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着手修订新志。时任总督蔡毓荣委任成都府知府钱受祺主纂,成书三十七卷,于十二年刊刻,是为康熙《四川总志》。此志在纂修传承,以及明末清初四川史料保存等方面,具有较高价值,然“以兵燹之后,文献无证,亦多所脱漏”(1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四川通志四十七卷”条,中华书局1965年。。
康熙二十五年,一统志开馆。雍正时,为修一统志,“勅下直省纂修通志”,四川通志再修开始。雍正十一年,成四十七卷,首一卷,刊刻于乾隆元年,是为雍正《四川通志》。全书较之明代与清初,部头有所增加,内容有所充实,虽误缪或存, “然其甄综排比,较旧志则可据多矣”(1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四川通志四十七卷”条,中华书局1965年。。
嘉庆十五年,常明“奉命制蜀,持节入栈,得以周览岷嶓,观风江汉”,于是“急索省志阅之”,发现“其间职官、建置、营制、边防,旧志与今多不符合。高宗纯皇帝平定两金川,我皇上剿灭教匪,庙谟睿算,均应恭载简端,昭示来许者,亦阙而未备”,原因就在于“旧志成于雍正八年,迄今八十年,未尝续修故也”。经理逾年,政事咸和,“重熙累洽,一道同风”,文献“凡当日湮没于山岩屋壁者尽发”,于是“自壬申春肇事,讫甲戌冬,稿本粗就”,而“删讹补遗,芟繁剔复,如是者又年余,乃得付剞劂而成书。”(12)【清】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嘉庆志所作,其来有自,“董观桥抚军任蜀藩时,尝有志于此,以迁去不果”。布政司方积“踵其议,请于制府,奏之朝”,朝廷报可。成都知府李尧栋“力主其事。先聚书数千卷,金石文复数百卷”,聘请杨芳灿、谭光祜“发凡起例,总其大纲。”(13)【清】李銮宣:《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常明(?—1817年),佟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历湖南桂阳知州、云南曲靖知府、贵州贵东道,擢贵州按察使,赐号智勇巴图鲁。后加布政使衔,历贵州布政使、巡抚,充伊犁领队大臣、库车办事大臣。嘉庆十年,授湖北盐法道,迁湖北巡抚。十五年,擢四川总督。十八年,署成都将军。二十二年,卒任。赠太子少保,謚襄恪。《清史稿》卷三五八有传。
杨芳灿(1754—1816年),字才叔,号蓉裳,江苏常州金匮人,乾隆五十二年拔贡生,历甘肃伏羌知县、灵州知州、户部员外郎,主纂《大清会典》,主讲锦江书院。诗文华赡,有《芙蓉山馆诗文钞》。《清史稿》卷四八五有传。
谭光祜(1772—1813年),尚忠子,字子受,号铁箫,江西南丰人。能诗文,善度曲,精骑射,历官叙州马边同知、四川夔州府通判、湖北归州知州,嘉庆十四年署知潼川府。
三
嘉庆志纂修时,组织了严密的机构,建立了庞大的队伍。总督常明任总裁,在政治与经济上为志书正常编修提供了保障。以四川学政赵佩湘、毛谟为参阅,布政使方积、陈若霖,按察使常发祥、曹六兴,分巡成绵道瞿曾辑、奇成额为提调。协理则包括成都知府曹六兴在内的四川各地要员。组成人员囊括了四川一省主要机构领导,尤其是学政,以及地方上道、府、直隶州、厅的一把手,包含了期间的人员变动,为修志协调不同部门,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监管,完成各地资料的采访收集,指定了具体责任人,这对于各司其职,避免互相扯皮推诿,是有利的。
以杨芳灿、谭光祜为编辑,二人皆为博学硕儒,文字功底深厚,杨芳灿曾任《大清会典》主纂,经验丰富,是有力的学术支撑。又以翰林院编修谭言霭、候选内阁中书严学淦,以及知县等下级官员、举人等为分辑。编辑和分辑是事实上的写作班子,分辑分类、分条目写作,最后汇总于编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布政使司经历王怀荫、熊瞻云作为督梓,即负责印刷事务。谭光祜负责绘图。这四个部门,涵盖了具体编纂时的所有方面,即“妙简僚属,广揽缙绅,俾之分司其目”(14)【清】李銮宣:《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经费有保障,组织和人事安排的得力有效,是为嘉庆志可取者一。
正是在组织得力、经费保障、人员精干的基础上,成书“计天文、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经籍、纪事、西域、杂类,志凡十二,每志各有子目。卷凡二百二十六”(15)【清】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其中卷首一到十三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圣训,十三到二十为四帝宸章,二十一为御赐匾联墨刻经典书籍、御制诗文集、颁发匾额墨刻书籍,二十二为历代诰敕。表明通志编修中贯穿着维护皇帝崇高地位的观念,体现着皇权的威严。正文卷一为天文志,下分分野一目。卷二至卷六一为舆地志,下设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山川、江源、堤堰、城池、公署、关隘、津梁、祠庙、寺观、陵墓、古迹、金石、风俗等目。卷六一至卷七五为食货志,下设田赋、户口、徭役、榷政、盐法、茶法、钱法、木政、仓储、蠲赈、物产等目。卷七六至卷八一为学校志,下设学校、书院、祀典等目。卷八二至卷九八为武备志,下分兵制、屯田、驿传、递铺、边防、土司等目。卷九九至卷一二一为职官志,下设题名、政绩、忠节、谪宦、杂传等目。卷一二二至卷一四二为选举志,下设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封荫、荐辟等目。卷一四三至卷一八一为人物志,下设人物、忠节、孝友、行谊、隐逸、流寓、艺术、仙释、列女、杂传等目。卷一八三至卷一八八为经籍志,下设经、史、子、集、别部及附录等目。卷一八九至卷一九〇为纪事志。卷一九一至卷一九六为西域志。卷一九七至卷二〇四为杂类志,下设纪闻、外纪、祥异、辨讹等目。各目下,依据具体需要,又分或附有细目,在屯田下附屯练、团练,列女下有贤淑、才艺、义烈、贞孝、完节等。
嘉庆志分十二门,门下设目,目下依据实际情况,分设或附有细目,是较为典型的纲目体志书,繁而不乱,条理明晰,包罗宏富,“视旧志撰次较为得体,而卷帙之增不啻十倍过之”(16)【清】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分门时专设经籍类,提要历代巴蜀人著述。这一安排,较有特色,且能突出巴蜀文风鼎盛的特点,可视为通志纂修中一个创举。舆地志下分设江源一目,标示出巴蜀地区地域方面学术上的一个专有部门,是方志能够通过门目设置或类别在门目中的分布层级,最大限度涵盖区域特色的具体体现。因散诗文等于具体篇章中,故无艺文类,增加了舆地与人物的篇幅,这一安排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是一致的,增强了嘉庆志的地理属性,提高了实用性。
再有,嘉庆志增加了较多内容,部分有精审考辨,尤以明末与清代为重要。常明云:“夫江水出于巴萨过拉木山,黑水实为喀喇木苏河,此桑钦、郦注未悉之山川也。职贡极于廓尔喀,郡县列于大小金川,此尧封禹甸未闻之疆域也。粮站抵于唐古特,屯戍接于巴勒布,此汉主、唐宗未立之边防也。賨人敛舞而力农,巴女罢歌而输织,此太史公未录之土风也。升庵以放废老滇,此度以乱离去蜀,此陈承祚未纪之耆旧也。眉山之义旗拒贼,石砫之嫠妇勤王,此常道将未志之士女也。献贼以窃据被诛,教匪以左道致戮,此张唐英未编之梼杌也。江源绘于蕃部,天文画于鹑首,此唐求未缉之图经也。茶纲通乎卫藏,盐井济于滇黔,此班固未书之食货也。呜呼!备矣。”(17)【清】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皆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文治武功,知己之言,可谓实录。在存史同时,“愿治斯土者读之,而知所为张弛”,提供资治之用。“生斯土者读之,而知所为劝惩”,兼有教化之功。所谓“是书之有裨益于蜀之吏民也,不亦伟欤”(18)【清】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虽嫌自矜,也正是方志功能的具体展现。
四
嘉庆志的西域门凡六卷,专述西藏事务,颇值一书。
西域篇序云:“我国家声教所讫,遐迩弥遗。自大渡河以西,万有余里,咸稽颡输诚,以时入贡。特令大臣驻藏,以镇辖之。分设营汛,置文武官弁,以抚驭之。”开宗明义,清在西藏设官分职,进行实际统治,即西藏被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又云:“西藏僻据西海,而与蜀接壤”,“旧以打箭炉迤西之里塘、巴塘属于西域,谓入藏之路自打箭炉始也。按,雍正五年,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于巴塘之西察木多之东,勘定疆界,立界碑于南登之宁静山。是南登以东为雅州府之舆地,南登迤西之江卡为入藏之门户矣。”一方面揭示,清中央政府曾派员明勘川藏二区具体辖区,以南登宁静山为界。雍正五年(1727年)这次勘界,带来的政区调整,对于西藏、云南、青海、四川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四省区在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以高度凝练的文字,概括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版图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四川的关联。
清朝入关之初,在青藏高原上的直接控制区基本上与明朝相同。今天大渡河以西的四川藏区,按照明末已形成的传统,在政治上向青海蒙古效忠并缴纳贡赋,而在宗教上深受西藏约束。对这些地区,清政府基本上处于听之任之的无任何控制权的状态。
其后,随着残明势力的肃清、三藩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日趋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边疆问题开始引起政府的重视。面对准噶尔部咄咄逼人的攻势,康熙帝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先后两次将其击败,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准噶尔部的称霸势头,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局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北,西宁等地的统治得到巩固。军威所震,青海蒙古纷纷请求归顺,接受清朝的册封。尽管此时清政府对青海的事务仍未加干涉,而双方的关系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青海由此逐渐成为清朝的内属藩地,为清朝加强同西藏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在川西藏区,出现了土司内附的第一次高潮,打箭炉、松藩、茂州等邻近内地的土司纷纷于此时向清朝效忠,接受清政府的册封。准噶尔部侵占西藏后,康熙帝力排众议,果断地下令进军,在恢复了西藏安定的同时,也使清朝的势力第一次深入到高原腹地,藏东半壁处于清军的直接控制之下,驻军和任免拉萨地方政府的统治官员,使西藏也纳入了清朝内属藩地的范围之内。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对青海蒙古的旗制分治和派驻西宁办事大臣,使青海已几乎等同于内地郡县。两次事件影响所及,四川藏区出现了第二次土司投诚的高潮,藏北七十九族渐次被招抚。清政府积极处置了康济鼐被袭杀事件,并设置驻藏大臣,对西藏的管辖进一步加强。此时,川西藏区出现了第三次土司归顺的高潮。随后,清政府正式派员勘分了藏、川、滇、青等省区的边界。
至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清朝基本上完成了对高原的控制,包括西藏在内的高原地区再次融入多民族大家庭之中。综观这一时期,青海蒙古和西藏地方政府都经历了逐渐接受并纳入清朝统治体系的过程,融入多民族大家庭趋势的不可逆转性,是本期本区政区变迁的最大特点。
这一融入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胜利起了推动作用,应该说军事上的强大和不断胜利是这一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最直接因素。
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在高原缘边的经营,特别是始自唐代的汉藏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西藏文明自身的东向性发展是其内在因素(19)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石硕在其《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有系统论述。。
清朝政府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是对青藏高原进行积极经营的外在因素。清朝是在形成同蒙古的结盟后才得以顺利入主中原的,蒙古对清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关系重大。准噶尔的强大和东进,严重影响到西北蒙古的稳定,成为三藩之后清政府的最大威胁,遏制准噶尔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康熙帝考虑的头等大事。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地区以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和对蒙古部族有力的宗教影响,引起了清朝极大的关注,为了避免青藏高原落入准噶尔之手,使川、滇、甘等区域屏藩尽失,军事上处于被动,也为了避免西藏受准噶尔的控制,从而影响到蒙古各部的稳定,除了正面军事上的反击外,积极经营青藏高原,消除隐患,并从侧翼牵制准噶尔,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回顾清代前期经营西藏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这一过程源自四川内部稳定后,从控制川西、藏东(康区)土司等地方势力逐步开始。稳定、强大而富裕的四川,对于经营康区,进而治理西藏,是强有力的后方保障。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判定的是,有川始有康、藏。自清初即已显现的西藏与四川的密切关系,既是嘉庆志单列西域门,专述西藏的原因,也是这种结果的呈现。民国以来,自任乃强等学者始,已达成治藏必先安康的共识,今人认为,这句话有必要加以补充,即安康首须定川。这是嘉庆志给今人的启示和警醒。
嘉庆志西域门凡六卷,资料丰富,每述一地,皆分星野、形势、风俗、塘铺诸目,记载明晰,事实上一地即是一篇独立方志,首尾完备,价值较高。何文金认为“此为迄今所见正式成书刊行的最早的西藏志书”(20)何文金:《四川方志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印1985年,第81页。,志中许多资料为独见,是研究晚清以前西藏问题的重要史料,诸如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以及各类诗文等。卷首二十二卷,亦包含不少有关藏区资料。这些资料,应当引起藏学研究界的关注。
五
常明修《四川通志》成书后,有嘉庆二十一年刻本,传世较广。今有国家图书馆等数十家图书馆收藏。四川省内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十余家图书馆,亦有收藏。然出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这些公共图书馆内收藏的嘉庆《四川通志》,普通读者使用并不容易。1967年,中国台湾华文书局曾影印出版,在大陆地区流传很少。1984年,巴蜀书社予以单行影印,是较为常见本。2011年,凤凰出版社以之作为《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之一种,影印出版,然这套书部头较大,亦非一般读者所能常见。截至目前,没有点校整理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