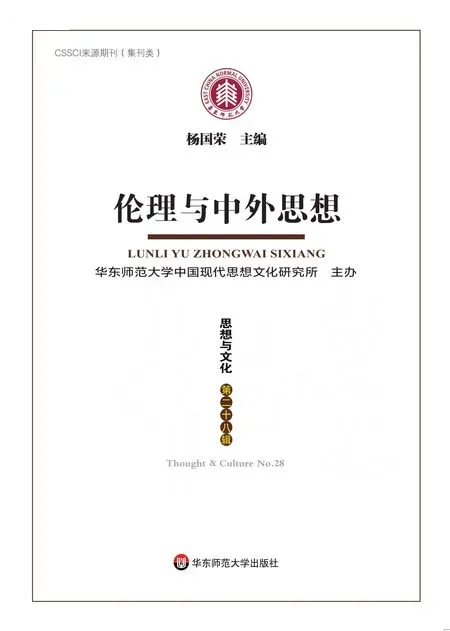阿多诺论哥白尼革命与虚无主义*
●
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系列讲座中,阿多诺主要从消极方面来理解康德式哥白尼革命的思想成就,在康德那里一个现代信念根深蒂固地被确立下来: 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根本预设,无论它们在实践生活当中多么重要,都不再能够享有理性论证的基础,“康德在作为认知对象的知识领域与作为信仰对象的形而上学范畴之间的截然对立的二元区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根本前提”(1)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odney Livingstone (trans.), London: Polity Press, 2001, p.6.。在康德式不可知论或所谓“康德式谦逊”(2)Rae Langton, Kantian Humility: Our Ignoran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阿多诺看到的是“对形而上学的理念、观念的资产阶级悬置”(3)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48.。康德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把握到时代症候,表述出一种更为现代的形而上学-宗教观。阿多诺关于哥白尼革命思想蕴涵的阐述,不是一般性的学究性诠释,而是思想家的匠心独运。
一、 哥白尼革命与认知的节制
阿多诺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纯粹理性批判》专题系列讲座的开场白,“我假设大家对《纯粹理性批判》一无所知”,接着他又补充说,“这个假设既恰当又不太恰当”。一般智识阶层对第一批判多少都曾有所耳闻,不可能一无所知,问题在于,一旦某个深刻的思想广泛流传,甚至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极可能会偏离原意,哥白尼革命亦不能幸免。按照一般的理解,康德通过发动一场“哥白尼革命”颠覆了传统认知模式,最终将认知基础从客体自身转向认知主体的思维结构,自康德之后世人才开始倾向于认为客观性是主观认知活动构建而成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哲学的主体转向早在康德之前就已开始,在现代哲学史上至少要回溯到笛卡尔,而休谟的主观主义色彩比康德浓厚得多。因此,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清除认知的客观性,并非康德想完成的事情。(4)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批判哲学是要将认知的客观性建立在主体之上,这与通过怀疑论来强调主体性的经验主义非常不一样。哥白尼式转向的思想旨趣,不是所谓的挺立主体性或弘扬主观理性等,而是要“建立或者拯救认知的客观属性”(5)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2.。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获得关于这些对象的知识?这才是康德真正关心的。
批判哲学一方面遭到大众的误解,另一方面又被实证主义视为过时的“偶像崇拜物”,莱茵巴赫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就明确提出: 第一批判提出的问题不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的实质性内容已经被科学知识的进步所替代,我们最好将康德哲学当成博物馆的历史文物来看待。(6)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5.不同于莱茵巴赫等人,阿多诺对第一批判始终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在他看来,哥白尼式哲学革命的成果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认知理论”,兼有积极与消极两种意义: 积极而言,康德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科学也就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消极而言,他严格限制了绝对概念运用的可能范围。“哥白尼革命”的哲学成就主要应从消极方面来理解,这尤其体现在“先验辩证论”对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的系统批驳中。(7)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5.对此,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评价说,康德用理性的武器“袭击了天国”,使万王之王的上帝“倒在血泊中”,
康德把上帝这一本体看成是先验观念里的虚构,是一种由自然幻觉产生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本体,关于上帝,一无所知,“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8)亨利希·海涅: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4页。
阿多诺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一句中,句子的重音应该放在“未经证明”(9)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5.,这句话强调了康德对关于上帝存在的任何可能证据的悬置。人们常常说,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家门,第二批判中又偷偷把上帝请回来。这个说法其实颇值得商榷,因为,第一批判自身并不是一部无神论著作,不是对绝对概念的简单否定,其“真正的蕴涵毋宁说是对证据之可能性的限制……它否认某些特定问题是理性的,因此把它们从我们的视域中驱逐出去,这才是它真正重要的地方,也是它改变整个智识氛围的地方,其深刻的蕴涵时至今日仍然回荡”(10)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5.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康德要表达的毋宁说是,任何关于上帝存在之真实性或虚假性的证明,都不再具有认知意义上的严肃性,借用一个尼采式说法,“其(这些证明)作为真理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ruth)不再被严肃看待”(11)Bernard Reginster,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0.。
阿多诺还援引观念史学家伯恩哈德·格雷图伊森(Bernhard Groethuysen)的考证。格雷图伊森详细考察了上帝、恶魔在十七世纪晚期及十八世纪早期如何逐渐消弭的过程,阿多诺提醒我们,这并非是一个走向无神论的趋势,而是说,关于绝对范畴的问题越来越不再被严肃看待。“绝对”、“超验”逐渐被视为信仰而非认知的对象。既然有限的人类理性没有能力解答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这些议题也就从理性讨论领域给排除出去了。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根基遭到摧毁后,我们不得不思考神的缺席给人类生存条件所带来的根本变化,思考如何“寻求离开与神的关联而存在”(12)赫伯特·施耐德巴赫指出,“我们都是在‘康德之后’思考的,这就是说,我们是在他弄清并教会我们尊重的那些条件下进行思考的”。参见施耐德巴赫: 《我们康德主义者——论当前的批判道路》,谢永康译,《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
否定神学认为,理性范畴只能把握自然之物,而绝对者是超自然的,凭靠任何认知性的理性工具,只会使人越来越悖离那个具有绝对超验性的他者。康德早在否定神学之前就提出,上帝对于人类理性而言是不可认知、不可理解的,绝对范畴不属于人类的认知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从克尔凯郭尔到卡尔·巴特的否定神学,可谓一部“哥白尼革命”的效应史。否定神学强调理性知识与神学信念之间不可通约的对立,指出有限的人类思维不能把握无限的终极实在,神的本质只能在消极的表述形式中得到理解,任何将信仰与知识混杂起来的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悖论性的信仰概念,唯有摒弃逻辑认知手段,人类才有可能趋近上帝。(13)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6.这里,信仰、理性之间的关联被认为是非常偶然、松散的,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 信仰所需要的不是知识与逻辑,而是对逻辑理性的弃绝,是韦伯所说的“理智的牺牲”(14)“虽然合理性在增长,但这世界上仍留存着一个无法消除的非理性的基础,并自其中孕育出信仰和信念等永不缩退的力量。价值和意义一样,都不内在于事物本身。只有靠我们的信念的强度,靠在通过行动征服或者维护这些事物时所投注的热切程度,这些事物才获得价值和意义。……所以,霸道地证明某一价值高于其他价值,乃是不可能的。只有以信仰为基础,某一价值才会为个人或大多数人所偏好。”韦伯: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页。。绝对范畴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前提假设,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科学理论根据。鉴于世俗语言、神圣言说之间存在这样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断言说“上帝即是上帝”,将人、神之间不可还原的绝对异质性强调到极致。
事物何以会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向我们显现?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现代的问题,我们不再能够诉诸绝对他者来寻求答案,甚至,“问题本身是不可回答的,无论根据任何标准,这已经逾越了可理解性的界限”(15)“以时间为体现形态我们向自身显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呢?我们真的向自身显现吗?或者,正是为了向自身显现,我们才向自身显现?这里的‘真的显现’是什么意思?问题本身是不可回答的,无论根据任何标准,这已经逾越了可理解性的界限。”P.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39.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根据这里的说法,要想回答对事物何以向我们显现,任何给出的答案都是赋予理性进入绝对领域的权利,因此是理性对自身权能的僭越。。在阿多诺看来,康德提出了一种如歌德所说的从每个有限方向来探求无限的认知主张,此一立场应与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相区别,简单的无神论立场,仍然是僭越了理性自身的界限而对关于“绝对”的问题妄下结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精髓,是强调指出“知道”、“相信”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汇。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视否定神学家为批判哲学的继承人,早在否定神学之前,第一批判就已对人-神之间的质的无限差异做出明确区分。
通常的理解是,“哥白尼革命”的核心是认知模式的翻转,即,由主体围绕客体转而强调客体围绕主体。如阿多诺所指出的,这一转向的根本所在,并非是主观力量的增强或理性的自我伸张等,而是剥夺了形而上学对象的客观属性。基于某种科学主义偏见,莱茵巴赫判断说康德哲学范式已然过时,事实上,批判哲学关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概念探究,“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根本前提”(16)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6.,“知道”与“相信”乃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语汇,二者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对现代人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基本常识。
康德哲学剥夺了“理性在绝对领域之内漫步的权利”,这种有所节制的认知立场被阿多诺称为“资产阶级生活的神义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记录下来的是资产阶级生活的神义论: 在对实现自身的乌托邦失去信心之后,它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活动”(17)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6-7.。而第一批判的力量就体现为它将认知领域的萎缩坦然接受下来。“《纯粹理性批判》之所以能够显示其力量,不在于说,它能够对形而上学问题做出反应,而在于说,一开始它就无畏而坦然地拒绝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18)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7.。人类能够对自身的理性进行反思,人类理性具有一种自反性,通过这一反思,为理性的运用范围划定了一道清晰的界限,“我们一方面为经验世界建立了牢固的根基,另一方面又阻止人们僭越了可能经验的范围而进入到绝对领域”(19)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7.。我们不再能够擅自闯入绝对领域,不再能够对形而上学对象妄加判断,“绝对”、“超验”从确然的认知对象成为实践反思的对象。从绝对领域撤退之后,人类反而能够坚实地站立在地面,欣欣然满足于眼下所占领的地盘。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图像通过两位10年以上阅片经验的放射医师在独立PACs系统上分别阅片。勾画双侧基底节区的苍白球区作为感兴趣区域,并测量T1 flair、T2 flair、DWI、ADC值图、SWI图及SWI相位图感兴趣区信号强度值。并针对所得感兴趣区域SWI及T1/T2/ADC/DWI数据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如果我把纯粹的和思辩的理性的一切知识的总和视为我们至少在自己心中已有其理念的一座建筑,那么我就可以说: 我们在先验要素论中已经估算建筑材料,并且规定了它们够建造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够建造多高和多么坚固。当然可以发现,尽管我们打算建造的是一座参天的高塔,但材料的储备却毕竟只够一座住宅,其宽敞恰恰够我们在经验的层面上的工作需要,其高度恰恰够俯瞰这些工作;但是,那个大胆的计划就由于缺乏材料而不得不搁浅了……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不是材料,而毋宁说是计划,而且由于我们受到过警告,不得以一种也许会超出我们全部能力的任意的、盲目的计划而冒险从事,但尽管如此却不能放弃建造一座坚固的住宅,所以就要设计一座与被给予我们、同时又适合我们的需求的材料储备相称的建筑。(20)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5页。
这里,康德所批评的“超出我们全部能力的任意的、盲目的计划而冒险从事”,体现的是一种认知上的虚妄,也就是,将理性的理念超出其内在使用范围而作超验的使用;相反,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应该止步于感性接受性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体现的是一种认知上的谦卑。这一认知上的大跨步后撤,被康德形象地说成是用所能找到的材料来“建造一座坚固的住宅”。
二、 形而上的疏离与生存性的荒谬
但我们必然要为认知的克制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承认,经验表象背后的非感性原因“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未知的”。
感性的直观能力真正说来只是一种接受性,即以某种方式伴随着表象被刺激,而种种表象的相互关系就是空间和时间的纯直观(纯粹是我们感性的形式),这些表象如果在这种关系中(在空间和时间中)按照经验的统一性的规律联结起来,并且是可规定的,就叫做对象。这些表象的非感性原因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未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原因当作客体来直观;因为诸如此类的对象必然既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空间和时间是纯然的感性表象条件)被表象,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根本不能思维直观。(21)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363页。
一边是作为表象向我们显现的现象,这是我们意识的材料,另一边是“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未知的”的物自身。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显像或单纯的幻相,真实的存在是完全不确定的、虚无缥缈的。如果确知的只是真实世界的摹本,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或物自身,那么,人类就被剥夺了对存在的真实本性做出任何确定性结论的权利,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对任何我们所能知道的东西,我们都不是在确定的意义上知道它。眼前的世界之于我们,只是真实世界的投影、摹本,至于这一摹本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确定的结论。这就是一直被后世哲学家攻讦甚至奚落的哲学二元论,阿多诺称它为“世界的摹本理论”(the theory of duplication of the world)(22)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09.。
我们所能经验到的世界,只是那个神秘未知的“第二世界”的摹本,原本外在于我的世界变成了我自身的产物,变成属我的世界,或者说,原本认为是客观世界属性的东西,被证明是我自身的心智构造的投射,“经验世界、物的世界是我自身的产物: 它就是我的世界。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动机,我所说的是形而上学经验的动机,一个客观的动机,世界历史的日晷的位置使得康德贸然提出这个摹本概念,即便他并没有被其内在困难所诱骗”(23)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0.。既然经验世界是“我的世界”,既然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必须合乎我们自身的理性,那么,世界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陌生的,它不再由一股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力量支配。人类就是这样通过将世界内在化来驱散对神秘未知之物的恐惧。我们置身的世界最终是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我们不用再担心“恶魔”会突然闯进来,这是康德的内在的物(the thing)概念所蕴涵的人类生活经验。
这个被经验的世界、这个内在的世界与我们协调一致的过程中,也就是,将它变成我们的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形而上学的疏离。产生这个说法多多少少有观念论的影子: 它表述的是一种客观事态,但它表述的方式,仿佛这一事态只不过是哲学反思的产物。世界越是被剥夺客观的意义,它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范畴共存,并因此变成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就越来越发现意义从世界中被消除了,也就越来有发现我们自身浸没在宇宙黑暗之中,用一个现代的说法。世界的去神秘化或无实化——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茫茫黑夜之中。(24)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110—111.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人类同时也为这种理知化付出沉重代价。我们不得不接受,熟悉的世界之外是神秘莫测的“第二世界”,这个幽灵般的世界是如何与我们栖居的世界相关联的,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上越感到安全,越稳妥地安置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发现自身与绝对者的联系越来越不确定。以形而上学的绝望为代价,我们换取对自己的世界的熟悉感”(26)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1.。康德式二元论将本体世界转换成为不可知的、神秘莫测的世界,将经验世界降格成为单纯的表象或显像,关键在于,熟知的经验世界与不可知的本体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也可以说是无意义的,这种无意义恰恰“描述了当下的人类境况”,凸显出人之为人生存于世的荒谬性。
如果有人觉得摹本理论在逻辑上没有意义,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 的确它没有意义,但这一没有意义却描述了当下的人类境况。它的无意义表达了反映了这一事实: 我们成为了理性的、合理的生物,我们越变得理性、合理,越会觉察到这个世界客观的非理性和它的异化。(27)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3.
根据加缪的说法,荒谬指的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清楚的东西,“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28)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0页。。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意识到把握本真、绝对的真实世界之不可能,同时,也承认了洞悉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抱负已经遭到挫败的事实,最终,我们发现自己成为了真实世界的局外人。一旦存在者把握到他跟世界之间的疏离关系,一种生存层面的荒谬感便油然而生。将生存于世的荒谬作为形而上学真理加以揭示,这是生存哲学家思考的出发点,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康德哲学的思想意图,“这一哲学全然无意描述荒谬这类哲学‘情绪’,而是相当严格地专注于知识机制的分析,然而,从中却自然而然地涌现出荒谬这样的概念,或者说,荒谬概念在其中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自我表述”(29)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2.。跟将荒诞性课题化的生存论哲学相比,将荒诞概念不经意地呈现出来的第一批判,包含了“更重要的生存论的经验内容”,它以一种未曾意识到的方式系统地把握到人生在世的基本境遇。在我们看来,这个认识论体系一开始想解释清楚一切,最终却不能对任何东西给出真正的解释,最大的荒诞也许莫过于此。
三、 作为救赎行为的自我立法
世界完全变成一个内在化的“我的世界”,我们发现自己被形而上学黑暗笼罩着。(30)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1.康德的经验世界不提供可以抵达超验领域的通道,对绝对他者的思考在一个封闭的内在语境中遭到悬置甚至是压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失怙,迫使人将自己放在绝对者即神圣立法者的位置,以此寻求自我救赎。(31)“绝望中唯一有实践担当的哲学是这样的尝试——依照世间万物从救赎视角出发自我呈现出来的样态,来对它们进行思考。”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Edmund Jephcott (trans.), London: Verso, 1974, p.247.客观意义上的确定性的丧失,迫使人转向自身,寻求一种主观意义上的确定性作为替代。
《实践理性批判》结尾处的两句话流传甚广,乃至于成了陈词滥调,“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 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32)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这个说法一下子将读者的情感调动起来,有意思的是,阿多诺却认为,对这句话我们大可不必当真。既然我们所看到的璀璨“星空”只是表象,其真实面目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一开始我们就对它的存在明确提出质疑,它怎么可能成为我们敬畏的对象呢?既然康德系统驳斥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认为它不能够作为知识的牢固基础,那么,此种敬畏不可能是对神学目的论之下的自然秩序的敬畏,或对于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敬畏。敬畏的对象也不可能是机械论的自然必然性。照此说来,我们敬畏的对象只可能是自然的合目的性(33)类似的观点,参见叶秀山: 《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哲学动态》,1994年第7期。,崇高感只可能来自人自身具有的赋予世界以秩序与律则的能力。
如果我们想说康德在这里欲行拯救之事,它指的就是,只要他能够根据自身的尺寸来裁剪衣服,那么,用一个康德式说法,人这个在客观上遭到抛弃、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家可归的存在者,就能够获得在家之感。人必须将自身的活动限制在自己知道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他自身的能力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他又必须尽可能寻求一个确定的东西来为这个世界做担保,这个担保不应到外部而要在自身之内来寻求。(34)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3.
此处,阿多诺将理性认知能力所受到的限制形象地说成是“根据自身的尺寸来裁剪衣服”,与前面建造宅子的比喻可谓异曲同工。他将康德式自我立法喻为照进形而上学黑夜的一束“内在光亮”(35)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3.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提出,认识论应该以救赎为根本旨趣,“除了在救赎来照亮世界外,知识没有别的光亮,此外的一切皆为重构,单纯技巧而已”。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p.247.。这一立法不光是实践层面的,同时也是理论层面的: 在理论层面,构成经验知识之必备要件的先天形式要素(感性直观、知性概念)是认知者心智结构的内在禀赋;在实践层面,康德式道德哲学就是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意志能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36)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康德哲学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2页。,自我立法的功能是“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37)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49页。。立法是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失怙后的自我拯救,人不得不在自身之内寻求一个确定的东西来为外部世界做担保。
然而,标志着意志的自我伸张的立法行为,只是现实世界实然状况的反面,真相是,正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的意志完全得不到声张,我们才需要从自我立法中变相得到补偿。从这一点出发,阿多诺认为康德式自我立法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作为认知对象,世界是人类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38)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3.,这是在应然意义上定义的,实然状况刚好相反,“康德哲学尝试将世界定义成一个应然的世界,正如在古典时期,索福克勒斯将人们当成应然意义上的人,而欧里皮德斯将他们描述成实然所是的人”(39)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3.。应然的自律世界与实然的他律世界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认知对象的世界是人类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并不是真的,正因为它不是真的,正因为我们仍然是他律的,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不自由之中,我们才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给我们呈现的是相当可疑的镜像,一个补偿性的意识形态”(40)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37.。从表面看,我们仿佛是世界的主人,事实上我们只是它的奴役,我们对它有一种盲目的依附性,无论怎么做都不能使它发生任何改变。
“我们仿佛是我们自身的奴役”,这是一个充满悖谬性的重言式。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一个重言式结构,其实这是人在他律之下的真实处境的表达: 作为认知主体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未跳出自身,在自身之内我们被囚禁起来。这是康德哲学中蕴藏着的一个深刻的真理,所谓的“体现在非真实之中的真实内容”(41)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37.: 将我们囚禁起来的世界,也就是,这个越来越趋向普遍同质化的商品世界,其实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它以客观性、“第二性”表象呈现于我们面前,“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42)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46.。
四、 康德体系中的虚无主义危机:“仿佛如此”的哲学
通过厘清理性认知能力的权能范围,康德将不得其解的形而上学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如果你们愿意,并且容许,我想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形而上学和神学观念的资产阶级悬置。一方面,这些观念被剥夺了理性权威,而另一方面,既然人们对它们全然不知晓,它们又被准许以一种影子般的形式存在。在资产阶级家庭内,它们一直被搁置到星期天才出现,就是说,在平日里被悬置,星期天(“礼拜天”)才显示其存在”(43)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48.。由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无知所导致的“资产阶级悬置”,神学-形而上学因素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影子般形式继续存活,“在限制它们的同时,怀疑论又为神学-形而上学偷偷溜进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44)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1.。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内,神学-形而上学属于私人信仰的对象,平日里被悬置,星期天(“礼拜天”)才显示其存在。
绝对范畴在公共生活中逐渐被放逐到边缘位置,最终成为阿多诺所说的高度私人化的“影子般的存在”。形而上学的私人化,其实意味着以终极实体为根据建立起来的价值世界最终宣告瓦解,“前康德时期作为价值超验来源的东西最终都变成空无”(45)Simon Critchle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ntinent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0.,关于生命意义的一切超验的观点被还原为“纯粹实践理性公设”,被还原为主观预设的纯粹价值。(46)Simon Critchle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ontinent Philosophy, p.80.这里所发生的,是对价值的认知属性的尼采式“价值重估”,重估的对象不是价值的实质内容而是其认知属性。这是走向“上帝之死”即最高价值的罢黜的关键一步,“上帝之死”,尼采说到,“意味着基督教上帝不再值得人们相信了”(47)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W. Kaufmann(t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346.,换句话说,即使人们仍然相信上帝,这种相信不再具有原来的认知属性,至少,已经不再能够获得来自理性理据的支持。
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更进一步促使人类改变关于形而上学-神学对象的提问方式。我们不再提出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一类永远不得其解的问题,正确的提问方式是——上帝的观念在什么意义上还能够具有说服力?“上帝之死”,意味着关于形而上学-神学对象的证明“不再被严肃看待”,“不信是因为信仰被驳倒了,或者其虚假性得到证明了。而一个信念被悬置起来,指的是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都不能够得到证明。一个信念成为可质疑的,不仅指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不能够得到证明,而且指其作为真理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ruth)不再被严肃看待”(48)Bernard Reginster,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p.40.。一旦绝对范畴“不再被严肃看待”,就成为阿多诺说的“星期天才显示自身”的“影子般的存在”,于是,人不得不为自己对上帝、对形而上学世界的信仰寻找一个“人性的、太过人性”(49)Bernard Reginster, The Affirmation of Life: Nietzsche on Overcoming Nihilism, p.41.的起源。
世界的本来面目超出人类认知能力的范围,我们只能在先验反思而不是在如其所是的实在论的意义上谈论这个本体世界。人们逐渐认识到,本体论不能独立存在,以世界的本来面目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并不是自足的。置身于认知过程中的“我”首先是一个认知者,或者说,是作为认知者的“我”要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世界原本是什么,而是“我”认为世界是什么。一个开放的认知过程,本身预设了是“我们”作为认知者在认识世界。如此一来,关注的重点从世界本来是什么转移到人如何看待世界,也就是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50)康德《形而上学课堂笔记》中的一段话清楚描述了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内在逻辑:“本体论教师从“某物”和“无”这两个概念开始,却忘记了这个区分已经是对一般对象这个概念的划分。而康德从一般对象或物开始,它被先验的肯定或否定划分为某物和无。然后物进一步被规定为经验的一个对象,继而最终被规定为知识的一个客体,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存在论的一个批判地改写的版本。”引自Howard Caygill, A Kant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Wiley-Blackwell, 1995, p.306。
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当然意味着世界的认知地位被降格了,作为人类认知目标的,不再是世界本来的面相,而是单纯表象或现象。世界的本来面目成为只能从先验反思层面来讨论的神秘未知的本体世界,而眼前的经验世界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仿佛如此”(as-if)的特性。阿多诺时代的一个康德解释者用“仿佛如此的哲学”(ThePhilosophyofAs-If)命名他的康德专著,这种解读因其相对主义嫌疑而遭到正统康德哲学家的嘲弄。按照阿多诺的论述,“仿佛如此”极其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客观的形而上学经验”,“这种形而上学经验在我看来是客观的——不是在康德自觉意识到的意义上——而是作为康德背后的客观驱动的力量而言”(51)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111.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现代性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自反性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意识到我们理解世界、调节日常生活凭借的那些东西具有建构性属性,意识到行动着的、做决定的那个自我有一种“仿佛如此”的特性。(52)转引自Maeve Cooke, Re-Presenting the Good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p.110。我们如此这般行动,仿佛我们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主体;有神论者如此这般生活,仿佛有神在场;对无神论者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如此等等。
后康德时代的人们不再坚持世界需要由终极实在来奠基,他们逐渐接受世俗的逻辑理性与超验的神圣话语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弥补的鸿沟,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人人都成为了否定神学家。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提议,我们要以“理智的诚实”面对一个不可逆的世俗化过程,“上帝作为道德、政治、科学的起作用的前提现在被抛弃了,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尽可能抛弃这些起作用的前提,乃是一种理智的诚实”(53)朋霍费尔: 《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73—174页。。形而上学-神学理念的缺席,乃至整全真理的缺席,将构成人类生活无法祛除的根本性背景文化。就此而言,哥白尼革命仿佛是文化现代性的宣言,宣告了古典时代欲图洞悉万物本质的苏格拉底式认知抱负的破灭,同时又预示着人类生活将会逐渐脱离神的指引而自行其是。
阿多诺从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康德悬置形而上学命题的划时代意义,着重凸显康德哲学的“虚无主义特征”。他并未明言这一二元论体系就是虚无主义,而是说它正确地标识出人们所处的“世界历史的日晷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对哥白尼革命的这一解读,不是雅克比批判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危机之翻版: 在后者眼里,康德理性主义体现出鲜明的唯我论特质,不可避免地导向虚无主义;而在阿多诺看来,该二元论本身不是虚无主义,也不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恰恰是康德的观念论后裔对它的悖离,使哲学的主体性转向最终陷入虚无主义。(54)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49.
结论就是,不是在某个具体表述上,而是在整个概念构架上,康德的二元论立场以其独特的方式如何将“世界历史的虚无主义阶段”记载下来,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在存在者之存在中经验到虚无之切近”(55)海德格尔: 《尼采》下,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1页。。最后,我想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为本文做结,对于哲学家来说,是否有能力记载这一历史性的形而上学体验,“乃是一块最坚硬、也最可靠的试金石,可以用来检验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是否纯真,是否有力。谁若经验不到虚无之切近,他就只能永远无望地站在哲学门外,不得其门而入”(56)海德格尔: 《尼采》下,第671页。。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