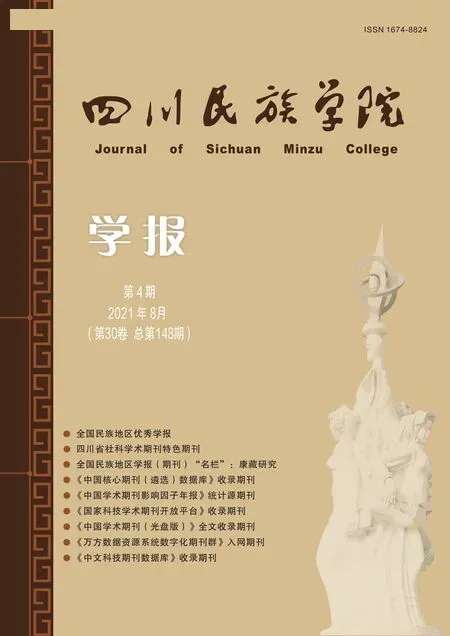18世纪清廷对川藏古道的使用与经营探微
公秋旦次
(西藏大学,西藏 拉萨 850000)
18世纪初,西藏地方的局势摇摆不定,动荡不安。第巴桑结嘉措(1633-1705)与蒙古和硕特后裔拉藏汗(?-1717)之间在藏争权夺利,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巴被拉藏汗攻杀,西藏地方由蒙古和硕特拉藏汗控制。此时,准噶尔部的新首领策妄阿喇布坦(?-1727)对拉藏汗所控制的西藏野心勃勃。策妄阿喇布坦借卫拉特蒙古各部间互通婚姻之俗,通过策妄阿喇布坦其女与拉藏汗长子联婚成亲之事,蛊惑了拉藏汗。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从伊犁遣兵,由将军策零敦多卜(?-1736)率领6000兵,经西藏阿里北部,挺进前藏,次年抵达拉萨北方当雄。准噶尔军从当雄开始与拉藏汗军队交锋,策零敦多卜率领的准噶尔军队势力极强,很快战胜了拉藏汗属下的蒙藏军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底拉藏汗被准噶尔追军所杀。西藏地方又被准噶尔部占据。准噶尔部在藏扰乱三年之久(1)1717年底至1720年9月。,期间清廷为“驱准保藏”,经青藏单一路线(2)即唐蕃古道路线,此为清军第一次进藏路线。,派军进藏,但此次清军进藏未能征剿准噶尔部军队。西藏那曲一带,清军被准军围困多久后,最终全军覆没。[1]122-123为此,朝中议论纷纭,康熙皇帝(1654-1722)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从青藏和川藏两条路线同时行进,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最终获胜。18世纪初期至18世纪20年代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促成了清廷既通过传统的青藏路线进军,也首次把川藏古道作为军事要道使用。(3)史称清军第二次进藏。那么,关于清朝在川藏古道上开拓一条军事要道的缘起、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已有前辈学者研究,如石硕和王丽娜的《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一文中从1717年准噶尔扰藏和清军第一次进藏失败开始,并就清廷开拓川藏驿道采取的措施、步骤以及沿着川藏古道进藏的过程做了比较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最后对清廷在建立川藏驿道上取得的成就和战略意义作为了总结。[2]136-146另外,赵心愚的《清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讯塘与粮台的设置及其特点》一文以清代早期有关西藏的地方志《四川通志》以及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等为一手材料,对清代康雍时期川藏驿道的讯塘和粮台设置的时间、若干特点与性质职能方面作出了专门的探讨。[3]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18世纪初期蒙藏关系史作为历史背景,对川藏古道成为军事要道和官方驿道的历史进程做了简要梳理,从而力求认识其道路本身的战略优势,并对清廷通过川藏古道的积极使用和经营来实现控制康区和直接治理西藏的史实加以阐释。
一、川藏古道成为军事要道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通过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的疏报,第一次接到关于准噶尔部袭扰西藏的确切消息,[4]198次年2月底又接到拉藏汗信使的救援报告[4]203。不久之后,清廷决定从西北两路进攻准噶尔部的根据地伊犁,这时又接到拉藏汗已经被准部杀死的消息,这时清廷终于把矛头指向在藏扰乱的准噶尔部策零敦多卜率领的军队上。康熙皇帝“今即令色楞统率军兵征剿西藏”[4]204,同时令西宁总督额伦特也率队与色楞一同进藏。两位将军先后从西宁入藏,但两者意见不同,进攻策略方面略存分歧。康熙五十七年七月(1718年8月)色楞和额伦特的军队抵达那曲一带,两位将军不久会合。与准部激烈交战,清军因对藏北地区“不晓天时地利”[5],后勤被准军袭击,加之二将军令不一,导致清军遭到准噶尔部军的围困,进退两难,军粮紧缺,九月二十九日(11月21日)色楞将军被俘虏,额伦特将军战死。[6]36
清廷为“驱准保藏”第一次派军进藏时,被准噶尔部军打败。准噶尔部军的挑战,震惊朝廷。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1718年12月3日),皇帝封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1688-1755)为抚远大将军(4)康熙皇十四子胤禛,雍正初年改为允禵。,决定让允禵率军入藏。十二月十日(1月31日)允禵从京城前往青海,在途中知晓,朝廷已决定除了青藏路线以外,另从四川至藏开辟进军一线(5)即从川藏古道进藏。,并要求允禵军中的护军统领噶尔弼派往西南四川,与四川巡抚年羹尧一同办理军务[6]21。与此同时,大将军允禵于五十八年三月(1719年4月)在西宁塔尔寺会见第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要求协助南路进军,遂同青海蒙古郡王察罕丹津分别派人去理塘、昌都、硕般多,携带转世灵童的安民告示,宣传清军南北路入藏“收复藏地,以兴黄教”的意义,[6]30-31从而得到了康区沿线民众的顺从和支持,为川军进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西宁派往四川的噶尔弼授为定西将军,率领兵丁进藏。[1]128
允禵在西宁办理诸多善后事宜以及朝廷继续观察藏中事态的需要,朝廷决定当年(1719)不进藏,令允禵暂停西进。[4]225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下旬(1719年11月)至五十九年正月下旬(1720年3月),清廷为进藏之事,用了整整四个月的工夫,终于确定了进藏方案:清廷决定从南北路分别进藏,以北路作为主力军,为获得青海众蒙古的联合出兵,在塔尔寺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将一同送往西藏,决议再拨兵增至一万二千名[1]128;由护军统领噶尔弼从打箭炉率川军二千七百人入藏,经理塘、巴塘、芒康、察雅至昌都,从云南调兵进藏的三千名在昌都与川军会合,共五千人从昌都前往拉萨。
北路的主力军四月二十二日(5月28日)自西宁启程,护送第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同时,八月中旬(9月)到达那曲一带,与策零敦多卜率领的准军交锋。至于南路,康熙五十八年(1719)噶尔弼将军驻扎于打箭炉的同时,按照年羹尧的建议向打箭炉以东的理塘、巴塘等地逐渐扩张并设立驿站。[4]213这时从成都至打箭炉已经设立较为完善的驿站。噶尔弼率领的川军抵达昌都,滇军三千名与川军会合,从昌都类乌齐分两路进入拉萨;一是经类乌齐、结结树、冰噶、三达奔卡(6)结结树、冰噶即今那曲比如县白嘎乡,藏语地名为rgyas xod pad dkar;三达奔卡即今比如县羊秀乡的桑达寺,藏文寺名为bsam mda’bon dgon;从地域路线来看文中部分沿途地名被忽略或未记载,路线的顺序应是类乌齐、丁青、江达(今索县东南)、沙丁(今边坝县西北)、白嘎、三达奔卡、拉里。、拉里;二是类乌齐、落隆宗、硕般多、达隆宗(边坝)、沙工拉、鲁工拉、拉里,从拉里一同进入工布江达、墨竹工卡,[7]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1720年9月24日)抵达拉萨。[8]335沿川藏古道的军队早于北路主力军,途中无阻,顺利进入前藏。此次清廷把川藏古道首次作为朝廷的军事要道,且顺利入藏,为清廷带来了巨大好处,在“驱准保藏”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军第二次进藏获胜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意义来看,清廷为控制康区及治理西藏地方必将继续重用川藏古道。
二、军事要道和官方驿道的一体化
康熙六十年(1721)抚远大将军允禵“闻进藏二将军(7)此处二将军为应是从青海入藏的平逆将军延信和从打箭炉入藏的定西将军噶尔弼。,大约十一月初头一齐回来,由巴尔喀木(8)巴尔喀木为藏文bar khams意为康区。路向四川来”。[9]1128允禵令“由打箭炉至藏所驻之站,断不可撤,流备驻藏大臣等奏报交由彼路行递。”原有的青藏路线“冬冷,驿马难以生存……其间地极远,格尔侧郭洛特等唐古忒人等妄行夺取马匹,致驿站中断。”[9]1128《抚远大将军允禵奏搞》中还提到了:“我与将军噶尔弼商议,将我来路撤驿(9)这时允禵在青甘一带。,将军噶尔弼来路驻驿,由藏至打箭炉,此路居人不断,而烧柴丰富。唐古忒人又帮送递,并无耽误……将军去路暖(10)这里的将军为噶尔弼。,而烧柴丰厚,理应准此设驿。”[9]1129-1130从上引材料的字里行间来看,至少可以透露如下信息,其一,从南、北路进藏的清军保藏后,次年从藏至打箭炉道路返回;其二,大将军允禵令南路返川的将军,无须撤回驿站,南路沿途驿站备用;其三,北路自然条件艰巨,人为隐患巨多,建议撤回驿站;其四,因川藏古道沿途采购粮食、放饲牲口较为便捷等缘故,南路作为日后的官方驿道。[10]71-78
雍正五年(1727),西藏诸噶伦之间发生内乱,清廷先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领玛拉、洮岷协副将颜清如前往西藏办理事务,他们先后从打箭炉、理塘、巴塘至昌都,再从昌都、落隆、边坝、拉里、江达进入拉萨。[1]158此时清廷派往西藏的官员军从南路进藏,显而易见,南路基本已成为朝廷的官方驿道。就在这一年,清廷为平定西藏的内乱,派军进藏,与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方针相似,使用北路的同时,再一次重用南路,[8]414-416使南路又一次成为朝廷的军事要道。这期间,清廷在南路的昌都等重要沿线枢纽上派驻军队[1]179。南路上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文书传递、人员接待、后勤供给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保障。其后,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份议奏中显示:川藏古道上设立的驿站、塘汛、粮台等沿线设备,1746年前后清廷仍在完善和优化当中。[4]250乾隆十五年(1750)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拉萨与驻藏大臣发生冲突,郡王随从在拉萨进行骚乱,且阻断汉藏官道。[11]43清廷准备从四川派兵八千人,[8]527-528后因藏地已平静,大军进藏计划取消,由四川总督策楞为首的大员从南路进入拉萨。[8]533到18世纪末,廓尔喀侵入西藏,清军先后两次进藏征剿廓尔喀。(11)廓尔喀第一次侵藏于1788年,第二次侵藏于1791年。1788年清廷派川军通过南路进藏,1791年清军南北两路入藏。总的来看,清廷自1720年从川藏古道上开辟军事要道以来,逐渐建成官方驿道,并建立健全驿道的运行机制。在清末成书的《西藏图考》中对川藏驿道的优势条件做出了如下肯定:“川、陕、滇入藏之路有三,惟云南中甸之路峻戏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10]78黄沛翘所撰《西藏图考》中的这一论断,一方面是清末人对18世纪初清廷开辟川藏驿道的历史和效能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黄沛翘虽生活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但长期居住四川,并悉心于川藏边地的钻研,故上引断论便可理解为他对进藏路线的研究成果。
三、川藏古道的路线及其驿站
从前所述,清军于1720年从川藏古道进藏的过程当中,在沿途建立零散的驿站、粮台、讯塘等,这是清廷首次把川藏古道作为军事要道,亦是清廷在川藏古道上奠定驿道基础的表现。18世纪20年代以来清廷治理西藏地方的过程当中,川藏古道上的驿站、粮台等逐步完善和优化,并把川藏古道作为朝廷势力进一步渗透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无论大规模军队的进出,还是央地官员的往来或物资的运输,均在川藏古道上进行流动。这是川藏古道成为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官方驿道的历史表现。那么清廷把川藏古道先后作为军事要道和官方驿道,在川藏古道上建立了制度性的驿道系统,即路线和驿站,这一内容在清代汉文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本文在川藏驿道的路线和驿站上主要参考18世纪末成书的《卫藏通志》,18世纪末正好亦是川藏古道的驿道网络发展到比较系统且具有制度性特点的成熟时期,因而《卫藏通志》所记载的川藏驿道路线和驿站应是18世纪的较为权威而可信的史料。根据乾隆六十年(1795)成书的《卫藏通志》记载,川藏驿道的干线为:成都至打箭炉、理塘、巴塘、芒康、察雅、昌都、落隆、硕般督、边坝、郎吉宗(金岭)、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12]227-240显而易见,从康定(打箭炉)到昌都的驿道路线与现今的318国道一致的,昌都到拉萨的古驿道路线与现今的349国道基本一致(12)G349国道线路不经过加贡与嘉黎之间的鲁工拉,从金岭进入尼屋乡再到嘉黎,到墨竹工卡时主线往山南乃东。,所谓干线,道路上人口流动、物资运输最为繁荣,沿线上村落和寺院较为密集,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所费时间较少、空间距离较近的道路。另外,川藏古道上也存在不少的支线,如康定至昌都可以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进入昌都:昌都至拉萨也可以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那曲、当雄进入拉萨等。支线多为民间商人、朝圣者以及游牧迁徙所开辟的羊肠小道,在此不赘述。
《卫藏通志》所记载的川藏驿道的驿站:打箭炉(康定)-折多-提茹-阿娘坝-瓦切-东俄落-高日寺-卧龙石-八角楼-中渡(雅江)-剪子湾-西俄落-咱马拉洞-火竹卡-火烧坡-里塘-头塘-乾海子-喇嘛丫-二郎湾-三坝-松林口-大朔塘-彭察木-小巴冲-巴塘-牛古-竹巴笼-公拉-莽里-南墩-古树-普拉-江卡(芒康)-山根-黎树-阿拉塘-石板沟-阿足塘-歌二塘-洛加宗-俄伦多-乍丫(察雅)-雨撒-昂地-噶喀-王卡-三道硚-巴贡-窟笼山-包墩-猛布-察木多(昌都)-俄洛桥-浪荡沟-拉贡-恩达-牛粪沟-瓦合寨-麻利-嘉裕桥-鼻奔山根-洛隆宗(落隆)-曲齿-硕般多-中义沟-巴里郎-索马郎-拉子-边坝-丹达-察罗松多-郎吉宗(金岭)-大窝-阿兰多-破寨子-甲贡(加贡)-大板桥-多洞-擦竹卡-拉哩(嘉黎)-阿咱-山湾-常多-宁多-过拉松多-江达(工布江达)-顺达-鹿马岭-堆达-乌苏江-仁进里-墨竹工卡-拉木-德庆-蔡里-拉萨。[12]227-240自雍正五年(1727)起康区分为川、藏两部分,芒康宁静山以东隶属川省,山以西为西藏地方辖区。随后驿道运行与管理方面,川内“康区驿站归四川总督具体负责,西藏驿站由驻藏大臣直接辖理”。[13]
四、结语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道路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在生活中是必不可缺的条件;从一个政权的视角来讲,道路不仅仅是一个人流物流的基础设施,更是扩大势力、权力渗透的重要渠道。那么我们从清朝角度出发,对川藏古道的优势条件以及清朝对川藏古道的使用和经营进行探讨的时候,道路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更加明显。川藏古道作为开辟的经商之路和朝圣之路的混合体。虽是古代时期的羊肠小道,但它的历史已有上千年。[14]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从地理位置的意义上讲,川、藏两地都处于中国的西南区域,无论在历史时期或着眼于现实意义,川、藏两地均有重要的固边、稳边的战略地位。川藏古道主要呈东西走向,连接着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贯穿横断山脉在内的川、藏两地的大部分地区。如从成都平原启程,经康区可以到达西藏腹地拉萨,甚至更远的山南、日喀则和阿里等地,途中必然要经过多年被蒙古和硕特部势力所左右的清廷尚未控制的康区。因此,从维护边疆和巩固地方的远景目标来讲,毋庸置疑,争取川藏古道的经营权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18世纪初以来,由于西藏地方的种种局势,导致了清廷不得不沿着川藏古道开拓一条军事要道。清廷对川藏古道的探索、琢磨以及正式经营的过程当中,充分认识了川藏古道所具备的优势远远胜于北路青藏线,“使清朝进藏道路由过去以西宁一路为主开始转向以南路为主”。[2]145从1720至1791年期间,首先,清廷在“驱准保藏”的同时开辟出川藏古道的军事要道,并为往后官方驿道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川藏古道上因军事需要而建立的零星的驿站、塘汛、粮仓在长期内逐步完善和优化,建立了系统和制度化的驿站制度,为清朝和西藏地方的关系联络上创建了较为全新的并且有保障的道路网络;再次,通过川藏古道上建立的驿道,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无论大规模军队的进出,还是官员的往返或大量物资的运输,发生了一系列的互动关系,在客观的结果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各民族间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最后,清廷因积极利用川藏古道的战略优势,不仅仅是驱逐在藏准噶尔部势力和廓尔喀的入侵等,并且对多年被蒙古势力所困扰的康区逐渐赢得控制,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治理,“将分散的领土连接成为一个国家的网络,便利了集中化政治治理的兴起”[15],从某种意义上讲,赢得川藏古道的经营权,对于推进、扩展清朝在内亚和中亚的影响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6]
综上所述,清廷因积极利用川藏古道的优势,从而川藏古道上的流动成为“既是物资的流动,更是权力的流动”。[17]从18世纪西藏地方历史处境来将,驿道应该是流通性和连通性极强的通道,那么对于清朝来说,川藏古道上的驿道,不仅仅是文书传递、人员接待、物资运输的物质存在的通道,更是权力渗透和势力输送的隐形渠道。从政治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的角度来思考,清廷在川藏古道上不断建立和完善驿站制度,可以认为是清中央政府主动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上的调整和对西藏地方秩序的重构,更是经营地方、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