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未知的前方,寻找生命的落点
文梁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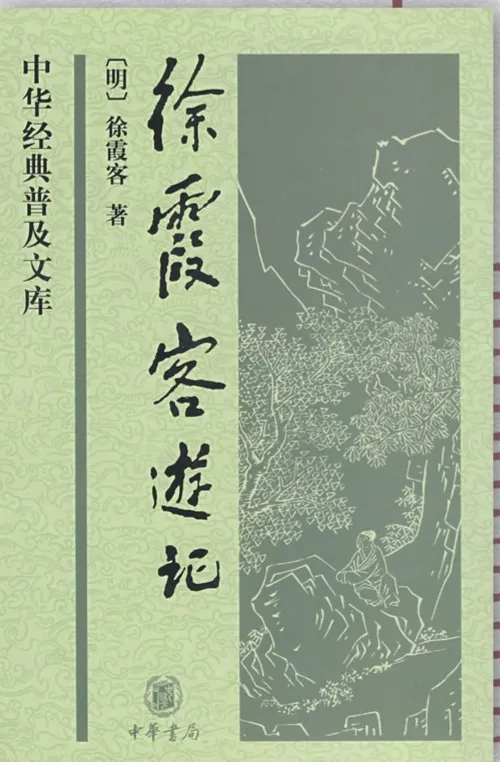
在云南旅行,时常想起徐霞客。从1638年5月到1640年1月,他游历了云南的十四个府,最后在大理鸡足山“忽病足,不良于行”,不得不返回故乡江阴,半年后去世。
深夜读《徐霞客游记》,感兴趣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从年轻时代开始行游天下,乘船、骑马、坐滑竿……最主要的还是步行,就靠一双脚,走遍了相当于今天十九个省的地域。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这个江南富家子弟,就这样执拗地走着。在云南,暑热让他“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理间”,天天忍受痒痛。即使如此,他每天晚上还要写下详尽的考察记录,发前人之所未见,汇集成四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读着读着,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徐霞客先后结过两次婚,21岁新婚不久,便开始经年累月地远游,并未见他在游记中流露一点儿对妻子的眷恋。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他对大自然的爱远胜家人,他过得自由而孤独,丰富而冷清。在人世间,他永远处于不断的告别中,唯有未知的前方,才是他生命的落点。临终前,他手里紧紧握着的,是两块石头。
也许他度过的,并不是最好的人生。最好的生活,是与息息相连的爱人执手前行,在共同的视野中,一起做两人都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生活中,平凡里时时有欣喜,无意间看到一个农户墙上的箩筐,也会相视而笑。英国勃朗宁夫妇的相遇相伴,正是这样的典范。1846年,30岁的勃朗宁夫人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与爱人私奔意大利,写下一首首美丽无比的十四行诗。“爱你,以昔日的剧痛和童年的忠诚;爱你,以眼泪、笑声及全部的生命。”如此深情,如此诗意,如此创造,两个人的生命都获得了再生。这是两性间的生死契阔,也是面向世界的自然之道。
然而,徐霞客的道路却是最可靠的选择。情感是一滴挂在芦苇叶尖上的露珠,很容易坠落。勃朗宁夫妇太稀少了,世上凤头猪尾的感情又太多,有把握达到的,往往是徐霞客式的独行天下,走到自由人生的极致。在极致之上,找到执手远行的相知相伴,少数像勃朗宁夫妇一类幸运的人,才可以体会。
以往读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第一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轻轻放过,更重视后面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读着《徐霞客游记》,蓦然感觉前一句更需要仔细体味。徐霞客和勃朗宁夫妇的区别,似乎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