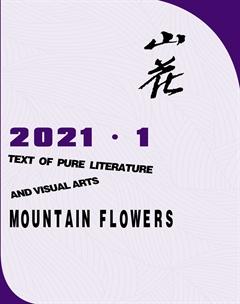北京练摊儿记?
2020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
我平常都是两点左右吃午饭,然后稍微躺一躺,可是今天不成,要出门练摊儿,为了后天周六《汪曾祺别集》个别编委的售书正式练摊儿,一个人先去体验,尝试尝试。
我是真正练过摊儿的。几十年前,我在东华门寒风中卖橘子,三轮板车上护栏里的一堆橘子被我一个个用白线手套擦拭得晶亮,闪耀着玻璃的彩光,橘子皮擦亮了就好卖了。我在中山公园售书,夏夜露天睡在折叠钢丝床上,白天那床上摆满了古籍。在北大,在人大,校园林荫弯道上,中午的食堂门外,鸟鸣和喷香的饭菜味道在空气里悬浮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多么庄重,多么干净好看,他们没有一个朝我看一眼,他们也很少注意我的书籍,他们步伐匆匆。
今天,午后脑袋昏昏沉沉。我提了两套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别集》,一套八本,一大瓶农夫山泉,还有一张粉红的塑料垫布,来到北四环路安徽大厦西侧一处过街地下通道。在出门前一刻,我又一回犹豫要不要带上小泰迪嘎嘎。那一瞬间,我望着它渴望和我一起出门的可怜眼神,下决心还是把它带上了。不带它去,是考虑到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总是累赘,它跟着也是受罪。带上它,是个伴儿,否则自己一个人不免孤单。这时,我想到曾经短期住在布拉格写作,有时一个人无所事事,从住处步行三五分钟来到那座闻名世界的查理大桥。桥头桥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在这座横跨伏尔塔瓦河两岸的古老桥梁两边,几乎布满一个连着一个的地摊儿,出售名城旅游纪念品的,演奏卖唱的,人像素描的,也不乏乞丐,他们永远把头深埋在石钉地面,罩着连帽外衣。乞丐的身边总是安静地趴伏着一条大狗。过路人看到那可怜巴巴的红眼大狗,也会给摆放在它嘴边的不锈钢狗食盆里丢下几个克朗硬币。硬币落入的动听声音,让那狗的眉头轻微舒展,它的眼皮也会跟着跳动几下,眼睛里都是无辜委屈。我想,我的嘎嘎兴许也会派上用场,它不是我的累赘,它从不给我麻烦,它只会给我帮助。所以,我要多多带上它的零食,牛肉奶酪小食棒,我们就这样去练摊儿了。嘎嘎出门即刻一泡大尿,尿得一滴不留,仿佛它知道接下来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
这是下午两点四十分。地下通道里已经有了一个水果地摊,一个旧书摊,一个花卉盆植摊,一个日用、拖鞋、钱包小皮具摊和一个出售立体动物、风光画片的摊子。在我的《汪曾祺别集》地摊摆出来之后,又加入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女性首饰摊。
“你賣书,我也是卖书的,能挨着你吗?”我问那个旧书摊主。
他站起身,“您别挨太近。”
“您看多远合适?这儿行吗?”我在与他的摊子相隔四五米的地方站住。
“不用不用,没那么远。”他追上来,似乎有一点过意不去。
我退后两步,“这儿,成吗?”
“成成,没问题。”他说,“瞅瞅,您带什么书?”
他看我牵着嘎嘎,一下子腾不出手,主动帮我铺展垫布,帮我摆放图书。一边做着,他说:“就这几本书?能卖什么钱啊!而且,你这还都是新书。现在有几个人看书啊,都看手机,走路都看手机,真看书的一般只认旧书。再说,新书哪儿都能买,你卖不出钱。”
我跟他说,你知道汪曾祺吗,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这个书的编者,这可是一套最好的选本,有必要的注释。他说他当然知道汪曾祺,却反反复复强调告诫我,你这书地摊儿上肯定卖不动。他说他摊子上的旧书一般都是十块二十块一本,到五十肯定就卖不动了。他的旧书都是人家当成垃圾废纸卖给他的。这位旧书摊主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和他谈谈书籍的同行。他哀叹北京某大学一位老教授夫妇离开人世后,他们的子女把那么多藏书当成垃圾处理,因为要马上腾空装修房子出租。他说那些子女根本不懂这些书籍的文化价值是可以变成很多钱的,也许几本书就顶得上一年的房租收入。
旧书摊主老陈,他比我晚出生四个月,我还是叫他老陈,他的上下门牙都是空的,张嘴两边各只有一两颗牙齿暴露出来。我的嘎嘎蹲在地摊上十分好奇老陈的大嗓门和飞快的语速,这时也在张嘴应和着,不过嘎嘎将要九岁了,它除了三四粒门牙,其它的牙都掉光了。
地下通道里手机信号全无。我想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屏蔽之前,最后看看有什么重要信息,特别是要通知《汪曾祺别集》的出版统筹、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分社的社长金马洛,他知道我要先行尝试练摊儿,也许他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我得告诉他我的手机没有信号,我在地下通道里。
我怀抱嘎嘎盘腿坐在地摊上,脚前是铺开的《汪曾祺别集》。通道里有微风荡来荡去,我把口罩一直拉到兜住下巴颏,我不想遮蔽自己。这处地下通道就在我住处大院门外,那些下班或出门的熟人有看到我的,也有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只有一位靠近了问一句,“你怎么摆起地摊儿了?”其他路过的熟人看到了,基本都赶紧回避着我,有的被我叫住了,个别热情地打打招呼,大多流露出对我这个城市无业居民的同情目光,还有的居然将我视为完全陌生人。后来碰到一位熟悉的博物馆馆长,我低声对他解释,我这是行为艺术,体验体验,拍拍照片搞宣传,因为今年是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诞生百年,我们编辑了这样一套他的作品。我觉得馆长大人似乎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思,其实我也说不透自己的意思。
再来说那旧书摊主老陈吧。我问他一天到晚摆摊儿,解手怎么办?他说,尿尿,就上去到街边小树后头解决,大的,早上出门前在家解决,摆摊儿基本不喝水少吃东西。他说,摆摊儿男的,哪个不得前列腺炎!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前列腺炎是否和憋尿或饮水少有关?要么就是长时间的低矮坐姿?老陈说,他家有一万多册图书,他经营旧书地摊儿已经有了十年。他现在照料着病中的老母亲,不一定天天出摊,每天也没有固定时间,照他话说:“咱们自由职业嘛!”说完,那张空落落的嘴巴哈哈自嘲一笑。老陈大概一周能卖两百元。他看出我的疑惑,补充说:“我当然不能靠它了,靠它还不得饿死!”
我问:“除了摆摊,你主要做什么?”
老陈站着说话,身体忽然轻飘起来,就势往白色脏污的瓷砖墙上一靠,“我做股票啊,做股票!”
这回可是轮到我哈哈大笑了,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笑了半天,我说:“你做股票,你做股票……”我简直说不下去了,连续咳嗽。
“唉,”老陈忽然显得有点羞涩,“我做股票,赚钱的。”
“你,做股票,賺钱?”我还是忍不住笑着。
老陈也笑了。不聊了,聊不下去了,他低头转身去照料他的摊子,并且他那边的水果摊主才是他说话的忠实听众。老陈后来又聊了一些,我就不写了,他的话题大多涉及鲁迅、徐志摩这些人物的历史典故,边说边乐,讲得真真切切,也颇为生动。
我盘腿坐在地摊垫布上,嘎嘎坐在我身边望着我。猛然想起它的零食,从腰包里掏出来给它吃。吃了,还要,再给它。吃了,又要,按说是不能再给了,想想,还是给它。我觉得靠在肮脏的瓷砖墙上,后背寒冷异常,赶紧坐直身体,我意识到这会引发一场严重的感冒发烧。
斜对过那位卖首饰的年轻女子出现了,很朴实的样子,人也富态。自行车后座驮个方正扁木箱,侧立起来,打开,箱盖边上镶一圈银色闪烁小灯泡,箱内和箱盖摆满挂满了耳饰、项链和发饰、戒指,这些廉价首饰都是外地生产的。她说,这里不能随便摆摊的,你也不要再招人来这里了,千万别招朋友来了,否则通道里摊位多,太乱,行人来不及看,大家生意都不会好。她说,摆摊儿多了,城管也要赶走我们。我问,现在城管会赶咱们吗,不是国家允许的吗?她说,谁说允许,再说,允许也可能是将来要指定地方的,那不叫地摊儿,是规划的大市场。我想起上面这些话,此前老陈也对我讲过。我把他们对我讲的在这里揉合起来了。
这位首饰女摊主隔天来地下通道摆摊,她说摆地摊儿属于兼职,她的主业是“前台”。
眼前是众多的腿脚往来穿梭,看久了头晕恶心。猛一抬头,出版人金马洛拎着两口袋书站在我面前,这时已是三点四十分,我已经在这里蹲了一个小时了。
马洛来了,我真高兴。他先是背着手弯腰到老陈的地摊看书,如同巡视一般,左右翻翻,立即买下三本,而我这里不要说开张,路过的没有一人注意我。刚刚一群放学的身着校服的高中生路过,我友好地问他们,同学你们知道汪曾祺先生吗?他们沉默,视而不见,赶紧走开。马洛给老陈开了张,一家伙老陈就收了四十多元的流水,我有一点嫉妒没了门牙的老陈。
那个首饰女摊主这时从提包里掏出塑料袋,把脸埋进袋子里吃东西。我问她,怎么才吃饭,这算午饭还是晚饭?她说不是饭,是水果,出来摆摊儿不吃饭也不喝水,就吃一点水果。
我对马洛说,自己大概受凉了,恐怕要生病。马洛赶紧返回停车的地方,从车上拿了两把便携式野外帆布小折椅。坐下来,马洛要我在他手机上看看他昨天的诗歌新作。可是,我这个时候的世界里完全没有诗意。我说了两声,你写得好。
我发现,老陈并不坐在自己的摊位上,而是甩手四处游荡,拎着他的小马扎找别的摊主聊天,或者坐在距离自己摊位一两米的地方。行人路过,老陈的摊子如同无主照料,在喧嚣中衬出了局部宁静的感觉,翻书的顾客得以安心专注地选书。直到有人拿起一本书扭头四下寻找摊主的那一刻,老陈好像脑袋后面也长了眼睛,慢慢走过去,这就又成交一笔。
我跟马洛说,我们不能坐在摊子上,离远一点,但是嘎嘎要在摊子上守着。嘎嘎真是少见的“好狗”,它不出声,也不怎么动。它在汪曾祺先生的后头蹲守着,时间长了,它会扭转身子歪起脑瓜,用两只后爪轮流挠挠耳朵,或者将头勾到腹部舔舔,然后改为卧姿,视线专注地左右望着来往的行人。时间很快过去了,天色渐晚,人流加大,可是没有人看我的书,在这个地下通道里,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没有读者,更没有粉丝,粉丝全都属于我的嘎嘎。
看,看,看啊,这小狗,多听话啊,看小狗,多好看啊,好萌啊,你好小狗你好,怎么这么老实呀,一动不动,你是假的吗?你多像个玩具狗狗啊……
有大长腿对嘎嘎招手,有爱情片里女主角模样的美丽姑娘向嘎嘎飞吻,努嘴亲亲,亲亲,亲亲……
已经过了傍晚六点半了,我们收摊走人,和老陈和首饰女摊主道了声再见。今天练摊儿近四个小时,没有开张,甚至就连开张的一丝一毫的迹象也没有。
我望着地摊上的《汪曾祺别集》,汪先生,我在这里,你还好吗?
附记:
2020年6月8日下午,北京作家龙冬手提一套《汪曾祺别集》主动到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亚运村执法队接受因摆摊违章的行政处罚,并向暑天战斗在基层一线的城管工作人员赠阅图书,表示慰问。
此前,6月4日下午,龙某在朝阳区北四环东路一处地下过街通道摆地摊售书。据龙某称,今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汪曾祺作品重要选本《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之一,又是汪曾祺的学生,有感于这套新近出版的编辑、校勘、注释精细的图书尚未被广大“汪迷”读者认识到,自己心急如焚,于是“头脑发烧”积极行动了起来。
龙某因这次摆摊撰写的《北京练摊儿记》于网络发布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得到广泛好评。但是,个别细心的网友从文章配图中发现了问题,那就是龙某摆摊有违反“交通道路法规”占道嫌疑,并且占用了人行道上铺设明显的“盲人通道”。有网友就此向作家严正指出,提出批评。作家得知后,当即逐一回复,自我检讨,并致以诚恳的道歉。
6月6日周六,作家龙某从微信上看到《北京日报》客户端标题为《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的新闻,获知城镇摆摊经营更要严格遵纪守法,执法部门今后也将加强执法检查,依法处理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龙某称,当他看到官方这个消息之后,深深陷入自责,寝食难安,发烧的头脑顿时冷却下来,于是决定在工作日的第一天主动到辖区城管部门检讨,并接受依法依规的处罚。
据悉,作家龙某摆摊售书占用地下通道及其“盲道”有近四个小时,他仅仅是为了推销《汪曾祺别集》。其间,未遇盲人通过,他的地摊生意也没有开张卖出一本书。城管值班负责人对作家龙某的主动认错和检讨给予肯定,对该作家的遵纪守法意识给予表扬,最终作出了口头批评教育、免于处罚的结论。正可谓,尊师占道摆地摊,竹篮打水一场空,遵纪守法讲公德,沿街摆摊须慎重。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也即,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路。龙某再三向城管负责人表示,今后自己一定杜绝在城市道路人多地方的摆摊行为,争做国家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