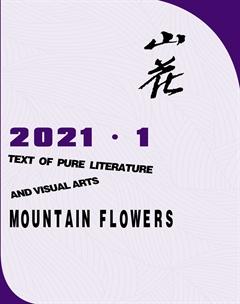时间的坐骑(外十首)?
王梆

时间的坐骑
旧货店里有一把椅子
它的皮革 是马栗子色的
中间沉淀着平凡的 凹陷
边缘闪着一圈艰硬的黑
它曾是时间的坐骑
走了很久 有两条腿
已经有些衰竭了
锉刀 在它们的胫骨上
书写过一种 我不熟悉的语言
像森林的恋人
用打击乐最原始的方式
在红叶的 锯齿里
与躺下的榉树告别
远方还有铁链的和歌
风正将它 切成烛火与刨花
今晚我应和衣而睡
而我的椅子将独自上路
今晚有一位受苦的木匠
将变成诗人
信
天还不太冷 昨晚
我为自己做了刺生鲈鱼
我的样子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许多更细致的事物裹住了我
每天 我乘火车上班
初冬的天空是银灰色的
树林里总是有鹿
掉了一颗牙的麋鹿
像谎言 在树叶的微笑里
打了一个孔
你的手越来越薄了
几乎磨成了一块空心的肥皂
但我还在用它 还有一些
光影重叠的钢琴曲
你告诉我 爱是模糊的
我们的皮肤切开晨光
到处都是回忆的兆点
顺着这行字 我将抵达墓地
我们的分离将更具体
也没有任何命运
将橘子的两瓣粘在一起
时间的老虎吞食着不朽
有一天 橘瓣会变蓝
在彻底忘记你之前
我想要 一场鱼刀式的流转
等 待
远方是盛大的,是拟声词的盛宴
你将为我采集坡鹿 鵟鹰和海鸟的声音
而等待是寂静的 是蒲公英
掳走的敲钟人的睡眠 每个寂静的夜晚
我佩戴着你的齿印 走在露珠的琴键上
我们曾在塔顶追逐对方 堕落地
相爱 我们的爱神秘 斑驳
像一枚小小的印第安银币 你是我的正面
我却是你的反面 我不是你
我将在你的最远处爱你 用钻木
蝴蝶和蚁骨 宇宙中一切微弱的引力
离 别
我们看上去已经旧了
像铁皮音乐盒里
两个穿驼绒大衣的人偶
嘴角靠近秋天的部位
也许还需要一点针线
声音却是好的
是肖邦的玛祖卡
毛毡礼帽也盛满了
清酒的诚意
每个离别的时刻都是一样的
走进沦陷区的桤木林
擦一根火柴
互相点燃彼此
独自在归途里熄灭
野 兽
野兽躺在台阶上等影子起来
它多年生的手 握着一只亮块
它有过四季的城堡 风爱过它
睡眠也爱过 而衰老是如此出乎意料
野兽的皮肤变得脆薄 氲暗
像一扇失聪的窄门 墓碑静静地长在门外
我的身体里也住着一头野兽
我喂它意志 音乐和一朵花开的时间
而它也会老 在一个明亮的早晨
我们将一同醒来 搀扶着对方
亲吻 坐上免费的村际巴士
春天将在晨雾中呼出新的野兽
吻
哪一样更糟 里面的
黑暗 外面的黑暗[1]
黑暗里 凹陷的脸
你的脸 守陵人送来
装不下睡眠的
床 床单阴凉
像泥土 你合上枕边的祷书
死亡 不过是
一棵裸树的躺姿
可你却不能
抵抗这最后的
吻 雨水的吻
从煮着时间的厨房
从火焰 火焰上空的蒸汽
两具肉体间的蒸汽
和玫瑰的 呼吸
从竖笛 六月的蜂巢
到所有 通往花芯的甜蜜的孔
涌出 乘积的云
一大片云 被虎鲸群逐的云
带着迫切 重叠的唇音
和稠密的白 除了钟杵的冲撞
谁都无法 稀释的白
黑暗也掩盖不住的 白
你既不能抵抗這最后
一吻
也不能抵抗记忆 湿润的
记忆 菱镜里的记忆和
那些 结晶的尘灰
你微张的口 说不
说死亡即是
记忆的 消失
而你的记忆正在
背叛你 雨水
只是它的替身
注释:
[1]“which is worse; the dark inside, or the darkness out”一句,出自Joseph Brodsky的I Sit by the Window.
坡 鹿
我的母亲坐在电视机旁
听着新闻联播
缝制皮囊 那是冬天
我们画押过的指纹是红色的
我在给一头远方的坡鹿写信
煤烟四起 眼泪流入澶湉的笔灰
没有再见 没有祝福
我关上门 独自走入安检处
一个脸上开满铁花的人
让我打开行李 那是什么
他数着一颗颗钉子 喷出嘴里的锈味
十颗用来封住记忆 我说
十颗用来加固未来 最后一颗
献给伟大的墙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我离开母亲 骑上未来
去寻找远方的坡鹿
我们分离之后的夜晚是无尽的
我的母亲坐在电视机旁
听着新闻联播
缝制着一具
从墙上取下的皮囊
山 顶
你出生在日光最短的一天
阴影 从午后迈入床沿
握着炭笔 用调音师的耐性
处理着 形体的边界
你试图 抓住光线的小手
愈来愈模糊
驱魔人替代你的父母
跪在 你的脚边
秣草遮住了马蹄声
你像雾一样张开嘴
将荒原吸入 童年
一个 比集体更宏大的
星体 一座巨梦 工整的睡裙
正一点点植入你的膝盖
你想把自己变小 变小 钙化成
心脏的结石 甩出某种慢性陶冶
你的少女时代是一把锉刀
划不破实木的 白
你的婚床也是单调的
印花之处洇满 油烟
你的手指揉搓在洗衣液和床单之间
剥开你的一切 直接 迅捷 (不假思索)
你闭上眼睛
远方
列车
顶上的风
将你钩入
海底隧道
比战争漫长
比百年短暂
那个靠你
卸下了俗世生活的男人
骑在海豚颈上
躲过了你的张望
当你学会向内生长 深入冬天 和微小的死亡
有时缓缓 落下 发酵 像苹果 在泥地里
品尝自我的冰甜
有时 玩呼吸的隐术 全心全力 致力于躲藏
像白色的蝴蝶 在灰烬里 翕飞 从此不再计较日光
你发现 你不过是一串字符 躺在自己的皮肤上 轻如竹简
绢帛 和纸张 一小蕞火焰 就可将你 带进密闭的存在
但你是欣喜的 你徹夜书写 在黎明 你将到达透凉的山顶
下雨的街道
下雨的街道
满地都是起皱的碎镜子
我低头走过high street
在面包摊前加快脚步
像想起了什么
其实只是为了
避开流浪者的眼睛
那两枚硬币底下的眼睛
我走回地下道
那里比雨更潮湿
有很多晶莹的水洼
每个水洼都是海
月光架起一座吊床
我开始用弧线写一首诗
它应该有你的微笑
你胸脯底下舒缓的呼吸
在路上
你是在梦里学会仰泳的
在去异国的路上
在一百个黑夜加起来的黑夜里
成群的乌鸦 正扑食田野的腐肉
你始终没有机会 摘下帽子
向高速路上 被车轮碾过的狐狸致哀
你离开 父母 家乡和祖庙
还有那个 住在石头里的圣人
一路向北 跨过海 北风
吹破你的单衣 而海不是
皱纹平静的 是“自上而下的深渊”[1]
如果你想跨过海 就要沉到海底
你是在梦里学会仰泳的 在路上
在冷柜里 连梦 也在蚕食你的体温
你的出埃及记 埋在
结冰的眼睑底下 像一滴咸的白蜡
我真想 捐给你 一口呼吸
让你游过黑夜 可我不能
我和其他人一样 懦弱 我也在海底
注释:
[1]自上而下的深渊:出自Eckhart Tolle的surface knowledge
家 书
没过甜菜根的泥土
是暖的
枕在你胸口上的被子
聚着你的体温
时差将虚空 分成两瓣
远山渐凉
暗黄色的草垛
像手帕里变小的发糕
或许 残缺本是
晚餐的一部分
长大以后
就再也画不出
啄木鸟的圆
往下走就是北半球
人们把冬天裹进
火焰 乌鸦的羽毛
和微小的丰收
我将越过你的视线
你的炊烟 越过
你用斜阳织的鸟巢
那比眼神单薄的
光的归宿
而我所能回赠的
只有一个手势
它将跟随你
在你独自
入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