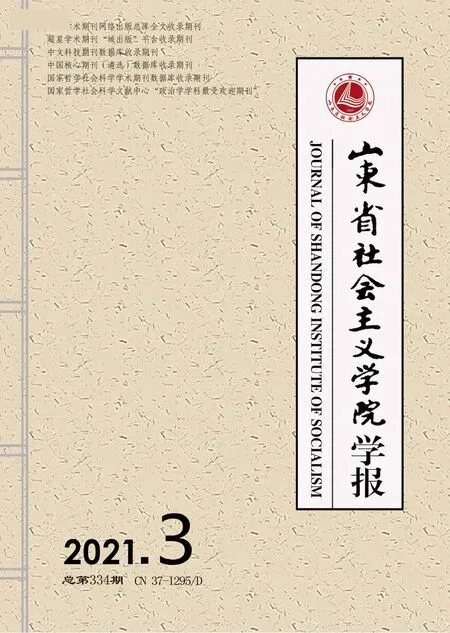《诗经》人文主义宗教观对儒家的影响
张 践
《诗经》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通过学习《诗经》,可以激发意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学会群体交往,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孔子认为《诗经》中包含着齐家治国的思想和方法,是做人的根本指南,告诫儿子和弟子们“不学诗,无以立”(《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是由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把《诗经》用于教化,使《诗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得以传承,其宗教思想也决定了中国宗教人文性的根本特点。正如《毛诗序》所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一、“畏天之威”思想影响了儒家“敬天法祖”的信仰倾向
《诗经》形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由当时的朝廷祭祀诗篇、民间诗人吟诵构成。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古代国家宗教当时仍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诗经》中对于天神、祖神的赞颂占有主要地位,从而决定了中国人宗教信仰中敬畏天命、崇尚祖先的主导倾向。
有学者统计,《诗经》中除诗题外,“天”字出现166 次,是一个高频词。[1]细致分析,《诗经》中的“天”包含三种含义,即“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可以说后世儒家对“天”理解的几种含义,在《诗经》中都已经包括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旱麓》),“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小雅·菀柳》),“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国风·黍离》)等几处所说的“天”,都是自然之天。但是在更多的地方,《诗经》所使用的“天”是作为“天神”的“主宰之天”,如“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小雅·天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小雅·北门》),“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等等。西周的宗教是从殷朝继承而来。宗教学家们考证,殷人信仰的对象是“帝”或“上帝”,并不把“天”作为祭祀对象。[2]但是周人在灭殷之前就有对“天”的崇拜,灭殷之后他们将自己的至上神与殷朝的至上神做了调和,“天”与“帝”并举,在上面所引《大雅·文王》一段诗中,这种情况就很明显。“天”与“帝”一样,都是有形象、有思虑、有作为的人格神。不过“上帝”是地上帝王在人们头脑的折射,人格性更强,而“天”作为一种从自然界抽象而来的“众神之长”,则相对玄远,人格性减弱了。有学者统计,在西周使用的宗教语言中,从早期“天”“帝”并用,到中后期渐渐过渡到主要使用“天”作为至上神,有一个过程,《诗经》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天”多于“帝”的情况。①据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统计,《诗经》中以“天”为神的记载共约106 次,以“帝”作“上帝”用者38 次。见顾立雅《释天》,载《燕京学报》1935年第18 期第65 页。第三种情况则是宗教中更富哲理性的“义理之天”,表明哲学已经开始在宗教的母体中生成。《诗经》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商颂·殷武》)等表明,西周时代的宗教已经摆脱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盲目崇拜状态。周公宗教改革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原则,赋予了宗教更多伦理性的内容。这时候“天”既是人与万物的创造者,也是自然与社会运行的规则,也就是宋明理学时代所说的“义理之天”。不过从《诗经》时代诗人们使用“天”的性质看,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三方面的蕴涵是相互融合的,并不像“轴心时代”由于思想的深化,出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区别。“天神”本来就是从茫茫苍天转化而来,其包纳宇宙万物的属性变成了主宰宇宙万物的神性。宇宙万物在天神的主宰下生存、发展,很容易被设想为宇宙万物按照天意运转,“天道”“天命”既是天神的指令,也是宇宙万物的规则。三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一直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的学术范式,一定要把中国古代的思想严格区分为宗教、哲学、伦理、科学等。
《诗经》中有大量的词句描写了殷人、周人诚惶诚恐祭祀天神、祖神的场景。《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人崇拜鸟图腾,《史记·商本纪》载:“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了宣扬殷王朝“君权神授”,执政者制造了其民族女始祖简狄在河边沐浴时,吞噬玄鸟之卵而生殷朝始祖契,以后逐步建立殷王朝的故事,说明殷王朝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武王伐纣,以周代殷,为了论证自己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也为自己祖先编造了一个得天命而生的故事。《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史记·周本纪》解释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周朝的女始祖姜嫄是踏着神人留下的足迹行走,所以生下了周朝的始祖后稷,故而周人也同样敬畏天命。《周颂·昊天有成命》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朝的历代先王都高度尊重天命,兢兢业业奉行天命,因此才有了王朝的兴盛,这就是“畏天之威”。《周颂·我将》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朝历代天子用牛、羊作为牺牲,按照文王留下的仪典,隆重祭祀天神,祈求天神时时保佑。
孔子对文、武、周公治理的西周盛世充满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把恢复西周的礼乐文化制度当成治理乱世的方法。孔子高度崇尚和认同西周的天命观,承认主宰之天的存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但是孔子对传统的天命观也有所损益,更强调自然之天的意义。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儒家理性主义天命观的视野中,天更多的是义理之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天命”或“天道”是人不论是否认识,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仍然肯定天命对人世的决定意义。“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在谈论世上的朝代变迁时,孟子十分肯定地说,天子不能把天下传给其他人,只有天才能决定谁可以掌握最高权力。但是他心目中的最高主宰者,并不是“谆谆然命之”那样的人格神,而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天何言哉”的自然神或“唯天为大”的义理。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天就是人们看不到、摸不着的某种神秘力量,在背后主导着世界的运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因此聪明的执政者,“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孟子·梁惠王下》)
总之,《诗经》基本包含了中国先民对待天命神权的态度,即必须敬畏天命。尽管后世的哲人们对天命的具体理解可能有差异,但没有人完全对天命置之不顾。正如新儒家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说:“但是孔子以下的思想家并没有切断人间价值超越性的源头——天。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意识,这个意识内在于人性,其源头乃在于天。”[3]承认天命对人世的决定意义,绝不能仅归结为封建迷信。且不说三千年前的周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尚未认识的自然、社会、生命规律依然有很多,应该学会对这些尚未被认知的规则的敬畏。
二、“以德配天”观念影响了儒家“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
“以德配天”不是《诗经》的原文,而是一个组合词,来自于“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大雅·文王》)、“帝迁明德,……天立厥配”(《大雅·皇矣》)、“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尚书·吕刑》)等。从殷人狂热、隆重、虔诚、“烝享无度”的祭祀活动,到周人“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尚书·洛诰》),殷周之际中国宗教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正如西方人类学家卡西尔所说:“一切较为成熟的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要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粗糙素材中提取它们的新品质,提取出它们对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4]原始的宗教关注的是神对人的态度,以丰厚的祭祀礼仪祈求神的保佑,而成熟的宗教则更多看到人的作用,把人的行为看成能否获取神的保佑的前提,宗教从此成为文明的伦理宗教。经过周公的宗教改革,中国的古代国家宗教就发生了这样一种质的变化,《尚书》用政府文件的形式阐明了这种变化,《诗经》用艺术的语言记录了这种变化。
周人提出“以德配天”的宗教改革理论,首要目的是解释以周代殷的社会革命。周人继承了殷人以“上帝-天神”崇拜为核心的古代宗教,那么当年殷王朝“受命于天”的神权到哪里去了呢?西周本来是殷朝的属国,臣下杀死君主的行为有什么道德依据?这些问题不回答,西周政权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全国臣民,特别是殷朝遗族的认同。周人承认按照“君权神授”的理论,殷朝曾经得到过“天命”保佑。《商颂·长发》说:“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殷朝的开国者商汤敬畏天命,恪守道德,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但是商朝后期特别是商纣王统治时期,完全背弃了对上帝的义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大雅·荡》)这是文王总结殷商失败的教训:并不是上帝不眷顾你们,而是你们不按规则行事,导致了国运的倾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同上)夏朝的覆亡就是殷朝的镜子,不能以史为鉴,只能重蹈覆辙。
周人提出,他们之所以能够战胜殷人,得到天命的眷顾,根本原因在于周朝列祖代代修德。“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大雅·皇矣》)按照周朝的族谱,周人从公刘之世开始,经过古公亶父、季历到文王,一直坚持以德治家、治国。“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从文王的母亲太任到他的妻子太姒,都是贤妻良母,以德治家,使得夫妻和睦,兄弟团结,形成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到了周文王的时代,“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虔诚地敬奉上帝,修行道德,因此能够领有天下。
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修德的根本就是爱民。《小雅·天保》说:“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祭祀神灵祈求保佑,关键是关心百姓,使他们食饱衣暖,就会感念统治者的恩德。《诗经》中还有周文王建灵台与民同乐的诗篇。“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大雅·灵台》)灵台是古代帝王的狩猎场,但是与历史上其他帝王不同,周文王建灵台不仅仅供王室的享乐,也让百姓们进入和分享。孟子在引用了这段原文之后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与民同乐”的出处,是中国历代执政者对自己的最高要求,表现出《诗经》教化的力量。
关于朝代的兴衰和天命的护佑,《诗经》的作者们得出一个结论:天命转移,祸福由人。“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上天的意志很难把握,但只保佑有德之人。《大雅·皇矣》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天明察四方,完全以民心为尺度。殷人失德暴虐百姓,而文王、武王的明德上天清清楚楚看在眼中。“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周朝的君王们应当以殷为鉴,努力修养自己的道德,从而保住得来不易的天命,使江山永固。至于普通臣民,也应当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求得天神的保佑。“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小雅·雄雉》)人只要修养道德,没有贪欲,有什么实现不了的目标呢?“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小雅·何人斯》)这句话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宗教的情怀,即“以人为本”。神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人,一定是人有过失在先。在人神关系上,决定性的因素在人而不在神。后世俗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也是从这个思想演化而来。英国学者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对“人文主义”定义道:“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5]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与人、自然与人的关系上,人已经处于核心、决定地位,所以说,西周的宗教已经开始变成人文主义的宗教。
《诗经》人文主义的政教思想,对春秋时代儒家宗教观、政治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周人文宗教浓厚的“敬德”思想影响下,孔子提出了“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执政者本人的道德品质,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有德之人,自然如北斗居于天枢,众星围绕。“德治”首先是对执政者的道德约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如果执政者都能够遵守道德和礼乐,那么百姓自然会遵守。上文提到孟子与学生万章谈论天授命于人的问题,认为天会通过一些现象显示自己是否授命某人统治天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万章上》)。但是如果相反呢?“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如果某一家族获得祭祀天神的权利,准备了丰盛的祭品,举行了隆重的活动,但是水旱灾害依然严重,这就说明上天不接受这个政权,“变置社稷”就是发生革命。孟子对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易经·革·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认为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不是以下犯上,而是替天行道的革命。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诗经》中关于神与个人成败关系的论断,也对儒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家认为成功基于个人努力,而不是依赖神的保佑。孔子引用《国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后发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礼记·中庸》)一个有道德的君子,把事业的成功基于自己的修养与努力,所以在生活中无怨无尤,尽人事而听天命,不像小人行险侥幸。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人的得失成败都是咎由自取,外在的天命不能决定个人的成败。即使遇到天降灾害,人通过主观努力也可以减少损失,但自己作孽则必然遭殃。孟子又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殷周时期对于人世具有决定作用的“天神”“天命”,到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一种客观的结果,人的主观努力则成为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点,即“尽人事听天命”。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他站在“天人相分”的立场上,完全否定了天地神鬼可以左右人世的祸福,把《诗经》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发挥到了极致。
三、“疑天”“怨天”诗歌影响了儒家对天人关系的人文主义思考
孔子说《诗》“可以怨”,可见哀怨之词在《诗经》中的重要价值。《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认为诗记录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西周王朝制定了“采诗”制度,把收集各地方民众的歌谣当成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所以这些哀怨之声才能够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目的。从宗教的角度阅读《诗经》,可以看出大量“疑天”“怨天”之诗对于中国传统宗教的转型和哲学思维的萌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诗经》各篇产生的时代看,产生于周初的诗篇主要是在歌颂天神的威力、智慧、严明。如“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大雅·文王》)、“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小雅·瞻彼洛矣》)等,都是周人子孙对文王、武王等先人修德配天的赞颂之词。
自周懿王之后,周室统治开始衰落,特别是周厉王、周幽王的统治更加昏庸、腐败,以至于镐京被焚,幽王被杀,王室东迁,结束了西周几百年的统治。西周的诗人看到王室腐败对国家的危害,用诗歌讽谏,以引起世人的重视,促进政治的改良。在他们的诗歌中,在各种严酷的天灾人祸面前,西周初天人和谐的画面不复存在,人们看到了天怒人怨的场景。地上黑暗统治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些仍然被无道昏君奉为护身符的“天神”,自然也遭到人民的怀疑。《小雅·十月之交》记载当时的可怕场面:“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电闪雷鸣、暴雨不停、山洪暴发、山峰崩颓、高岸塌陷、深沟凸起,一副遭遇灭顶之灾的景象。但就是这样的大灾难,仍然不能引起昏聩统治者的警醒。《诗经》记录了当时人们“疑天”“怨天”甚至诅咒“天神”的一些诗句。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天神崇拜”和“祖神崇拜”,可现实与宗教理论的矛盾却使人感到天神的可疑。古代宗教宣扬天地为民父母,“降福穰穰”,养育万民,可为什么“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大雅·云汉》)?天神本应该耳聪目明,无所不知,扬善惩恶,可为什么“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雨无正》)?天为什么是非颠倒、降罪无辜呢?天子本为皇天元子,当统领万邦,可现在天下混乱,诸侯侵夺,“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小雅·节南山》),天为什么不保祐王呢?人们不仅怀疑天神,而且也怀疑祖神。“群公先王,则我不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大雅·云汉》)祖先之灵为什么看着子孙受难而不拯救呢?人们由怀疑转而埋怨。“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上帝虽然有很大威力,但他的命令多是错误的。“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小雅·雨无正》)这如同说:老天爷你的道德在哪里呢?对天神的道德属性表示了怀疑。“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小雅·雨无正》)为什么老天不听良言,专行暴虐呢?似你这般行动迟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开始对天神主宰能力的怀疑。“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小雅·正月》),人民正在受难,老天却昏昏如睡,天神的主宰能力何在?不过,《诗经》中记载的一些民谚对天的疑怨、诅咒,虽然言辞激烈,但还是以天神存在为前提的,还停留在情感的阶段。
在“以德配天”思维框架下,诗人们开始思考天灾背后的真正原因。“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自然灾害会对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灾害的原因在于人祸,是上天对一些违背天意的统治者的惩罚。《国风·东方未明》载:“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首诗描写东方未明,连衣服的正反都看不清,国人便要起床去为国王服劳役。《小雅·杕杜》说:“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这是征人之妻埋怨王室徭役沉重、想念丈夫的诗。她的丈夫奉命去开发北山,家里的花儿都开了,可是丈夫不回归,无人照料年迈的父母。《国风·鸨羽》吟诵道:“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大雁飞来落在栎树上,可是王公老爷派的差遣干不完,自己家的田地无人耕种,我的父母靠什么生活?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可是贵族们却过着清闲优裕的生活。《国风·伐檀》说:“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贵族们不耕种也不收割,但是却得到了三百捆粮食,不打猎也不畜牧,他们的墙上却挂着干肉。贵族们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诗人把他们称为“硕鼠”,怒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国风·硕鼠》)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论述,“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向,预示了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将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上。
受《诗经》等古代经典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儒学关注的重点在此岸世界。《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怪异、暴力、动乱、神秘的东西,孔子从来不说。对于学生关于彼岸世界的提问,孔子都给予了不可知的回答。“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回答,还没有学会事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呢?子路又问人死后是否会变成鬼,孔子回答人活着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能知道死后的世界呢?庄子在总结孔子宗教思想的特点时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在当时宗教氛围仍然浓郁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提倡“复礼”,不可能走向彻底的无神论,但是对彼岸世界存而不论,把学术的重心放到了现实的人生问题上。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人对此超越源头只做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6]正因为中国儒家对天命神权只肯定不深究的态度,使得儒家的宗教性没有进一步深化发展。
关于人世的治乱兴衰,儒家将是否行德政看成问题的根本。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只要执政者践行礼、义、信等道德,民众自然拥护,国家就会兴盛。在对宗教人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待古代宗教的方法。《论语·雍也》载:樊迟问什么是“知”。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待鬼神“敬而远之”,孔子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在春秋时代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既保持了对各种宗教必要的尊重,又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中国政治文化的依据从天国转向了现世,但也没有走上彻底无神论的道路。中国政治文化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持一种中庸、二元的立场。不过,“远鬼神”必然会近人文,这使人本主义的儒家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比较中国与欧洲轴心时代的异同,可以发现中国不同于欧洲对古风时代采取批判性割裂的立场,而是采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继承性发展的立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前轴心时代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就包括《诗经》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