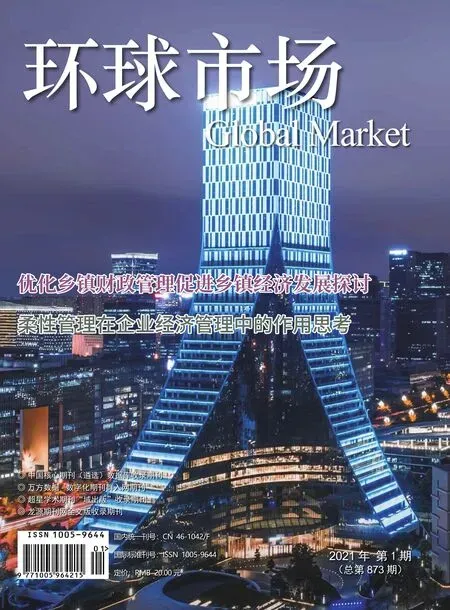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一、引言
农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农业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促进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土地资源非常丰富,是古老农业区之一。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近年来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农村土地荒废现象严重,用于农业生产的粮食生产用地逐年减少,产业规模逐年降低,市场竞争力下降。
二、模型分析与研究设计
模型概述:
1. DEA模型
根据DEA模型方法,综合效率反映的是该市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利用和规模集聚效率,而纯技术效率则指的是该市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规模效率表示的是市农业资源投入规模集聚的效率。
2.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主要被应用于动态效率变化趋势的研究。公式可改写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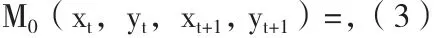
式中:第一项表,规模效率变化,第二项表示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三,表示技术变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fp,h)可由这三项乘积进行表示。规模效率变化大于,表示市投入集聚规模改变,规模效率提高;纯技术效率变化,于1表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改善使效率提高;技术变化大于,则表示生产技术改进;tfpch大于1表示综合生产,有所改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时间分异特征
运用DEAP2.1软件,选择基于规模报酬可变模型VRS(以投入为导向),分别计算2008~2017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报酬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各年份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在[0.92,0.98]之间波动,且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948,此外,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纯技术效率在[0.94,1]之间波动,平均值为0.972。纯技术效率的增长趋势与综合效率的增长趋势极为相似,可见纯技术效率是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规模效率在[0.96,1]之间波动且平均值为0.973。故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规模效率整体规模效率水平高。
(二)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将2008~2013年各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取平均值得到代表各市2008~2013年各分项的平均水平。研究发现:在空间分布上,各地级市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小,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土地利用效率相对高低区交错分布,总体趋势为东部高,西部低。在研究期间11个山西省地级市中有太原市、长治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共5个地级市的综合效率值为1,可见这些市农业用地处于有效运营的状态;其余的6市农业土地效率综合利用率<1,存在一定改进空间。
(1)5个综合效率值为1的地级市受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对农业发展投入较大,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分析5个地级市的基础数据可以发现:他们共同的优势是注重资本和技术的投入。这5个地级市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值、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相对较大,可见资本和技术增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较高。
(2)在技术无效的6个地级市中,大同市、吕梁市和晋城市依次位列综合效率排名的第9、10、11名。其中,晋城市因投入要素过多导致纯技术效率低,吕梁市因投入要素不足而导致纯技术效率低,两市规模效率虽低于平均值但与均值相差较小,技术无效主要由纯技术效率低导致。大同市规模效率在11个地级市中相对最低,纯技术效率高于平均值,因此,综合效率值低主要由规模效率低导致。大同市2008~2017年均农业生产面积为302533.5公顷,年均农业生产面积在11个地级市中排第6位,规模较大,因此,大同市应适当减少农业生产规模,以缩短与前沿面的距离,提高规模效率。
(三)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变化趋势分析
2008~2017年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MPI除了在2014~2015年大于1以外,其他时段均小于1,其均值为0.7982。总体来看,各分项要素在研究期间内均呈现负增长,技术退步是MPI生产率指数降低的主要因素,而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也有待提升。技术退步的主要原因是山西省科技创新体系不科学、创新能力不足。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农科教职责不清晰、高效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建立、科技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也无长远考虑。
四、启示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表明山西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均较高,但高效率背后的降低趋势启示我们山西省农业需加速构建新型农业经营和创新体系,尽快调整生产方式、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农业土地利用效率,进而助力农业生产、振兴农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