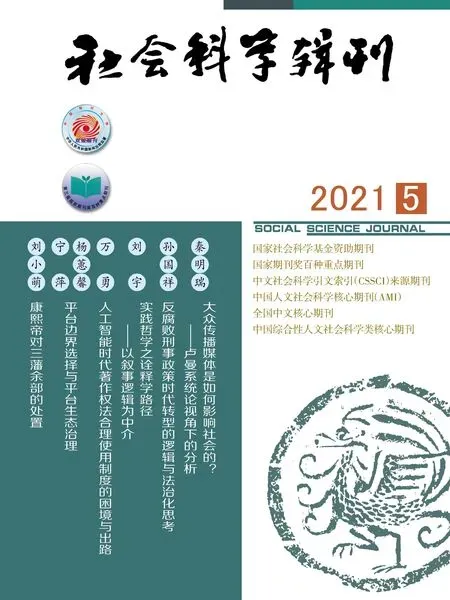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正义与问题
龚 群
自从1963年David Sachs发表AFallacyinPlato’s Republic一文以来,学界对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对正义的论证以及相应论点进行了相当多的争论。David Sachs的观点是:柏拉图式的正义与粗俗的(vulgar)正义不相干,因而柏拉图没有回答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提出的问题。人们围绕着David Sachs提出的论点展开了长期的争论①这一问题得到持续的讨论,如 Norman O.Dahl,“Plato’s Defense of Justic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ol.51,no.4(Dec.1991),pp.809-834;Nicholas D.Smith,“Plato’s Analogy of Soul and State,”The Journal of Ethics,vol.3,no.1(1999),pp.31-49;Jiyuan Yu,“Justice in the‘Republic’:An Evolving Paradox,”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17,no.2(Apr.2000),pp.121-143;Robert Heinaman,“Why Justice Does Not Pay in Plato’s‘Republic’,”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54,no.2(Dec.2004),pp.379-393 ;Bernard Williams,“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The Sense of the Past Book: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Mehmet M.Erginel,“Inconsistency and Ambiguity in Republic IX,”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vol.61,no.2(2011),pp.493-521 ;Lloyd P.Gerson,“Plato’s Rational Soul,”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vol.68,no.1(Sep.2014),pp.37-59。近年来此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如张立立:《柏拉图真的在〈理想国〉中犯下了‘不相干的谬误’吗?》,《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本文拟从David Sachs提出的问题入手,对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的论证以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推进中文学界对于柏拉图《国家篇》的研究。
一、粗俗的正义
David Sachs提出柏拉图的《国家篇》中有两类正义:一类为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粗俗的正义,另一类是为了回答这些智者提出的不正义比正义对于个人幸福更为有利或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为幸福的问题而提出的柏拉图自己的正义。David Sachs认为柏拉图的正义与前者是不相干的,因而没有回答智者提出的问题。〔1〕
“粗俗的正义”的说法是在442d10—443b2①此为柏拉图全集希腊文标码,此后不是引文但需说明、叙述原文处,都用希腊文标码。这段话中由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在这段话里,进一步从国家职业三分到每个人的灵魂三分、从国家正义到每个人的灵魂正义的一致论证了正义的人的品质是什么。柏拉图认为当理智在人的灵魂中起主导作用而激情与欲望(情欲)都服从理智,即当人是节制的人时,他也就是正义的人。苏格拉底可能觉得这样说比较抽象,因而以“粗俗的”(vulgar)方式来检验。这种粗俗的方式就是看是否会鲸吞为他人保管的财产、渎神、偷窃、出卖朋友、背叛国家等。格劳孔和苏格拉底都同意正义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而不正义的人则会做这样的事。其所列出的这些事,都是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换言之,符合“粗俗的正义”的人不做不道德或非法的事,而不正义的人恰恰是做不道德或非法的事。David Sachs指出,这正是在第1卷和第2卷中,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他们所运用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人的概念。正义也就是不做不道德和非法之事,不正义则相反。苏格拉底以粗俗的方式来检验柏拉图式的正义,并非意味着这两者可以等同。柏拉图以此为例,仅仅是为了指出柏拉图式正义的人不会做从粗俗的正义来看是不正义的事。为了说明这两者的不同,我们需要将两者进一步展开。
在第1卷343d—344d,色拉叙马霍斯指出正义与不正义的不同。他认为,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如合伙经营做生意,总是不正义的人多得,而从来没有看过正义的人多得;要交税,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义的人交得少。正义的人不肯损公肥私,得罪了亲朋好友,而不正义的人则处处相反。色拉叙马霍斯说:“你如愿弄明白,对于个人不正义比起正义是多么的有利这一点,你就去想想这种人。如果举极端的例子,你就更容易明白了: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苦恼的人。极端的不正义就是大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巧取豪夺。”〔2〕他还指出,普通人犯了罪,就是强盗、拐子、骗子、扒手,而那些窃国者,不仅没有恶名,还被认为是有福。苏格拉底指出,这是一个正义还是不正义哪个对人更有益或是正义还是不正义更能使人幸福的问题,因而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即做哪一种人更为有利?在这样讨论正义与不正义行为的后果时,色拉叙马霍斯就是使用粗俗的正义概念,即正义的人不做什么,而不正义的人会做什么。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是,正义对人不利或没有益处,而不正义恰恰对人更有益。在这里,“有益”都可换成“使人快乐或满足的状态”或“幸福状态”。
随后,在第2卷358e—367e中,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发表了长篇大论,不仅提出了正义与不正义对人的功效(行为后果)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正义本身或正义之名与利相区分的问题。格劳孔以吕底亚人古各斯的祖先为例,进一步强化了色拉叙马霍斯关于窃国大盗的论点,即只要把不道德或非法的事做大而又能像获得隐身戒指的古格斯的祖先一样不为人知,那么,所谓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没有两样,他说:“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3〕其次,格劳孔与阿得曼托斯将正义的名利与正义本身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前提是,他们也承认人们追求正义会给人们带来名利,或者干脆说,在智者们看来,世人们所追求的正义,无非是追求正义的好名声和所带来的利益,而并非是真正追求正义本身。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分,因此,智者们认为可以有这样两种假设,即所有那些干不道德或非法之事如偷窃、渎神、强奸、杀人越货以及窃国的人,都假以正义之名去干,坏事做尽却获得好名声;而那些真正追求正义的人,除去一切表象,只剩下正义本身,甚至为了正义而受尽折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世上还有没有人会追求正义。在智者们看来,正义除去一切外表或带来的名利,是没有人会追求的,因为“‘貌似’远胜‘真是’,而且是幸福的关键”〔4〕。何为正义本身?如我们说花的美,这不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仅仅是因为美本身而喜欢;如一场球赛,我们喜欢观看,不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仅仅是因为这场球打得好这本身令我们喜欢。正义本身也就是,不是因为它的后果或行事正义所产生的后果而认为正义就是善的或好的。但如果正义本身不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带来厄运,你还会坚守正义吗?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太多了。智者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不正义与个人利益或幸福的相关性如何?二是正义与不正义本身是什么?三是正义与不正义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或正义与不正义的力量(power)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也可以合并,即到底是正义还是不正义对于个人幸福更为有利或有益?因为智者们明确提出,只有行事不正义或行事做得像正义但实际上不是正义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而柏拉图毫无疑问是站在智者观点的对立面。然而,如何才能反驳智者的论点?如果不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可以说,柏拉图并没有真正反驳或驳倒智者们。
二、城邦与灵魂的正义
正是为了反驳智者们的不正义给个人带来幸福而正义则根本不符合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基本观点,柏拉图展开论证。David Sachs说:“面对格劳孔,苏格拉底不得不证明,为格劳孔所描述的条件,一个正义的人比那些如他所表明的那样不正义的人,将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依据幸福,这是柏拉图在不同的生活中选择的标准,而依据幸福,一个人应当选择正义的生活。”〔5〕在他看来,柏拉图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即正义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所回答的是行事正义的效果或后果问题。柏拉图提出只有正义才真正能使人幸福,为此他提出了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即在城邦国家中的正义和在个人灵魂中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寻找真正的正义,只有在一个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在他看来,正义的人与正义的城邦是内在一致的,并且,我们只有首先找到一个正义的城邦,才可以从中找到正义的人。而在一个不正义的城邦中,正义之人是十分稀少的。这一观点隐含的意思是,只有有了大字的正义,才可能有小字的正义。我们可能会说,这反映了柏拉图对一个社会共同体制度的高度重视,即只有理想正义的政治制度,才可以确保这样的共同体是一个正义的共同体。但这样的理解不符合柏拉图的思路。柏拉图把一个城邦共同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如果能够和谐配合有序运作,就是一个正义的共同体。那么,如何做到使这样一个共同体能够有序运作呢?柏拉图认为,只有德性(áρετή)能够使共同体有序地运作。不过,在《国家篇》中,仅有一处(444e)有对于德性这一概念的定义。柏拉图说:“德性是灵魂的一种健康、良善的状态与存在(wellbeing),而恶则是心灵的疾病、羞耻和软弱的状态。”〔6〕柏拉图的这个定义是在心灵品质或内在品质的意义上给德性下的定义,指出德性的功能在于维持灵魂内在的良善和健康的状态。就古希腊德性概念的本义而言,德性又可称为“卓越”,因为所谓德性也就是某一功能的卓越的发挥,如眼睛的功能在于看得见,而眼睛的德性就在于看得远而且清晰。
在古希腊观念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功能,其功能的良好或卓越发挥,都表现为德性。灵魂的德性就是灵魂内在功能的卓越发挥。柏拉图把一个国家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的功能,而功能的卓越发挥也就是它的德性。柏拉图把国家或城邦共同体看作是由三个部分有机组成的:统治者、护卫者和普通劳动者(商人等)。统治者的功能在于能够良好地治理这个国家,他的功能的卓越发挥也就是智慧;护卫者的功能在于保卫国家,他的功能的卓越发挥离不开军人的勇敢,因而勇敢也就是护卫者的德性。然而,普通劳动者的德性是什么?我们会认为应当是勤劳吧。然而,柏拉图几乎没有提及。在他看来,普通劳动者的德性主要是节制。节制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控制自己的欲望或情欲。为什么普通劳动者的德性主要是节制?柏拉图主要是从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来考虑。在他看来,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的三类职业,是由三类人来承担的,这三类人应当是生来具有什么素质,就应当承担什么职责。柏拉图认为,人们的天分规定人们生来只能从事某一种职业。但柏拉图并不是完全的血统论者。在他看来,如果下层人的孩子从小被发现有很高的天赋,那么,他就不应当像他的父母那样从事低下的工作。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应当让他相信像“金银铜铁”这样“高贵的谎言”,从而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所有人都有欲望或情欲,这种欲望或情欲也就是如格劳孔等智者所说的那样,总是处于希望获得满足或更多满足的欲求状态之中;并且,处于社会下层或底层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满足,因而要有更多的节制德性才可以使他们不去追求非分的欲望。不过,柏拉图认为,欲望或情欲是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的,因而所有人都应当有节制的德性,但在普通劳动者这里,则是主要德性。柏拉图认为,当这三种德性在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那里都发挥了作用,这样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7〕。
为什么三种人各做各的事就是国家的正义或社会的正义?柏拉图通过分析个人灵魂的三分结构来论证。在柏拉图看来,国家职业三分从而使三种德性起主要作用是与个人灵魂的三分结构相一致的。在《国家篇》中,灵魂是理性、情欲(欲望)与激情三分的结构,这一灵魂仅仅是指人的灵魂;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三分是包括了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在内的。可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对人的灵魂没有进行区分,灵魂仅仅是与人的肉体相对立的精神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国家篇》中的灵魂说是为了能够解释在城邦共同体中三种德性共同起作用而构造的。“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且数目相同。”〔8〕这三种不同的部分中,理性与情欲或欲望在本性上是对立的,激情则是理性的协助者。理智是理性的体现,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理智教给激情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因而这样的人表现为勇敢的人。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它的领导,这样的人也就是节制的人。由于理性控制和支配了情欲或欲望,同时得到了激情的协助,因此,灵魂内部也就是和谐而有序的,从而也就实现了灵魂内部的正义。柏拉图认为,从灵魂内部的正义也就能够清楚城邦的“各人做各人的事”这样一种正义的说法,他说:“真实的正义确实是如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东西。然而,它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部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并且在这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破坏这种状态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9〕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类似,因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对灵魂内部的正义的理解来理解城邦的正义,城邦的正义由于灵魂的正义的说法而得到加强。
应当看到,柏拉图多处讨论关于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相类似或一致的说法,这些讨论迂回曲折,也产生了不少理解的分歧。威廉斯就指出,在434e处,柏拉图并没有完全确信我们可能会发现那种类比。〔10〕事实确实是,在434e处,柏拉图要求我们在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来回对比,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类似或一致。而在435e处,柏拉图认为他确实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类似和意义的一致。然而,柏拉图的类比论证确实存在问题。威廉斯指出:“在435e处,柏拉图给出了三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那三个例子……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支持先前那一原则,即找到一种共同的特征(品质)说明,并且藉由那种特征(品质),城邦与人都可以这么称呼。但我们发现这是失败的。因为,如果我们说,‘F’适用于城邦仅仅是因为它也适用于人,那我们实际上已经解释了为何那个词同时适用于城邦与人,而如果从那里出发,继而为为何‘F’适用于人再寻求类似的解释,这至少就是无意义的。”〔11〕威廉斯在这里指出柏拉图循环论证的逻辑问题。
我们在前面的简述中指出,柏拉图的城邦正义在于三个阶层的人都具有相应的德性。这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柏拉图的正义在于:一、城邦中每一种德性都能够履行相应的职责;二、理性施行其治理职能;三、这意味着当且仅当城邦的人是正义的时,城邦才是正义的。威廉斯指出:“对城邦来说正如对个人一样,我们所需的必要条件是,城邦的正义取决于〔第一条件〕的真实性。但〔第一条件〕对于后面两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如同城邦一样,城邦的成份也由个人组成,然而,如何解释那些成份的特征呢?”〔12〕柏拉图仅仅强调了统治者要有理性或理智智慧,护卫者要有勇敢的德性,普通劳动者要有节制的德性,认为当这三部分人如他所说的那样由各自的德性起了作用,则城邦就是正义的。然而,矛盾的是,他又强调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应由理性或理智智慧来支配,个人的心灵或灵魂才是正义的。换言之,如在普通劳动者那里,那种与理性不合的情欲虽然为理性所制约,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灵中理性的成份像统治者——哲学王那样占优势,我们怎能说他的内在灵魂与哲学王一样是正义的呢?威廉斯的分析实际上说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这个矛盾在《国家篇》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仅仅承认“各做各的事”就是正义,而处于普通劳动者地位的人仅仅承认自己的低下地位就是符合正义的,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以欲望为主体的低下阶层的灵魂正义只是承认被统治的合法性而已。
关于柏拉图式的正义,还有一个问题,即柏拉图式的正义的哲学特征。聂敏里认为粗俗的正义是一种经验性的正义,而柏拉图式的正义是抽象意义的,是康德式先天综合意义上的正义。〔13〕然而,我们认为,如果把柏拉图式的正义说成是一种正义,那么也只能说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社会正义论。柏拉图的建构主义正义论,是在只有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德性在相对应的职责阶层起作用的前提下才可存在。这三种德性为不同阶层的人履行职责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并且,作为正义的建构性元素,三者缺一不可。在柏拉图看来,在这三者中,理性或智慧起决定性作用,在柏拉图的正义社会或灵魂图景中,有了理性的支配或主导作用,才有其他两种德性正常发挥作用的可能。换言之,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出现正义这一概念,有了理性,也就有了柏拉图所说的社会和谐秩序或灵魂和谐秩序。因此,如果说还有正义这一概念,则正义是完全虚化的,并没有起实质性作用。正如Robert Heinaman所说:“当正义要承担某种特别任务的作用时,正义在城邦中根本就没有起作用。”〔14〕而柏拉图强调因理性或理智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产生的和谐秩序,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心灵秩序,都是秩序正义观,实际上是对于自荷马以来的宙斯的正义概念的回响。在荷马的宇宙那里,宙斯的统治体现为这个宇宙的正义秩序,或以宙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则的正义秩序。但是,进入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希腊时代,宙斯的秩序正义观已经化为不同城邦国家的正义观,统一的宇宙秩序已经不存在了,尤其是统一的希腊社会秩序已经化为不同城邦国家的秩序了。从历史意义上,柏拉图的这三种主要德性建构起来的正义,不过是久远的荷马时代宇宙观的反响而已。
三、柏拉图式的正义回答了智者们的问题吗?
我们再回到David Sachs对于柏拉图式的正义的质疑上来,即他认为柏拉图没有回答格劳孔等智者的问题。首先,关于正义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行使正义是因为正义本身而不是因为它带来的好处。柏拉图建构了两种正义即大字的和小字的正义,他认为社会或人们的灵魂需要它,是因为上述原因吗?不是,柏拉图所强调的是它的功能。希腊的德性概念是一个功能概念,正义概念也不例外。而谈到功能,即正义(或行事正义)对人产生好的后果,不正义对人产生恶或坏的后果。其次,柏拉图面对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提出的不正义可以使个人幸福而正义或真正的正义恰恰并不能够使人幸福的论点,他感到仅仅从希腊所流行的粗俗的正义观难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因而另起炉灶,提出他自己的正义概念。柏拉图重新建构了正义概念,是为了与希腊当时所使用的粗俗的正义概念相区别,然而这使得他的理论内部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必须回答柏拉图式的正义与粗俗的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David Sachs说:“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排除了一般被判断为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但他必须证明,他的正义的人的行为是与普通的或粗俗的正义标准相符合的。第二,他的正义的人的概念运用到每一个人或被例示为这般是正义,这些人也应依据粗俗的正义标准是正义的。简单地说,因为他并没有表明,与粗俗的正义人一致是不可能的,并且与那些不这样做的相比,那些人是较不幸福的。假如他关于正义与幸福的结论是成功地反对了色拉叙马霍斯的论点和满足了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要求,他就不得不满足这样两个要求。《国家篇》里的有些段落表明,他意识到了第一个要求没有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第二个要求。而不论怎么看,他两个要求都没有满足。”〔15〕David Sachs认为他没有回答智者们的问题,或没有满足两个要求。就第一个要求而言,在442d10—443b2处,柏拉图在说到自己的正义概念时,就以粗俗的正义的说法来进行印证,说明柏拉图至少是回应了这个要求。
对于第二个要求,即柏拉图必须证明不仅是他自己的正义,而且从粗俗的正义看,也应当是可以证明成功地反驳了智者们的论点。换言之,履行他的正义观的人是幸福的,并从他的正义观上看,那些不正义的人是不幸福的。但从柏拉图对于他的正义概念的建构来看,我们没有发现柏拉图有这样的意图,甚至当讨论到护卫者的幸福问题(第3卷结尾处和第4卷开卷处),柏拉图给人的印象是,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护卫者们并不幸福,甚至过着很悲惨的生活。阿得曼托斯在第4卷开卷处说:“假如有人反对你的主张,说你这是要使我们的护卫者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不幸的原因,虽然城邦确乎是他们的,但他们从城邦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能象平常人那样获得土地,建造华丽的住宅,置办各种奢侈的家具,用自己的东西献祭神明,款待宾客,以争取神和人们常有的一切,我们的护卫者竟穷得全象那些驻防城市的雇佣兵,除了站岗放哨而外什么事都没有份儿那样。”〔16〕按照柏拉图与智者们对立的出发点,即正义的人是幸福的人,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城邦中,护卫者无疑是正义的人,但却过着悲惨不幸的生活,这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吗?正是在这里,关于幸福,柏拉图没有再遵循第1卷和第2卷中的经验论证,而是搁置这一问题不谈,转而提出一种观点,即这个国家整体的幸福在于这个国家各部分的和谐发展。柏拉图说:“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当割裂开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的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17〕在《国家篇》中,正是从这里开始,柏拉图没有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讨论正义,而是从城邦整体幸福的视域来讨论问题,即提出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关于城邦与灵魂正义的说法。不过,这里柏拉图明确地承诺,他不是仅仅要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幸福,而是要城邦全体的幸福。这里的问题是,难道整体的幸福不体现在某一部分的幸福中吗?其次,其论述的整体的幸福无法体现他所提出的“各做各的事”的正义与整体幸福的关联。不过,我们可以将其推演为城邦共同体在理智的统治和主导下,内部和谐既是正义也是幸福,灵魂内部在理性或理智的主导或支配下,既是正义也是幸福。但确实如David Sachs所说,我们无法从他的上述论证中看到,以粗俗的正义观来看,不这样做的人是不幸福的。并且,即使是从他的正义观来看,也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柏拉图因此而否定了智者们所提出的幸福原则吗?我们认为没有。智者们的幸福即是阿得曼托斯在第4卷开篇中所说的那些实际的物质利益。以此为基本内容的幸福原则是智者们的,同时也是柏拉图没有否认的,否则他不会说要把这个幸福原则放在国家整体中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偏离了这样一种整体和谐的正义论而追求自己的幸福,柏拉图的正义论没有办法否定他们仍然是幸福的,甚至比柏拉图式的正义意义上的更幸福。而这也是霍布斯式的“愚人”或通常所说的逃票乘客的问题。柏拉图式的正义没有回答甚至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以护卫者为例来讨论《国家篇》中的所有正义之士的幸福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他的理想城邦共同体中,正义的人并不是幸福的人。因为柏拉图虽然要说不能单独讨论护卫者的幸福,而要放在整个城邦共同体中来讨论,并且要从整体和谐出发来讨论,但他并没有否定智者们提出的这个幸福原则。然而,我们看看在第3卷末尾处,苏格拉底关于护卫者的生活状况的描述:“如果他们做优秀的护卫者,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生活方式:……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财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也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象士兵在战场上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他们不应该让它同世俗的金银混杂在一起而受到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18〕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这样规定了他心中理想城邦的护卫者的生活条件,从而引发了阿得曼托斯的议论,认为理想城邦的护卫者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仅仅只有绝对的生活必需品)。苏格拉底认为,我们不应仅从某一阶层来看待他们是否幸福的问题,而应从整体来看待,要追求整个城邦所有人的幸福。但苏格拉底上述对阿得曼托斯在第4卷开卷处所说的回答,实际上是承认了理想城邦的护卫者并不幸福,只不过在苏格拉底那里,他们的不幸福是换来整个城邦和谐幸福的前提。然而,如果这个理想城邦的护卫者并不幸福,即三个阶层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不幸福,我们能够说这是一个全体幸福的城邦吗?
柏拉图式的正义并没有回应智者们的行事不正义比正义幸福的论点,但在第8卷和第9卷中,柏拉图在理想正义城邦下的四种政体的讨论中,以灵魂背离理想正义从而导致不幸福进行了逐步降级式的处理。在柏拉图看来,离理想正义城邦越远,也就越不正义,从而也就越不幸福。柏拉图为其正义辩护,可以看作是对智者观点的集中回应。他虽然不是从他建构的正义及其功能或积极意义来回应,但是从消极意义即做不到柏拉图式的正义必然是不幸福的这样一种观点进行回应也应当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不过,非常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第1卷和第2卷中,智者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进行大量讨论,提出不正义的人的生活好于正义的人的生活是从“行为”的角度,即行事不正义对人有利,而行事正义则不利,如在第1卷的343d—344d中和在第2卷358e—367e中,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他们所有涉及正义与不正义的说法,都在说行为,而不是指灵魂;而在第8卷和第9卷中柏拉图提出不正义的人的不幸福则是从内在灵魂的角度提出的。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柏拉图自己的正义概念是以灵魂内在的德性即理智或智慧、勇敢和节制为建构要素提出的在城邦共同体和个人灵魂中的正义。因此,斯巴达式的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这四种现实的政体是灵魂的堕落。加上哲学家为王的王制政体,即为五种政体。有五种政体,也就有五种灵魂。柏拉图没有忘记,他的这一整个浩大写作是为了回应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他说:“我们要考察一下较差的几种。一种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他们相应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依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这样我们在考察了最不正义的一种人之后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人加以比较,最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究竟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这以后我们便可以或者听信色拉叙马霍斯,走不正义的路,或者相信我们现在的论述,走正义的路了。”〔19〕柏拉图认为,他可以从国家制度的道德品质和个人的道德品质这样两个方面来考察,实际上就是从灵魂意义的德性品质来考察。然而,这里的现实问题是,从道德品质来考察一个或一种现实的城邦共同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城邦共同体中的公民都具有某一种突出的灵魂品质呢?如他认为,斯巴达式的荣誉政体是崇尚军人的勇敢和荣誉,贵族寡头政体则是贪图财富和金钱,而民主政体则是对民众欲望的放纵,因而所有不道德的或非法的欲望都可能表现出来,他们的德性已经一扫而净。最后则是僭主政体。在柏拉图的笔下,僭主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邪恶欲望的暴君,因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德性品质,并且由于他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是神经错乱的疯子,从而成了自己邪恶品质的最不幸的受害者。柏拉图所设想的这样四种等级政体,因为没有了理性的内在支配,从而都是不正义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生活的人都只具有不正义的品质。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当我们这样提到一个社会共同体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在某种政体下,100%的人都完全具有同样的心理品质或德性品质呢?在任何邪恶的政体之下,都可能会出现反叛者、革命者,而我们不可能把这样的人归于具有与邪恶政体相同品质的人。尤其是,对于僭主政体,柏拉图仅仅着重描述了作为无法无天的僭主暴君的黑暗内心。然而,这样的暴君根本不能代表在暴君统治下的所有国民的道德品质或精神品质。柏拉图的描述只是表达了柏拉图内心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没有理性支配或主导,欲望或情欲的一步步放纵只会导致越来越大的不幸。在如此多漏洞的论证中,正义与不正义同样也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柏拉图的《国家篇》以正义为基本主题,但却为人们留下了一份未竟的答卷:正义本身或正义的本性是什么?正义是功能概念吗?正义的功能是智者们所说的,还是柏拉图所说的?柏拉图式的德性要素建构的正义是成功的吗?如果它不成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柏拉图式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