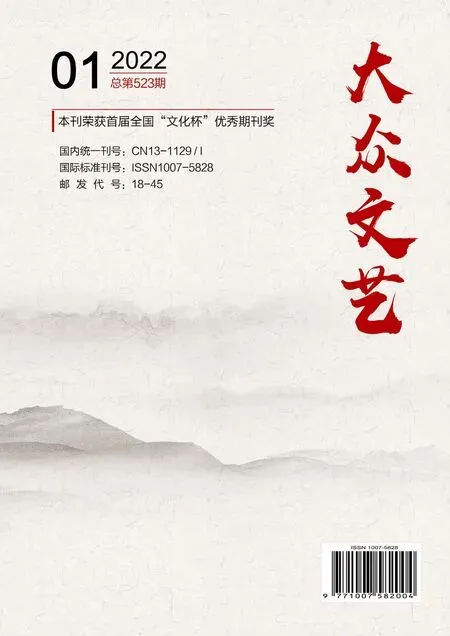病房、监狱与战场
——从薛忆沩《空巢》看老妇人的三重空间体验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510006)
薛忆沩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巢》,以电信诈骗事件揭开帷幕,以空巢老人为主角,用一天的时间维度承载一生的生命力度,上演了一场触目惊心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事实上,《空巢》更倾向是一桩精神事件,它着眼于老妇人介入诈骗风波后愈演愈烈的恐惧焦灼以及无处安妥的孤独与困厄。小说中“病房”和“监狱”空间形成对抗的“战场”意义生成并逐渐强化,最终指向救赎。那么,“病房”“监狱”“战场”三重空间是如何生成并有何联系?老妇人在三重空间里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情感体验,于她而言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与启示,最终指向了怎样的旨归,这将是本文提出并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病房——焦虑与孤独
小说借助顾警官的一通电话,引出了一桩当下社会司空见惯的电信诈骗事件,而老妇人在卷入这场诈骗电话后一天的行动经历与心路历程,则呈现的是一桩令人触目惊心的精神事件——老妇人所固守的平衡的生活与心理结构状态被彻底打破,伴随而来的是破碎感、羞耻感与不确定性,而这也进一步将她的恐惧强化为焦虑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指出,“人类遭受这类恐惧总是预言最可怕的所有可能性,解释每种巧合,作为一个邪恶的预兆,认为一种可怕的含义具有所有的不确定性……我将它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病’。”阿兰·德波顿认为,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取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因此,老妇人焦虑的根由,在于“犯罪分子”这一重不可逃遁与改变的身份对她所认同和引以为傲的清白身份形成动摇与威胁,动摇周围的亲人朋友对她的认同,也许她再也无法从别人的目光中获得赞美、同情或支持,只有厌恶与唾弃。
归结来看,病房的空间意义,是基于“空巢老人”和“罪犯”两重身份以及附带的病征所生成的,也可以说,病房意义的生成,为老妇人增多一重身份——病患,相对应地,也必然存在疗救病患的“医者”。针对老妇人陷入诈骗事件后的恐惧与焦虑,诚然这是顾警官设下的圈套,但毋庸置疑他在这场虚张声势的灾难中扮演的是医者的妙手仁心的形象。他准确地抓住了老妇人的弱点,把握她多疑、敏感以及惶恐的“疾病”心理,施于巧妙的疗法,先营造森严恐怖的氛围,确保老妇人在这场骗局的怪圈中没有周旋的空间,使她先入为主地将“罪犯”的身份代入思考逻辑,强化危机情绪,继而以退为进,为老妇人营造有希望洗刷罪名和有退路的假象。“我很快就被这种魔力慑服了。我觉得顾警官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我着想,我对他充满了依赖和信赖。”从骗术看,顾警官未必高明;但从医者的角度看,顾警官进退有度,一举博得了老妇人的信任。与此同时,对于“空巢”所引发的病症核心在于孤独,缓解情绪的关键在于情感的填补与精神的慰藉,无疑,小雷与幻象的母亲完成了这项治疗工作。小雷的出现无异于雪中送炭,让空巢老人感受到了亲生女儿所无法给予的厚实的温存,弥补了内心的遗憾,一定程度冲散了亲生女儿所带给她的难以言状的挫败感。而母亲的出现尽管只是老妇人的幻象,是老妇人一道心理防御机制,但此时她确实为老妇人带来了安定与宽慰,用母性的温存软化了老妇人意念深处惊恐万分又无处安妥的坚冰。实际上,只要有着足够清晰的目的与明确的行动,老妇人“疾病”的痊愈易如反掌,不论由“罪犯”身份所引发的焦虑,亦或由“空巢老人”身份所带来的孤独与困窘,都能找到解脱的路径,走出困厄的境地。然而,顾警官也好,小雷或幻象里的母亲也罢,最终不仅没能使老妇人的病情得到控制,相反她的焦虑与孤独被强化和放大。此时,老妇人的儿女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扮演着老妇人疾病的疗救者这一角色,也在与老妇人频繁的通话中,关注着他们母亲的身心状况。如果老妇人当前的生存体验只是如病房空间一般,为何医者的施救力度与老妇人的病态呈现负相关的悖谬?病房机能的失效背后,暗含着怎样吊诡的元素?
二、监狱——规训与屈从
老妇人是如何在振振有词的“顾警官”面前陷入失语,手足无措?由于顾警官巧妙地作出了匪夷所思的让步,他承认老妇人一定程度也是这桩事件的受害者,而这于老妇人而言是难得的转机,于是她顺着顾警官“退”的引导展开了“进”的行动,看似替自己洗刷罪名,实则逐步沦为诈骗集团的奴隶。无独有偶,老妇人与小雷间的相处亦是呈现着相似的轨迹——“不管小雷向我推荐的那些保健药品和器械对我的身体有没有用,它们能够带给我幸福感。因此我的钱花得痛快、花得开心、花得心甘情愿。”老妇人的心甘情愿固然是源于她对亲情体验的强烈渴求,这隐示着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层权力关系。在福柯“权力/话语”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具有生产性、创造性与渗透性在小说中,权力的施行主体是顾警官与小雷,而老妇人是承压主体。在这种规训权力的运作间,顾警官和小雷与老妇人间形成了是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前者是凝视的主体,后者是凝视的对象,前者在凝视后者的过程中,要求后者要与外部世界、与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与促成犯罪的集团隔离开,顾警官为保证“转账行动”的顺利,美其名为绝密事件,鼓吹它的神圣性与庄严性,让老妇人断绝与身边人的联系,使她处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便于“规训”计划的有效落成。而小雷对待老妇人日益加重的便秘病情,并没有第一时间鼓励她前往医院进行检查,而是不断地鼓吹她的医药产品能多大程度地缓解她的疾病,不厌其烦地营造着药到病除甚至根除的假象,但事实上,她利用老妇人对她的信任,一再地隔绝开患者与正规医疗机构的联系,拖延病情。归结起来,从本质上看,这种由凝视与被凝视所建构起来的规训权力关系,促成了第二重空间——监狱的生成与浮现,也使得老妇人与诈欺分子的结构关系实现了由“病患——医者”向“囚犯——监管者”的转化。
颇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被囚禁者老人与监管者顾警官和小雷的凝视状态是一种囚犯能被监视,但囚犯捕捉不到监管者的真实存在;监管者能借助各种媒介监视囚犯,但他自身不会被看到。约翰·伯格在介绍观看方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中指出,女性把内在于她的“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看作构成其女性身份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是截然不同的因素,通过将自我纳入角色考量与评判的规训体系,女性俨然将自我对象化为一道“景观”,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迎合凝视对象的目光与需求,而不是为了舒展自我。约克·伯格的观点实际成为了老妇人陷入“罪犯”身份风波后怪谬行为的证词,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老妇人在接到顾警官的电话后,会失去身为政治教师乃至常人应有的清醒的判断力,而直接进入“顾警官”所建构的犯罪情境中?只能说,比起这件事本身真实与否的问题,这件事的存在以及大范围地广布所带来的身份危机更让老妇人感到恐惧与无所适从。她所赖以生存的的“一生的清白”的心理基础是需要紧密依赖于亲朋好友对其的接纳与体认,而一旦事件公诸于众,原初平衡而稳定的心理寄托以及她苦心经营与维持的被凝视的形象便会遭到挑战甚至面临颠覆的危险。因而不可否认,在监狱这一空间隐喻中,老妇人无意识地成为了顾警官与小雷的共犯,合谋着一场丧尽天良的“规训”。
三、战场——反思与忏悔
从表面上看,老妇人深陷监狱囹圄无法自拔,实际上,正如福柯所预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权力的博弈必然导向权力的制衡。通过向记忆游走以及沿着现实展开追问,老妇人逐步挣脱着“病房”和“监狱”的桎梏与束缚,在反思中对抗凝视,在忏悔中重返自我。
转账意味着“完战”,而后老妇人的精神开始向“疑战”游走。与前一阶段相比较,她的恐惧感依旧在升级与强化,但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恐慌已由对未知的恐惧转移到对等待的焦灼上。表面上看,她等待的是顾警官的到来,她期待着“顾警官”的来电却又对电话铃声的频频响起抱有强烈的抵触。实际上,站在记忆的尽头往回看,她传递着自己对丈夫、儿女、一个完整意义的家的等待诉求以及一种不复存在的情感体验的念想与企盼。在失约的“顾警官”,与记忆深处里昔日风光无限而今罹患脑瘫的革命组织者、名存实亡的婚姻、远走高飞的一双儿女、热衷网络的妹妹和鳞次栉的现代化符号之间,她等待的是“重返”,是一种与矛盾和解后的归来,是揭开隔膜后的相认。然而,“我们这个已经拆散的家,其实就不应该重新凑合在一起了。”小雷从温顺体贴的“女儿”到无恶不作“诈骗分子”的角色置换,谎言背后更为离其荒谬的骗局的揭露,才是推动老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直接因素,才使她完整地看清了命运的残酷、生存的吊诡以及人性的脆弱,“他们用他们的假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真。”由“疑战”到“悔战”的过程,老妇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实现了质的飞跃,她凭借“出走”的意志与“在路上”的姿态,向着存在的空缺挑战与超越,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展开了通透的追问,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自救。
那么,老妇人在回溯记忆与审思现实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战场”空间,呈现了怎样的景观特征?首先,与薛忆沩的战争系列小说《首战告捷》进行比照,不难发现,《空巢》里的战场,无《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的杀戮,却也处处刀光剑影,触目惊心;无《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的暴虐,却也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无《那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中对宿命循环往复与无可逃遁的渲染,但《空巢》所流露的人性的卑微与惶惑力度也丝毫不弱。因而实际上,空巢某种程度上可以列入薛忆沩的战争小说系列,因为《空巢》呈现的精神事件与《首战告捷》的战争事件都传达了革命的暴力本质,只是后者的暴力手段更多地在于革命者不论在现实亦或历史都难以找到精神的依傍,而前者的暴力图景集中表现为一种以关怀为幌子的规训权力,因而,借助思想与精神的革命出走,老妇人必须要从权力的支配与操控中将自己解救出来,反抗凝视,打破自我景观化的藩篱,重返自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革命的成功。归结起来,战场这一空间意义对老妇人生存与生命的启示,是建立在“凝视”层面的。这里所讲的凝视,不仅限于别有用心的监视,还包含了善意的“看护”或“关怀”成分。从母亲慈蔼的凝视中,老妇人看到了自己与“旧家庭”决裂的历史罪过,但同时也从母亲温婉的宽慰与包容中获得了安抚;从儿子劝导式的凝视中,一方面,她从儿子对她的关怀,以及处理事情的理性与明智上,找回了在女儿那里遗失的母亲角色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在与儿子的对话中,老妇人开始反思顾警官的“凝视”,忏悔着自己的罪过,最终获得醍醐灌顶的彻悟,走出对象化的我,重归主体的我,她虽然被凝视,但她同样掌控着凝视他人的权力,他者便由凝视的主体转变为凝视的对象,纳入“被看”的行列中。“他们用他们的‘假’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真’”,老妇人不再是在骗局中轻易就范的屈服者,她超越了企图凝视她的目光,在迭出不穷的骗局中目睹了真相的残酷,看到了顾警官的假,也透过监狱看到了小雷的真实面目,从被看到看,在凝视权力的流转间,老妇人实现了革命式的反抗,完成了对自我的找寻与重塑。
四、结语
从自以为光明磊落到被迫承受罪与罚,在清白与戴罪间,老妇人完成了一次“空巢老人——罪人——受害者——空巢老人”的身份转移,且在爱与恨、罪与罚、恐慌与焦虑的纠葛间缠绕徘徊,通过与历史和现实、生者与亡灵的对话,拨开惶惑的迷雾,最终抵达思想的觉醒与精神的顿悟。实际上,这样的精神游历轨迹可以对应本文所阐释的三重生存空间——病房、监狱与战场。这三重空间,如同交叉圆视图,相交但不重合。交合的部分,可以理解成一种共享性或对话性,这种特性未必有着明朗的表征,但它潜在的可能性是应当要被剖析和阐释的。比方说,同一个经纬坐标的生存空间,它对老妇人的精神压迫是如同由病房性质过渡并生成监狱性能的?正是因为病房与监狱一种共有的压迫、封闭的场所特征,尽管二者不能等同,病房根本上还是以疗养为主要功能的,而监狱则是规训与改造,但共有的管束性就为交融与潜在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它们并非简单的重叠并现或遵循线性时间的排列逻辑,而是伴随着其空间景观与特征的变化而形成了相互影响、促进与演化的递进式关联,分别呈现着这样的景观特色:病房的疗养性被置换成压迫性,监狱以规训为目的,以凝视为手段,兼具拯救与惩罚的双重性质,而战场的特殊性在毫无硝烟却遍布精神暴力的尖刺,无血腥却千疮百孔。假若将老妇人的受难视为老年人的一次再成长历程,那么病房与监狱的空间体验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代价,而战场是磨难的转机,能为老妇人的精神困境带来突围的曙光,最终实现生命与自我的浴火重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重空间体验所呈现的精神困境外,老妇人的空巢病态还隐含着人性与历史、人性与社会、时代与生存的褶皱。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多大程度抚平了灵魂深处的精神褶皱,在人性与精神向度的开掘上,薛忆沩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才能抵达一种深邃的观照与旷世的悲悯,是《空巢》以及一系列精神写作留给我们,甚至作者本人不可回避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