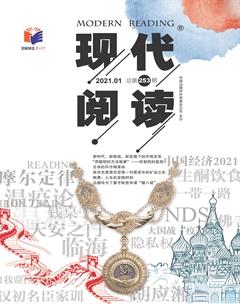普利策获奖新闻《几米的世界》乌龙事件
迈克尔?法夸尔 康怡

报纸上唯一可靠的真新闻只剩广告了。——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那是一个被业内人士称为“天哪”一类的故事,也是令所有新闻从业者垂涎三尺的平地惊雷式爆料。“吉米今年8岁,已经是家里第三代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了。”记者珍妮特·库克在其刊登于《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上的这篇令人揪心的报道中为大家展现了一个幼小的吸毒者的悲惨境遇:“这个惹人怜爱的小男孩有着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水汪汪的棕眼睛,他的胳膊瘦骨嶙峋,娇嫩的棕色皮肤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儿。”
这篇题为《吉米的世界》的文章于1980年9月28日甫一见报,便在美国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读者们不能理解,什么样的母亲才能眼看着同居男友给她的孩子注射海洛因却无动于衷?而隐去当事人身份的《华盛顿邮报》又怎能心安理得地保护这样的人渣?华盛顿警方迅速对小男孩的下落开展了大规模的排查,同时,华盛顿时任市长马利安·巴里也声称市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吉米的真实身份,而且即将对他实施救助。次年4月,这篇深度翔实地记载城市吸毒人群亚文化的文章荣获了普利策奖。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后来《华盛顿邮报》也惊悚地发觉了,那就是《吉米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珍妮特·库克从头到尾都在编故事。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华盛顿邮报》那种身披“水门事件揭露者”光环的业界翘楚怎么能被忽悠得那么彻底?答案出奇的简单:要造成这种重大出版事故只需要编辑部层层审核方面的几个漏洞,再加上“一个万里挑一的骗子”——这是《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本杰明·C.布拉德利对炮制出“吉米”的年轻女子珍妮特·库克的评价。库克获奖没过几天,奖杯在手里还没焐热就被责令退回了。《华盛顿邮报》的独立调查人比尔·格林用1.5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在该报的头版向读者们披露了库克造假的来龙去脉。
对于任何一家追求多样性的媒体,珍妮特·库克都是天选之人——她是一位聪慧机敏、追求上进的黑人女性,于1976年毕业于瓦萨学院,曾经是斐陶斐荣誉学会成员,而且文笔优美、才华横溢。《华盛顿邮报》在1979年把库克从《托雷多刀锋报》挖了过来,以为慧眼识得了新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库克的表现的确没有让人失望。在加入《华盛顿邮报》的头9个月里,她写出了42篇广受好评的新闻稿。在比尔·格林的报告中,库克“在编辑部里显得鹤立鸡群,十分突出”,“她走路从来都是昂首阔步,她一笑起来总能迷倒众生,她的穿着打扮从不重样、永远无可挑剔并且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但是库克的第一任编辑薇薇安·阿普林-布朗利注意到了这个姑娘的另一面:“她的理智被盲目扩张的野心所吞噬,虽然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这种张扬的个性却不足以否定她的才华。”
事件伊始,库克被派去调查华盛顿坊间流传的一种新型海洛因毒品,并搜集了大量翔实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材料。在库克上交的资料中有关于某个海洛因上瘾的孩子的记载。“城市版”编辑米尔顿·科尔曼当场就拍板说:“就是它了!继续深挖,这是头版头条的材料。”两周之后,库克向科尔曼汇报说无法找到那个孩子,但是又过了一周,她声称自己挖出了另一个吸毒的孩子,他就是即将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吉米”。由于科尔曼承诺他手下的记者对采访对象享有保密权,也就没有过问那个孩子的真实姓名或地址。所以,就像格林报道的那样,“编辑对记者必须持有某种程度的信任,这就是新闻业暴露在外的死穴”。
科尔曼对库克确实没有质疑的理由。别的不说,就说资料的详细程度吧,库克在长达13页的手稿里仔细地描述了“吉米”的一切。比如 “(他)穿着一件蓝绿相间的艾佐牌T恤,唉,小可怜儿,那样的T恤我也有6件”。她事无巨细地罗列了这个假想出来的孩子家里客厅的各种零碎摆设,包括一盆橡胶树、窗子上的人造竹条卷帘、棕色的长毛地毯、两盏灯,以及一张金属架镶玻璃台面的咖啡桌。库克的记录里还包括“吉米”上学的学校和他家所在的大致街区。她甚至给科尔曼喂下了另一颗定心丸,对他透露了那孩子的所谓真名——“泰伦”。
编辑部其他各级编审人员也对库克毫不怀疑,于是《吉米的世界》一步一步地朝着出版日进发。“珍妮特写了篇好文章啊!”曾经和卡尔·伯恩斯坦共同报道了“水门事件”载誉而归的“都会版”编辑鲍勃·伍德沃德如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库克本人和那篇报道都完美得不像真的。我曾经亲眼见过她领走一份十分复杂的采编任务,仅仅过了一个钟头她就能交出精彩的稿子。吉米的故事文笔之优美,条理之清晰令人折服,我审稿的时候卸下了心里的警觉,质疑的能力完全下线。从个人角度讲,我的确是大意了。”执行总编布拉德利在《吉米的世界》见报前一周读了文章,当场叫绝,立刻拍板让它在《华盛顿邮报》发行量最大的星期天登上头版头条。于是就像比尔·格林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由于布拉德利大开绿灯,“《吉米的世界》带着各种溢美的称赞冲过了固若金汤的最后一道关卡”。
就在《吉米的世界》见报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编辑室里关于该篇报道的真实性也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由于警方搜寻了数日也未能确定吉米的下落,编辑科尔曼感到一丝不安。同社记者科特兰·米尔洛伊曾开车拉着库克四处寻找吉米的住所,但库克却语焉不详,最后也没有找到,于是他也开始对库克产生了怀疑。在编辑部之外,质疑之声也日渐高涨。市长巴里声称:“我听说那个故事真假参半。我们都觉得不论是吉米的母亲还是给吉米注射海洛因的人都不太可能当着新闻记者的面儿扎针。”
即便是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华盛顿邮报》仍然把《吉米的世界》送选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1981年4月13日,按照布拉德利在自传中的说法:“《吉米的世界》荣获了普利策奖,万事休矣。”由谎言编织成的故事在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压力之下开始不攻自破。各大媒体对库克获奖一事进行的详细报道使得她在个人资历方面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开始浮出水面,并最终引起了《华盛顿邮报》的关注。
很快,人们就发现不论是库克在1979年递交给《华盛顿邮报》的简历,还是她后来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的个人资料都存在虚假内容。她在材料中吹嘘自己能够驾驭4门语言,于1976年在瓦萨学院以极优等学士的身份毕业,1975年在索邦学院游学进修,还在1977年取得了托雷多大学的硕士学位。但是《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此时发现以上所有都是假的。库克仅在瓦萨学院读过一年书,也从来没进过索邦学院和托雷多大学。
最后,珍妮特·库克在重压之下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吉米的世界》系我个人杜撰之产物。我从未采访过一位8岁的海洛因吸毒人员。本人于1980年9月28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上述文章存在重大失实内容,我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在此我向《华盛顿邮报》、向整个新闻业、向普利策奖评审机构,以及所有追求真相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至此,我在事实面前提出辞呈。”
被布拉德利称为“个人职業生涯上最不光彩的污点”的库克事件的余波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盛顿邮报》作为一份老字号严肃报纸,其可信度遭到重创,原本就对该报吹毛求疵的人扬扬得意地在一边看热闹,而忠实读者则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震惊。《华盛顿邮报》为此刊发的编辑部声明指出:“所谓的‘吉米的故事及其后续的风波令广大读者感到被本报误导,实际上,同为受害人的本报所有工作人员也对此事件感到强烈愤慨与懊恼。虽然库克小姐的文章纯属虚构,但是对该类型事件的深层次报道,本报将遵循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这种重大失误以后我们将严格杜绝。”
虽然看上去很严重,但是珍妮特·库克事件在新闻史上掀起波澜的飓风里顶多算是一股乱气流。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骗局:历史上的骗子、赝品和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