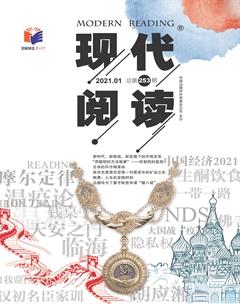在曼利海滩玩滑板
比尔?布莱森 张颖等

悉尼人在英文中被稀奇古怪地唤作Sydney sider(坚决站在悉尼一边的人),他们有着一种显而易见、不屈不挠的欲望向来客展示自己的城市。而这次,又有人友善地提出想做我的导游,她就是《悉尼晨锋报》的记者戴尔德丽·麦肯。戴尔德丽是个活泼开朗的女人,刚刚步入中年,她带着年轻摄影师格伦·亨特到旅馆与我会面。
“我们马上就会散步到环形码头,搭渡轮横穿海港到达悉尼塔瑞噶动物园的码头。我们不参观动物园,只在小悉立斯湾周边逛一逛,向北越过克莱蒙尼一些坡陡林密的小山,到达戴尔德丽的住所,我们在那里会拿上毛巾和布基板,然后驾车去曼利——一个鸟瞰太平洋的海滩郊区城镇。我们会在曼利匆忙解决午饭,接着来一场振奋人心的布基滑板,再擦干身子,奔向——”
“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插嘴说,“到底什么是布基滑板?”
“哦,它很有趣。你会爱上它的。”她轻快地说。不过我觉得她有点儿回避问题。
“好吧,可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项水上运动。乐趣无穷,格伦,对吧?”
“乐趣无穷。”格伦同意道。他正用“所有胶卷有人埋单”的那种架势没完没了地拍着照片。“哔吱、哔吱、哔吱”,他的相机唱着歌,他快速拍下了3张戴尔德丽和我谈话的照片,碰巧3张都一模一样。
“可它到底怎么玩呢?”我锲而不舍。
“你拿上一种小型冲浪板,涉水走进大海,然后你逮着一个大浪头,驾浪回到岸上。挺简单。你会爱上它的。”
“那鲨鱼呢?”我不安地问。
“哦,这里基本没有鲨鱼。格伦,上次有人被鲨鱼咬死是多久之前的事啊?”
“哦,好久啦,”格伦思忖着说,“至少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我尖叫起来。
“至少啊。鲨鱼的危险性被估计得太高了,”格伦又说,“估计得太高了。最可能毁掉你的是离岸流。”他又回去拍照了。
“离岸流?”
“水下的潜流,和海岸成一定角度,有时候会把人冲进大海,”戴尔德丽解释说,“不过别担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儿守护你啊。”她露出安详的微笑,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提醒我们该赶路了。
3个小时之后,其他活动都告一段落,我们站在一处看似偏远的海滩上。此地叫清水滩,在曼利附近。这是个U形大海湾,灌木丛生的低矮山丘环抱着它,广阔而莫测的大海咆哮着,在我看来大得骇人的海浪直涌进来。在不太远的地方,几个有勇无谋的人穿着湿式潜水服,驾浪冲向岩石陆岬上泛着泡沫的激浪;更近一点,星星点点的涉水人被暴躁的波涛不断地吞没,似乎还很开心。
戴尔德丽看上去非常热衷于扎进去喝咸水,她催促着,我们开始脱衣裳——我慢吞吞的,她则心急火燎——她事前就关照我们在衣服里面穿好了泳衣。
“如果你遭遇了离岸流,”戴尔德丽说,“脱险的诀窍就是别惊慌失措。”
我看着她:“你是叫我冷静地淹死?”
“不是不是。只是要你沉着,不要试图逆流游水。拦腰游过它,如果你还没脱险,那就像这样挥挥胳膊——”她這胳膊挥得幅度大而且动作柔缓,只有澳大利亚人才可能认为这是海难临头情况下的合宜反应,“然后等救生员来。”
“如果救生员没看见我,该怎么办?”
“他会看见你的。”
“可如果他没看见呢?”
但戴尔德丽已经夹着布基板,蹚进了碎浪之中。
我忸怩地把汗衫丢在沙滩上,赤裸裸地站着,只穿着松垂的游泳裤。格伦从没在澳大利亚海滩上看见过这样奇形怪状、独树一帜的并且还活着的东西,他抄起相机,兴奋地给我的大肚腩拍特写。“哔吱、哔吱……”,照相机快乐地唱着歌,他跟着我走进碎浪。
让我在此处做个停顿,插入两个小故事。1935年,距我们目前所站位置不远处,一些渔民捕获了一条14英尺(1英尺合0.3048米)长的鲨鱼,并将它带到了库吉海滩上的一家公共水族馆进行展示。鲨鱼在它的新家巡游了一两天,突然间一阵反胃,吐出一条人类胳膊,让参观的人群大吃一惊。这条手臂最后为人所见的时候还长在一个名叫吉米·史密斯的年轻人身上。我敢肯定,他曾经柔缓地大幅度挥动着胳膊表明自己身处危境。
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3年前,一个晴朗平静的周日午后,同样在距此不远的邦迪海滩,不知从何处涌来四波反常的浪涛,每一浪都高达25英尺。退浪回卷,把超过200个人带进大海。所幸当日有50名救生员在岗,他们成功救起了几乎所有人,只有6人罹难。我明白,我们正在讲的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故。我并不在乎。我只是想说明,海洋是个变幻莫测的地方。
我叹着气,一步一拖地走进泛着点点奶油样白沫的浅绿色海水中。这海湾浅得让人不敢相信。我们费力地走出约100英尺,水还仅仅没过膝盖而已,然而即便是在这里,水流也已经异常强劲了——强得足以推你个四脚朝天,如果你不全神戒备的话。再往前50英尺,水上升到腰际,浪头就开花了。我基本上没有一点儿大海的历练。我发现步入时起时落的水中,着实让人惊慌失措。戴尔德丽愉快地尖叫着。
接着,她给我演示怎么玩布基滑板。理论上,玩法简单,让人觉得挺好把握。当一波海浪经过,她就跳到板上,沿着波峰飞掠好多码。然后轮到格伦,他滑得更远。毫无疑问,看起来挺有趣的,看起来也不太难。我怯生生地蠢蠢欲动,想试一把。
我摆好姿势,等第一波海浪过来,然后跳上板,像铁砧一样沉了下去。
“你怎么会这样?”格伦诧异地问。
“不知道。”
我重复练习,结果总是这样。
“真奇怪。”他说。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他们两人看着我一而再地消失在海浪下面,先是偷着乐,再是有点儿惊诧莫名,最后成了不折不扣的同情。我呢,海底大概有艾奥瓦州波克县那么大块地儿都被我蹭过一遍。经过一段有诸多变数的漫长时间之后,我能倒抽着气儿不明就里地浮着漂出4英尺到1.25英里(1英里合1609.344米)远,然后下一浪扑来,立刻又被打入水下。不久之后,海滩上的人们都站定了,在我身上押宝:大家普遍认为我正在做的事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或许因为缺氧吧,我迷失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在我又要沉下去的当口,戴尔德丽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当心有个小蓝。”
格伦立刻面露警觉之色:“哪儿?”
“小蓝是什么东西?”我问道,发觉此处还有自己未被告知的其他危险存在,吓得魂不附体。
“蓝瓶子。”她指着一个小水母解释说(后来我查阅一本大厚书才知道,若没记错该书是《澳大利亚恐怖杀人动物》,第十九卷),这东西在其他地方叫作僧帽水母。我眯着眼睛看它漂过。它看起来并不讨人喜欢,像一个系了带子的蓝色避孕套。
“它危险吗?”我问。
我站在那里,神经脆弱,遍体鳞伤,颤抖着,身上光溜溜的,还被淹得半死不活。不过现在,在我们聆听戴尔德丽对那样的我作出回答之前,先让我直接引用一段她后来发表在《晨锋报》周末杂志上的文章吧!
布莱森和布基板在一股离岸流中被拽到了离海滩40米的地方。他没有读海滩上的警告牌。他也不知道蓝瓶子水母正被吹往他那个方向——现在还差不到一米的距离了——蛰一下能让他痛上20分钟,如果不走运,他的四肢会就此患上看不出表征的过敏反应,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危险?不,”在我们站立着张嘴凝视蓝瓶子的时候,戴尔德丽回答说,“不过别碰它。”
我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饶有趣味的表情。长时间乘坐巴士会不舒服,坐板条木头长椅会不舒服,谈话冷场会不舒服,而被僧帽水母蜇一下——就连美国的艾奥瓦人都知道——会痛。我突然想到,澳大利亚人身处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于是他们就此发展出一整套新的词汇来应对。
“嗨,这儿又有一个。”格伦说。
我们看着另一个漂过。戴尔德丽扫视水面。
“它们有时随波而来,”她说,“我们别在水里待了。”
这话我可不需要别人说两遍哦。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全民发呆的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