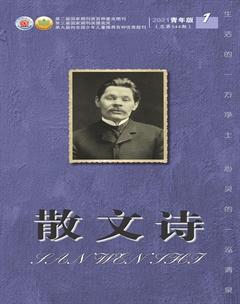一封潦草的信
迷迭香
失去味觉的方言
翻过八月的院墙,爬至木桥边。
青春像面前滑过的水上漂。无痕无迹。
磨盘转动时光的轴线。舔舐过的时光甜饼,在熏黑的中指尖随烟圈消融。
搬动云梯才能钻进往事的被窝。漏风的窗台,讲述十八岁半的青涩。
稻谷变形,风铃走样。
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不断增加册页。
秋日里窃窃私语:蝉鸣荒凉,苞谷结舌。
裹进混泥土里的方言,失去味觉。
走下高空的雨水
圆号和长笛在冬日的最后一个黄昏摁下休止符。它们曾经取笑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
蝙蝠在夜间无声地飞翔,黑暗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就像习惯在水底生长的鱼类,短气流和暴雨天气对它们就像习惯于反常天空中的云朵。
走下高空的雨水,最终倒流进自己的眼睛,变成眼泪。走向废墟园的,是绿得发黑的紫竹和红得发紫的果实。开始沉静。
之后,走向虚空的是盛极一时的庄园。
母亲为我点亮整个世界
桐花一天比一天白。白过五月的白头翁、十月瓦楞上的霜花,和倒春寒里雪花的忧伤。桐籽串联起来的微光中,母亲为我点亮整个世界,父亲用星星做的摇篮挂在我咿咿呀呀的唱腔边。我的梦想锁进童年黑色的罂粟花里,努力地想要爆裂,却又努力地攥紧血色的拳头。外表看起来,我像黑牡丹或黑玫瑰,耸立在人群中,而内心堆积的毒素很难破译出岁月的密码。这世界没有抛弃我,就像散了架的自行车,又重拾信心,更换刹车和轮毂,回到露天的车棚。整个夜晚,在露水中。而白天,它将回到逼仄的车道,缓缓流淌。
一封潦草的信
村口的老井盖上邮戳,至今忘了回家的路。
渐趋枯萎的容颜,我甚至不敢拥抱和亲吻它,像燃烧后的纸张那么脆弱。
且不说好哭的小辣椒属尘土,还是属小猫,属小狗。
它一流泪,河里的石头就滚上山坡。没有了石头的河水,像没有骨头的风筝,想要飞,也飞不高。
软着身子着陆,青苔布满近乎坍塌的村庄。
在乡愁里,从未离开过的老人们撑住星光和房梁。而我是一封从稻草写到潦草的信。
苦 瓜
一出生,它就想着爬出藩篱。爬过七月的火炉、隔夜的苦胆。
总有雨露,像月亮和星星的光一样普灑。
它从生锈的丝网中爬出来,就像从账单里抽掉柴米油盐的借据。
酱醋茶是真实的现实。
它撕掉保鲜膜一样的自尊。
全然不知无人区内同样围墙林立,马路斑驳。
顺着风奔跑,一夜间,白了头发,碎了心。
仅有的一根触须,撞倒南墙也不回头。
黄 昏
他的一生是有层次感的:青葱岁月里白桦树林一样的茂密。说到挺拔,他拔高过自己,又退回到平静的水面,像雷阵雨前的鱼儿一样试着跳跃,却终究没有跃过龙门。雷声治好他结舌的中年。那些慵懒的日子,漫不经心地磨平他想说出的词语:雨水,风车,贝壳。他的鞋底把时间磨得瘦骨嶙峋,他骨头上的棱角也不再分明。这个世界爱过他。他也爱过这个世界。晚霞是他最后的晚餐。他知道,他将去向哪里,虽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灵魂分离。一部分留在身后。他看着另一部分在摇晃和逼仄的人间奔向火烧云。他想用金属钳夹拢它们,但金属的光线已抵达生锈的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