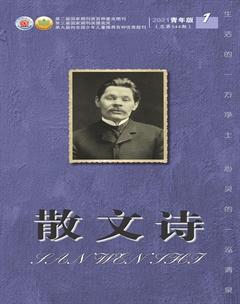青云
马硕
追 驹
白驹过隙。
我还记得上一次在这里分别——我站在银川站对面的马路中央,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沙子迷了眼睛,我看不清前路。
拥挤吵闹的候车室里,我坐在行李箱上。一双双皮鞋和布鞋从面前走过,噔噔哒哒,每双脚跟都沾走一点落日余晖。
室內灯光明亮。窗外,广场上的马兰花永远地盛开着,逐渐被庞大的阴影吞没。
天黑了。三伏天,身边的凉意和喧嚣一浪高过一浪。
你还记得列车驶入黑暗的隧道吗?漫长的寂静。月亮在那个夜晚融化了。而那晚的列车,就这样在轨道上滑行;安静地,不发出任何声音。
——这正是我的二十一岁。
不再有风沙迷眼,我依然眺望前路。
青 云
我从没想到,再次回到家乡,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也从没敢想过,有些已经难以为继、摇摇欲坠的希望,真的会实现——在某个看似平常的白天。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一个电话把我从梦里唤醒,唤入另一场梦中。我想,世界奇妙:理所当然。
生活把我摁在水里,我拼命质问:水里满是氧气,为什么会让人窒息?而当她朝我莞尔一笑,我却愣住了,报以微笑。
那些沉在水底的日子里,身边还漂浮着王勃,和他的不坠青云之志。
如果这只是,青天白云之下的一场大梦,也请至少在今晚,让我梦到些什么——江郎酩酊大醉,随手递给我一支从贺兰山架上取下的毛笔。
龟 图
再次分别,第二日便落了雪。
雪花扬了很远很远吧,不愿落下。
镶嵌在轮胎里,像所有寄生在某一节铁皮车厢里的人一样。
不。我想我应该是一颗晶体,没有风,也不旋转在公路上,而是粘在这座城市温暖的脸上。化成小小的水珠,滴进马兰花里。
小时候,半透明的青山,永远浮在田野与天空的尽头,不远不近。曾给我以同样缥缈的盼望。
我曾经一直走,走到夜里,山却依然浮在边际线上,不远不近。当爷爷终于找到我,跟我说了五个字:望山跑死马。
那时我不懂,在背上泪眼婆娑,一抬头,就看见了漫天星河。
不需要星座,也不需要用龟背占卜,灼烧出的裂纹像掌纹一样握在手心里,图形和符号失去意义。
前路未知。
马兰花都还没有开。
我重返远方的远方,踏上归途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