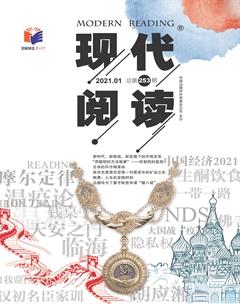论历史的真与美
林中泽
一部理想的历史作品,应当达到真与美的统一。
求真是历史学的最终目标和本质。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虽然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载了不少荒诞不经的传闻,但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信以为真,由此显示出其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本性未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首次将考证的方法引入历史领域,他因而也便成了将求真当作历史撰述目的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早期的教会历史学者,在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也并没有忘记史学的求真本质,例如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便认为在基督教真理与历史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二者完全可以获得高度的统一。在近代的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之后,史学界门派林立,历史理论众说纷纭,可是作为历史学的目标和本质,求真却成了大家的基本共识。中国传统史学虽有过发掘史书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但较为接近求真精神的“直笔”传统,似乎更占主导地位。这说明在求真问题上,中西史学不谋而合。
如果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那么历史学的求真便是科学求真。历史学家的作用与一名诊病医生的作用非常相似。医生的诊治过程一般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为诊断出什么疾病;第二步为探明该病的起因;第三步为对症下药,进行治疗。历史学家却只能迈出两步:第一步是说出或找出历史真相;第二步是弄清这些事实真相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至于第三步,即如何借鉴这些历史真相,并将之服务于现实社会和生活,历史学家则无法越俎代庖,只好留给政治家、政客及其他与现实生活直接相关联的专家们去完成。
显然,历史学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应当是全方位的。历史真相往往包含着善与恶两个方面,历史学不能只揭示其中一个方面,而隐匿另一个方面。例如,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有关“和亲”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唱赞歌,即从促进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大一统汉族政权等“民族大义”的高度去对公主们的壮行作积极的叙述和评价。殊不知,对于当事者而言,一部和亲史实际上是一部放逐史。又如,教科书告诉我们,早期的基督徒具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们在迫害面前,常常为了基督的事业而勇敢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许是历史事实。可是,史料也向我们披露了历史事实的另一面:在一些基督徒争先去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的同时,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以告密、出卖和叛教等卑劣的方式去换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可见,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不应当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就会失之片面。
既然历史的真相是全方位的,历史学家就不能够同时充当道德学家,当然,道德学家也不能兼任历史学家。因为道德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扬善去恶,这意味着在对待历史真相时,道德学家是有所取舍的,这恰恰与历史学的求真原则直接相悖。历史学家既显示善良,又揭示丑恶,只要这些善、恶是历史的真相,就会毫不隐讳地将之公之于世,不管是善行和良政,抑或是恶行和暴政。
如此看来,历史既具有教人为善的功能,也具有诱人作恶的作用,历史教化便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而是道德学家和政治家的义务。虽然历史研究的成果,完全可以被利用来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可是,政治家和道德学家如何断章取义地利用历史资源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可耻的),均应当与历史研究的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历史撰述应当是历史学者独立自主的工作,它除了求真之外,不必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世俗目的。
我们从当前的学术实践中遗憾地发现,某些历史研究者并没有将求真当作是历史学的本质和目标来追求,他们热衷于发扬“六经注我”的传统,采用牵强附会的手段来实现其成名的目的。上个世纪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历史学界开始有人撰写开放的历史,他们竟然把中国的开放追溯到秦汉时期;既然一两千年前的古人已经拥有了如此气魄和智慧,今人的开创之功不就一笔勾销啦,这不是弄巧成拙吗?1992年,有人更是鼓噪开会和出书纪念东晋和尚法显到达美洲1580周年,媒体也趁机大肆炒作,理由竟是法显自传中的“耶婆提”,被他们认定就是美洲,于是法显的“发现新大陆”,便足足比哥伦布早了一千多年!这些选题本身就是虚假的,其研究也自然就变得毫无意义。此外,不少人喜欢用后来才出现的名词术语来指称先前的历史场景,从而导致场景失真。例如,对联是五代时期才出现的现象,有人却误称某一唐诗是“对联”;“广世界”是借助佛经引入汉地的外来词,有人却将其提前使用于秦汉时期的天下格局;歌剧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有人却将其挪用于中世纪欧洲的神迹剧,等等,不一而足。场景失真表面看来似乎无损大局,可是其所导致的时代错位,却与历史的求真本质格格不入,因而也被看作是历史研究之大忌。
既然历史以求真为目的和本质,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作品必定要以枯燥无味和艰涩难懂为特征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相反,成功的历史作品无一例外是美文。如果以“古香古色”来描述历史作品的古典美,那么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鄂图的《双城志》、司马迁的《史记》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的确当之无愧;倘若以“美轮美奂”去形容历史作品的现代美,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确实受之有理。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杰作,把内容上的求真与形式上的求美巧妙地融为一体,几乎达到了臻于完善的程度,这便是它们得以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时至今日,每当我们吟诵起司马迁的“孔子赞”和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讲词”时,那优雅流畅且富有感染力的话语,配合着自然的韵律,在吟者与听者之间必会形成一种唱和交流及互动,最终产生出美不胜收的效果,仿佛又回到了文中的古时场景,这绝对是一次激荡灵魂的精神享受。
众所周知,历史作品中的内容也必须被装进适当的语言框架之内,因此,使用何种语言风格来表达相应的历史事项,就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历史学者的聪明才智。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名语言大师;相反,一名语言能力平淡无奇的撰史者,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如今历史学发展的最大困境是,太多的历史撰述者是语言方面的低能儿,因而便创作不出真与美相统一的优秀历史作品,这就难怪社会大众把阅读当代历史作品视若畏途。事实证明,历史的真与美,是完全可以相得益彰的:美的形式使真的内容更显其真;真的内容则使美的形式更显其美。于是我们就能理解,為何司马迁及修昔底德等人的历史作品,既被用作历史专业学生的读本,又被用作文学专业学生的范文。
至于历史文学,则应另当别论。历史文学(包括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本质上是文学而非历史,因此它就当服从文学的原则,亦即允许合理的虚构。换言之,历史文学基本上不需要遵从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可是,既然这种文学形式贴上了历史的名目,其虚构就必须以一定的历史趋势和背景为依据,否则就不可称作是历史文学。大众评判一部历史文学作品的优劣,除了从情节构思及语言提炼等方面入手之外,更多地是从其所反映的时代是否具备某种真实性方面去考量。如果历史的本质在于求真,那么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求善和求美;可是正如求真的历史离不开美的形式一样,求善和求美的文学也不能完全失真,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当今的文学市场比较多元化,各种穿越时空的无厘头文学作品,迎合了大众的各种趣味,
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涉及相对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品时,创作者仍然应当赋予作品以一定的时代真实感,至少必须设法使读者(观众)“信以为真”,不然就会是败笔。例如在一部反映北宋历史的电视剧中,主人公竟留着刮过之后,新长出来的胡茬子;在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过生日吹红蜡烛和闭目许愿的情景;在一部反映延安抗日青年生活的连续剧中,主要角色赫然留着近年来才开始流行的飞机头,等等。这种胡编乱造既然太过于蔑视读者和观众的智商,它们反过来遭到读者和观众的蔑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秋夜的反思——从历史角度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