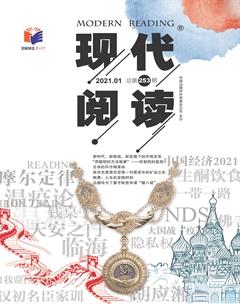徽章的力量
项静


时下文学市场,青春文学作家们往往喜欢铺排华丽而揉捏到位的文艺腔调,孤注一掷坦白给世界看的风格,废话流般让人没有喘息空间的语速,让读者们在集体妄图现实主义的焦虑中放了个风。如果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作品称为小说,小说的本体论任务就在于为我们重新找回昆德拉漂亮地称之为“生命的散文”的东西,而“没有任何事物像生命的散文如此众说纷纭”。
一旦被列入“生命的散文”这样宽泛而没有现成章法的体裁,就会发现这样的小说世界也是丰满而又诱人的。例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部后青春回忆录,是一部掺杂了七情六欲的青春奏鸣曲,“全世界”从作品来看,就是爱情、青春、友情、游历、放荡、豪迈、不羁等等,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到处串场,转身却又不见,有温暖的,有明亮的,有落单的,有疯狂的,有无聊的,也有莫名其妙的,还有信口乱侃、胡说八道的,每一个人之于这个“全世界”来说,都是飘荡的碎片,但它们拒绝成为漫长而有教益的人生故事,它们是“另外的写作”,却未必是另类的。
迈克尔·伍德在论及昆德拉的小说人物时,有一个说法,不管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他们的人生。所有令人难忘的小说人物,既是真实的,也是想象的历史的片段,是搜集起来用语言重新创造的历史的片段,所以他们像我们见过的人,而且比这更好的是,也像我们还没有见到的人。
“他们的需要对我们而言是否真实”这个标准应该有两层意思。首先用英国作家毛姆的话说,可能就是人物的个性,他们的行为应该源于他们的性格,决
不能让读者议论说,某某人决不会干那种事的,相反,要让读者不得不承认,某某人那样做,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次,还是一个“他们是怎样的人”与“他们是谁”之间的差别,很多专注内心的小说一直缠绕的问题是他们是怎样的人,而有纵深感觉的小说才会关注他们是谁的问题。“张嘉佳们”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简单组合一个群落:他们有过微时的落魄,他们说着废话流抵御着生活中的那些伤害、分手或者离婚;他们有过赚钱的幻想,被打击了之后沉迷于游戏;他们爱着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姑娘,用全部的心血和热情,但有的成功共同回忆往事,有的失败完成自我成全;他们爱着自己的狗伙伴,他们知道不是狗离不开他们,而是他们离不开那只狗;他们爱着那些消失了的人、姐姐或者某个让你心动的姑娘;他们离开脚下的土地,去放开那个被捆缚住的自己。他们是一些面目不甚清爽、真实生活着的青年人,他们的生活因为小说的叙述而有了一种戏剧性,但万宗归一,他们就是“那些细碎却美好的存在”。
如果所谓的“历史”是重大事件的话,80后一代人几乎没有进入过“历史”,80后作家往往不是去复制经历过的生活,而是有意识地制造一种历史感,来营造的一种与其说是差强人意的历史感觉,不如说是一种熟悉感。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期这一段时间内,异地恋的校园电话卡这种时光渐逝的见证物,初恋的兵荒马乱的情绪,还有那些具体而又潜藏着共同记忆的生命中的时间制造了一种熟悉感。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可能是来自东北的一个姑娘,可能是江苏的某个小城市男孩,与当代中国电影电视剧中的小镇青年面目相似。他们所归属的是城市中的中等阶级,如今他们有着不差的收入,或者还有一些来历不明无需确证的富二代,他们能够转身就离开困境之地,下个决心就能做到去周游世界。这不是普通凡俗的人可以拥有的选择,他们非常便利地追尋和享用旅行的意义,笃信“美食和风景可以抵抗全世界所有的悲伤和迷惘”。
80后一代兴起的青春文学中看不到太多明晰的文化背景,作品的叙述往往是直白而坦诚的,这些人在流行文化中长养着,并被流行文化塑造了人生和世界,它们是这一代人的文化基础,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基础,也是他们情感共同体的入场券。男欢女爱的模式,对情感的态度,还有自我解脱的方式,戏谑而无奈的语调,基本上都是来自这种流行文化的滋养。
张嘉佳的“全世界”作品不是这个时代的孤例,我们可以推而广之。韩寒的APP“一个”,他的电影《后会无期》,新媒体上的非虚构写作“记载人生”“果仁小说”等;写《谁的青春不迷茫》《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以“坦白说”作为口头语和个人标志,分享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捕获大量在校生拥趸的刘同;《最小说》中厉害的写手安东尼,写作从来不加标点符号,擅长从平淡生活中发现闪光点,来一个看上去完美但又粗糙、简单的生命“解释”。
俄国作家纳博科夫说,风格与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所在。流行文学简单粗浅的风格,机关枪一样的语速,写作者乐在其中,奇异的排比句,句子空洞而炫丽,说过好像没有说过一样,可能他们与读者的快感全在于说出的这个华丽的过程,那些呢喃的话语的确具有按摩治愈的疗效。华丽的语言文字以及唯美的故事容易让人沉迷,以至于我们会暂时搁浅这一代人不言自明的生活语境,憧憬着有一种生活如他们一样绽放或者放浪。他们无一例外都不谈时代的艰难,没有腐败、矿难、贫富差距、自我囚禁、时代板结,没有彻底的绝望,庞然怪物般的空虚,当然他们也很少以正面的方式谈论历史、政治,这些几乎都是一种简单的装饰性背景,毕竟无论写作者如何回避经验都无法抹擦干净历史的痕迹。比如“文革”,以青春文学习惯的“镶嵌”方式出现在一篇故事中,一个老三届的妈妈,教训年轻儿子不敢表白爱情,说“我上山下乡,知青当过,饥荒挨过,这你们没办法体会。但我今儿平安喜乐,没事打几圈牌,早睡早起,你以为凭空得来的心静自然凉?老和尚说终归要见山是山,但你们经历见山不是山了吗?不趁着年轻拔腿就走,去刀山火海,不入世就自以为出世,以为自己是活佛涅槃来的?我的平平淡淡是苦出来的,你们的平平淡淡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女人留不住就不会去追?还把责任推到我老太婆身上!”(《老情书》)。沉重的历史、残酷的往事以一个老太太戏谑的方式拉平到爱情的俗套上,这是时下多数文学的一种通病,只不过有病理深浅的区别。
1947年,阿尔贝·加缪创作了《鼠疫》,在法国文坛引来无数批评,主要批评者还是他的好朋友萨特和波伏瓦。他们认为当一个社会被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能政府制造出来的黑暗笼罩的时候,身处其中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作家,其创作如果不涉及政治和历史立场,不主动担负起深厚的历史责任,不指认(即便是隐喻的形式)罪恶的来源,那么,他的写作就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不道德的。由此推之,如果在一个涌动着无数暗流、贫富差距每天都制造不同故事的时代,不涉及现实,不主动担负起历史责任的写作也同样是不道德的。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这种道德基本是针对严肃文学的,也会在许多偶然时刻,比如通俗文学太招摇过市时,成为挥向它们的定制武器,虽然结果都是各说各话。
无论我们如何谈论通俗流行文学,亦或者避而不谈,都不能阻止这种文学的突然疯狂成长,或者一直成长。销量和影响大到成为现象的此类通俗大众文学,改革开放以后是从琼瑶风靡开始的,历经岑凯伦、安妮宝贝、知音体、读者文、张小娴、连岳、陆琪等,其实我怀疑村上春树、昆德拉也是部分被以通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这个名单上似乎还可以加上王朔、王小波、石康等人,不管是经典作家,还是二流段子手,在大众读者接受的角度上可能都是被扯平了的,都是我们心灵的按摩师。而不得不说的是,现在的流行文学写作者们是一个个定制版的综合体。我们可以在张嘉佳的暖男体小说中时时遇到熟悉的声调、故事,有波拉尼奥式漫游的不羁,有王朔式的痞气,有青春的粗糙杂乱,也有周星驰式的戏谑无厘头,有琼瑶爱情女神的执着,有連岳、陆琪的鸡汤风范,还有韩寒电影中的类似的“没有看过世界,怎么会有世界观”的行动哲学,还有许多其他面目熟悉的二手哲学。总之,他们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慢慢浸染中成长出来的一颗饱满硕大的果实。
每一个文学青年都知道阅读文学名著的重要性,要读经典和名著几乎成为文艺青年的标配,它们是营养和方法。而当下流行的书,都是速朽的。经典是什么?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为此给经典下了定义:“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经典的定义流毒深远,经典几乎成为了精神桀骜的标杆。文学当然也是如此,畅销书这一类文学作品可能是“过分审美”观点之外,与现实最短兵相接的部位。
在严肃文学(或者说杂志、出版社文学)之外,当代中国一直有一批拥趸众多的作家,他们很难说属于通俗文学,但他们属于和鸣最多的作家,他们轻剪人们心翼上的星点,有时候也不过是蹈常习故,但他们始终是体察时代人心的一条明晰的线索。从张嘉佳到刘同、安东尼以及新的微信写作,好像我们都在诉说自己,对忠实地想象他人的生活,失去了兴趣,或者丧失了这种能力。美国文学批评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特别关注美国文学中60年代作品中的坦白趋势,这种趋势试图把文学从某种停滞不前的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使他接近于个体的体验。我们也面临某种停滞不前的文学形式,作家们延续着重新模拟事实发生的世界,并由此模仿前辈作家们的思想承担,并幻想获得道德和责任上的光荣与梦想,对现实发出一种声音。此外,新的文学形式比如说网络小说等以乖张庞杂的形式吸引了大量予取予求的读者。青春文学拒绝、回避承担透视生活的窗口的作用,它是写给自己和同类的,就像公众微信号“记载人生”的口号,“和对的人在一起”。
“唯我一代”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懈怠,过于关注自我,或者缺乏想象力而造成的,但也可能和某种贬低技艺和创新、鼓励自我表达的文化氛围有关。将创作者带入作品,可以消除幻想和对生活的平庸模仿,使得读者听众更加关注形式。坦白式的写作方式,不需要辛辛苦苦地设计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周遭环境,也不需要提出曾经让现实主义小说荣耀一时的历史洞见。莫里斯·迪克斯坦说这些小说的作家“仅仅只是作者自己,而不是就现实和再现的关系提出问题,进行反思。他们没有让我们走到幕后,去看艺术创作的过程,看作品在表述中如何观看自身,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人物,拥有无限可能的神秘和意外,他们只是写作的人: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将那些素材写下来,尽管他们也让故事的主人公陷入爱情与战争,但人物角色只可能生活在作者无处不在的光环之下”。
广袤世界的任何一个为我而存在的地方,都是掷地有声的徽章,散发着它微小而顽强持久的力量。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说,“每个作家都是带着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给予他的安全感来写作,他被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所保护,所支撑”。这当然也是许多流行作家没有选择的选择,写作只能是袖子上的一枚徽章,不会成为一具躯体,但我们能看到它各个角度的闪亮。
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说过自己的任务是探索一种文学记号的历史,因为形式的历史表现了写作与社会历史的深层联系。流行小说、散文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记号,或者是肩膀上徽章,或许正是靠着他们所提示的形式,才会指引下一次文学形式的变革,如果还会有变革的话。小说家卡萨塔尔不只把作家看作艺术家,也看作见证者,看作有偏见、有人性、愿意学习的人,他认为我们需要从关心这个世界的人身上反观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只是关心,也享受这个世界,从唯我一代这种写作倾向的作家身上,似乎看不到对世界的关心,却有享受的热情和耐心。在平滑、鲜亮、炙热、奶白色的光晕之外,伸展的是一片雾气和不安的深渊。但有时候,“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结束的地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