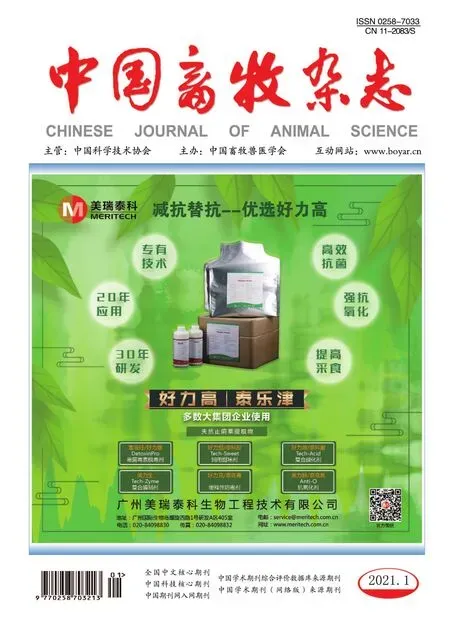胃肠道褪黑素的合成及其对消化道微生物群体影响的研究进展
薛 纯,欧阳佳良,陈培根,王梦芝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褪黑素(Melatonin,MT),即N-乙酰基-5-甲氧基色胺,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大自然的多功能分子,在单细胞生物、植物、真菌和动物中都具有功能活性[1]。MT 是一种吲哚类激素,主要是由机体的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的松果体分泌[2]。松果体作为神经内分泌传感器在光/ 暗周期的黑暗阶段分泌MT,因此,MT 也被称为黑暗激素[3]。研究发现,MT 在抗氧化、调节免疫等方面起重要作用[4]。
有研究发现,胃肠道也能合成分泌大量的MT,并在调控胃肠道动力、炎症和抗氧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5]。动物胃肠道中存在大量共生微生物,部分具有振荡节律的肠道微生物可驱动宿主昼夜节律转录、表观遗传和代谢物振荡[6]。MT 可作为一种信号分子参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通讯,通过释放细胞调节因子来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代谢产物。肠道细菌通过MT 结合位点识别并响应来自肠道的MT 信号,进一步激活肠道免疫细胞的功能[7-8]。MT 通过NF-κB 信号转导协同参与免疫调节,并影响微生物代谢的昼夜时钟[9]。但目前MT 在肠道内进行信号转导的通路尚未明确,了解MT 如何在细菌产生的炎症信号下介导肠黏膜免疫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以及微生物通过何种信号途径参与MT 免疫调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近年来MT 在胃肠道中的分泌合成、昼夜节律性、胃肠道微生物代谢的节律性以及MT 与胃肠道微生物的节律互作影响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阐明MT 与胃肠道微生物群体节律变化提供一定参考。
1 胃肠道MT 的合成与分布
早期研究认为,MT 是由哺乳动物下丘脑视交叉上核(SCN)的松果体合成分泌的一种胺类激素[10]。机体SCN 损伤会丧失昼夜节律,而移植SCN 可以恢复损伤SCN 动物的昼夜节律[11]。SCN 作为机体的核心生物钟系统,可通过多接触交感神经通路抑制或激活松果体合成MT[12-13]。MT 的分泌具昼夜节律性,一般呈现昼低夜高的趋势,在02:00—03:00 分泌量达到峰值[14]。在松果体中,以色氨酸为原料,在色氨酸羟化酶(TPH)作用下转化为5-羟基色氨酸;在5-羟基色氨酸脱羧酶(5-HT-POC)催化下成为5-羟色胺(5-HT);在N-乙酰转移酶(NAT)作用下转化为N-乙酰-5-羟色胺;最后在羟基吲哚-氧位-甲基转移酶(HIOMT)作用下生成MT[14]。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MT 除了由松果体分泌外,在视网膜[15]、皮肤[16]、淋巴细胞[17]、骨髓[18]、胃肠道[19]等组织中也可以被合成分泌。胃肠道是产生MT 的重要场所之一,主要是由胃肠道黏膜的肠嗜铬细胞(Entero Chromaffin Cell,EC)分泌,EC 中含有大量的5-HT 和MT[20]。人类胃肠道 EC 细胞含有大量的MT 受体,且MT 受体含量高于5-HT[21-22]。胃肠道与松果体虽然分泌MT 机制不同,但都具昼夜节律性[23]。胃肠道MT 的合成主要是以色氨酸为原料,在色氨酸羟化酶(TPH)作用下合成5-羟色氨酸;5-羟色氨酸通过芳香族L-氨基酸酶(AADC)脱羧生成5-HT;5-HT分别以2 种途径分泌生成MT:其一,在5-羟色胺-N-乙酰转移酶(SNAT)作用下转化成乙酰5-羟色胺,最后通过N-乙酰血清素-O-甲基转移酶(ASMT)生成MT;其二,5-HT 在ASMT 作用下转化成5-甲氧基色胺,最后在SNAT 作用下生成MT[24]。
在胃肠道不同部位,MT 含量不同。大鼠胃肠道中MT 含量最高的是十二指肠(主要在上皮细胞),回肠中也检测到MT,而空肠几乎不含MT;越接近直肠,MT含量越高(主要在上皮细胞中)[25]。Muoz-Pérez 等[26]在虹鳟鱼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虹鳟鱼食道到后肠不同位置均检测到MT,摘除松果体后发现,胃肠道中仍可以合成MT 且MT 生物合成酶基因aanat1、aanat2和hiomtmRNA 呈节律性表达。这说明一部分胃肠道MT 是不依靠于松果体分泌的,分泌的MT 呈节律性表达。Steful 等[27]在小鼠试验中,通过检测MT 生物合成关键酶SNAT 和HIOMT 的组织特异性表达,在小鼠肠道中发现了MT 合成关键酶的基因表达,其结果说明胃肠道可以通过自身合成分泌MT,进一步维持胃肠道内MT 浓度的稳定性。除了哺乳动物、单胃动物外,在反刍动物胃肠道中也发现MT 的存在。检测奶牛胃肠道各部位MT 含量,发现瘤胃和回肠中MT 含量较其他组织显著升高,说明MT 在反刍动物胃肠道各部位中的水平和分布也具有特异性和差异性[28]。目前,在反刍动物中关于MT 在胃肠道具体的调控机制以及通路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仍需进行大量的研究。
另外有研究发现,动物机体胃肠道中主要有2 种MT 特定受体MT1(MT1a) 和MT2(MT1b),都属于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在纳摩尔范围内具有高亲和力[29]。MT3 是从MT2 分离出的一个假定的强亲和性MT 结合点,是醌还原酶QR(2),与细胞的异种代谢有关[30]。小鼠十二指肠、结肠存在MT1 mRNA转录物[31]及MT2 mRNA 转录物,其中,十二指肠中MT1 mRNA 表达较高;结肠中,MT2 mRNA 表达较高[32]。除十二指肠外,小肠的其他部位也存在MT1 和MT2 mRNA 转录物[33]。人类胃肠道中的直肠、结肠、十二指肠、肌间神经丛、胃肠道血管和胰腺组织均含有MT1、MT2 受体表达[34]。
2 MT 在胃肠道中的生理功能
2.1 调节胃肠道运动 MT 参与调控动物机体采食及消化过程,调节胃肠运动。限制小鼠饮食能够增加小鼠肠道中MT 浓度,禁食可增加小鼠小肠黏膜中EC 数量,从而提高MT 浓度[35]。体外研究发现,添加MT 后,大鼠小肠以及结肠的自发性收缩力减小[36]。通过给小鼠腹腔注射不同剂量的MT,发现低剂量MT 促进小肠运动,而高剂量起抑制作用;非选择性MT 受体拮抗剂Luzindole 可减弱MT 引起的肠肌电活动[37]。由肠黏膜内分泌细胞释放胆囊收缩素(CCK),可激活迷走神经传入纤维末梢上的CCK1 受体,进而启动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反射对胃运动功能的抑制[38]。MT 可激活肠内分泌细胞释放CCK,通过CCK1 受体启动胃排空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抑制[39]。进行MT 治疗后,可恢复被切除松果体大鼠的回肠运动[40]。这些研究表明MT 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了CCK 对肠道运动的调节作用。
2.2 抗氧化作用 MT 作为一种特殊的抗氧化剂,在胃肠道中参与调控胃肠道动力、炎症和抗氧化[41]。MT 在体外具有给电子能力,可减少自由基;MT 除了通过细胞膜上和细胞核内的受体发挥作用外,还可以与潜在的损伤因子直接相互作用[42]。MT 不仅在水溶液中具有清除羟基自由基(·OH)能力[43],在脂质环境中也具自由基清除剂的作用,可以自由通过生理屏障[44]。MT 通过5-甲氧基直接清除·OH、过氧化氢(H2O2)、一氧化氮(NO˙)[45]等氧自由基。在MT 抗氧化联级反应中,MT 清除2 分子·OH 后形成的代谢产物之一是3-羟基褪黑素(C-3-OHM)[46]。有研究表明通过电离辐射刺激大鼠,使大鼠血液产生大量的·OH,尿中C-3-OHM 含量显著增加,表明C-3-OHM 含量可做吲哚胺自由基解毒的指标,MT 可作为·OH 清除剂作用的一个足迹[46]。MT 逐步进行级联反应生成的N1-乙酰基-N2-甲酰基-5-甲氧基犬尿氨酸(AFMK)和N1-乙酰基-5-甲氧基犬尿氨酸(AMK)都是自由基清除剂。这一系列反应大大提高了MT 抗氧化的效果[47]。马玉娥等[48]在黄羽肉鸡饲粮中添加色氨酸,血清中谷胱甘肽过氧化酶(GSH-Px)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谷胱甘肽(GSH)含量和总抗氧化力(T-AOC)升高,说明作为MT 前体物的色氨酸可增强肉种鸡的抗氧化能力。Dan 等[49]通过MT 治疗结肠炎小鼠,小鼠血清中抗坏血酸量显著增加,说明MT 能提高结肠炎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2.3 免疫调节作用 MT 可以通过受体依赖性和非依赖性途径对肠黏膜进行免疫调节。MT 受体依赖性途径有3 种受体参与[50],分别为MT、ROR(孤核受体亚家族,是免疫平衡的重要调节因子)和RZR(维甲酸Z 受体);非依赖性途径存在于细胞质和线粒体中的各种结合域,如钙网蛋白、QR(2)。胃肠道MT 除了清除羟自由基、增强免疫以及抗氧化作用外,还可以增加黏膜血流量和调节粪便含水量等[51]。T 细胞通过与褪黑素受体结合来调节免疫反应,T 细胞含有合成MT 所需的4种酶(AADC、TPH、ASMT 和SNAT)和4 种褪黑素受 体(MT1、MT2、RZRβ和RORα、β、γ),AADC和TPH 参与T 细胞5-HT 的形成[52]。其中,ASMT基因在Th 细胞和细胞毒性T 细胞中强烈表达[53]。SNAT和ASMT 的激活导致大量MT 的释放,ASMT 或TPH的抑制相应降低MT 含量[54]。不仅如此,MT 还能控制T 细胞的活化、分化和增殖,其调节作用包括:降低IFN-γ的产生,抑制Th1 的分化;增加IL-4 和IL-10 的产生,促进Th2 的分化;抑制Th17 细胞的分化[55]。添加MT 可导致淋巴结Th17 细胞数量降低,伴随着一些炎症因子的减少,如IL-1β、IL-6,促进T17 细胞的分化,这表明MT 有助于抗炎作用[56]。
3 胃肠道微生物及其节律性
肠道微生物与宿主健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胃肠道菌群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参与营养物质吸收代谢从而维持机体健康[57]。肠道菌群还有助于形成抗癌免疫反应,有助于更好地治疗某些癌症,如结直肠癌[58]。肠道微生物数量众多,但并非都是有益于机体代谢。研究发现,将患乳房炎的奶牛粪便移植给无菌小鼠,无菌小鼠感染乳房炎,表明某些肠道微生物群也能危害机体健康[59]。
胃肠道在许多生理功能上表现出昼夜节律性。在其每个细胞中,节律性转录程序由核心时钟转录因子网络执行,如周期(Per)、隐色素(cryptochrome)、Bmal和Clock,这些因素控制着昼夜节律启动子处表观遗传标记的节律性变化[60]。通过检测大鼠结肠上皮细胞中节律基因的表达,发现Per1、Per2、Cry1、Bmal1、Clock、Rev erbα、NHE3的表达及Per1、Bmal1蛋白的表达均呈昼夜节律性[61]。除了肠道上皮细胞具有昼夜节律,最近还在哺乳动物胃肠道内发现定植的细菌群落也会经历昼夜振荡,大肠中细菌在定位和分泌代谢物方面都具节律性[62]。肠道微生物呈现出自己的生物钟模式,在关键代谢介质中产生振荡,这些介质被整合到宿主的昼夜节律中,维持代谢内环境的稳定[63]。还有研究证明,真菌和蓝细菌也存在昼夜节律。例如,蓝细菌中的起搏器通过振荡日光信号转导来调节基因表达以及时间细胞分裂[64]。Liang 等[65]在细菌基因组丰度水平上观察野生型小鼠粪便微生物群的昼夜节律,发现雄性小鼠粪便中的细菌总数比雌性小鼠多,但雌性小鼠比雄性小鼠表现出更显著的昼夜振荡;通过16S rRNA 基因拷贝数测量的粪便细菌负荷,发现拟杆菌的绝对丰度在白天波动,而厚壁菌的绝对丰度仅随时间略有波动;另外,蛋白质细菌的绝对丰度是振荡的。此外,有学者利用综合多组学和影像学的方法,证明了肠道微生物群具有振荡的生物地理分布和代谢组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肠道上皮细胞在一天内对不同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的节律性;反过来,这种昼夜微生物行为驱动宿主昼夜节律转录、表观遗传和代谢物振荡[66]。Per1和Per2基因是宿主生物钟的关键组成部分,而Per1和Per2基因被切除后,微生物群节律性大多丧失,删除Bmal1可消除粪便微生物群的昼夜振荡[67]。由此可知,宿主核心时钟中的激活基因(Bmal1)和抑制基因(Per1、Per2)可引起粪便微生物群组成振荡,进一步说明了宿主生物钟与微生物节律性的联系。稳态微生物群节律性的破坏不仅使宿主的正常染色质和转录振荡消失,也会在肠道中激发全基因组的从头振荡,从而影响宿主生理以及对疾病的易感性[66]。
4 MT 与肠道微生物的调控关系
4.1 MT 对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体变化和MT 之间的相互联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Xu等[68]研究发现对雄性小鼠灌注MT 显著降低肠道厚壁菌门(Firmicutes)与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比例,增加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的相对丰度,减少了肠道微生物群的数量,降低了肠道微生物群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明小鼠体内MT 可以通过改变肠胃微生物区系结构从而抑制肥胖,对调节胰岛素抵抗、肝脂肪变性和低级炎症有积极作用。Ren 等[69]比较患结肠炎小鼠和MT 治疗结肠炎小鼠,发现MT 组小鼠的抗氧化能力明显强于结肠炎小鼠,且两试验组微生物最丰富类群发生改变(如乳酸菌的丰度增加),但两组在多样性指数(Shannon 和Simpson)、细菌培养丰度(Chao1 和ACE)和覆盖率(Good's coverage estimator)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此研究结果支持MT 对结肠炎小鼠抗氧化能力和微生物群的调节作用,有助于预防肠道疾病,改善肠道健康。
营养物质显著影响微生物代谢物的产生和规模,微生物代谢物在动物机体的肠道和相关的黏膜免疫系统中大量存在,通常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70]。作为MT 的前体物,色氨酸通过乳酸杆菌代谢,产生吲哚-3-醛,吲哚-3-醛可与芳香烃受体(AHR)结合,然后由含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转运体通过上皮细胞层转运[71]。Tatsuo 等[72]研究发现,Ace2 可控制肠道中性氨基酸水平,其中包括Trp;当小鼠体内Ace2缺乏,可导致肠道炎症易感性增高和肠道微生物组成改变,通过添加色氨酸可以平衡微生物菌群。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膳食纤维发酵产生许多代谢物,其中包括短链脂肪酸(SCFAs)。部分肠道微生物(如属于丁基里维布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和真细菌属的细菌)也可产生SCFAs,并被微生物群利用[73]。微生物产生的SCFAs能够激活腺苷5'-单磷酸活化蛋白激酶,从而诱导线粒体的生成[74]。作为原始需氧多态性细菌后代的线粒体,是真核细胞合成MT 的重要场所[75]。真核细胞代谢产生的SCFAs 介导了许多重要的功能,其中包括为肠上皮细胞供能以及参与T 细胞、调节性T 细胞(Tregs)、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多种免疫信号通路[76]。因此,可以假设MT 作为一种信号,参与肠道微生物群线粒体代谢。
4.2 MT 对肠道微生物调控的机制
4.2.1L-色氨酸(Trp)代谢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人类胃肠道中的产气肠杆菌对胃肠道分泌的MT 敏感,其在群集以及运动模式上表现出昼夜节律性。研究发现,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杆菌,以及实验室培养的大肠杆菌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成群结队的模式(蜂群),而当添加MT 后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培养物中,蜂群数量增加[21]。利用motA启动子驱动luxCDABE 构建,将产气大肠杆菌培养物转化为表达荧光素酶,通过检测培养物发光量发现,未添加MT 的产气肠杆菌的昼夜节律是高度可变的;然而在1 nnmol/L MT 存在下,这些节律的相位同步[77]。证实了产气肠杆菌与NF-κB 依赖性荧光素酶活性的昼夜节律变化相关,产气肠杆菌对MT的敏感性是通过其大规模的蜂群节律变化而表现出来的,表明人类生物钟系统可能通过携带细菌钟来调节其微生物群[78]。因此,推测MT 可能是一个宿主信号,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和介导宿主适应性免疫活动,但其具体调节机制不清晰。
作为营养增强剂的Trp 在维持肠道免疫耐受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研究发现,Trp、内源性Trp 代谢物(酪氨酸、5-HT 和MT)和细菌Trp 代谢物(吲哚、吲哚酸和色胺)对肠道微生物组成、微生物代谢有着深远的影响[79]。其中有1%~2%Trp 通过5-HT 途径转化为5-HT 和MT。通过研究MT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发现,肠道微生物决定Trp 对机体的有效性,其中氨基酸代谢物尤其受到影响。例如,Trp 通过细菌介导,生成含吲哚的生物活性代谢物,其中硫酸吲哚和抗氧化剂吲哚-3-丙酸(IPA)受到影响[80]。IPA 的产生完全依赖于肠道菌群的存在,可以通过产孢梭菌的定植来建立。Trp 在肠道致孢梭状芽孢杆菌和瘤胃球菌共同作用下脱羧生成色胺;吲哚乙酸可以被肠道中的乳酸杆菌、梭状芽孢杆菌、类杆菌等脱羧转化为3-甲基吲哚(图1)。这些研究都表明Trp 及其代谢产物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而Trp 及其代谢物与MT 合成代谢息息相关,因此,MT 有可能通过Trp代谢通路调控肠道微生物。

图1 肠道内与微生物群相关的色氨酸代谢[80]
4.2.2 多种微生物成分 通过NF-κB 和STAT1 等细胞内信号途径参与MT 对免疫系统的调节 包括脂多糖(LPS)和淀粉样β肽(Aβ)在内的多种微生物成分通过NF-κB 和STAT1 等多种细胞内信号途径参与MT 对免疫系统的调节。NF-κB 是NF-κB 亚基家族的一种二聚体,包括常见的二聚体p50、p65(也称为Rel-a)、P52、Rel-c 和Rel-b[81]。活化的NF-κB 二聚体从细胞质转运到细胞核,与靶基因的启动子区(如iNOS 和IL-6)连接,从而刺激NF-κB 二聚体的转录。大多数细菌和TLR(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可以刺激NF-κB 信号通路,改变各种促炎症介质的表达。作为肠道中最主要的革兰氏阴性菌,拟杆菌约占肠道细菌的30%,它可以分泌促炎症神经毒素,包括LPS、毒性蛋白水解肽和Aβ[82]。在松果体中,Aβ激活NF-κB 通路,使腺体产生应激反应,损害MT 产生。Aβ还通过MT 受体MT1 和MT2 来影响MT 信号传导,Aβ显著减少了MT1 结合位点的数量。Aβ对松果体功能的影响是通过诱导和抑制MT 合成来加以影响。这揭示了松果体和MT 系统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Aβ调节MT 受体功能的确切机制[83]。LPS 是革兰氏阴性菌表面的细胞壁成分,LPS 可激活多种细胞内信号通路,如TOLL 样受体刺激NF-κB 下游,从而促进iNOS 热休克蛋白的表达[84]。作为拟杆菌一种的中间芽孢杆菌,从中间芽孢杆菌中提取的LPS 不同于从肠杆菌科(包括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中提取的传统LPS,从中间芽孢杆菌中提取的LPS 可以刺激巨噬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如免疫细胞中的NO 和IL-6。MT 通过减少核移位和抑制NF-κB 的p50 活性,有效地阻断了芽孢杆菌LPS 诱导的NF-κB 信号传导[83]。除NF-κB 外,STAT 信号通路也参与炎症反应。STAT1、STAT2、STAT3、STAT4和STAT6 是STAT 蛋白家族的成员,在调节促炎和抗炎反应中起转录因子的作用[85]。
5 小 结
MT 具有调节机体生物昼夜节律、抗氧化、抗炎症等多种生理作用。近年来,MT 在胃肠道中的生理功能以及对肠道微生物群体的影响备受关注。对其影响消化道微生物群体和代谢的研究已经初步表明,MT 能够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和平衡肠道微生物群体区系结构,有助于预防肠道疾病,改善肠道健康;另外,消化道微生物的组成也会通过影响Trp 代谢产物水平,进而影响消化道MT 代谢水平。然而,对于MT 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体结构及其生物节律影响的规律还都不明了;MT 调控消化道微生物的的受体和通路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同时,微生物影响消化道中MT 代谢水平及其进一步对消化道的反馈作用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阐明,为消化道微生物的研究和改善消化道健康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