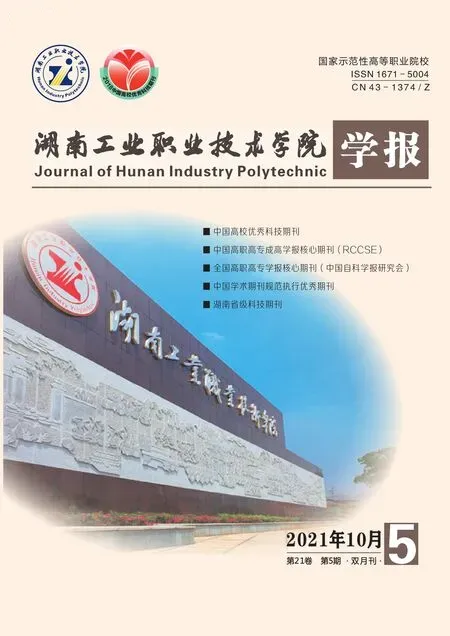政党协商的内涵与价值意蕴分析
孙佳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06)
政党协商是一种有效发挥新型政党制度基本功能的政治制度,也是一项充分发挥各党派优势的协商民主形式。国家治理中,政党协商包容与代表不同阶层、群体多样化的政治表达与利益诉求,巧妙实现了对多元利益的社会整合,夯实了政治共识的思想基础,保障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新时代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政党协商机制的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当共同努力,不仅要加强对政党协商意识的建设,还要加强对政党协商手段和方式的改进,把政党协商这一社会主义政治民主重要优势的价值和意义真实、有效地体现出来[1]。
一、政党协商的地位与内涵
(一)政党协商的地位
政党协商的实践可以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历经联合革命、协商建国到合作治国的历史进程,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推进不断发展、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各党派都能够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应有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与建设。1982年制定并历经1994年、2000年、2004年、2018年四次修改完善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规范不同党派以人民政协为平台,参与到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中,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出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宣示了协商民主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意见和建议,并探索构建健全的民主党派直接向中央提出建议的工作制度[2]。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业已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而这种政治协商已经开始呈现出突破界别性的政协协商、回归到党派性的政党协商路径之趋势。201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界定为“政党协商”,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政党协商”这一概念,并将其摆在协商民主多种渠道之核心环节。随后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15)从概念、内涵、内容、形式、程序、保障机制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有关政党协商的总体要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提出对政党协商要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2021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正式施行,新时代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与政治协商能力提出了新的期望,各党派必然要以更加创新的姿态参与到政党协商的运作中,将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价值体现出来[3]。
(二)政党协商的性质
政党协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4]。这一机制能够让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行使政治权利,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并与执政党互动协作,共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它“代表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推进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化的发展”[5]。
政党协商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从一国政党制度的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政党协商是一种基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它发挥着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间桥梁中介的功能,智慧地照顾与吸纳了不同党派与多元群体的政治利益,巧妙地凝聚社会共识,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体现。从一国民主政治的运作实践分析,政党协商又被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是不同党派实现政治意见交流与统一的政治平台。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政党协商及其所代表的多党合作机制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承担着对各党派、各行业以及各群体之间利益诉求进行协调的使命,最大程度上发挥着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作用,同时贡献了有效的决策咨询功能,业已成为未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6]。
二、政党协商的特点
政党协商因其独特的价值意蕴,在新时代新阶段集中体现出我国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一)主导包容性
为确保政党协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政党协商工作的组织推进发挥直接领导和统领全局的重要作用,其他各民主党派在参与政党协商工作中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基于国家治理中的重大政策与重要议题参与协商活动,并且协商的主题、基本内容、形式等也一般由中国共产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确定。因此,主导性是政党协商的首要属性。
另一方面,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与政治目标下,执政党当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求同存异”的思想,在政党协商中做到虚怀若谷,宽容谦和,集思广益,避免“做样子、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具体操作中,各级党委要支持、鼓励、帮扶各个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到政治协商中,并包容与理解多元主体的意见分歧与利益差异。
(二)平等参与性
新型政党制度拓展国家治理主体,把各民主党派直接吸收到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体系中,以领导-合作的党际关系引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的立体式民主格局。政党协商中,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执政党又居于平等参与的合作地位,在此基础上政党协商又进一步超越了原有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中传统的“咨政”属性,实现了“咨政协商”与“平等协商”的二维统一、“纵向领导与横向平等”的内在统一以及“民主与集中”的内在统一[7]。这一纵横双向性协商民主的模式意味着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肩负起多元主体治理与多向度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因此,平等合作是政党协商的显著特征。
(三)公共合理性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也克服了苏联式一党制的政治垄断,创建了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基础上互利共赢的复合型政党政治,并以其广泛的政治参与优势创造性地消弭了传统的代表制民主之局限性。政党协商作为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政党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应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基石,以公共理性为原则,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当以巨大的利益包容性摆脱政治经验的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则要摆脱团体利益的局限,调整自身偏好;双方都需要以公共利益为皈依,客观陈述理由,合乎逻辑地回应质疑,共画同心圆。因此公共合理性是政党协商的底色。
三、政党协商的价值
新时代新阶段,要以创新理念推进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出一条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道路,政党协商机制的运作在其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肯定政党的主体地位,保障政党权利,实现政党民主
政党之于民主的意义在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那就是政党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工具;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离不开政党,并必然围绕政党而展开。政党协商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8]。它肯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保证了政党权利的发挥,规范了政党权力的行使。更巧妙的是,参政党特有的政治参与方式有力衔接了传统的代表制民主模式与新兴的协商民主模式,真正体现了“民主性是政党最主要的特性”[9],体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对传统的选举式民主模式与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发挥政党的桥梁中介作用,促进民主决策,实现多元治理
政党应具有把社会公众与国家政权有机联系起来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技巧。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特定的联系和发展对象,反映对应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同时从公共性与大局性的角度与执政党平等协商,求同存异。政党协商制度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提出了政治沟通的要求,要求各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协商工作中,通过各方主体之间开放有效的交流,实现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换言之,政党协商机制以党派为组织单位在国家正式制度内为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就国家重要决策发声的平台,让不同党派在这个平台中实现政治沟通;不同的政治意见、建议和政治诉求被平等表达出来,经过公共讨论,被执政党参考、采纳和吸收,从而确保国家各项决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价值和意义。
推进民主决策常态化的政党协商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不断完善,正体现了国家治理由单一治理与单向度治理转入到多元治理与多向度治理的改革与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平等参与到政党协商中;多元主体借助于政党协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度展开政党合作,同时扩大了其所联系的多层次、多领域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
(三)充当利益协调的“安全阀”,增进政治共识,实现社会整合
利益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代表不同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恰恰是政党协商的基本功能之一。借助于政党协商这一规范渠道,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公共利益为基石,理性对话、开放交流,广大人民与各党派及其所联系群众间的差异性诉求得以表达与平衡,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区隔与紧张关系得以协调与缓和,政党协商机制有力地防止了社会分歧被激化趋向分裂,成为体制内合法合理地消弭冲突的“安全阀”[10]。在实现妥协-共赢的基础上,执政党在与民主党派的政党协商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吸纳社会支持,成功将转型社会中各个阶层与社会力量整合进政治体系框架中,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并在这种不断强化的政治认同中潜移默化地增进了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
四、结语
政党协商机制建构了平等合作、开放包容的政党关系,突破了传统的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局限性;它扩大了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克服了传统的代表制民主的弊端。政党协商由此成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中国式创新的本质体现,并被公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渠道。它是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总结,又为当今纷繁复杂的各个民主国家贡献了多元社会中凝聚共识、消除分裂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