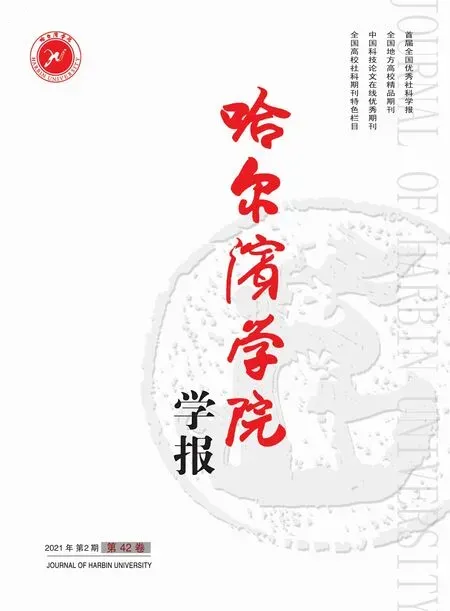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建构与责任承担
何 溪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夫妻关系的隐秘性使得夫妻债务的认定与责任承担易产生分歧,因此该问题一直在学界与实务界饱受争议,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①的规定,使相关争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2月颁布了该解释的补充规定,②但是这一“补丁”做法并未有效制止各界人士对第24条的批判。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简称《夫妻债务纠纷解释》),虽然其将第24条所确立的夫妻债务的认定标准进行了颠覆从而限缩了夫妻债务的范围,但是我国夫妻债务类型体系并没有因此建立。认定标准不明晰导致各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出现因未正确区分夫妻债务类型而判决一方承担不公平责任的现象。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我国夫妻债务类型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夫妻债务认定标准之演变
夫妻债务类型化重构的关键一步是明确认定标准。当夫妻双方任何一方负债牵扯到第三方利益时,不论是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是配偶一方的利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配偶一方从而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结果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举债人与债权人串通损害配偶一方利益的事件。《夫妻债务纠纷解释》则偏向于保护配偶一方的利益。有学者认为,在维护婚姻关系中较弱一方的利益时不应当忽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当将债权人的地位等同或高于举债人无婚状态下的地位。[1]即妥当的在债权人与配偶一方之间分配风险,基于双方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与获益可能性大小来进行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区分,从而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债务认定标准,但是并没有规定“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导致各级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认定标准不统一。与此同时,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通常将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加诸于债权人。鉴于夫妻生活的隐私性,债权人很难进行举证借款确实用于举债方夫妻的共同生活,从而加剧了债权人的参与成本,并有可能出现债权人侵犯夫妻隐私的事件;③债权人的利益因举债方夫妻之间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而受损的事件也屡禁不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所确定的认定标准,使“婚内标准”取代“共同生活标准”。虽然规定了除外情形,但由于实践中符合除外情形的案件并不常见,以至于只要该债务出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经常被当做夫妻债务进行处理。该标准不仅扩大了夫妻债务的外延,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配偶一方,导致实践中出现配偶一方的利益被举债人与债权人恶意损害以及分居期间无辜一方“被巨额负债”的事件。
2018年《夫妻债务纠纷解释》变更了认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婚姻法》第41条的认定标准,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夫妻债务的问题,其认定标准还存在着适用不明确的问题,如“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共同生产经营”标准界定不明确等。
二、夫妻债务类型的认定
一般认为,我国夫妻债务的类型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该种分类法被称为“二分法”。[2]学术界亦将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认定为连带债务,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该思路虽然满足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但不能进一步根据债务产生的原因对用于清偿的责任财产的范围进行限定,从而对配偶一方多有不公。因为此举并不能实现债权人保护与配偶一方保护的平衡,所以该种思路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长久以来,我国受“夫妻一体”观念的影响,倾向于以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来确定夫妻财产的性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婚姻中个人主义崛起,通过单一的身份关系来确定夫妻财产性质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国际流行的婚姻分别财产制看似简单明确,但与我国国情差距甚大。因此,有学者提出夫妻债务的有限责任形态,即在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情形下,举债方承担无限责任,非举债方仅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3-4]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基于这一观点进行审判。④笔者认为,引入有限责任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基于此,可以将夫妻债务分为三种类型,即除了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外有限债务也应被包含在内。[5]
(一)基于双方行为所负债务
“双方行为”主要是指双方基于合意针对某一事件所做出的共同行为,合意表示可以分为明示与推定。首先,明示的意思表示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双方共签、配偶一方口头或书面的事后追认等。推定的意思表示是指通过双方的行为能够推定其具有共同负债的意思表示,如举债方与债权人签订负债协议时,配偶一方在场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举债方所借的款项汇入配偶一方所掌握的银行账户等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明知且没有表示反对的情形。双方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可以分为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针对意定之债,应当基于夫妻双方的约定来判断所负债务是连带债务还是有限债务。但双方约定不明时,如果认定其所负债务为连带债务,则倾向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如果认定为有限债务,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基于此种情况,如果仅因夫妻双方约定不明则认为其为有限债务,可能会滋生夫妻双方为逃避连带责任而假意约定不明的情况,因此认定为连带债务更有助于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针对法定之债,一般适用《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规则。
(二)基于配偶一方行为所负债务
1.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的规定可见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夫妻债务纠纷解释》第2条。日常家事为夫妻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其代理权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基于此可以推定配偶一方同意而无需其事后追认,其行为后果及于另一方配偶。最高人民法院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解释是家庭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方面的消费。[6]由此可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立足于“必要”两字,是依据一般生活经验的必要开支。一般而言,如果配偶一方的举债目的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其所负债务应认定为连带债务,但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可能高消费问题上有较大分歧。如果因此类问题而进行日常花销,应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但是遇到子女外出留学、老人重大疾病等大额支出项是否符合“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则需要根据其他客观标准来认定。
2.用于“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的外延比“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大,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等也被认为包含在“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内。[7](P273)因此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形通常具有金额高、支出方式多样等特点。如果举债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除了需要考虑负债是否用于“共同生活”,还要考虑是否获得夫妻合意以及该举债行为是否具有使家庭受益的可能性,即获得“家庭利益”。若配偶一方直接或间接从中获得利益,则可认定为该笔债务用于“共同生活”。若不考虑配偶一方的受益可能性,有可能过于倾斜保护债权人利益而使得配偶一方的权益不受保护,易增加家庭生活的风险。[8]当然,潜在的家庭利益也被认为是“家庭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若不存在使家庭获益的可能,则该债务应当被认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如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进行担保产生的债务。因为对外担保的法律行为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不存在使家庭受益的可能性,配偶一方若是为此承担清偿责任,将违背债的相对性。如果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经夫妻合意并获得了家庭利益,该债务的定性可以同上述“基于双方行为所负债务”,被认定为连带债务。但是,如果一方的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有获得家庭利益的可能性但未经夫妻合意,该债务的性质应该如何认定?例如,举债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花巨额贷款为家人购买住宅,此举完全有使配偶另一方获益的可能性,但是依据每个人的消费观念、生活习惯等不同,配偶一方完全有可能不同意背负巨额债务用于购买房产,那么此时应当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表见代理可以适用于夫妻债务之中,只要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且形成了举债方夫妻合意的外观并受债权人的信赖,该债务就可以按照连带债务进行处理。⑤也有学者认为,表见代理并不适用于夫妻债务中,夫妻关系的隐秘性、伦理性等导致影响因素众多使得其与民商事交易行为差别巨大而无法进行类型化。[9]笔者也认为不应适用表见代理以此认定为连带债务,而应当基于配偶一方的有限责任,将该债务认定为有限债务。除此之外,对于夫妻一方所生的法定之债,如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也应采纳“间接利益说”,从而判定其是否为夫妻债务。例如,配偶一方斗殴等所负的侵权之债应为其个人债务,因为该侵权行为不能带来家庭利益。
三、夫妻债务的责任承担
夫妻债务的责任承担归根到底是责任财产的承担。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所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有财产制,夫妻双方在婚后所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因此形成了财产一体化的外观。但夫妻共同体即家庭(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除外)并不是法定的民事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因此家庭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属性。基于此,夫妻共同财产的整体并不是归属于“夫妻共同体”即家庭,而是属于夫妻双方。但是,基于“资产分割原理”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拥有体现在抽象的份额之上,而不是体现在有体物的拥有上,因此使得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有所分别。[10]在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从各自的概括财产中分割出一部分而组成。在婚姻正常存续状态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是抽象的份额。当夫妻债务被认定为连带债务时,理应以夫妻间的共同财产及双方的个人财产进行清偿。当夫妻债务被认定为有限债务时,用于清偿的财产范围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夫妻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与获益可得性,由举债方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以其个人财产与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为限用于清偿债务是具有正当性的。与此相反,配偶一方基于有限责任,如果让其以个人财产用于清偿是不符合常理的,[4]其所需承担的责任财产应当以其拥有的共同财产里的潜在份额为限。在承担责任之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5条赋予配偶一方向举债方进行追偿的权利。
当夫妻债务被认定为是举债方的个人债务时,此时与配偶一方无关,举债方个人的财产应当用于清偿。因为举债方个人的财产由其个人财产与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这两部分构成,所以在清偿过程中,为了获得完全的清偿有可能会出现债权人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求获得举债方所有的潜在份额。如若举债方夫妻之间已经离婚,则不存在此种问题。但是债权人如何在举债方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其夫妻共同财产以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为了避免对夫妻共同体的破坏,《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无重大事由不能随意请求分割其共有财产。有学者认为,对第4条所列“重大事由”应做扩大解释为“只要夫妻一方的负债损害了另一方利益,则另一方就具有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正当性”,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诉求。[9]笔者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允许分割共同财产这一做法既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障,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举债方婚姻关系的稳定。除分割共同财产用于清偿的途径之外,配偶一方也可以代举债方进行债务清偿,事后再向其追偿以实现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四、结语
基于有限责任的引进,夫妻债务依据用途、双方合意、利益可得性等因素不同可以分为连带债务、有限债务、个人债务。债务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用于承担的责任财产也有所不同。夫妻共同财产与双方的个人财产构成了连带债务的责任财产承担范围;有限债务的责任财产包括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与夫妻全部共同财产;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理所应当由举债方个人的财产组成。由于家庭生活的繁琐多变导致其影响因素多样,关于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建构,只有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才能构建一个明确的体系。因此,本文仅提出一个基本的框架,以改变现有法律“两分法”的不足。
注释:
①《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25号。
④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民再提字第0057号;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7民终829号等。
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