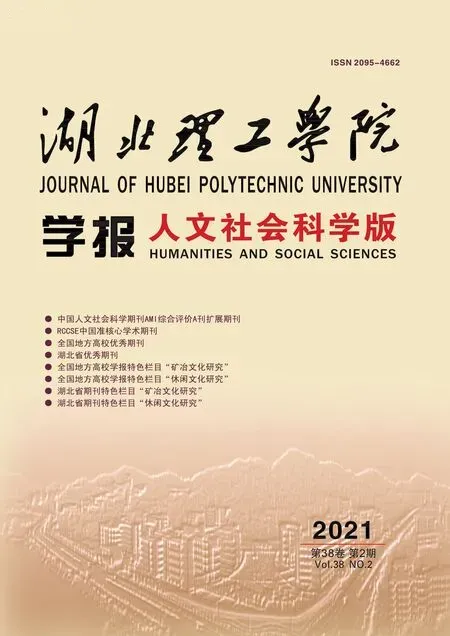“传奇”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从《穗儿红》《潘七爷》《垢壶》管窥胡金洲小小说艺术之魅
张治国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胡金洲,男,笔名金鼎,1945年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2013年入选《中国小说家大辞典》。迄今已在全国知名报刊发表小小说500余篇,出版《绝活》《唱棋》《打蝴蝶结的红皮鞋》等小说集多部。其作品多篇入选《小小说选刊》《中国微型小说选刊》《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精萃》《名家精品小小说选》等选刊选集,多次入选中国年度小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入选全国或地方中学语文教材;荣获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优秀奖、中国当代小说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其作品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多篇小小说随选集入藏美国、加拿大国家图书馆。经过近四十年的深耕细作,胡金洲先生已然成为全国小小说领域的领军者之一。
2020年2月14日,其原创新作《穗儿红》及昔日佳构《潘七爷》《垢壶》等三篇作品,以“集束”方式呈现于当下大陆最具人气和文坛影响力的原创小小说网络传播平台《活字纪》“重磅推介”栏目,让受众对这位年逾七旬老作家的独到审美眼光和深厚艺术功力有了更为真切的感知。这三篇作品,题材相异,叙述的聚焦点也各不相同:《潘七爷》重在写人,《穗儿红》重在叙事,《垢壶》重在状物,但艺术风格比较接近,宜作整体观。在笔者看来,这组小说集中体现了胡金洲小小说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魅力:富有传奇性的叙述建构,对鲜活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生动呈现,以及“传奇”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带给受众极具张力的审美体验,圆满实现了小小说咫尺之间涵纳万里之象、以小博大的美学意图,开启了文化审美的新路径。
一、富有传奇性的叙述构建
(一)精彩的传奇故事
三篇小说都讲述了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是作者小小说艺术性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其作品引人入胜的魅力所在。
《穗儿红》讲述了抗战时期鄂西北小镇陶艺匠人智斗侵华日酋的传奇故事:屈旺生于制陶世家,练就了一手烧制“穗儿红”泥壶的绝技,远近闻名。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家中珍藏着一套祖传宝贝:全国独一份的 “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制作精美、功能奇绝的泥茶套壶“九套壶”①。生逢乱世的屈旺凭着处事的机敏与警觉,很快就识破了假扮哈尔滨商人、侵华日军驻南漳谷城先遣队大佐石川的身份,虚与委蛇,将计就计,利用本地山重水复的地理特点,巧设迷魂阵,挫败了日军进犯鄂西北保康、恩施,打通进川通道的阴谋。接着,又施出“狸猫换太子”之计,让九套壶免落日寇之手,为保护中华民族的陶艺文化瑰宝立下了不朽之勋。小说还写了游击队抗击日军的事迹,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传奇色彩。
较之《穗儿红》,《潘七爷》情节更为曲折跌宕,传奇色彩也更加浓烈。小说讲述了清末巫山船夫潘大爷与王爷之女婉云格格的爱情传奇:潘大爷是川江有名的驾船高手,被誉为“捉船之魁”。某日,他在险滩龙头滩捡回了随父离京逃难进川、遭遇水难失怙的十六七岁的小兄弟,认作兄弟,因在潘家六兄弟中排行老七,人称“潘七爷”。三年来,潘大爷对潘七爷护爱有加,潘七爷也随潘大爷练就了一身戏水捉船的硬功夫。辛亥革命爆发后,潘大爷的船队承担了运输军用辎重、装备响应武昌起义川军的重任。潘七爷不顾潘大爷的叱骂,执意上船、拉纤,随船队一同赶路。为避免船队重蹈三年前其父船毁人亡的覆辙,当天夜里,潘七爷独自一人到龙头滩探查水情。返回后警示哥哥们:水情有变,届时一定改左道行船。但潘大爷却固执己见,不听劝告,为悲剧埋下了隐患。翌日一大早,船队重新出发,潘七爷改变潘大爷的安排,将自己驾驶的尾船变为第二条船,为的是“万一有变”,第二条船能代替首船,担负旗船的指挥之责。经过岸上纤夫和船上船工们的戮力配合,船队艰难地逆流而上,终于,潘大爷驾驶的第一条船顺利闯过龙头滩,驶入水面宽阔的右江道。正当潘大爷高举手旗向后面的五条船发出继续前行“旗语”之时,突然,江上冲出一团排天巨浪,“托起船头猛地将船回抛到龙头滩上”②,一瞬间,潘大爷的船便连人带物被巨浪吞噬。目睹惨剧的潘七爷悲痛不已,但他冷静地制止了六爷跳江救兄、自寻死路的莽撞行为,迅速向身后四船发出旗语,引导船队驶入左江道,最后平安到达目的地。当天,得到军火资助的四川宣告脱离清政府。卸罢辎重,潘家五弟兄就要返程寻找潘大爷,却不见了七爷人影。这时,六爷接到了岸上店家送来的七爷的一封书信,才得知相伴三年的小兄弟却是女儿身。原来,潘七爷是满清王爷的女儿婉云格格,因父亲同情变法被朝廷追杀、流落至此。信中婉云真挚地表达了对六兄弟抚养与厚爱自己的感谢之意,以及对潘大爷生死相依的深情。后来,潘氏五兄弟在龙头滩头找到了投江殉情的婉云格格的尸体,并将七弟与失踪大哥的衣冠合葬于龙头滩左岸之上,“碑文以兄长与七弟夫妻合茔而书之”。
整篇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且始终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它既是一首以潘大爷为代表的粗犷无畏、充满血性的劳动者与凶险大自然英勇搏斗的壮美生命赞歌,也是一曲纯洁、朴素、真挚、炽烈、感人肺腑的爱情颂歌。
如果说《穗儿红》是由“九套壶”勾连的抗战传奇,《潘七爷》是人与自然搏击的生命传奇、川江船夫与王爷格格的爱情传奇,那么《垢壶》就是一段关于紫砂壶的传奇。故事发生在当下,以第一人称讲述:父亲有一把祖传紫砂壶,“自祖上把玩此壶之后,我家至今好几代人从来未清洗过茶垢”③,以至于传到父亲手上时,该壶茶垢成团,成为行家眼中的“垢壶”。为把它变成价值连城的“极垢壶”,父亲坚持每天养垢,从不懈怠,乐此不疲。后来,一位大名鼎鼎的陶艺大师慕名前来赏壶,在亲口品尝父亲用垢壶沏泡的茶汤之后,赞叹不已,认定“此壶在中国陶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令父亲十分得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父亲送走大师返回客厅后却惊讶地看到,原本放在桌上自己视为心肝宝贝的垢壶,转眼已变成 “一把毫无垢迹、鲜亮如新的泥壶”——原来,是“我”老婆乘父亲送客的空档,擦拭了茶壶表面的浮尘,清理了经年的茶垢,改变了茶壶的命运,让它褪去了漫漫岁月和痴迷于养垢的主人赋予的沉重“华表”,回归本真,回归自我。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父亲痛心疾首、老泪纵横:全家几代人精心养垢的珍贵成果不仅毁于一旦,且原本指望将它卖个大价钱而一夜暴富的美梦也成了泡影。
(二)传奇性的叙述建构
传奇性故事所产生的好看、耐读的审美效果,得益于作家对叙事艺术、修辞策略的娴熟运用与恰当调度。富有艺术张力的小小说所采用的叙事艺术和修辞策略,落实到具体的艺术手段,就是“省略”和“暗示”:省略是叙事的空缺艺术,而暗示则隐藏在字里行间,将无法省略的重要信息用隐蔽的方式点到为止,当省略和暗示有机地协调之后,小说的艺术韵味自然就会流露出来[1]。
在《穗儿红》中,存在着两条叙事线索:屈旺智斗日酋、保护“穗儿红”九套壶是主线,写得详细、完整;游击队抗击日军是副线,则采用了只写结果、“省略”过程的艺术处理。如游击队在猴头山伏击日军,重创敌人,只用了两句话:“忽然一日,屈旺隐隐约约听见枪声从深山里传来。隔了半天时辰,一群日本兵死的死伤的伤出现在小镇上。”而游击队袭击日军则仅用一句叙事性文字来表现:“日本鬼子的兵营响起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省略处理,造成了事件过程的空缺,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有利于突出主线。两条线索又借助主人公屈旺的叙事视角相互交织,形成一体,并据此揭示了军民团结、同仇御敌的宏大主题,也显示出作者以谈笑从容态度描摹风云变幻的浪漫主义风格。
与《穗儿红》的艺术技法有所不同,《潘七爷》的着力点在于把控叙事节奏,营造情节的张弛效果;采用暗示手法,为事件结果或故事结局埋下伏笔。作品开头用平稳的静态叙事交代故事背景、地点,引出潘大爷、潘七爷两个主要人物,分别介绍其身份、功夫与来历,为情节展开蓄势;在潘家三年,七爷强壮起来,并跟随大哥练就了一身驾船的过硬本领,但六爷不服,欲与老七比试——这成为情节启动的触发点。比试项目为两人各驾一船夜走瞿塘峡。作者用“月黑风高,水流马奔”渲染环境的恶劣与江流的凶险,用“抢过瞿塘峡”的“抢”字突出了行船的惊险,从而构建了第一个情节波澜。接着,作者放缓叙事节奏,回叙七爷三年的生活,表现潘大爷对七爷的照顾与厚爱,既是对文末七爷书信内容的巧妙暗示,也使之成为高潮前的缓冲和过渡。潘大爷率领运送援川军用辎重的船队逆水经过龙头滩,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对其过程的描写也成为小说最精彩的片段。首先,作者用“早三坨晚三坨,龙头扬起冇得活”的当地民谚来突出龙头滩的凶险;接着,用潘七爷“明天有你们好哭的”一句谶语预示结果的悲剧性。待船队接近龙头滩时,作品写道:
七弟兄上岸拉纤。潘大爷大声吆喝:龙王爷!保佑啰!潘家兄弟闯滩啰!众人呵嗨嗨!呵嗨嗨!扯开喉咙,吼起川江号子:举义旗,应武昌,剪长辫,得解放……嗨呦,嗨呦!高亢之音在江面上回荡播扬。一群银色江鸡前后相随,上下翻飞,翙翙其羽,久久不去。
过了龙头滩,潘大爷重新上船复行右江道,右江道水面宽阔。潘大爷高举手旗,发出旗语:继续前行。突然间,江上一个回流窝出,接着水柱趵突,似巨擘出水,托起船头猛地将船回抛到龙头滩上……随之,连人带物吞噬腹中,如龙激流翻滚着席卷而去……
第一段为场景描写,展现的场面十分壮观,潘大爷的吆喝声、众人扯嗓吼起的川江号子声、天空江鸡上下翻飞的“翙翙”振翅声连成一片,汇成了一首气势磅礴、壮美激越的生命交响曲;第二段为环境描写,将大自然狂野、乖戾的毁灭性力量渲染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潘七爷》的暗示手法,主要见于对潘七爷的刻画上,共有四处。第一处是肖像描写:“七爷个小,白净,细眉大眼,像个女娃”;第二处是“自被收留的那日起,一直独处一室,从不与六位哥哥同居”;第三处是“潘七爷来潘家三年却从没赤着脚板趟过一次刀一般的石滩,肩膀依然白皮细肉一堆”;第四处是潘七爷查探过龙头滩水情后向正熟睡的六兄弟报警,六个人“个个赤身而起”,潘七爷则“侧过脸”与他们说话。小说结尾通过一封书信解开了潘七爷原是女儿身的性别之谜,产生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而这些暗示性文字则为“意外”提供了合情合理的逻辑依据,显示了作家构思的新奇巧妙。总之,省略与暗示手法的运用,赋予了《潘七爷》故事情节的传奇色彩,给予读者强烈的感情冲击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增强了文本的艺术张力。
《垢壶》在叙事艺术上,对暗示与省略技巧的运用也十分熟稔得当。暗示部分体现在对“我”老婆职业的介绍和与家人关系的展现。她“是某大医院的护士”,不难想象,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决定了她比一般人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看重家人的个人卫生和身体健康。事实正是这样,在她的影响下,“我”和父亲戒了烟、酒。不仅如此,“她见父亲手指甲内窝有甲垢,拿起小剪刀,抓起他的一双手剪了起来……感动得父亲当时差点落下泪来”。这处细节描写,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为的是突出她孝顺老人的家庭美德;而从小说修辞角度看,则显然是为了强化其职业身份、为其后来的“毁货”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支持,即出于叙事技术与艺术效果的考虑。而省略的运用则体现在,当父亲发现垢壶变成普通泥壶,气急败坏地质问“这是谁干的”之时,“我”老婆“爸,是我。不干净吗”的一句“娇嗔”回答。这里,作者明确交代了“我”老婆是“肇事”者,却悬置了人物的施事心理和行为过程。省略,造成了叙事空白,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而读者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生活常识,依据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结合小说暗示性叙述,做出相应的推测,从而实现对人物心理动机和行为过程的合理还原:如前所述,“我”老婆是医务工作者,讲卫生、重健康是她的“职业病”,也是她的生活方式。因此,她无法接受父亲指甲的污垢,所以才主动地为他剪去垢甲。她也无法认同父亲“垢越厚实,茶垢越发香甜”的理论——在她的职业认知中,积满茶垢的茶壶易生细菌,用垢壶饮茶有害健康,用干净茶壶饮茶才延年益寿。她才不管什么“极垢壶”价值连城的壶道说辞,她才不顾“家有‘极垢’,黄金为垢”的所谓“祖上遗训”呢,干净、健康才是硬道理!因此,她一定会寻找机会去清理垢壶的茶垢。更何况,父亲的“甲垢是养壶垢留下来的”,她必须将垢壶的茶垢清除而后快,以消除污染源。然而,要完成此事谈何容易!父亲是壶痴,“爱此壶如亲生儿郎”。平时对垢壶更是严管死守,“从来不准别人碰摸一下”。每次养垢之后,总是“严严锁进柜内。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掖着” 。这次,大师来家赏壶,“我”老婆终于有了千载难逢的下手机会。于是,乘着父亲出门送客的须臾,她迅速冲进客厅,三下五除二地清除了垢壶里外的污垢,把它变成了“一把毫无垢迹、鲜亮如新的泥壶”,然后,从容退出,站在父亲面前,“一副春风拂面的样子”。由此可见,作者的“省略”手法有着重要的叙事意义,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张力。同时,人物的“毁货”行为,不仅改变了这把紫砂壶的命运,具有某种传奇意味,也造成了情节的陡转,导致父亲由“兴冲冲”到“气急败坏”的情绪失控,具有喜剧色彩。这种审美效果,充分验证了“欧·亨利式结尾”叙事策略的艺术表现力。
二、 鲜活民族文化的生动呈现
胡金洲先生的这三篇小小说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作者对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中那些极具地域性、历史感的鲜活民间文化形态进行了生动描写和艺术观照,既展示了文化之韵、文化之趣、文化之美,也对文化之莠、文化之弊进行了理性反思,对传承、弘扬和优化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雄壮瑰丽的川江船夫文化
《潘七爷》借助回肠荡气的生命传奇、爱情传奇,生动呈现了瑰丽雄伟的川江船夫文化。
船夫文化与特定河流的水道状貌与航运历史、运载工具与操控技艺、物资流通与文化交流相关,航道、船筏、船夫与船歌是其构成要素[2]。受小小说篇幅所限,作者并未对川江船夫文化的构成要素予以全面展示,而是精选了与时代背景、自然环境、人物生活密切相关,有利于演绎情节、塑造性格、表达情感、揭示主题的某些因素,即把航道、船夫、船歌三要素作为观照对象,以实现以少胜多、以一斑窥全豹的美学目标。
川江航运历史悠久,但水运条件十分恶劣。自古以来,千里川江,航道弯曲狭窄,明礁暗石林立,急流险滩无数。小说中引用的当地民谚“早三坨晚三坨,龙头扬起冇得活”,表现的就是龙头滩“三坨石”早晚水情变化无常、“极为藏险”的情况。潘七爷之父船撞龙头滩的船毁人亡事件,六爷与七爷比试驾船功夫“抢过瞿塘峡”的情节,都是对川江航道凶险恶劣的具体化表现。而文中对川江凶险特征的最具现场感和震撼力的呈现,则是对潘大爷被巨浪吞噬的描写:“突然间,江上一个回流窝出,接着水柱趵突,似巨擘出水,托起船头猛地将船回抛到龙头滩上……随之,连人带物吞噬腹中,如龙激流翻滚着席卷而去……”
川江船夫靠行船拉货为生,在民间被喻为“血盆里抓饭吃”。为避祸自保,船夫们需要在劳动实践中传承先辈的生存智慧,练就过硬的驾船本领。对此,小说篇首通过介绍“捉船之魁”潘大爷,对驾船高手的驾船技术要领做了形象解说:“捉船之关键在于把舵,凭眼手腿三种功夫。眼看,看江上急湍缓湍还是左湍右湍,把舵的手便视此而着劲,一双腿始终如船桩一般稳立不动。”
由于航道水情复杂,川江行船绝非一两个功夫高手即可驾驭,而是需要众多船夫的通力配合、分工协作,尤其在逆水行船或航道狭窄的激流险滩之处。通常的情况是,在水中船上,站立船头者为谙熟水情的驾长(船老大),负责行船的组织指挥和领唱号子;处于船尾者为经验丰富的艄公(舵手),负责掌控船只行驶方向;船两边为桡桨船工,负责划桨。在岸上,则为纤夫,负责合力拽船。为聚神凝气,相互配合动作,船上的船工和岸上的纤夫常会在驾长的组织引领下吼唱高亢粗犷的川江号子,场面十分壮观。对此,作品有细腻生动的描写。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所写的川江号子,成为表现川江文化的一大亮点。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被誉为川江文化的“活化石”。川江号子歌词内容极为丰富,多以沿江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船夫生活为题材,尽显川渝风情[3]。文中所写船夫们在船过龙头滩时所唱川江号子“举义旗,应武昌,剪长辫,得解放”,其简短的组织形式和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与传统的川江号子相一致,但内容却是表现辛亥革命的政治事件,以及民众觉悟、盼望翻身解放的政治诉求,充分表现了川江号子的时代性,是对既有文学作品表现川江文化的一种创新。
川江船夫整日与船筏为伍、与江水为伴,生活习性与陆地百姓大相径庭。为减轻累赘和保护衣物,船夫撑船划桨、攀爬峭壁和涉水泅渡尽量少着衣服[4]。尤其是下船纤夫,“因为所行纤道坎坷崎岖,或在山腰仅容人弯腰通行的小道、或在乱石滩衣服不被石头弄破,加之纤道多在人迹罕至的区域,纤夫们的常见打扮就是赤身,在腰间搭一块白帕子,无论春夏秋冬”[3]。对此,作品巧妙地借潘大爷的一句话“大家需改往日赤身习惯,穿鞋抿裤披坎肩”,反映了船夫们常年赤身的生活习性及其异常艰苦的生活状况。
总之,作品对川江船夫文化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具有鲜明地域性、行业性特征文化形态的艺术魅力,拓展了文本内容,也为整篇故事和人物形象涂抹了一道神奇瑰丽的文化色彩。
(二)诗意隽永的陶艺文化
同样是表现民族文化,但与《潘七爷》观照的具有地域行业性、江湖色彩较浓的川江船夫文化不同,《穗儿红》《垢壶》呈现的是更具工艺性、文人气的非遗文化中的一大品类陶文化,分别表现陶文化中的两个分支:泥壶文化,紫砂壶文化。
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十分悠久,其文化构成通常有原材料、胎体颜色、器型、做工、装饰图案等要素。陶器制品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而陶器中的精品即陶制工艺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文学作品将陶制工艺品作为观照对象的美学意义,除了其叙事功能,还在于其文化价值。1984年,邓友梅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烟壶》,一时间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究其原因,在小说中,“烟壶”固然是演绎主人公人生遭际和悲喜命运不可或缺的道具,更重要的它是表征“古月轩”高超民族传统工艺的文化符号。因而,《烟壶》在展示乌世保和聂小轩的生活道路时,从鼻烟壶到烟壶艺术再到古月轩的烧制过程的介绍,“都内蕴着丰富的文物工艺知识和民俗掌故”。因而,该作品的成就,“不仅限于展现破落贵族子弟的生活道路,而且还在于这些生活经历所引带出来的市井风俗和在这市井风俗中而蕴含的历史文化情致和美学意蕴”[5]。由此可见,烟壶虽是小容器、小物件,却蕴藏着历史文化的大乾坤。正如邓友梅所言:“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6]
胡金洲小小说《穗儿红》中的“穗儿红”,是当地人对本地所产的一种具有独特颜色泥茶壶的俗称,也是对所有泥壶的统称、代称。以“穗儿红”作小说篇名,体现了作者既以泥茶壶为情节纽带讲述传奇故事,又将其作为文化观照载体的巧妙构思。该作对泥壶文化的描写,侧重于以下方面。一是泥料:质地“腻而不滑,黏而不润”;二是颜色独特:“壶腹上都有一嘟嘟儿被紫黑两色围绕的红点儿,比大米穗儿小,比小米穗儿大,恰似开镰季节风中摇摆的高粱穗儿”;三是款式:“壶中套壶,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可各自分开,亦可集中在一起。多的据说套了九把壶。壶中最小的一把能左右旋转。小壶盛上水,壶嘴插入外壶,茶水从最外层大壶嘴里流出,滴水不漏”,把陶壶的精巧结构和实用功能表现得十分神奇;四是艺术价值:“上档次的茶壶尿壶每把都刻有图案与文字,或山水草虫,或经文诗词。屈旺祖父那把尿壶就有两句诗:文秀玉璧夜夜满,壶落珠玑时时香。他给自己也烧了一把,上面刻着:夜阑春深通今古,半月如水落玉壶”。精细的描写,诗词的运用,把本来用于盛装人的腌臜排泄物的尿壶的文化韵味及其所承载的文人的诗意情怀表现得极为传神。而九套壶壶腹上镌刻的跋文与诗句,则进一步表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高雅的审美追求。
紫砂壶的文化构成要素与上述陶文化基本相同。《垢壶》对紫砂壶文化的审美观照,尽管也有对其基本文化元素项的展示,如小说开头的一段精细描写:
父亲有一把紫砂壶。祖上传下来的。两个并起来的拳头大小,井篮状。壶上有印章三款,壶盖、壶底、壶把各一,喻意天地人和。壶系上等泥料烧制,硬如铁滑如缎。壶口笼在灯下,通体透亮,一团赭红。
但其表现的重点却是养壶文化,即茶垢文化,或曰垢壶文化,以及由紫砂壶文化衍生而来的茶道文化,避免了与《穗儿红》的雷同,别开生面。
小说中垢壶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承者是“我”父亲。他顽固坚守着“家有‘极垢’,黄金为垢”的祖上遗训,信奉“垢越厚实,茶垢越发香甜”的壶道说辞,一心想着如何把壶中“俗称玉花”的成团状茶垢变成“海绵体”,让自己的垢壶变成“价值连城”的“极垢壶”。为此,他坚持天天为茶壶“养垢”,还总结了一套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的养垢理论(或曰“心经”):“养垢看季节,所谓春垢为金,秋垢为银,夏垢为玉,冬垢为石。春秋养的是垢花,夏冬养的是垢茎。无论春夏秋冬,须一日三养,分早、午、晚三次。但养垢次数不能过频,否则垢花就要枯萎凋零”,云云。以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手指甲里积满污垢。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通过迂腐的父亲形象,展示了可笑甚至病态的“养垢文化”,并借助富有戏剧性和喜剧性的“我”老婆的“除垢”举动,含蓄地否定了有害健康的“垢壶文化”,隐含着作者对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的理性批判。
小说对茶道文化的描写也十分精细:
十分鲜亮的茶具早已摆放在古色古香的四方桌中央。四个比酒盅大一圈的赭红色小茶碗两厢落定,茶钳、茶棒、茶盒、茶巾一应俱全。
大师坐在上首,父亲坐下首。两人寒暄一番之后,他打开柜门,小心翼翼取出垢壶。启壶盖,开茶盒,茶钳夹出一小撮银毫,沏沸水,茶巾拭去壶口周边水珠……
茶具齐备、精美,奉茶者礼节周到,泡茶程序讲究。富有诗意地展现了中国茶道文化的典雅气质和隽永韵味。
综上所述,胡金洲先生的小小说,以精湛的叙事艺术和精当的修辞策略,将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有机融合:传奇为“形”,文化为“神”,“形”“神”兼备,从而圆满实现了小小说咫尺之间涵纳万里之象、以小博大的美学意图。此类“文化传奇”作品,既开启了文学创作上文化审美化的新路径,也打开了文学接受中品鉴传统文化的新窗口,在小小说领域尚不多见,其价值意义值得肯定。
注 释
① 胡金洲《穗儿红》,载于《活字纪》,2020年2月14日。网址:https://www.sohu.com/a/373066922_699210。凡本文引自该文文字,不再标明出处。
② 胡金洲《潘七爷》,载于《襄阳晚报》,2013年5月17日,第4版。凡本文引自该文文字,不再标明出处。
③ 胡金洲《垢壶》,载于《百花园》,2013年第7期。凡本文引自该文文字,不再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