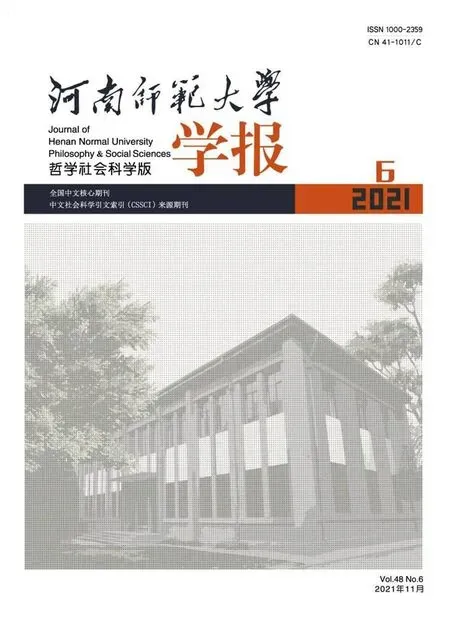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叙事策略及其效果
许 晶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6)
美国后现代消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的初具规模到发展至今,人们对“物”与“商品”的顶礼膜拜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制造欲望或刺激欲望,从而形成一种“炫耀性”消费,此时的消费已不追求物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它们的符号象征价值。毫无疑问,物的“丰盛”之中暗藏着诸如生态、技术、能源、环境及伦理等隐患。在影视、传媒、网络、游戏等冲击下,传统文学写作日渐式微,但后现代作家如海勒、品钦、巴斯及巴塞尔姆等却在不断地尝试进行着新的文学实验:经典改写、元小说、科幻、自动书写,等等。他们试图创新语言的表达形式,利用“新奇”的叙述,期望通过制造出“震惊”的阅读效果,来打破传统小说乏味与平庸的局面。这些文学实验为读者的阅读增加了游戏性、幽默性及讽刺性的成分,但其背后也包含着作家们对于消费文化价值观的质疑,以及对于文学创作前途的焦虑等内容,这些焦虑以小写或大写的形式载入了后现代实验派小说中。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便是后现代文学实验的典型作品。这篇小说戏仿经典童话《白雪公主》,将人物进行了降格化处理,即白雪由公主化身为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罗由“王子”变身为无业游民,小矮人们也被塑造为平庸贪婪与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代表。该作品自发表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人们大多关注它对碎片化叙事、元语言、拼贴戏仿技巧及对无意义的追求,却忽视了这篇小说“为了形式而形式”(1)Nealon, Jeffrey T.Disastrous Aesthetics: Irony, Ethics, and Gender in Barthelme’s Snow White,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2005); Kusnir,Jaroslav.Subversion of myth: high and low cultures in Donald Barthelme’s Snow White and Robert Coover’s Briar Rose,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1(2004); 程锡麟:《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谈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创作》,《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真正用意所在,因为在语言游戏与嘲讽阐释的背后,其实潜含着作家对于消费社会中万物“商品”化的质疑,以及文学产业化之后的焦虑、惶恐和无所适从。本文尝试从身体、碎片与“降格”三个层面探讨巴塞尔姆的叙事技巧,与其背后所隐藏的创作焦虑,具体表现为:白雪的“被凝视——自我凝视——俯视”的身体叙事,反隐喻碎片化叙事,以及反标签化“降格”叙事,力图从人物欲挣脱身份标签与命运摆布的种种努力与徒劳中,揭示人物的命运悲剧、作品的虚无光晕以及作家的焦虑无奈。
一、反凝视的身体叙事
巴塞尔姆将白雪从经典童话故事的叙述情境中拉出来,不仅使她摆脱了男性“救世主”的垂怜,而且利用“俯视”视角来回应男性对她的“凝视”。遗憾的是,这种“俯视”既不足以改变消费社会将女性身体商品化的事实,也不足以消除男性目光的“注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得不发出对于消费社会的无奈和感叹。
在小说中,白雪与其他女性的身体一直是男性凝视的对象,她们是男性目光下的“客体”,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将男性目光内化,并以此开始“自我凝视”,这是用男性视角审视自身的凝视,不管男性在场与否,女性就如同戴上了一副“面具”,这一“面具”呈现的则是男性所期待的女性面容与身姿。这种“自我凝视”是女性将男性目光深度内化的结果,也是女性反凝视的初级阶段。随后,女性开始与男性对视,这种对视并不是平视,更好像是一种俯视,即女性戴着“面具”去审视男性,掌控男性期待,“面具”的后面隐藏的是女性的真实想法与真正“面貌”,她们将男性简化为符号与工具,以期达到某种理想或现实的目的。女性的这种策略可简化为“被凝视——自我凝视——俯视”模式,从中可见女性迂回与折中的反凝视路线。
小说在一开始就将白雪碎片化了。她不是作为整体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以她的“胸、膝、脚、臀及脖子”等身体的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很显然,作为男性注视与欲望的对象,白雪被做了叙述的“转喻”化处理,她被碎片成身体器官,而不是作为整体形象对象或主题来获得她的完整性。男性的目光发挥着“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的“监视”(surveillance)作用,这种凝视使“犯人永远都不知晓他们此刻是否受监控,因而认定自身时时受监视并将这种受监视之感内化”(2)Hawthorn,Jeremy.The Reader as Peeping Tom.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4,p53.。白雪内化了男性凝视后转向自我凝视:“这对乳房,我自己的乳房,理所当然地微微耸出躯干”,“躯干也是迷人的”,“奶油般的腹部!洛可可风格镜子中极漂亮的屁股!然后是特别棒的双腿,包括重要的膝盖。我唯有赞美这美妙的组合”(3)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第174页。。白雪自我凝视的目光是他者的目光,不管他者此刻是否正在注视她,白雪感受到的都是他者的目光,正如萨特对“注视”的阐释,“我的为他人而存在是由他人所决定的。在他者的世界里,我只是一个客体”,“而我的世界被瓦解了,去成就了他的世界”。这便是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我不再是自己,我成为我所不是,我成为他者的某人,而这个某人“不是我自己造就的。这个存在是我的‘为他人而存在’”(4)达伊格尔:《导读萨特》,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93页。。白雪的自我凝视其实是内化了的男性视角,她丢弃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成为“为他者而存在的”存在。然而,这种内化了的凝视却可用来操控男性对女性的预期与印象,是女性“面具”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女性反凝视的开始。
在《白雪公主》中,女性在小矮人们的目光下形成“景观”,她们操控着男性的标准对自身进行评判:“当她们穿着比基尼坐在小汽车前座,耸肩俯身要下来前,或车门已开她们还没有下来时”,“有时能看见一个女人在大热天,只穿比基尼,耸肩变换姿势,挪着她的屁股下车,她甩了甩头发,让它们自然地落下来,所有这一切令人心醉”(5)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87-88页。。女性从自身的姿势、动作及服饰来展现她们的“风度”,她们集“观察者”(surveyor)与“被观察者”(surveyed)于一身,男性对女性的印象、评价与判断取代了后者“原有的自我感觉”,“女子的举手投足——无论其直接目的或动机是什么——也被视为她希望别人如何对待她的暗示”(6)伯格:《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63页。。女性 “耸肩俯身”,及甩动头发的动作都是男性视角内化的表现。女性在渴望被注视的同时,也自我凝视,性感身躯、光泽皮肤与飘逸长发都构成了女性身体的“景观”,这是一种炫耀,一种身体背后性经济的炫耀,此时的身体是一种“符号”,是“幸福、健康、美丽、得意的动物性的可见符号”,它“独自垄断了一切所谓正常的(对其他真实的人的)情感性”,戴上“美好情感”的面具,操纵着观察者的印象及评判(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小说中男性的“俯视”与“窥探”看似高高在上,实则是女性期待的折射。女性以一种“无形之眼”审视男性的行为,她们将身体赋值并功用化,进而掌控男性的情感倾向,这是女性迂回与折中的反凝视路线。
除了“自我凝视”,“俯视”也是女性反凝视的策略之一,白雪用“俯视”回应男性的凝视,在厌倦了矮人们的无聊后,她开始将头发伸出窗外,寻求生活中新的刺激。白雪将长发伸出窗外这一情节其实是结合了另一篇格林故事《长发公主》的内容,“头发”体现了女性的性魅力,吸引着“王子”的到来和命运的改写。艾略特曾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提及海妖用长发与海藻缠住男人,并将他们溺死的场景,头发此时是女人俘获男人的性武器。白雪的长发也是她性猎奇的手段之一,她渴望用“新奇”来改变生活的平庸,此时的她在享受着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性解放”“福利”的同时,也承担着由此而来的社会谴责。因为消费社会要求的是女性的“性”被解放,而不是女性的地位被解放,男性只有把 “性”作为消费品的红利和舒适来享受时,才会宣扬解放女性的“性”。而“实际上,表面上解放了的女性被混同于表面上解放了的身体”。身体、美丽与色情皆在消费社会的意识体系中被出售与贩卖,“性解放的所有社会危害都规定在女性及其身体的概念中”(8)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0-131页。。也就是说,女性通过“性”解放而被“消费”。她们表面上享有了“性”的自由与乐趣,实则被进一步物化和商品化了,女性不仅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反而由此承担起了因“性”解放而来的所有社会危害:颓废与衰败。可以说,巴塞尔姆解放了经典叙事中白雪的身体,却只能任其在消费社会中沦为商品而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是人类面对消费社会商品浪潮狂欢后的真实写照。
白雪将“俯视”等同于优越感和幸福感。她将“头发”作为欲望载体,运用身体符号的神奇,将身体与幸福感、安全感对等,并因此产生了幸福幻影和眩晕之感。此时,白雪意识到女性的身体并不限于物品的经济价值,也存在于“那种贵族式或资产阶级式游手好闲派生出来的名望功能”中,这一意识正源于女性“正式的无用性”才体现出男性名望力的价值(9)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81页。的观念。白雪期待男性竞争者们之间的“角斗”与挑战,但是很多男性或受困于经济地位、道德束缚,或受困于健康风险、社会地位和名誉的顾虑,而只能贪婪地去“仰视”她,这种“仰视”暴露出男性赤裸的欲望。白雪所说的“王子”,也不再是经典童话中拯救公主的宏大形象,反而成了男性权力、地位、金钱及欲望的符码标志。白雪想把男性塑造成心中的“完美形象”,并以此达到俘获男性的目的,这里隐藏的是白雪对男性操纵的快感,是“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10)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45页.。的体现。然而,白雪将欲望符号与幸福感等同,以至于最终迷失在消费社会幸福感的模拟物和符号幻影之中。她在利用身体获取男人的青睐与经济利润的同时,也深陷消费的牢笼之中,她的这种反凝视饱含拜物教色彩,始终没有逃脱被商品化、被男性凝视和物化的命运。巴塞尔姆没有将白雪塑造成社会的“精英”,源于他要打破传统文学俗套的构想,戏谑的口吻、风趣的描述和辛辣的讽刺,打破了传统文学中道德说教与意义追寻的旧有模式,它们以一种“新奇”的叙述形式打破人们思维定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寻找“深层意义”的窠臼,而且具有了使人们重新回到直觉与感官的世界之中,去身临其境般地体验人物的困顿、无奈和失落之情的功能。
二、反隐喻的碎片叙事
巴塞尔姆在《白雪公主》中用了大量的大写单词形成句子,他的这一做法不仅打断了正常的叙述流,而且随意选取一些词汇进行堆积,还形成了一群毫无意义的“辞藻山”。这些中断、无关与偏离的碎片叙事,让巴塞尔姆远离正常的线性叙事和情节构建,这些“异常”的碎片打破了传统的叙事常规,嘲讽了消费社会中经济利润至上及文化产业化的趋势。“辞藻山”中的辞藻堆积如下:“非正式声明 所有权和海关的难处 是你吃惊的是 交换爱 画它 理解没有一分钱的棕色皮肤的孩子 我曾是 土匪帽 昨天的问题在等待 成员 想要藏掉发烧的黏糊糊的清澈牛奶。”(11)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122页。垃圾是城市身体自身循环的排泄物,“辞藻山”是人类的文化排泄物,它没有任何意义,从中挖掘意义是徒劳而可笑的,这是巴塞尔姆对读者期待的戏谑性调侃和对文本过度阐释的嘲讽。面对这堆无法阅读的,随意堆积的文字垃圾,没有任何隐喻所在,读者们既无法吸收,也无法逃避,而是感到恶心或心烦意乱。戏谑与嘲讽的背后是巴塞尔姆对文学无用论的焦虑与失落。“辞藻山”是消费社会中的文字垃圾,巴塞尔姆扮演了“拾荒者”、闲逛者、诗人及作家等多重角色。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写道,“拾垃圾者和诗人——二者都对垃圾感兴趣”,“游荡、寻找韵律的诗人的步态,这也是拾垃圾者的步态,他一路不时地停下来,拾起所碰到的垃圾”(12)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白雪公主》是经典叙事,但其精神意旨早已不符合后现代社会的需求,因为社会“现实已无法承载童话故事的完美结局与英雄人物所需的价值观”(13)MacCaffery, Larry.The Metafictional Muse.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2,p144.。当经典化了的《白雪公主》被当作垃圾而捡拾回来,翻新后再次使用时,其实也就意味着经典的塌陷。英雄被谋杀后以食利者、投机者、流氓等身份返回人间,公主降格为妓女,连作家也沦为商贩,其间的含义正如波德莱尔所说:“为了有鞋穿,她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仁慈的上帝会嘲笑我,向这贱人靠近,/充当伪君子,装作高贵/祈望成为作家而出卖我的思想。”(14)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88页。巴塞尔姆既嘲讽了经典,也揶揄了自身。作家放下了高贵的身段,就像小说中的妓女兜售身体一样贩卖自身的思想,巴塞尔姆在讽刺文化产业中经济目的与利润追逐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文学商品化的屈从与无奈。
文中穿插的大量的黑体字片段,截断了正常的叙事流,其中包含了对狄金森的缅怀,对宗教影响的评价,对弗洛伊德的嘲讽以及对家庭主驸(horsewife)史的胡乱编撰,等等。这些碎片化的叙事与正常叙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全在于巴塞尔姆对文学神圣性不敬、嘲讽的态度,以及他对创作“随意性和虚假性”(15)Kusnir,Jaroslav.Subversion of myth:high and low cultures in Donald Barthelme’s Snow White and Robert Coover’s Briar Rose,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1(2004).的揭露过于主观和片面。巴塞尔姆的确追求文学上的形式创新,但新形式的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未来的惶恐与焦虑,这种焦虑就像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对“新奇”感受表达的那样:“是一种虚幻意象的根源——这种虚幻意象完全属于由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意象。它是那种以不断翻新的时尚为载体的虚假意识的精髓。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那样,这种新奇幻觉也反映在循环往复的幻觉中。”(16)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22页。碎片叙事、经典坍塌以及神圣性丧失都是巴塞尔姆追求文学“新奇”观念的写作体现,表面上是对传统文学的解构,是对文化商品化的嘲讽和揶揄,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一种对文学未来发展的焦虑情绪。如果文学完全拒绝商品化,那么作家该如何谋取生计?如果旧的文学形式已无法吸引现代读者,那么新的碎片化的叙事是否如同人们追求时尚一样短暂,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新颖和别致,是否会沦为下一个“新奇”叙事的牺牲品?甚至,文学如果丢弃了思想深度、道德选择与文艺的重要性,那么是否意味着文学就只是一堆华而不实的语言碎片?这些恐慌与焦虑在《白雪公主》的开篇时便已显现,“焦虑”(anxiety)一词在小说首页竟出现了五次之多,这表明,巴塞尔姆在解构经典的同时,也带着深深的焦虑之情。
三、反标签化的“降格”叙事
“降格”叙事,其实是反-英雄叙事,将白雪、王子、小矮人们经典的身份标签撕除,将他们降格为妓女、乞丐和流氓,起到了一种“震惊”(shock)的审美效果。意大利思想家乔万尼·凡蒂莫认为:“震惊是普遍化交流时代中艺术的创作性所能存留下来的唯一东西”,“艺术焦点已不再是作品,而是体验,一种紧张的、过敏的与兴奋的体验。”(17)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既然艺术不再以作品为终极目标,而是以体验为标准,那么小说也可追求如电影般的感觉刺激,用夸张的人物形象与情节叙事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经典童话版本中,叙述者是这样描绘白雪公主的: “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脸颊像血一样红,头发像乌木一样黑。”(18)Bacchilega, Cristina.Cracking the Mirror Three Re-Vision of Snow White,Boundary 2,15/16(1988).这里的“白”有几层意思,首先,女性的身体必须符合男性欲望的标准,如肤白、大眼、面红、发黑以及身材匀称,等等,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要求;其次,“白”是“纯真”“无知”的代表,指女性思想的贫瘠、空洞与浅薄,正反衬男性智力上的深邃与广博;再次,“白”也指“空白”,指主人公社会经验的缺乏,尤其是性经验。总之,它们是男权话语下的写作,而白雪公主的身体则是由男权话标记了的身体。巴塞尔姆撕掉了经典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身上的标签,将白雪降格为暗娼,这种降格的叙述处理完全“震惊”了读者,其叙述目的就是,将读者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庸俗中拯救出来,迫使他们去感受和体验人物内心的真情实感。
在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中,白雪是一名毕业于“比弗学院”(Beaver College)的普通大学生。Beaver一词在英语中意为“海狸”,俚语中有“女性生殖器、女阴”之意。“比弗学院”隐含着对女性的歧视与嘲讽。白雪的大学课程毫无学术深度,也毫无职能功用,就像是家庭主妇为维系家庭关系、照顾丈夫起居或消磨时光而学习的闲散课程,譬如,《心理学理论基础》《现代妇女:特权与责任》《个人智谋I、II》,等等,课程内容则是“家务、带孩子”,“治疗与奉献”,“一体化和精神健康”(19)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31-32页。,等等。白雪虽然已经逃脱经典叙事的符码标记,但是却无法摆脱消费社会将其物化的命运,因为她的身体仍是男性凝视的目标:“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子后面一颗。它们全长在左边,从上到下,几乎能列成一排。”(20)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1页。对美人痣的关注,停留并沉迷于“局部对象”等叙事,是典型的男性欲望叙事。可以说,将白雪“降格”的叙事把读者从长期的心理麻木和身心疲乏中解救了出来,但问题在于,新叙事没有使人物逃脱被“标记”、被凝视与被束缚的宿命。
保罗由“王子”降格为底层游民,他生活落魄以至于要到修道院去谋生。血统在有闲的上层阶级,尤其在欧洲的贵族中十分受重视,而“闲适”(leisure)更是被当作贵族们“值得的、美丽的或无瑕疵的”人生前提,相反,“劳动”(labor)则是“弱小并屈从主人的”标志,是一个“不名誉的”、“低贱的”和“劣等的”,与“高尚的思想与高贵的生活”不相符(21)Veblen, Thorstei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53,p41-42.的名词或概念。凡勃伦(Veblen)甚至记载,波利尼西亚的部分首领为保持优雅,直至饿死也不自己动手吃食物的事件,事件虽然有些极端,但是却印证了劳动在贵族眼中的无价值性和卑贱性。保罗在《白雪公主》中是一位落魄的贵族后裔,整日无所事事,却将得到“白雪”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和恢复贵族荣耀的契机,“保罗以前从未真正把白雪公主当作女人看”(22)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180页。,他在离白雪房子不远的地方安上了“地下基地”,可以“通过镜子和受过训练的狗长期监视她”(23)巴塞尔姆:《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第189页。。当发现简用毒酒毒害白雪时,便自告奋勇喝下毒酒身亡,试图用“死亡”印证其血统的高贵和行为的英勇。保罗的“英勇”绝不是充满集体主义的“爱国情怀”,也不是为爱而“决斗”的男子气概的显示(24)Veblen, Thorstei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p165-167.,而是为了彰显他的“血统”之名。保罗其实是为他自己而死,为了成全旧贵族的“高尚”与“英勇”而死,他“以爱之名”的死充满了虚伪与荒谬,他内化了旧有的身份标记,成为“旧时代”遗留物,也成为巴塞尔姆文字游戏中演技拙劣的生命符号。
小矮人们也不再是森林中的精灵,他们被降格为普通职员,做着清洁大楼和生产婴儿食品的工作。他们的性格特征模糊不清,是那些典型的观点陈腐、心理阴暗和言语怪异的丈夫们的代表,他们的身材矮小,也是人类精神荒芜、道德低下的象征(25)MacCaffery,Larry.The Metafictional Muse,p142.。小矮人们摆脱了经典叙事中善良可爱的身份标签,化身为陈腐、嫉妒、好逸恶劳的中年男子。他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目特征,这是后现代社会中另一身份标签的象征:没有个性,贪婪好色又庸俗无为。在这里,小矮人们的身体再一次被标签化、商品化、荒谬化和庸俗化,他们也无法逃脱再一次被标签化的命运。
巴塞尔姆解构了传统童话的经典叙事,将时代的气息和灵韵注入了主人公们的生命之中,期待他们能逃脱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命运,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人物迷失在消费社会幸福符号的模拟物中,他们的身体也再次被商品化和符号化。毫无疑问,巴塞尔姆以反英雄式的降格叙事给读者们带了阅读上的“震惊”效果,读者或许会因此体验到作家的焦虑:在不满意文学的“载道”形式之后,后现代书写能走多远,而假如后者也无法超脱这一消费社会时,文学“载道”的形式是否还能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