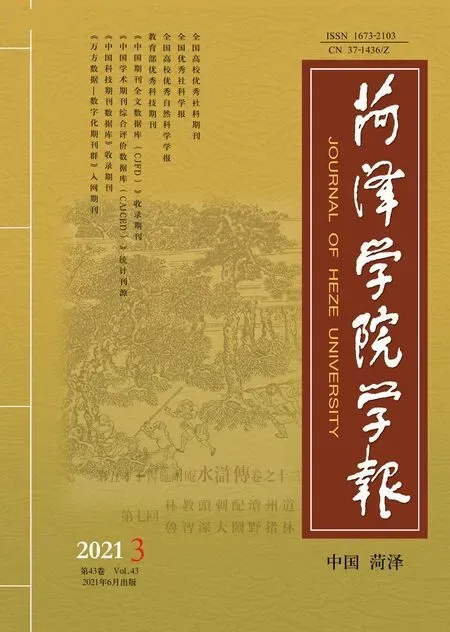不可靠叙述背后的伦理反思
——论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愤怒》 *
盛永宏,洪春梅
(1.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2.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0;3.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愤怒》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发表于2008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时间定位于1950年的美国,表层上“我”(马库斯)必须面对身为屠夫、曾经慈爱但现今比较狂躁的父亲,躁动不安、不易拉近关系的室友们,无法有效沟通的训导主任等;深层上是“我”(马库斯)及家人对朝鲜战争的恐惧及作出的相应选择(好好读书以逃离战场),小说以“我”(马库斯)死于朝鲜战场而告终。大段的对话再现了马库斯和周围人的相处方式及心理状态,“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1]从叙事学角度深入分析后发现,叙述者“我”(马库斯)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有强烈的主观性,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距离很远,但却与隐含作者的意图达成一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思考),揭示了叙述者个体化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将形式分析与道德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2],以此将读者引向对小说伦理意蕴的思考中。
一、对“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界定及在《愤怒》中的阐释
“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是叙事学中的两个术语,在对《愤怒》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意图指向并不一致,由此引发对文本内涵的思考,即对伦理关系的失衡与个体化趋利避害心理和行为间关系的思考。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等概念。其中“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涉及到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3]由这一概念出发,其他的叙事者们进行了不同的阐发。如查特曼认为隐含作者是“文中的规范”,“是信息的发出者或文本的创造者”[4]。而安斯加·纽宁在《叙事理论大百科全书》中则认为布斯对“隐含作者”的理论界定存有潜在矛盾,即隐含作者就是文本规范的结构与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中具有发话者的地位之间的矛盾。方丹在《什么是隐含作者》中指出:“这一矛盾的确存在,但不存在于布斯本人的理论界定,而是存在于以查特曼为代表的众多叙事学家对布斯理论的阐发。”[5]由此,关注点再次回归到布斯对“隐含作者”的界定上,即“是以特定立场、方式或面貌来创作作品的人”。
从布斯对“隐含作者”的界定出发,《愤怒》的隐含作者就是指站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纵向坐标系的立场上,回忆并反思、进而处于创作《愤怒》状态中的罗斯,也是读者通过阅读文本后,可以推导出的特定时间段内的罗斯。罗斯出生于1933年,《愤怒》发表于2008年,由此可以推断罗斯写作《愤怒》时已年过七旬,人生阅历丰富,对待曾经的历史有更深刻的看法;同时,作为一个享有声誉、对社会负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不断地反思,然后将思考的所得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从内容上看,《愤怒》基本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不突出,语言大胆直白,整体看来并无批评色彩,但在细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隐含作者的意图指向是揭示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中各种伦理关系失衡对人的影响,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经济不景气的持续,直接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并引起心理上的恐慌,同时,伦理关系的失衡加重了人的心理创伤,个体化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的更为明显,所以在无法大力调整外在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亟需通过调整伦理规则,来缓解人的内在伤痛并给予正向的指引。
关于“叙述者”的界定,我们借用修订后的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如下: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6]
图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叙述者”,依照普利斯的定义,“叙述者”是指“叙述(故事)的人”(the one who narrates)[7]。《愤怒》的叙述者是“我”(马库斯),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我”出生的年代、经历过的事情,及与父母、大学室友、训导主任、女友、不被认可的朋友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附带着“我”内心的挣扎、恐惧和焦虑。读者从“我”的视角看周围的人、事、物,能切身体会到叙述者的痛苦和不甘,对叙述者所处的状态、环境感同身受,也更容易体会叙述者的情绪变化。这样的叙事角度,可以使读者近距离地了解叙述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在这样背景下的种种状态,“叙述语与人物想法之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因此读者可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8],这使读者能够通过马库斯的外在言行,去猜测他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如痛苦、压抑等)。
而作为独立个体的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既有进入文本、感同身受的直观感受,同时也有跳出文本并对其进行积极地阐释、尽量做出合理判断的理性思维。所以,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可能评价马库斯是一个冲动、压抑、痛苦、无法掌控情绪、无法融入团体的人,很可悲;也可能评价马库斯是个不幸的、处处受到牵制的小人物等。马库斯的痛苦、压抑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但他的负面情绪也会使读者心情糟糕,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受。由此更能引发读者对马库斯言论的质疑:他叙述的都是真实的吗?周围的人都那么糟糕吗?是校规过于严格还是马库斯无法适应新学校的生活?亦或是伦理道德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
至此,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意图指向不谋而合,虽不完全一致,但已经将读者引入对当时伦理规则的思考中,认识到当时外在环境带给人的压力,及个体化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的不合理性,即合理化伦理规则的缺失和失衡。
二、不可靠叙述
《愤怒》的开篇是这样叙述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艰苦的朝鲜战争爆发。开战大约两个半月后,我进了罗伯特·崔特,纽瓦克市中心的一所小型大学,……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但“差不多从我开始在罗伯特·崔特上学那天起,我父亲就变得忧心忡忡,担心我会死掉。”叙事由此展开,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作可靠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靠的。”[9]此处的“作品的思想规范”指向两个方面:故事实事和价值判断。“当某个实事通过人物叙述传递给读者时,读者需要判断究竟是否为客观实事,是否为人物的主观性所扭曲。”[10]马库斯的叙述看起来是客观实事,但在价值判断上他对于事件的理解和评价,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是不可靠的,偏离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
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马库斯上大学、父亲担忧三件事,这三件事看似无关,实则三者间存在着隐形联系。“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有高中以上学历,我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连小学也没念完。”所以,马库斯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对他们家人来说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马库斯及家人对学习机会就更加珍惜,但父亲却表现出“忧心忡忡”,这与常理不符。由此推测“他(父亲)的担忧也许和那场战争有关”;也许和重大伤亡有关,因为那样“我会被征召入伍”,像两个堂兄那样战死在朝鲜战场;也许“与他财务状况发愁有关”。但不管是哪种原因,或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是父亲的担忧日益加重。“从一月我高中毕业到九月大学开学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店里工作”,充当助手,学习采购、清理、“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我把它视作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样的日子疲惫且充实。马库斯大学一年级在罗伯特·崔特过的很舒服,和老师、同学都能很好地相处,因为离家较近,每天都回家住宿,所以花费不多。但父亲的担忧及焦虑使他感觉无处可逃,关键还有父亲对他的不信任。于是,“仅仅一年后,我便离开了罗伯特·崔特”,“我转到了温斯堡,……离我家后门的两道锁有五百英里。”校园风景优美,好比“大学电影音乐剧的效果”,学生们在那里唱、跳等,而不是念书。这样的校园环境富有灵动性,朝鲜战争的阴影好像不存在于这所学校,一切井然有序,与马库斯的焦虑和紧张形成反差。马库斯认为新的校园生活会更加美好,因为他已经逃离了父亲的监视,但来此读书,家人要支付比之前更多的费用,父亲不得不辞退助手,“唯有这样,他才不至于入不敷出。”这也使父亲对马库斯抱有更多的期待,同时,通过犹太人团体等给予马库斯更多的关注和帮助,父亲对马库斯的爱与监管杂糅在一起,使马库斯无法理解父亲对他的爱。
在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马库斯家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经济紧缩,人心浮动、焦虑、压抑。父亲和马库斯之间好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担忧与逃离),但目标又一致。从根本上讲,这与朝鲜战争相关,父亲和马库斯都希望通过上大学获得学位,作为军官走上战场,不用直接冲锋陷阵,可免一死,保住性命是父亲和马库斯的共同目标。所以当马库斯来温斯堡读书,即使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父亲也努力支持。马库斯对温斯堡的生活并不充满期待,来温斯堡上大学只是他的解脱之路、希望所在,所以在面对新室友、新校园、新环境时,马库斯的内心并没有更多的波澜,只是感觉温斯堡的校风与罗伯特·崔特完全不同,并采用一简一繁两种方式来叙述两所学校的情况:先是简略地介绍了罗伯特·崔特,可概括为那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满意和温馨。因为马库斯只关心读书,学校里无人干涉私人生活,这与马库斯的目标(能拿到学位即可)相一致,整体感觉自由、自主;之后用比较详细的叙述与对话相结合的方式,叙述马库斯在温斯堡的学习生活:包括室友们参与的活动、马库斯与新室友的关系、奥丽维娅的生活、兄弟会成员的情况、马库斯与训导主任的对话等,可概括为这里的一切都糟糕透了,因为这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与马库斯的想法冲突,这使马库斯感到痛苦、无奈、愤怒。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归纳马库斯的心路历程为:为逃离父亲,所以来到温斯堡;想逃离直接上战场前线,所以努力学习;期待上战场前摆脱童身,所以与女孩子奥丽维娅相处;因为无法容忍室友的恶习(深夜练习及侮辱性语言),所以一个人住;因为这些过往,与训导主任对话并被质疑;因为愤怒,被开除并上战场、死去。从叙述者马库斯的角度出发,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无耐、逃离、坚持等,能理解他没有选择、苦苦挣扎的状态。但这一切都是马库斯在叙述,他所处的时代与史实相符,学校情况也都属实,但在价值判断上却有出入,将马库斯的叙述转换成图谱后看起来更清晰:
不满父亲的束缚→来到温斯堡;不满室友→换寝室;不满课程设置等→忍耐;不能接受训导主任的指导→愤怒走向战场→死去。
马库斯的叙述一直在关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读者认同他是无辜的、被伤害的、任人宰割的。一方面,读者看到马库斯关于所有实事的陈述基本上是真实的,但同时,叙述者对事件的理解与评价却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与隐含作者的规范距离很远,是不可靠的。这需要读者进行“解码”,即通过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去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及合理的价值判断。
作为读者,我们在情感层面同情马库斯,但在理性的深层次上我们要反思:马库斯为什么不能和周围的人达成共识?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所有的冲突都是其他人的错吗?一定不是,那是什么原因使然?从马库斯与家人、朋友、老师的关系处理看,他希望突破,与周围的一切抗争,但没有成功,这指出了马库斯的个体化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使他不能融于学校生活,也无法与周围的人进行有效地沟通,马库斯的心理失衡与时代相关,与父子间的相处方式相关,但本质上是伦理道德观念的缺失使然。叙述者在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性将我们引入对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及伦理道德的思考上。
三、对伦理反思的探析
《愤怒》中关于伦理规范并没有直接表述,马库斯与父亲间的关系是他自己言说的,与训导主任间的关系是用大段的对话直接再现出来的,读者可以由此作为切入点进行判断,思考伦理道德规则、观念等对现代人的意义。
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文学中常出现的主题,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父亲对儿子往往都负有教养的责任和义务,代表着权威,即使现代以来有很多改观,强调民主、平等,但父亲的话语权还是高于儿子。相应地,儿子对父亲要恭敬、顺从,有个人话语权,但权限有限,特别是在年龄较低时。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大体情况相似。从马库斯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知他的父亲很爱他,很为他骄傲,特别是能升入大学读书这件事,父亲即使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多的费用,他也心甘情愿,这能很好地证明父亲对马库斯的爱。反过来,从马库斯在店里帮忙,努力克服自己的不适,对父亲充满同情和认同来看,马库斯对父亲是恭敬、顺从的。父与子都遵循了伦理规则,所以此时他们并没有大的冲突和矛盾。但随着马库斯年龄的增长,外加朝鲜战争的爆发,父与子之间的伦理平衡被打破了。如上述,父亲出于关心要更多地保护儿子,情绪激动时表现出来的就是啰嗦、大吼、随时询问等,这一切导致了马库斯的逃离。从伦理规则的角度讲,父亲对儿子有更多的话语权,但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话语权是逐年递减的,当儿子长大成人时,这种关系应该逐渐转变到平等对话,需要给儿子更多的个人空间,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因为父亲的执著和儿子的不理解,所以马库斯产生了极为反感、愤怒的情绪,以逃离的方式来对抗父亲的保护,矛盾加剧。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伦理道德观念下滑,经历的二战的伤痛,对人生有更多的感悟,部分年轻人陷入迷惘、彷徨中,也更加自我,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这种感受,所以,在面对传统的伦理规则时,他们希望以特有的方式去打破,但走向何处并不清楚。此处亟需新的能适应当时情况的伦理规则出现,去平衡父子间的关系。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尊师重道”也一直被人们认可,不同阶段师生关系的具体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高校师生关系是指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为完成一定的教育任务,以‘教’和‘学’为中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学校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11]具体可以归结为教育关系、心理关系和伦理关系三个层次。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师生间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其中的规则、规范实则是社会伦理的一种。师生二者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道德共同体,各自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对教育关系和心理关系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教师的言行、品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而高校中没有直接教学的教师,在行为规范上对学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作用是相同的。
从教师的角度讲,训导主任以责任为主导,希望按照优秀的标准来培养他的学生,“除了学习拔尖,你在温斯堡这儿需要学会的,还有怎么与人相处,怎么敞开胸怀,宽容和你不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每门成绩都是“A”的马库斯一入学就引起了训导主任的关注,如此优秀的学生一定要好好培养的期待已经扎根于训导主任的头脑中,当得知马库斯两个月内换了两个寝室并住在一个几乎废弃的寝室时,训导主任就很迫切地想知道马库斯的想法,于是约谈。对话涉及到马库斯与室友的矛盾所在、与家人的相处情况、与奥丽维娅间的关系,及关于课程设置的态度等。并和马库斯探讨其中的原因和解决的可能性,及如何避免一个人独处。当提及所住的寝室时,“你出生于犹太家庭,依照学校尽量协助学生、让他们与信仰相同的同学住在一起的做法,你最初被分配到的是犹太人室友。”如此安排虽然与马库斯要逃离的想法相冲突,但从职责角度看,训导主任希望他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期间不断地用语言安抚劝慰、倒水给马库斯等都证实了这一点。作为学生的马库斯以个人的想法为准则,拒绝与周围的人、事和解,趋利避害的心理明显。“我的军事科学课每周课时一个半小时”,马库斯认为这门课程浪费时间,教官为人也比较呆板,但他仍然会认真对待,因为“假如我能以一个军官身份入伍”,在战场上我的存活几率就比较大。“虽然我报了法律预科,但我不是真的想当律师。”这样做就是为了向父亲证明,他们的花费是值得的。同时,马库斯对学校里安排的基督教活动也极为不满,认为不需要这样的仪式。另外,他希望自己在上战场之前告别童身,是目的也是释放压力和无耐的手段,所以他开始关注周围的女生。恋爱没在他预想的范畴内,但在和奥丽维娅的接触中,马库斯却陷入到情感的纠结中。特别是在出院后,因为奥丽维娅离校的事,马库斯主动去找训导主任,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不符合规范,可能会被勒令退学,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与训导主任沟通并被怀疑,在解释不清的情况下不得不离校,走向朝鲜战场。
马库斯与教导主任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言说,马库斯作为学生、年轻人,思想比较开放,在50年代的校园里希望自由,破除传统的信仰,特立独行,以达到个人目的,同时校园内的其他学生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释放压抑的情绪,如“温斯堡大学轰动的白色内裤抢夺战”。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不需要忍受其他人的无礼行为,也不需要与他们和解,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过学习生活,个体化倾向明显。卡德威尔作为教师(训导主任),他认为要尽职尽责,将学生引导到一定的规范框架内,与周围的人和社会相融合,有一定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身份不同的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足点,但处于二者间的道德观念需要适度调整,以调和矛盾,利于师生身心的发展。
从当时的社会风尚来讲,整体趋于保守,但各种反文化倾向已经出现,年轻人思维活跃,要求突破陈规。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与子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会产生冲突和对抗,这说明当时的伦理价值观念需要适当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根据不同的伦理境遇,需要针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和外在行为,不断地更新具有可操作性的伦理规则,以使人们相对客观、清楚地认识自身,与他人形成和谐的关系。
结语
通过分析隐含作者的意图和叙事者的不可靠叙述,发现《愤怒》中的马库斯处于朝鲜战争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中,他是那一代年轻人的代表,明确自己的追求,但不清楚人生的意义,所以在迷茫中陷入到与周围人的对抗中,命终于朝鲜战场。他的悲剧带有时代特征,但本质上是个体化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所致。隐含作者揭示并谴责了这种个体化社会道德无序的状况,希望人们能以理性思考面对各种伦理困境,树立相应的道德观念,达到各种伦理关系的平衡,从而益于个体的身心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