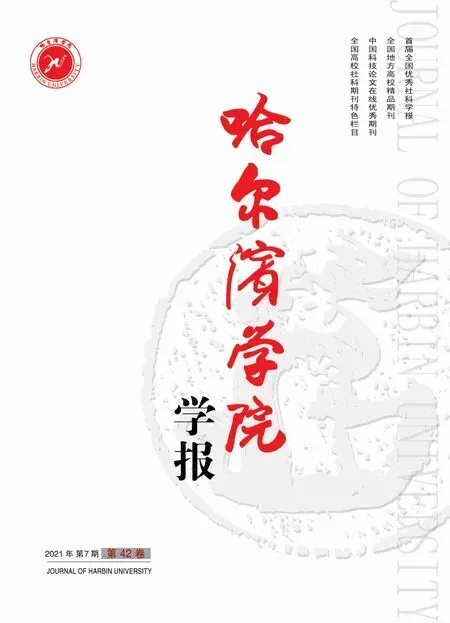李泽厚“两种道德论”思想研究
张蕴睿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李泽厚将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现代社会性道德,两种道德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他认为在以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以“情”为本、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并重的中国,人和人际关系不可能用纯粹的理性来支撑,应以宗教性道德为范导,以现代社会性道德为基础,构建合情合理、情理和谐统一的中国模式。其理论框架中虽然有概念混淆等漏洞,但却为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道德提供了理论启迪。
一、两种道德的界定与异同
李泽厚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道德进行了界定,认为“道德是个体对社会人际(某群体如家庭、宗族、集团、民族、国家、党派、阶级等等)关系在行为上的承诺和规范。”[1](P20)他将道德范围限制在行为上,突出道德具有的实践性。因为道德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品格、德性,更具有现实后果,其最根本的意义便在于个体将经由历史积淀内化于心的理性的行为规范付诸实践。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内容,后者是心理形式,道德的心理形式由个体行为得以表现,这就是“自由意志”,是区别于动物本能的。
同时,道德区别于法律的外在强制,是内在的靠良心约束的行为规范。这种内在自律并非本能的、天生的,而是人经由理性的长期的培育和训练将历史的积淀内化于心所形成的控制个人行为的心理规范,随着不断实践、认同,逐渐从自觉意识发展为无意识的道德直觉。
(一)宗教性道德
李泽厚对宗教性道德的认识深受康德“绝对律令”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的天意、上帝或理性,正是它们制定了人类(当然更包括个体)所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1](P22)在宗教性道德中,包括个体价值、人生意义等一切个体的权利均被放置在“绝对律令”之下,将制定律令的上帝、天意或理性作为信仰、灵魂寄托,以这个绝对的、先验的道德律令作为自我约束行为的根本准则,以求灵魂的超脱。这种绝对律令具有不可抗拒的使人的内心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追根溯源,宗教性道德是由经验到超验,礼源于俗的,以传统来维持。自古以来,在人类法律诞生之前就存在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此行为规范来源于人们从社会实践中汲取的适于人类总体发展进步的经验习俗,并以人类能够主观选择的记忆能力加以传承,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被印证,遵从必定得到好处,不遵从则会有所损失,人们内心的认同感不断被加强,理性判断逐渐转变为道德直觉,行为规范便由经验走向先验。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群体的生存密不可分,甚至是由群体生存所决定的。个体想要生存发展必须要为群体的生存发展而奋斗甚至牺牲,为了使种群繁衍壮大,个体必须具有这种自觉意识,先验的宗教性道德由此出现,其神秘和神圣使其凌驾于人类之上,带有个体不能抗拒的力量,将适合种群生存与发展的经验赋以神的权威与意志,以其绝对的律令指导人类总体更好地发展。
(二)社会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
社会性道德指的是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为维持、保护、延续其生存、生活所要求的共同的行为方式、准则或标准。其具有阶段性及历史性:一方面,其行为方式、准则、标准都是在某一特定社会条件、历史时期的语境内实现的;另一方面,它为一定的民族、集团、阶级生存、延续、统治服务,与宗教性道德旨在为人类总体更好地发展相区别。
受卢梭契约论的影响,李泽厚认为现代社会性道德是指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现代社会性道德以个体为基本单位,个体第一,群体第二。私利第一,公益第二。”[1](P34)社会和公益都建立在个体、私利的契约之上,社会不高于个体,而为个体服务。基于个体利益之上的人际之间的社会契约,“是一切现代社会性道德从而是现代法律、政治的根本基础”。[1](P34)由于世界主旋律趋向于和平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达到崭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合作分工程度,基于社会合作分工而产生的“公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制约力。李泽厚认为形式正义、程序第一优先于实质正义、内容第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两种道德的异同
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个人行为规范,都是个人理性对自身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的控制和命令,都表现为一种主动自觉的心理活动。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是个体追求的最高自身价值或超人世的价值,以信仰的方式将自身与超验联结,执行超验的意志与命令,以求个人精神层面的超脱与升华。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特定时代社会群体对个体的客观要求,是个体生于群体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与具体时空条件相关联,以法律、制度等为常见形式。宗教性道德提出的行为准则原则上好像是绝对的,要求人们必须遵照律令,实践上却是相对的,基于个人的信仰与追求,因人而异;社会性道德提出的行为准则原则上好像是相对的,但实践上是绝对的,要求群体内成员必须履行。宗教性道德有关个人的修养水平,是一种道德期待,有特殊性;社会性道德则是个体生于群体必须履行的规约、责任与义务,是道德底线,具有普遍性。在李泽厚看来,宗教性道德属于积极道德,社会性道德属于消极道德,社会性道德更具有优先性,是保障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两种道德的内在联系
李泽厚认为,将道德划分为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是一种理想型的理论构建。任一时期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一种道德,两种道德看似对立却紧密联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宗教性道德依托于社会性道德,所谓“礼源于俗”。宗教性道德源于经验、传统、习俗,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这些经验、传统、习俗以超人世、超验的形式展现于世人面前以保障其权威,使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宗教性道德的不可抗拒,信服并以此指导生活,保障着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宗教性道德常以天意、绝对律令的形式出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进步,以前的对于绝对律令的解释与猜测随之逐渐被披露,为保护宗教性道德的神圣与权威,就需要在传统形式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求助于新的社会性道德,以基于新的历史条件给予绝对律令新的注解的方式,使其重新具有对人类生活的指导意义。
关于社会性道德,李泽厚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答,他认为社会性道德以该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由现代经济生活所决定的具有优先性的道德。现代社会性道德建立在现代化工具——社会本体之上,以个人为基础,以契约为原则,理论上逐渐与宗教性道德脱钩,对宗教性道德传统产生巨大的破坏。的确,已走向理性的人类不应再以宗教性道德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但人和人际关系不可能有纯粹的理性。特别是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无论是对内的血缘、宗族,还是对外“由己及人”的差序格局,都离不开一个“情”字。“对现代社会性道德的片面强调就会导致现代社会原子个体之间冷漠孤立局面的出现”,[2]这是非人性的,也是非中国的。李泽厚认为,宗教性道德应作为范导指引现代社会性道德在中国的建立。“私德”与“情”不仅巩固了社会结构,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的特征,对现代社会性道德起润滑、引导作用,将个人基础上的理性给予适度软化,以“情”润“理”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中国模式”。
可以说,在中国,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始终没有真正分离,“前者是一种期待性的理想要求,后者是一种规约性的现实规范。”[3]在李泽厚看来,宗教性道德一直占据传统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历史传统没有真正具有人格神的上帝,两种道德全面渗透合一,形成了儒家传统之“礼”。中国古代圣贤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将社会性道德升华成为宗教性道德。在这其中,后者主宰前者,并将升华的结果誉为“天道”“天意”,与“人道”“人意”相通,在数千年儒家传统中,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礼制无处不在,社会统治体制与精神信仰体制有机融合形成了“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使个体不仅有宗教性道德追求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更有关注现实世界和日常经验的生活、行为、情感和心境。
三、“两种道德论”的反思
李泽厚对道德的划分引发争论,正如陈来先生所讲,李泽厚对于道德概念的使用产生混淆。首先,他认为社会性道德是决定法律制定与道德裁决的道德,但实际上他将社会性道德与制度、体制、法律法规相关联甚至等同,让道德与法律产生了混淆。[4]马工程在《伦理学》一书中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根据经济发展现状及规律,客观的、消极的、具有优先性和普世意义的“社会性道德”定义是成立且存在的,具有非强制力约束性,所以当李泽厚认为现代社会性道德取得法律形式的确认和支持的时候,其所谓的道德也就不复存在了。其次,李泽厚的道德概念界定不明晰。他认为,道德是指“群体规范要求,经由历史和教育(广义),培育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和心理,从自觉意识一直到无意识的直觉,所以道德不是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外在群体的伦理规范,通过个体自觉意识及道德心理中的观念,而主宰个体的道德行为。”[5]这一道德概念与伦理概念产生混淆,且其在《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一文中提出“现代社会性道德是以现代经济生活为基础所生发出来的一套观念系统”,[6]其观念系统的定义淡化了它与主体行为的联系。
现代社会性道德,在某些方面确如李泽厚所言,是一种以物质生活为根基、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社会和公益都建立在个体、私利的契约之上,社会为个体服务,以保障人类的物质性生存延续的道德。但这所谓的“现代社会性道德”实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非道德。他认为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基于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所以能够冲破地区、种族、宗教、文化,成为“普遍必然”,具有普世性。相对于他的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概念而言,学界公认的“道德”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地制宜的观念品质、原则规范、行为活动的总和。这种现代社会性道德显然与道德的定义背道而驰。道德不具有现代社会性道德所有的普遍性,道德具有的发展必然性,仅存在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落后于社会存在时,由社会存在引导道德发展的过程。而由于地域文化多元的限制,元道德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的条件,所以能够冲破地区、种族、宗教、文化的“普遍必然”还有待考量,这种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普遍性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另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社会性道德还是一种社会性道德,局限于“现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时空条件发生改变时社会性道德也将随之改变,改变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这种社会性道德是短期的,具有时效性。而宗教性道德对比于社会性道德,时常体现于“绝对律令”“天意”等看似永世的准则,但从李泽厚所说的“礼源于俗”来看,“俗”不断随着物质社会发生变化的同时,“礼”定然也变化,不过是以在新的社会性道德中寻求注解的方式而已。从理性视角来看,否定宗教性道德绝对性的同时,应看到宗教性道德较社会性道德所具有的长存于世的特点。且对于李泽厚所说的社会性道德皆以该时代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当社会物质条件发生质的转变时,社会性道德会随之重构,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基于新社会物质条件对宗教性道德的批判继承。基于上一时代的社会性道德虽不再适用于当下,但有长期效用、作为道德期待的宗教性道德却为新社会性道德的重构提供了批判、继承的道德基础。
对于李泽厚所提出的善恶应与对错脱钩、权利优先于善的思想,笔者持不同看法。
首先,善恶应当与对错脱钩吗?李泽厚认为,对错与善恶的分开和脱钩。这种观点认为善恶与对错相互影响,将善恶与对错视为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应当脱钩看待以求公正、自由。这样就忽视了善恶与对错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只在“对错”维度进行道德审判,善恶与对错脱钩,即抛弃了日常生活中事物的道德属性,仅从法理视角对事物加以审视,这样的确可以更公正、合理地对事物作出判断。但同时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失去非强制力约束,人们对事物善恶的评判被局限于精神世界中,沦为了一种消遣。同样,单纯从善恶维度进行道德评判也不恰当,如果只用舆论等软性束缚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道德审判的效果就完全系于人的良知上了。只有将对错辅以善恶手段,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案。
其次,权利是否应当优先于善?不能一言以蔽之。在当下实施的优先性上,权利的确应当优先于善。上文提到,权利所对应的现代社会性道德是一种“底线”道德,一旦有所逾越则会损及他人利益,当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时,遑论道德,所以权利思想应当是主体行为的基本思想。但在教育、个人追求的优先性上,善应当优先于权利。善是一种道德期待,具有社会引领力,是远超于权利思想的崇高道德追求,它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关系。只有将善的思想始终怀揣于心,作为行为的终极指导,人的行为才能在道德底线之上。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一样,人的行为终是善的思想的摹本,只能不断接近,无法超越。若将权利思想作为终极追求,那么人的行为将浮动于底线上下,道德就成了虚幻的存在。
人对于善的追求能够极大地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必然性。权利优先于善是针对当下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的道德问题而言的,并非长久之计。且单纯强调权利、强调法治,不论效果,带来的社会损耗将是巨大的。而人对于善的追求与修养可有效弥补这一点,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保护他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向善而行。由此观之,从效果与损耗视角来看,善优先于权利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当下中国道德建设应以权利为基本思想,以善为崇高追求,寓善于权利,以权利为善,实现善与权利的有机统一。
四、对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启示
现代社会性道德要求的是个人履行现代生活最低限度的义务,是基于经济生活的时代发展的基本的道德,具有普遍性;宗教性道德也具有普遍性,表现为一种道德期待。现代社会性道德应与宗教性道德区别进行理论发展,而后联系指导实践,也就是政治—文化领域中具体的“西体中用”。基于以上讨论,李泽厚所言的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普世性实际来源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西体中用”的模式即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以宗教性道德即人之感性认知进行范导,达到合情合理的境界。
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应将现代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并重。正如李泽厚所言,形式正义、程序第一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不应是纯粹的现代社会性道德,应是“理”和“情”中国化的和谐统一,也是权利与善的和谐统一,建构“中国模式”。李泽厚这种以现代社会性道德为基础,以宗教性道德为范导的模式与近代道德主流趋向一致,与中国问题解决方向也一致,所以其“两种道德论”虽有争议,但仍对中国道德建设具有理论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