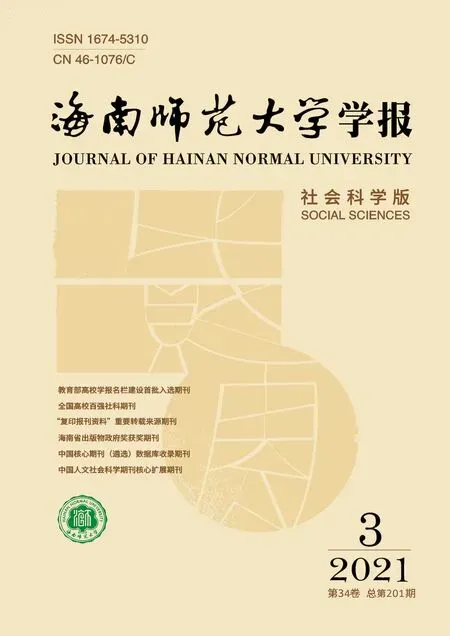风景书写、自然史与社会主义记忆
——以王安忆《匿名》为中心
王 植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作为一个有着数十年创作生涯的作家,王安忆一直是当代文坛无法忽视的存在,其稳定高产而又向来不失水准的写作状态,也使得她具有更多的独特性和话题性。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王安忆逐渐被大众传媒塑造为小资化的海派作家,但她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从不因这种塑造而磨失了锐气。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女儿”,社会主义记忆一直是她不愿回避的,因而选择一次次地以作品去反思。本文即从其晚近长篇《匿名》入手,试图重探这一问题。
一、从寻根“文”学谈起
被命名为“寻根”的文学实践,在文本呈现上表现出“新时期”文学对风景的自觉书写。这种自觉在有些论者看来是一种新的审美启蒙,是文学对此前意识形态的“生态性的反驳”。对自然风景的书写缔造出独特的民族性景观和空间,成为文学在新时期获得诗性救赎的必要手段;其对文化和生命两个层次的寻根,也让文学拥有更为纯粹的个体诗性特征。(1)傅元峰:《景象的困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87-111页。这样的讨论不免忽视了寻根文学发生的具体动因,正如洪子诚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初因种种政治名教、运动(2)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而带来的改革受挫,寻根文学其实成为受挫后“‘文化热’转向的结果”(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1页。。而另一方面,寻根文学也是新时期文学自身完成现代化的要求。彼时的中国,现代化既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也是集体性的历史冲动,在感官、审美和形式方面的自律性,与技术领域和理性层面上对现代的肯定是同构的。它要重新宣布时间的开始,成为此后一切的标准,一个新的叙事框架。
根据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著名理论,文本形式被功能决定,功能决定了某种文本形式是否被询唤。在詹姆逊的论述框架里,询唤形式的是历史(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信奉的“现代”的神话是一种文化落后的危机感的体现,所以召唤的形式是在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下被仓促定义的“现代”。(5)陈晓明亦对此有直接的批评:“在文学方面,普遍为一种乐观情绪所支配,似乎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可以标志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变得理直气壮,因为它被认为是反映了历史的主导精神——它是现代化进步的文化象征,也是现代化必然胜利的精神成果。这种想当然的推论使历史的内在冲突被严重强化,自以为与历史的支配力量同步并且同化,但实际却是在撕扯和突破疆界。”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5-326页。故而寻根文学既“呼应”着“现代”的诉求,也为之“辩护”。张旭东同样指出,孕育这种求新性格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另一母体,乃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经验,也即“结晶在国家概念中的大众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国家体制的支持和庇护。(6)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访谈》第12页。这两方面的基础,造就了这种“现代主义”一方面追求现代性、努力完成形式自律,另一方面也在抵御着对外国的单纯模仿,超越彼时具有普遍价值霸权的文化秩序和政治意图,并塑造一种文化的乌托邦,以文化空间的异质性为表象,重建民族文化谱系。(7)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第141-146页。
因此,在文本呈现上,寻根文学犹如一种新型的“风景之发现”,对现代的诉求在无意识中与早年“上山下乡”的经验相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人类学性质的遭遇,在中国内部发现种种“前现代时间在空间上的遗存”,那是传统中国在主流文化、思想与父权之外深沉而分散的蕴积,“不止关涉民族自我精神的重建,也是一种民间精神的考古学。”(8)黄锦树:《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6年,第319页。因此,新时期文学的风景书写,肇生于革命的经验、现代的诉求、“上山下乡”的后遗效应和政治上的道路选择,并非仅仅是恢复被压抑的诗性那么简单,而它对民族文化的玩味和迷醉,也带来忽视现实与启蒙的诟病,成为一种含带“逃逸”性格的实践,陈晓明更认为它“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历史地讲述着自己身为新时代主体的所思。当然,在美学意义上,它也“总算没有完全迷失于虚幻的历史空间,实际完成了一次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的变异……关于历史、现实以及个人情感,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新时期文学建立了一整套的表意体系,它有效地成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实践。”(9)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这是寻根文学诞生的历史原境,也是王安忆的《大刘庄》(1984)、《小鲍庄》(1985)等寻根文学代表作的诞生空间。而王安忆彼时精神状态的形构,直接的刺激是1983年的美国之行,一种亲历的震惊体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身文化语境的本质与特性的反思。贺桂梅在分析王安忆这段经历时,将之视为一种微弱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先声,是“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发达国家面前所体验的复杂心境”。(10)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0-183页。结合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著名论断,本就沉溺在抽象而虚幻的历史空间的寻根文学,更拥有了国族寓言的品格,就像《小鲍庄》营造出仁义而充满生命力、残酷、古朴、凄楚的人间风景,却也时时夹杂着种种时代政治的元素(最明显如鲍仁文在政府的帮助下,对小孩救人的仁义之举的报告文学写作)。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王安忆笔下的民间风景,总还有一种不透明度,在技术操作上,它借助的是方言、歌谣、明快简洁的短句,而非后来的“叙述”“描绘”与“表现”这种通过纵深度来实现现实主义模式之建立的必需手段。在那一段段不知所自何来的花鼓戏唱词响起之时,王安忆似乎仍能沟通、映现出古老的昔日民间礼乐秩序的熙光,而不是现代民俗学视野之下所发现的风景。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中,这种不透明度,其实就是“文”的程度。这样的操作也让小说的写作并无太多抒情色彩,王安忆的寻根实践相比起阿城、贾平凹来,还是比较冷峻、旁观(“隔”)的。王德威援引宇文所安的论述,认为“‘文’如果是符号、纹理、艺术记号,‘文学’便是记录人类克服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隔’的艺术。”(11)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p.306.比较《小鲍庄》与走出寻根时代之后的王安忆的创作,“文”的程度在不断减弱,“文学”的程度在不断增长。如果《小鲍庄》式风景书写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文”的变形与小规模恢复,那么寻根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作80年代“文学”朝向“文”的一次短暂的无意识“回顾”;易言之,一种“现代主义”之“文”,或者,以“文”的手段达到的“现代主义”。如此,王安忆寻根实践的那个终结点——也即从“文”转向“文学”的转折点在哪里?这关联着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也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有着繁复构成来源的当代文化政治,是如何促进了某一种特殊审美意识形态的构成。
二、文、象征秩序与抒情:《匿名》中的风景书写
关于王安忆在寻根实践之后的创作,本文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准备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长篇小说《匿名》入手,进行一定程度的逆推。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匿名》在一定意义上与王安忆早年的寻根实践息息相关,不仅在内容,更在思想的扩展;二是王安忆这样高产、丰富、复杂的创作主体,作品之间在思想上的跳跃性很大,并非每一部作品都真正体现了她深层的社会主义记忆,故而线性的阐释未必能取到比较好的效果。
《匿名》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素来过着普通、安稳日子的上海老白领,某一天突然被一伙要债者强行绑架到远离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深山中,事后虽知绑错了人,但他并没有因此得以回归,而是被要债者“麻和尚”所收养的、胎生于天地自然中的颟顸者“哑子”带往更深的荒野。小说上部夹叙其妻对其的诸般寻找,在上海这象征着文明之极致、人间风景之极盛而繁复的空间内,在亲人失踪但日子依旧要过下去的日常空洞的时间中。哑子离开后,老白领在荒山中与自然万有为伴,先后度过自我垦殖、被山里居民发现、送到小镇收容所与诸种“小镇畸人”为伍的时光,同时他丧失了对过去、文明、语言、文字的记忆,连形容亦有大改,渐渐脱去往日的一切痕迹。老白领不断获得不同的姓名与称谓,小说结尾他已是收容所里众人口中的“老新”,在陪着白化病少年鹏飞回到都市上海为先天性心脏病幼童治疗时,被失踪人口调查部门发现并确认了身份,却在家人前来认领的前几天,在与收容所众人一起出游时落入江水,不知所终。这样的情节让我们想起王安忆创作谱系中的《遍地枭雄》,而小说对林窟、九丈、藤了根这些身处文明与自然缝隙的地方的书写,以及对这些地方的种种畸、老、伤、废的颟顸人事的展现,又清晰地具有当年寻根文学作品的笔法,所以全书类乎一种多重的文本回声。在这样一个“归去来兮”的循环中的每个阶段,对风景与自然的描写都占据了大量篇幅,而且勾连着对中国传统哲学、自然史、文字语言的思索。为方便计,本文对主人公的称呼一律采用最后出现的“老新”。小说描写老新第一次看见、感知到自然风景,是在他刚刚被绑架、文明的意识仍然十分清晰、被从黑车中扔出来时的视景:
他舒展开身子,忽就看见满天星斗。苍穹之下,影子在迅速变小,小到像一颗豌豆。……他很奇怪的具有一种全视的功能,就好像处在俯瞰的位置。公路,公路两边的天地、树丛、高压线、隔离板、河塘——云母般发亮,他的视线辐射得越来越远,远到地平线。有一瞬,他忘记自己的处境,被惊诧攫住,他想不到天地的大,宽广与高远都是无限。无限的天地在向他收拢,星斗倾倒地面,伸手即可触摸似的,无限又变的有限。地平线也在逼近,看得见刀锋般的边缘上跑着瓢虫(指汽车,引者注)。河塘,那发光的云母上有一只水鸟飞起,纤长的双足与地面平行,飞,飞,一缕游云在它上方,渐渐地,两者都融进夜空,天地又无限地扩张开。(12)王安忆:《匿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类似的风景描写,全书所在多有,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则是将时间空间化,突出为一个乌托邦瞬间,含带着些许救赎的意味。那“惊诧”,则是老新走入自然荒野这又一种“启蒙”时所经历的情感反应。当将他带入深山的哑子离开之后,他开始自我刀耕火种,此时他对事物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像哑子了,用肢体进行思考、解析、记忆,一系列精神活动,因此这一系列精神活动无法辐射得更远,更多是在视力可见范围。”(13)王安忆:《匿名》,第103页。虽然视觉仍然占据着优先性,但精神的活动却不再能突破视觉的有限范围,如此,所能发现的“风景”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用身体去发现”,意味着彻底脱去文明所给予的种种外壳,“汇入整体性的时间,蜕下一张外壳,就是伤心。”(14)王安忆:《匿名》,第107页。在混沌的梦中痛哭,最后喊出一声妻子的闺名之后,便自此绝了语言和泪水。在这个过程中,眼泪是沟通文明与自然的最后一道屏障,便如将他带出荒山的另一颟顸子,心智不全的二点,以及他住在这荒山附近名为“林窟”的偏狭之地的兄长。这兄长纵没有老新般带自繁复文明社会的记忆,却也在心中埋着幼时全家在林窟受苦求活的往昔,当听傻兄弟认放牛时偶遇的老新如亡父,他的进山寻找打开了往日之种种。亡父的面貌、深山之景令他勃生的恐惧、四下地寻找与迷失,摆荡在象征秩序的边界之处,感受着心底深浓、充满诱惑而朝向死亡的浩浩黑暗,让眼泪成为走出这一状态后残余的灰烬:“从小就有人教,没有路的陡崖,如何用绳挂着攀上去。嘴里衔着一枚竹削的哨子,可吹出蛇鸣的音,哄得过虫蝎的听觉。佩戴一件件安置妥,不知不觉,他泪流满面,待到起步迈出门槛,已经哭得说不出话。哭着上坡道,所谓坡道,不过是几块石头,之间相距二三尺,背树背米人踩出的一条。他不敢回头看,回头也看不到,转身间,林窟就被树林掩埋,埋到地心里去了。”(15)王安忆:《匿名》,第142页。而当时光如流,旧历年关将至,一边是老新的妻子眼中上海璀璨的新年夜景,另一边则是老新、林窟男人、哑子、麻和尚的并置呈现,他们都因各自不同的记忆而伤心,小说也在此借风景书写达到一个高潮。林窟男人带着傻兄弟,“车沿着瓯江走,瓯江的水都是伤心泪”(16)王安忆:《匿名》,第160页。;站在瓯江边的麻和尚:
天色越发沉暗,云层垂下来,终于天水相连,合成一个混沌世界。有汽笛的咽声,连麻和尚这样伦常之外的人,都要觉得凄楚了。……车在漆黑里行走,分不清天上还是人间,雨雪冻寒阻住的人都到了家,凡生灵都有暖巢,没暖巢的都寂灭,下一世再生。江鸥飞起来了,呱呱叫嚷,追了数十里江岸,又回到江心洲。……没有游人,游人走在从冬到夏的途中,未曾抵达。卵石道过去是苗圃,苗圃过去是采石场,终于到了良种场,良种场那家人的院落里,灯火通明。(17)王安忆:《匿名》,北第201-202页。
在小说的下部中,自然的景象不再是生活的主要环境,不同的小村庄、收容所等暖老温贫的人间之景成为重点,夹杂着许多“民间哲学”式的思考,它们生发自老新以仅有的文明之痕迹与种种畸老伤废者的交流。眼泪仍然是过去与现在、文明与自然的边界,透过泪眼看到风景,依旧是模糊而混沌,摆荡于无意识的边界。而除了眼泪之外,汽车(作者比喻为“小虫子”)这一带老新远离文明的工具成为屡次出现的另一沟通的意象,表征着一种来与去的反复周折中的恍惚点缀。(18)比如:“天放大了,无边无际,盘山公路上的汽车成了小虫子,轮子转得离了地面,几乎飞起来,却动不了一寸。……周围静廓,听得见沙沙的脚步。望向山谷,澄明中有流水人家浮起,牛羊猪狗,青麦子,黄粟米,杜鹃花红一丛粉一丛……男人的眼泪落下来了,豆大的,啪啪打在方向盘上。……小虫子是在眼泪里泡大的,简直是眼泪珠子。这两颗眼泪珠子在环山公路上爬啊爬,越来越远,彼此看不见,天各一方。”(王安忆:《匿名》,第244-245页)“公路变得繁忙,汽车竞相追逐,喇叭声声。……日头在水面碎成鳞片,波光闪闪。真是亮啊,眼睛揭去一层白翳,无论远近,全历历在目。车速加快,超出前边的,又被后边超出。车走着流线,不再盘桓。窗外的江面,路面,竹林,树丛,倏地掠过去。这世界不只是变响、变亮,并且在加速,视线来不及停留,就已经过去,过去,过去!”(王安忆:《匿名》,第296页)如前文所述,在小说中,这些风景的书写其实都涉及到无意识层次乃至象征秩序的危机问题,且不仅仅限于老新,它们既表征着主体于自然风景中的投射和两者间共振式的运作,也借由不同的场景(荒山、林窟、九丈小村洼、收容所等等)、人物(哑子、二点、林窟男人、九丈派出所所长、收容所里的鹏飞和小先心)、事件与语词意象间相互回音、转喻的方式,延展着这种远离文明的主体与风景、自然总是在象征层面相会的状态。这样的结构被反复安排,为最终老新沉江的结局做出预示;场面、风景调度的无尽反射,最终回归黑暗不仁的自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成为文明神圣的遗迹。
换个角度来看,《匿名》是个从婚姻、家庭、文明等早已建制化的“关键词”之中走出的故事,从被动到主动,其所打破的正是这些关键词的神圣性。存在于这些关键词之中的,是层累于人类相互交往历史而被广泛接受、甚至不言自明的那些决定性、允诺性、仪式性、伦理性、超越性,它们共同赋予了这些名词以神圣感。老新先后放弃了这些,然后连自然与风景显像之美也一并放弃,直达象征层面——这是沉寂的美,只有扬弃表面的显像才能达到;老新在这种美中对追忆、视像、声音、身心的感知,或许整体构成一个更大的“家”的空间。此处达成“文明”的完满蜕变,小说提供的解释是“用身体去感知”一切,其实本质上还是象征秩序的问题。在具体历史的层面,风景所具有的这种沉寂的美,曾被用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神圣性与超越性;老新之死逼显出这种美的阴暗面,那是被压抑之物的复归,语言所无法触及的层面。如此,是否可以说,在肇生于自然的“文”向建制化的“文学”转折的过程中,变化、失落的东西其实被压抑进无意识之中?小说下部老新历经重新学习语言、创造文字以及种种“哲学”思索的过程,其断片性、艰困性,让语言成为逝去的回忆、远方的音乐与意象,犹如总是缭绕于老新头顶的那颗星、那段歌声。如此,《匿名》的故事亦成为语言的寓言。流利的文字提供给我们追忆的材料,一方面它是过去悠远的声音与音乐,另一方面它也阻隔我们借之来企望救赎的可能性,而必须回到叙事的发生状态,那叙事活动和徽记的草创阶段,“文”,才能感知到救赎的瞬间性,因为那被压抑之物的混沌与“文”之原初、丰沛、广博正是同构的。也由于“文”脱胎于自然,故而面对自然与风景之时,王安忆写出了它如何引起主体象征秩序的悸动。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颇具抒情性。根据海外汉学界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抒情传统的最大特色——借由文字‘把经验凝定在某一范畴内,加以深化和本体化’。……这是所谓的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相应的技术程序则是“对时间的处理——当下瞬时化、空间化”。(19)黄锦树:《论尝试文》,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6年,第72页。《匿名》的风景书写虽然有种种将时间空间化的操作,却笼罩在作者王安忆本人的全知视角之中,所以并没有以叙事制造出那种类似于抒情的冥想时刻,如弥赛亚、乌托邦时间。在王安忆这里,由于全知视角的笼罩,老新等人面对风景与自然呈现出的精神状态,重点并不在抒情——抒情说到底仍是诞生自文明,是文明的“发现”——而在那原初的、混沌的象征的层面,在象征秩序悸动的面纱下,展现着追忆与救赎。如此,面对巨大壮绝的自然与风景,“震惊”之下所感知到的并不是清晰的过去,而只是过去的痕迹及其潜藏于心中的能量,那是无法表达、说不清楚的。在那个时刻,过去和现在同样是不足的,只能获得不完整的实现,投射于文字,即清晰地展现出象征层面对抒情的牵制。这种状态已经启动风景与生命的交合,却又还未能寻找到其现实性使自身得以传承下去,因此,它是悬置而摆荡的存在,无法言诠,如果赋形于的文字,便毋宁已昭示着一种影像自身未能超越悬置的败落,一种“废墟”。这是《匿名》风景书写的复杂特色,那么其意义又何在?
虽然风景勾连着主体象征层面的“废墟”,但《匿名》提到的“废墟”,却是绑架老新离开文明社会的麻和尚那已经沉于水底的故乡——在最后一章,老新亦同样沉于水底。麻和尚的故乡是曾经盛极一时的青莲碗窑,却终究也在文明的变迁之中沉于一派大水。王安忆同样赋予麻和尚这“伦常之外的人”以无意识的瞬间影像,“你潜得够久的了,再浮起来些,就会震惊,一片连绵的黑瓦。……暗礁上的窑眼,水汪着它,好像泪眼盈盈。”(20)王安忆:《匿名》,第338页。在那个时刻,麻和尚眼中风景也模糊地关联着故乡曾经之于自身的一切,生死、情欲、生活、家庭、族群、伦理等等文明的“关键词”的最终沉沦,“生活先于故土溃决,随后才沉入库底”(21)王安忆:《匿名》,第358-359页。。从麻和尚这里“下一次文明是上一次的简单重复,还是递进式的,或者偏离出去,形成崭新的文明?那旧文明的壳,会不会固化成模型,规定新文明的格式?”(22)王安忆:《匿名》,第340页。到老新在沉入水底的凝结时刻,“世界上所有的城,都有相像之处,或者说,本质上都差不多。不外是群居,繁衍,生产,交易,组织化和社会化。这座城就像是那座城的倒影,水下原本就是水上的倒影。还像梦,水下是水上的梦。”(23)王安忆:《匿名》,第436页。王冰冰指出王安忆通过这样的设置和比较,反思了关于上海的城市考古学,以及“废墟”的积极意义:“一种文明,如‘青莲碗窑’,虽遭遇了毁灭,但其存在的历史、曾经的辉煌及其留存的现代性经验,却可以以遗迹的形式,被更高更上一层的文明所吸收、覆盖,成为其地基。文明遗迹一改其末世与颓废的内涵,而具有了某种建设性的积极意义。”(24)王冰冰:《后寻根时代的名实之惑——王安忆〈匿名〉及其他》,《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她同时认为这是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性、主体性之重建的历史反思,但最终却只能经由某一些个体(如老新、麻和尚等)的主体性重建之途,去接近这一目标。准此,《匿名》成为一种“拯救上海这个城市”的努力。
这确是精彩的论断。但问题在于,如果《匿名》的意义核心真像王冰冰所言,“对于已然在后现代都市丛林、景观社会中迷失方向、自我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只有将其与现代世界彻底的距离化、陌生化,才有可能使其在某种震惊中,获取重构自我的契机,舍此别无他途”(25)王冰冰:《后寻根时代的名实之惑——王安忆〈匿名〉及其他》,《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那么如何看待王安忆之前的大量作品?它们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吗?
如此,我们需要回到王安忆创作系谱之中别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长恨歌》博得茅盾文学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获得大众性关注之后的创作,看《匿名》究竟在她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又是如何反映了她的社会主义记忆的针对性、如何完成“拯救”——而那也是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
三、风景书写与社会主义记忆
以下以《纪实与虚构》(1993)、《长恨歌》(1995)、《启蒙时代》(2007)这三部王安忆创作生涯中路标式的长篇小说为讨论对象,做一番简要的回顾性讨论。这几部作品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关涉着王安忆本人的社会主义记忆。《纪实与虚构》反思自身的来源与母亲姓氏的来源,小说中对英雄历史的迷醉与自豪式的书写,投射的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无意识,这是非常男性中心的操作,与从女性角度叙写对来源的关注这一初衷相悖。而在革命时代,母亲茹志鹃作为革命同志,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没有历史,因为革命给予了其新生,让其日后处于只有横向关系而无纵向关系的世界中。此外,作为大都市上海的子女,其历史更是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这是一种现代性问题,再深厚的家族神话也必然被其吞噬,所以小说的另一条线,王安忆驾轻就熟的上海俗世生活风景的书写(不过突出的是革命者的生活),也最终成为她的寻根神话的消隐之处。小说的创作方法方面,黄锦树由王安忆彼时曾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化”的创作逻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人美学无法促成西方式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批评,(26)王安忆:《故事不是什么》,《王安忆研究资料》(上),张新颖、金理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7页。指出王安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成为一种她个人用以形构“深刻与宏伟”的长篇的形式逻辑和规范诗学(27)黄锦树:《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从〈纪实与虚构〉论王安忆》,黄锦树:《谎言或真理的技艺:当代中文小说论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第157页。。
《长恨歌》以绮丽的风景营造出一种“怀旧”式的风格与文体,在大众传媒的有意解读与引导之下,那常被认为是接续了张爱玲的传统。然而,突出上海历史所拥有的资产阶级性、怀旧性,并不能消解其也曾是左翼革命、社会主义现代性重镇的历史,张旭东认为,王安忆其实献给自己的阶级“真诚而又显出‘反讽’的挽歌”,因为,即使“上海的资产阶级证明自己‘超越’了毛泽东式的革命,却经历了一种诡异的死亡,即在复活和凯旋中最终消亡。残余的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一种概念或形象,而是在具体的事物中被非地域化了——它被推延、被仪式化、被散播、被普遍化,在大量繁殖的同时也被掏空了。”(28)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如此,《长恨歌》的怀旧不过是王安忆所动用的材料,且在她对上海的处理之中,没有救赎,没有乐观,就连那个怀旧性的民国老上海,也不过是被当代发明出来的东西,让其内容、氛围与技术都成为一种“枯竭的完美”。(29)[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62页。竹内好分析鲁迅《兄弟》与《离婚》两篇小说虽然技艺完美,但这“小说的世界构筑在自己之外,完美也是走向枯竭的完美”,恰如王安忆《长恨歌》的世界,是自己意识形态世界的他者而已,纵然有完美恢弘的皮相。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这种“将重新发明了的过去合并进尚不确定的未来,将会创造出某种新的城市文化和政治文化。”(30)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第225页。为何王安忆会这样处理上海风景?张旭东大胆猜想其衍生自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上海革命子女的社会主义记忆,因为王安忆们的“经验和记忆丧失了直接的过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段记忆与经验是被政治否定的,但也正因此而带给他们一种历史性的“忧郁”。而在陈晓明的论述中,这“忧郁”则被具体化为《长恨歌》中对种种光线照射不到的“阴面”的重视与书写,暗示着王安忆对主人公王琦瑶的否定,对“怀旧”的不以为然。此外,王晓明也同样通过对《富萍》结尾的分析,指出那种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式浪漫主义,其实已经被王安忆拉开距离了。(31)参见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所以,《长恨歌》这样的书写,其实可以说是历史的忧郁之灵对外在怀旧的反讽性触摸。(32)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第225页。如此,王安忆的文学其实与当年的上海左翼文学一样不与时代同流,以及和张爱玲或海派文学的关系,也不是什么骨子里的传承。张旭东、陈晓明、王晓明的解读都撕开了《长恨歌》怀旧式的面纱,而且前两位学者对王安忆社会主义记忆的探微与黄锦树亦是相类似的。
至于《启蒙时代》这部王安忆自承十分看重的“大的东西”(33)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页。,较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确实难以处理得多。黄锦树曾批判王安忆将文革的特殊语境视作给予了一群年轻人(红卫兵为主)以成长、性等方面的“启蒙”是对历史的轻灵消解,这“启蒙”也与从康德到福柯的定义完全相反。(34)黄锦树:《文革作为启蒙,或启蒙的反讽——论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华文文学》2014年第4期。主人公南昌虽然经历了各种“启蒙”:革命、理论、性、资产阶级历史、市民社会……但王安忆自己也承认,小说对这些“启蒙”的叙写可以说只有个引子,并无深刻性可言,而且这些“启蒙”究竟有多少真正是与文革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也很难说,很多仍旧是每个人在别的时间性中也会经历的。另一方面,小说比较出彩的部分还是革命年代背后的世道人心、俗世风景,这本就是王安忆擅长的部分,那些琐细、隐微又浅薄的小心思、小算计、小倔强、小气性、小残忍,方寸间的拿捏早已为她所驾轻就熟;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其实可以说为张鸿声从宏观视角所论述的文革时期的上海风景,补充进一种个人视线下的影像。(35)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整部小说的基调是很亢奋的,种种人物、理论与思绪交杂而又迅速地转变,使得全书一直处于一种不自然的精神强度之中,而非更日常、充实、理性、物质的生活。对此,王安忆的核心阐释是:
这个革命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全被打得粉碎,新的还未建立起来,他们就像站在废墟上,无遮无拦,赤裸着向着天地。时间和空间全是涣散无形,从他们身边铺张流淌。要说,他们的天地真是大,浩浩荡荡,他们穷尽目力,还是看不到边。可正因为如此,他们看见了天地的大——这就是理性,自生自长,自己找食,自己拉巴自己。这样养成的理性,只需有那么一点点,空茫的天地就约略画出了分界,有了立足之地。他们还没有踩实,摇摇摆摆。他们在懵懂中遭受的际遇,以及断章取义得来的知识,七拼八凑,组合成世界观,企图给无名以有名,给无规定的以规定。不晓得出了百错还是千错,在错误中犁开一条路,危险是有些危险,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无知的运命,那就是向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然中来。(36)王安忆:《启蒙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71页。
这样的解释可以说虚拟了一种人与自然、眼中影像之间在特殊语境之下关系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她认为“有一种正面的东西在里面”,无法言诠,而决定了她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思想剧”式的小说形式。(37)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第38页。这是一种存在于历史中的除不尽的残余,在她的认识中,社会主义的启蒙,正是建立在这种“正面的东西”之上。在她个人的认知中,这种思考是很可贵的,即使她未进行延展。而张旭东则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的层面,解释了王安忆想表达的这种“启蒙”可能为何。不是猛然间获得质的飞跃,那样只会中断了生活世界,故而必须也在个体经验层面不断力图重建生活世界,也即社会主义“启蒙”之下的风景显象,作为相应的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精神既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寻求对现实的克服与超越,又同时在这种克服与超越的过程中寻找和界定自身的现实性,寻求被现实所克服和超越,寻求在现实的感悟和把握中超越自身。”(38)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第94页。只有如此,才能为那“正面的东西”提供绵绵不绝的动力。那并不繁华绮丽的人世风景一如那时代,却正是社会主义“启蒙”得以获得彰显与延续的生命力的来源。
结合这三部体现王安忆书写难度的作品,我们能更清晰地认清《匿名》究竟意味着什么。《启蒙时代》在本质上其实与《匿名》共享着同一种方法论,即走出当下个人线性生活经验(新自由主义),探讨新的主体性的建立与发展的可能性。它延伸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乌托邦瞬间和维度,在象征牵制的抒情文字之下,在枯淡的现实主义文字之下(不同的“文”),展现不同的风景,寻不同的“根”。这是王安忆迥异于当代其他作家的风景书写的地方,她理论性地打开了多个维度,在《启蒙时代》里是对那种“正面的东西”的尝试赋形,在《匿名》则顺承地转变为在壮绝自然之中的尝试。从《纪实与虚构》到《长恨歌》再到《启蒙时代》,每一次的转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可或缺。《纪实与虚构》可谓是自己意识形态的第一次宣示,《长恨歌》则在绮丽的资本主义风景与文体之中透显出属于自己社会主义记忆的“忧郁”品格,从而试图捕捉其意义;《启蒙时代》则更进一步尝试去打开它,而且是直截了当、必定引起相当的争论的。这三部作品体现的逻辑其实是对社会主义记忆思考的不断延展。如果《启蒙时代》仍然建基于自己的经验,《匿名》则将之放入更大更广的世界,其思想和知识已经超越自己个体的生命经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更复杂地理解历史,以一种更为辩证的总体性的眼光重新看待现实。而这个更广大的世界,直接来源其实是曾身为革命者的母亲茹志鹃居住过的地方——“林窟”。“林窟这地方决不是杜撰,它确有其地,就在括苍山脉之中,沿楠溪江一路进去。方才说的有人去过,那人就是我妈妈,去的时间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相隔四十年,我于二零一二年走近它,走近它,然后弃它而去。”(39)王安忆:《林窟》,王安忆:《众声喧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在这个意义上,《匿名》也直接沟通了《纪实与虚构》,以及王安忆之前的寻根文学实践。只不过比诸寻根文学的虚幻缥缈、支离破碎、幽微难测,《匿名》是对寻根文学的清晰化、丰富化,也是对寻根本身的反思以及终结,一个属于王安忆个人的终结。
四、结语:文本内外的“自然史”
从《纪实与虚构》到《匿名》,王安忆每次只取一种媒介,来对自身的社会主义记忆进行反思。这些媒介都是超脱当下生活经验、线性历史的另外的可能性,另外的历史,也是本雅明所定义的“自然史”。虽然在《匿名》中,王安忆直接提出“不要以为文明史终结了自然史,自然史永远是文明史的最高原则,只是文明使之变得复杂和混淆。”(40)王安忆:《匿名》,第175页。但“自然史”的概念光谱十分复杂,从马克思、本雅明到柄谷行人,都有不同的解释,《匿名》所采用的应该是比较朴素的理解,也即自然诞生至今的过程,文明发端于它。但王安忆整个创作谱系,那种在更多的可能性中反思己身的操作,呼应的则应该是本雅明的定义。自然史是拥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但我们所身处的不过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其他的历史都成为已经败落的碎片与废墟,只有通过对这些“废墟”进行想象与分析,才能重新打开它。(41)[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9页。而以此方式去反思自身,便是一种自然史式的广博、辩证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匿名》已经显示出个人面对风景时的自然史式的反应,那种在个人象征层面如“废墟”的、悬置而又似乎通往别的可能性的风景,正是这种自然史式的思考延伸、行进到文本内部之时会产生的、无法绕过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王安忆并无意去探讨这些自然史的真正内涵,她只是用自然史的方式去反思线性史的内容、本质与未来的生命力之所在,从文本之外一直走到文本之内,才呈现出《匿名》现有的样态。而在自然史式的处理中,作者是不会得到固定的结果的,即使真的存在王冰冰所言,“只有远离文明社会才能重建自身,别无他途”的意味,也不是什么关键的问题了。所以,正如朱康所言,自然史式的操作是一种智慧型的操作,就像他所引施莱格尔的话,“不仅把诗之所有被割裂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而且让诗接触哲学和修辞学。”(42)朱康:《王安忆〈匿名〉是献给读者智慧的普遍诗》,《文艺报》2016年5月3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