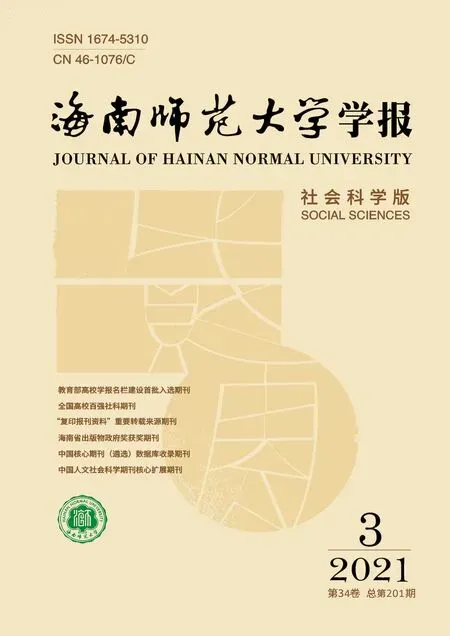主持人语 城乡互涉:观察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视角
赵 牧
(广西大学 文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4)
在《乡村与城市》一书里,雷蒙·威廉斯指出,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学传统中,乡村(Country)与城市(city)的对立互涉由来已久,人们对于乡村,往往以为它一方面代表了“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但也同时意味着“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而对于城市,它当然可以让人想起“智力、交流、知识”,但也不免让人产生负面的联想,那就是认为那里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1)[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对立却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与乡村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当然是存在的,但在传统士绅阶层那里,它们所分别对应的是庙堂之高和田园之乐,这中间进取或隐逸,就成了它们所各自被赋予的文化想象。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但工商业在城市集中而扩大了其功能,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本相对单一的晋身之途,不得已谋求多样的职业化生存之道,这就既在客观上扩大了城乡的区隔,又在文化想象上给乡村社会贴上了传统、落后乃至蒙昧的标签。
作为现代乡土文学开创者的鲁迅,就曾在其小说《风波》的开场白中,揶揄了古典诗文传统中的田园想象。晚饭时分的临河土场上,乌桕树叶、花脚蚊子、农家炊烟,以及乱跑的孩子、端饭的女人、摇扇的老人等,让酒船上的“文豪”禁不住感叹,“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啊”,但鲁迅对于这文本化的“诗兴”挖苦道:“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2)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1页。九斤老太是一个守旧的老太婆,她所能代表的,应该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为古典诗文传统看不到的残酷现实,而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现实,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辛亥革命的冲击而日渐破败,另一方面却又在“共和”的旗帜下继续遭遇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内的宗法制度及军阀混战的多重压迫。然而在启蒙主义的视角下,鲁迅不仅打破了古典诗词歌赋里的乡土幻象,而且用所谓“现实主义”的方法,揭示多重重压下的广大农民的精神病苦。正是在鲁迅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兴起了一股乡土文学的叙事风潮,而在其中,萧杀破败的农村就被裹上了一抹浓浓的阴影,似乎侧身于其间的广大农民,背负着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枷锁,而成了混沌、困厄、麻木、蒙昧和无望的一群。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理解乡野群氓的方式。
然而这群乡野群氓难道就是现实的写照吗?鲁迅曾说,“五四”时期的小说,让广大知识分子和农民登了场,而在那些流寓于城市的广大知识分子笔下,为什么偏偏是这群农民充当了有待拯救的“国民性”的代表呢?那些挟洋自重的知识分子为何就有资格自外于民族文化的总体而自信满满地承担了疗救者的角色?像这种开启于鲁迅的现代中国文学乡村书写中的启蒙视角,最初并没有受到多少质疑,而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随着后现代、后殖民思想的引入,才逐渐成为学者们饶舌的话题,但其时,社会政治的思想文化氛围,已经从最初的启蒙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巨变,而转入“后革命”的语境了。很大程度上,本专栏中魏策策的《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城乡视角》,就是通过分析鲁迅启蒙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其借以批判国民性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启蒙话语下的乡村书写范式其实存在着对于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极大误解。“重要的是教育农民”,从根本上来说,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将阿Q身上所深藏的国民精神的劣根性加诸无知无识的乡野群氓,显然并不符合鲁迅的出发点。事实上,启蒙主义的乡村书写到了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一度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而改弦易辙,而后随着阶级革命的群众动员,更进一步地让灰头土脸的农民充当了主人翁的角色。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冲突却从来没有止息,这其中,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保守与激进、蒙昧与文明等等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无不隐含着乡村与城市的对比与互涉。
毕竟任何文学的书写总是离不开现实的折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充满着剧烈的动荡与转型,而新时期以来以“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指引,国家经济生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从内陆经济到沿海经济转型、从生产主导型经济到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对广大在土地上刨食的农民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比如,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新时期之初农民发家致富的梦想;20世纪90年代,伴随乡镇企业发展而引发的城乡和工农冲突;新世纪以来,巨大的农民工迁徙及有关“留守”与“出走”的矛盾等,都是这些影响的折射。而所有这些影响,基本在当代以城市与乡村二元对峙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叙事中得到曲折反映。在城乡互涉的结构中表现广大农民被动参与其间的现代化进程,揭示他们迁徙与流转及由此带来的“留守”与“出走”创痛,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为了必须严肃以待的叙事伦理问题。迁延已久的乡土怀旧仍被重复,但农民工涌入经济发达省份的工矿厂房,这也势必造成书写转移,于是城乡文学成为了乡土文学的新变,而这些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试图影响或者改变生活,一种可称之为“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东西,就成为作家们试图表达而理论家试图阐释的对象。所以,在这个专栏中其他两篇文章中,就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问题,他们“进城”之难,“返乡”之苦,都在其中有着深入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