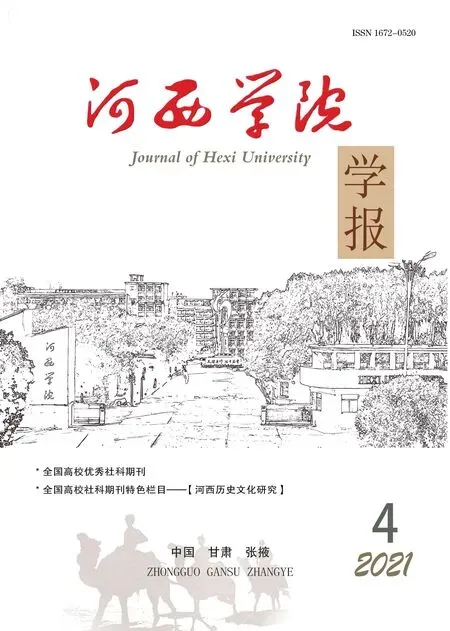晚唐五代宋初敦煌诗僧与归义军政权
冯家兴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引言
诗僧,顾名思义即善于作诗的僧人。作为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诗僧与其诗作也是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然而长期以来,对诗僧群体与其诗歌作品的评价难于客观,对于这一群体本身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僧侣历来被认为是游离于世俗之外的方外之人,僧人的诗歌作品难以被中国传统士大夫等主流创作群体所接受。因此在历代的诗歌整理中,僧人诗歌作品作为传统诗歌的异类,经常是被一笔带过或者不加提及。近代以来,特别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后,大量的敦煌诗僧诗歌作品重新出现在研究者们面前,打破了人们对僧人诗歌作品的固有印象。这些诗歌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不乏古典诗歌中的精品之作。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诗歌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了当时的敦煌诗僧与地方政权之间的互动,这对于人们深入了解当时敦煌地区僧人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敦煌文书中的诗僧诗歌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分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两个具体的地方政权统治时期,对敦煌诗僧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探讨。
一、张氏归义军政权的股肱之力
(一)张议潮起义的坚定支持者
吐蕃赞普郎达玛于842年被僧人刺杀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内斗不休,其在敦煌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豪强张议潮率部起义,855年,唐朝同意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兼领十一州观察使,敦煌从此进入张氏归义军时期。据《张淮深碑》所载:“盘桓卧龙,候时而起。率貔貅之众,募敢死之师,俱怀合辙之欢,引阵云而野战;六甲运孤虚之术,三宫显天一之神;吞陈平之六奇,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破吐蕃之围。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1]127说明了张议潮起义之举经过了相当充分的谋划,而且与吐蕃之间的战争是相当激烈的。《张议潮变文》中也用“星夜排兵奔疾道,此时用命总须擒。”[2]的诗句描述当时凉州之战中将士奋勇杀敌的过程。从这点上来看,在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的艰难过程中,一定是得到了敦煌军民的大力支持,非如此则不能最终战胜吐蕃而收复敦煌乃至河西之地,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敦煌僧团就是当时张议潮的坚定支持者之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姜亮夫先生曾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见过一份编号为P.3249的敦煌写卷,其背面为一份军籍名簿,姜亮夫先生将其抄录下来后,定名为《军籍残卷》。后经冯培红先生研究,认为其“很可能是克复凉州之后,前线将领上报给节度使张议潮的除阵亡将士之外的残剩军士名单。”[3]这份名单所记载兵将共177人,而确定无疑为僧人身份的竟达16人之多,分别为僧曹道、僧邓惠寂、僧李达、僧石胡胡、僧价明因、僧明振、僧法义、僧李智成、僧康灵满、僧裴晏练、僧王眼眼、僧杨神赞、僧建绍、僧安王多、僧安信行、僧□□□,几乎占到名单总数的九分之一之多。另外像任佛奴、石佛僭等名字,也难说和佛教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份名单说明僧人在张议潮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当然,这其中最为突出和耀眼的,还是当属著名的敦煌诗僧唐悟真。作为张氏归义军初期最重要的敦煌佛教僧人领袖,唐悟真参与了张议潮起义,并在后续的政权稳定和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敦煌文书P3720号所载第三件唐悟真告身中曾有“特蒙前河西节度使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4]138的表达,这说明他曾跟随张议潮在军中效力,贡献颇多。同时应当想到,悟真当时作为河西僧团最高领袖洪辩法师的弟子,能够长期随侍张议潮军中显然是得到了洪辩的同意和支持,这也代表了河西僧团最高层对张议潮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上文所提到《军籍残卷》中所记载的大量的僧人加入张议潮军中,直接参与对蕃做战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这些僧兵的产生本身就是河西僧团最高层直接动员的结果。
(二)联接唐中央政府与归义军政权的纽带
敦煌诗僧凭借着自身的特殊身份条件,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出使长安,实际上成为了联系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敦煌诗僧唐悟真。唐悟真在归义军政权建设初期的入京奏事之举,也是其平生最重要的事迹之一。而关于悟真入京奏事的时间,学术界历来有争议,荣新江认为是大中五年,项楚则持大中二年之说。根据《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记载:“入京奏事,履践丹墀。升阶进策,献烈宏规。忻欢万乘,颖脱囊锥。”[4]116以及唐悟真本人所作《百岁诗十首》中“男儿特达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至立一生身。”[5]116及《三五年来复圣唐》中“三五年来复圣唐,去年新赐紫罗裳。千花座上宣佛教,万岁楼前赞我皇。”[5]116之句都可以看出,唐悟真确实曾万里入朝面见唐宣宗,这也是他平生最引以为傲的事之一。但是在唐悟真所作《张淮深碑》中在记载大中二年收复敦煌之后遣使入京报捷之事时,只说“敦煌,晋昌收复已迄,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上达天闻,皇明披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岂虚也哉!”[1]127并未提及自己。对大中五年入京之事,则完全没有提及。
笔者认为,唐悟真应当于大中二年及大中五年两次入京最为可靠。之所以在《张淮深碑》中没有提及,应当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张淮深碑》中所记主人公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建立者张议潮,碑文全篇所赞颂的主角只有一个,即张议潮。根据古人的尊卑观念,在碑文中提及自己的功业恐有喧宾夺主之感,故而没有提及。而且,在大中二年的出使任务中,除了向唐王朝送达瓜、沙二州光复的捷报外,应当还有一个重大使命,即向唐中央政府请求派兵支援张议潮起义军。瓜、沙二州虽已光复,但吐蕃在河西的势力尤在,相比而言,张议潮的军力仍处于弱势,况且张议潮的目标绝不仅止于瓜、沙二州,而是收复整个河西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能取得唐王朝的军力支持,对于张议潮来说,帮助是巨大的。但是从后来的结果可以得知,这个使命并没有完成,唐中央政府并没有给予张议潮太多实际上的支持。因此,如果悟真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自己的出使未获全功而没有提及自己,是可以理解的。同理,大中五年悟真再次入京,仍没有完全获得唐王朝的信任,两个月后,张议潮之兄张议谭被迫入朝为质,咸通八年(867),张议谭卒于长安。而后张议潮被迫接替其兄入京,从此也一去不返,终身未再踏足河西之地,于咸通十三年(872)卒于长安。很难完全排除,作为辅佐张议潮起事并建立归义军政权的唐悟真对此事心怀愧疚,因此在碑中不加提及也是有可能的。
唐悟真进京奏事虽未获全功,但从《悟真与京僧朝官酬答诗十七首》中可知,唐中央政府及京城高僧大德对其在收复河西过程中所立之功勋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从敦煌文书P.3720唐悟真的四件告身中所题序言:“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累在军营所立功勋,题之于后。”[4]139可知,《悟真与京僧朝官酬答诗十七首》当为大中五年入京奏事时所留作品。其中有悟真诗一首,京僧诗十三首,京僧词一首,朝官诗两首。现将文书中京城大德辨章和悟真之间的三首酬答之作录文如下。辨章《赞奖词》云:
“我国家德被遐荒,道高尧舜,万方归依,四海来王。咸歌有道之君,共乐无为之化。瓜沙僧悟真生自西蕃,来趨上国,召入丹墀,面奉龙颜,竭忠墾之诚,申人臣之礼。圣君念以聪慧,贤臣赏以精持,诏许两街巡礼诸寺,因兹诘问佛法因由。大国戎州,是同是异,辨章才非默识,学寡生知,惭当讲论之科,对接瓜沙之后。略申浅薄,词理乖疏,却请致言,俾听美说。”[5]111
悟真作《未感酬答和尚,故有辞谢》答辞曰:
“生居狐貃地,长在碛边城。未能学吐凤,徒事聚飞萤。”[5]111
辨章又作《依韵奉酬》:
“生居忠正地,远慕凤凰城。已见三冬学,何言徒聚萤。”[5]112
从这三首辩章与悟真的酬答诗词中可以看出辨章可谓是充分肯定了悟真对唐王朝的忠贞之志,称他“竭忠墾之诚,申人臣之礼。”“生居忠正地,远慕凤凰城。”并用“圣君念以聪慧,贤臣赏以精持。”这样的溢美之词来表达朝廷上下对他的赞赏。悟真的答辞却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称自己是自边塞苦寒之地而来,并用自己没有像杨雄著《太玄经》那样“梦吐凤凰,集《玄》之上。”的才华,还处在像车胤“聚萤”读书的刻苦修学阶段。悟真的这种回应固然是谦虚之辞,但自己从边塞之地来到唐王朝的京都长安,面对这么多的京城大德,所言未尝不是内心的真实感受。类似这样京城大德对悟真的赞美之词还有很多,如彦楚《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中“辨清能击论,学富早成功。大教从西得,敷筵愿向东。”[5]112子言《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中“愿移戎虏地,却作义礼乡。博学词多雅,清谈义更长。”[5]113等。这些都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悟真献款之义举的充分肯定和对其本人才华德行的钦服。从这点上来看,悟真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让当时的权贵们体会到了边陲之地也有像自己这样的能人义士,同时体会到了张议潮政权对唐王朝的忠心,这对之后归义军的成功建立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从辨章《赞奖词》“我国家德被遐荒,道高尧舜,万方归依,四海来王。咸歌有道之君,共乐无为之化。”可以看出,辨章认为唐王朝之所以“万方归依,四海来王。”是仰仗“有道之君”所施的“无为之化”,那么换言之,河西之地的收复,首功也并非是起义军领袖张议潮,而是当时的唐朝皇帝。类似这样的表达在《悟真与京僧朝官酬答诗十七首》中多次出现,如宗茞《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有“如今政是无为代,尧舜聪明莫比肩。”之言,又如佚名京僧所作《又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中“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的表述等。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当时的唐王朝亦推崇佛教,作为京城的高僧大德,这些僧人与最高决策层接触的机会应当是很多的,之所以出现大量只颂扬唐王圣德而对于张议潮等人收河西之功却只字不提的现象,应当是和当时张议潮势力的快速扩张有关。大中五年,悟真入京奏事,献上瓜、沙等十一州图籍,说明此时除凉州外,河西之地户口百万已尽归于张议潮手中。对于唐王朝来说,陷蕃长达百年之久的河西旧地重归于其治下固然可喜,但是张议潮集团势力的做大也让其心怀不安,担心其封王裂土,成为下一个吐蕃。在这种不信任感和威胁感的驱使下,有意打压和削弱张议潮的功劳,避免其居功自傲,功高震主,是不难理解的。这从同年后于悟真入朝的张议潮之兄张议谭入朝的结果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张议谭入朝后,同年十一月,唐廷虽然下令在沙州设归义军,并以张议潮为节度使,但同时也将张议谭作为人质扣留长安,这说明当时的唐廷对于张议潮政权的确并非完全信任。
以使者身份往来于张氏归义军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的,唐悟真绝不是孤例。在唐悟真为其前任都僧统,诗僧翟法荣所撰的《翟家碑》的最后,悟真特意作诗一首以彰其德,其中有“导众生兮示真诠,播芳名兮振大千。敕赐紫兮日下传,镌龛窟兮福无边。”[4]54之句,点出了法荣曾被朝廷赐紫的事实。同为唐悟真所撰的《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中亦有“名驰京阙,恩被遐荒。”[4]175的表述。说明在张氏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出使长安的活动中,翟法荣也是参与者之一,而且受到了较高的礼遇。
(三)节度使眼中的股肱之臣
敦煌诗僧在张氏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在其历代节度使所授给高级僧官的牒文中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些牒文中毫不掩饰的赞美与肯定的措辞,将敦煌诗僧在统治者心中的分量表露无遗。
如河西节度使张议潮所授给诗僧悟真的牒文就真切的表达了其对唐悟真的喜爱与信任。从敦煌文书P.3770所载大中四年的《敕河西节度使牒》[4]138来看,唐悟真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洞晓五乘,解图八藏;释宗□奥,儒学兼知。纵辩流臻,谈玄写玉。导引群迷,津梁品物。绍隆为务,夙夜为务。”二是“入京奏事,为国赤心,对策龙庭,申论展效。□流凤阁,敕赐紫冠。因我股肱,更为耳目。”三是“又随军幕,修表题书;非为继绍真师,亦军务要害,□前勤效,切宜飘□。”除第一点是称赞唐悟真在佛法上的精深造诣外,另外两点都是对其在张议潮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成绩予以肯定,特别是“因我股肱,更为耳目。”一句,是对其很高的评价。充分说明了唐悟真不仅参与张议潮幕府,且绝非一般的幕僚,而是张议潮的股肱之臣,中坚力量。
又如敦煌文书P.3720《沙州刺史张淮深奏白当道请立悟真为都僧统牒并敕文》中张淮深对唐悟真的评价。张淮深为张议潮之侄,在张议潮入京为质之后统领归义军政权。在这篇向唐廷奏请立唐悟真为都僧统的敕文中,有“悟真深开阐喻,动迹微言,劝导戎夷,实凭海辩。今请替亡僧法荣,更充河西都僧统,裨臣弊政,谨具如前。”[4]139的表达,指出唐悟真有“劝导戎夷”之力,“裨臣弊政”之能。特别是“裨臣弊政”四字,很具有说服力,一般来说,僧人属方外之人,不参与政治,而张淮深却说唐悟真能弥补他做的不足的地方,可见其对归义军政权的参与程度之深。
(四)官学里的名师大德
除了涉足内政外交之外,诗僧还涉足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官学。如诗僧慧菀在张议潮统治时期就曾任“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而且取得了相当成绩,《燉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中记载他:“开张法门,显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徇国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领生徒坐于学校,贵服色举以临坛,若非出群之才,岂获兼荣之授,勉弘两教,用化新邦。”[6]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敦煌诗僧对敦煌官学的参与程度。应当可以认为,以上敦煌诗僧对张氏归义军政权内政外交各种事务的深度参与并非是个案,而是当时时代背景下诗僧参政的一个缩影,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些诗僧对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和河西地区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当予以肯定。
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释吏
(一)唐朝灭亡与敦煌诗僧政治地位的下降
张淮深死后,归义军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多次内乱,最终由张承奉依靠敦煌大族的支持夺回权力,成为归义军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天复十年(910),张承奉知唐已亡,遂建立金山国,自立为白衣天子。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号,复称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归义军时代开始。
曹氏归义军时期,由于唐朝已经灭亡,敦煌高级僧官的任命由张氏归义军时期的节度使向朝廷请求任命变为节度使自行任命,中央政府向僧官们授予封号和“赐紫”等抬高其政治地位的程序消失了。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和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也随之消失,僧团和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更为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再加上归义军政权为防止僧团势力过度膨胀而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僧团的政治地位已急剧下降,张氏归义军时期那些著名诗僧们出入幕府,参与政权各个方面事务的盛况已经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统治者的“释吏”。
(二)世俗政权与僧团更严格上下级关系的确立
曹氏归义军时期,世俗政权和僧团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更加简单的上下级关系,统治者对僧人的控制更加严格,僧俗内外界限也更加分明。这在曾任曹氏时期高级僧官的著名诗僧释道真诗歌作品中有明显表现,如《某人述》:
“能将净意作禅家,唯驾牛羊白鹿车。嫌闹砌前栽树少,怕空不种后园花。菩提上路因修得,佛果无生证有涯。此处涅槃观净土,自然捷路到龙华。”[7]108
又如《依韵》:
“白璧虽然好丹青,无间迷愚难悟醒。纵有百般僧氏巧,也有文徒书号名。定留佳妙不题宣,却入五趣陷尘境。唯报往来游观者,起听前词□□□。”[7]108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作为高级僧官的道真在更为严格的世俗政权控制下,更多地回归到了原本的宗教身份,希望通过诗歌来勉励僧人努力修行,劝诫俗众增加对佛教的虔诚与尊重,不要在石窟中涂鸦。诗中已经没有对现实世界的关照,而基本是从僧人本身的宗教职能角度进行创作。
曹氏归义军时期政权与僧团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从现存的部分敦煌文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清泰肆年(937)都僧统龙辩等牒》所载:
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
“草豆豉壹斗,麦酒壹瓮,谨因来旨,跪奉领讫。右龙辩等忝为释吏,一无助君之功;希履道门,又阙课念之力。昨者司空出境,巡历遐遥。严风冒犯于威严。冷气每临于贵体。不得资荐,兢束倍常。特蒙仁恩,远垂重礼。龙辩等万生荣幸。准合趋步,铭荷军前,伏为奉守城治,不敢专擅。谨遣都头张信盈往彼驰状陈谢,谨录状上。(某乙等阙是从台慈恩赐,诚恐诚惶,无任跃之至,例合趋诣幕下,面拜威容,王格难违,远离怠慢社稷,伏增战惧。)
牒件状如前,谨牒。
清泰肆年十一月十八日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谨牒。”[8]
从牒文所见,当时僧团的最高层僧官包括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在节度使曹元德面前一概称自己为“释吏”。牒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万生荣幸”“诚恐诚惶”“伏增战惧”等表达,这些极度谦卑的用词说明了当时归义军政权和僧团之间上下级关系的严格,任命权掌握在归义军节度手中的高级僧官们似乎变成了归义军节度使的下属,对节度使的一举一动都十分的关心。
(三)颂扬统治者作品的大量出现
曹氏归义军时期,诗僧诗歌作品数量和质量相较于张氏归义军时期都存在明显下降的情况,尤其是表达僧人内心真实感受、体现僧人社会与人文关怀的作品明显不足,而歌颂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阶级的作品增多。如在诗僧道真所存诗篇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道真《上曹都头诗》:
“谯国门传缙以绅,善男即是帝王孙。文商碑背题八字,武盛弓弦重六钧。既出四门观生老,便知六贼不相亲。夜达将心登峻岭,必定菩提转法轮。”[7]109
诗中赞扬曹氏为三国曹魏帝王之后,文则兼通儒释,才学广博,武则兵强马壮,有安定一方之能。此诗无论是序言还是诗歌部分,无不流露着作者对于此“曹都头”的膜拜和敬仰之情。
又如其随节度使曹元忠巡礼莫高窟时所作七言:
“三危山内枲圣贤,结此道场下停闲。侍送门人往不绝,圣是山谷水未觉。一旬僧久住,感动三神赐霜树。□值牟尼威力重,此山本□住僧田。”[7]110诗中将节度使曹元忠比为驾临三危山内的“圣贤”,对其巡礼“道场”(即莫高窟)感到无比的光荣。
佚名诗僧的《仆射颂》(三首)[7]199同样也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当时的统治者曹元忠的赞扬,现将其录文如下:
其一:“自从仆射镇四方,继统旌幢左大梁,致孝仁慈超舜禹,文萌宣迈殷汤。”
其二:“分茅列土忧三面,旰食临朝念一方。经上分明亲说着,观音菩萨作仁王。”
其三:“圣德臣聪四海传,蛮夷向化静风烟。邻封发使和三面,航海馀琛到九天。大洽生灵垂雨露,广敷释教赞花篇。小僧愿讲功德经,更祝仆射万万年。”
诗中充分肯定了曹元忠执政以来的丰功伟绩,称他已经超过了禹舜,是观音菩萨化身来统治人间的。其三中更是称自己为“小僧”,愿意为其讲经祈福。
从道真的两首诗以及佚名诗僧的《仆射颂》(三首)来看,基本没有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诗僧的家国之思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境界,也缺少了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诗僧们出入宫廷、幕府之中,申效展论,在世俗政权各个方面积极发挥作用的大气与豪迈。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对当时统治者依附明显增强,内容上也逐渐单一,基本只有对当政者的赞颂溢美。
由于几乎不再受到中央王朝的节制,当时的归义军政权几乎成为独立王国,节度使掌握了其辖区内的绝对控制权。因此,诗僧的升迁荣辱主要取决于节度使的好恶,而不是完全依靠他在佛学上的修养及处理世俗事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诗僧们为了保住其身份和地位,不得不努力搞好和统治者的关系,听从其驱使,颂扬他们的文治武功和高贵品质,由此逐渐沦落为统治阶级的“释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