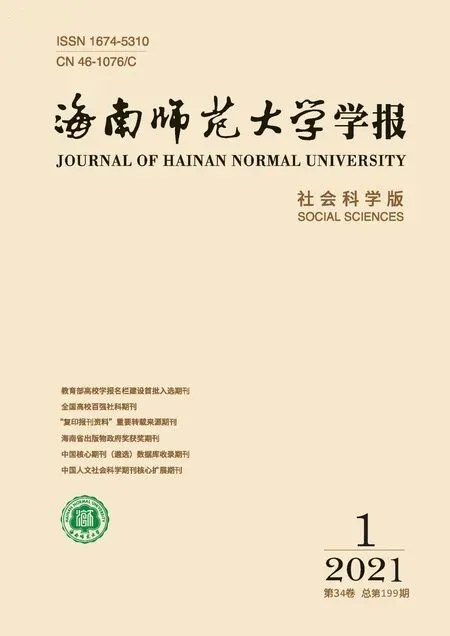反思性与老舍的异域写作
刘东玲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老舍从赴英到返回国内近五六年的时间,即从1924年7月到1929年7月,这段在英国的生活经验,对其影响具有文学发生学的意义。老舍在此期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创作始于1924年9月,1925年完成并寄回国,1926年7月在《小说月报》开始连载;1926年11月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1927年3月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1928年开始创作《二马》,1929年春完成,5月在《小说月报》开始连载。1929年夏老舍结束伦敦生活,在游览了一些欧洲国家后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时老舍担任一所华文中学的教员,一是为经济原因,二是他也颇打算获取一些小说写作的材料,创作了反殖民主义色彩浓烈的《小坡的生日》。
老舍始于英伦的写作源于怀乡,异域生活唤起的写作诉求作为情绪性的无意识投射,固然是直接原因,但于此同时,老舍城市平民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观察现实社会的平民立场,使他对流行的新思潮的审视更多了一层平民视角,这与新思潮的倡导者们的精英主义立场稍有疏离。因此,平民生活经验对于老舍写作的反思性倾向的形成颇有影响。
一、平民生活经验与反思性
老舍出生于北京护国寺西侧小羊圈胡同一个贫寒的满族家庭,其父舒永寿是清朝满族皇城护军,一个下等士兵。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时老舍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靠母亲马氏做佣工维持生活。老舍幼年时在刘寿锦的资助下得以进入私塾读书,1913年考入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7月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9月,京师学务局委任老舍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这段时间的工作使老舍对教育界与社会颇多了解。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厚的待遇和工作的清闲,另一方面则因污浊的社会环境而心生苦闷,老舍一度自我放纵,学会了抽烟喝酒唱戏打麻将,并拒绝母亲为自己娶亲的请求和建议。也是在这一时期,老舍加入了基督教,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担任“知事”,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老舍这些经历和体验对于他感受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人性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后因被上司申斥,老舍辞差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
老舍成长阶段的生活经验对他影响颇深,以至他成年后依然不断强调这种从普通平民的视角观察社会人生的立场,形成了老舍从经验到自觉的独特视角。老舍在1935年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时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这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1)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一期),《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社会与人生经验给予老舍朴素的认知,即关注下层的不幸,但同时对于人性又有深刻的省察,这种认知使老舍对社会与人性的表现并不停留于单一的维度,因而他能在作品中展示复杂的人性与繁杂的世界。《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都是老舍将自己心中记得的人和事进行编排的结果,小说的材料都源于现实生活,因此其现实主义的色彩极为浓郁。
平民立场赋予了老舍看取世界的平视视角,平民生活与传统、世俗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平民对社会的认知是朴素的。这种认知是经验主义的,来自平民阶层的老舍对于平民世界有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因而他对传统与世俗也能从朴素的感知中发现其价值;于此同时,老舍的知识分子视角又使他站在现代理性的立场上审视传统中恶劣与僵化的一面。这种经验与理性兼容的视角给予老舍看取社会与文化的独特视角,避免了精英知识分子疏离大众与世俗社会的有限性:新文学精英大多站在启蒙的制高点上俯视芸芸众生,以知识理性审视大众,大众的知识与理智的匮乏往往成为其批判的目标,以启蒙为主流的 “新文学”普遍呈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众定位。鲁迅小说《彷徨》中叙述人“我”对祥林嫂追问“有无灵魂”时面临的窘迫,恰恰折射出启蒙理性面对启蒙对象时的尴尬与虚无,在传统与世俗中寻求存在价值的普通国民与试图以理性改造国民的精英在现实经验中是缺乏可沟通性的。
老舍旅居英国时期的小说,显然与新文学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颇有不同,后者的写作大多呈现强烈的启蒙色彩。比较而言,老舍则表现出一种平民立场,他来自城市贫民,对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颇能感同身受;又加之老舍并非受新文化的直接影响——老舍是一个在新旧教育下成长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在北平省立师范学校接受的教育更偏于古典的教育,相较于“新文化”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老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开始工作,平民生活经验与社会经验使其获得了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的朴素理解,现实社会有其自身的生存逻辑。老舍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情感与“象牙塔”的青年想象,浪漫主义的态度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老舍对人情风俗、和谐宁静的旧式生活的怀旧,与他的个人生活经验关系密切。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学表现,集批判与留恋于一体,反映出他对传统复杂的情感态度。这些都是造成老舍与新文化之间隔膜的原因,同时这种隔膜又使他对新文化有一种审视的距离,不同于深居其中的新文化人。老舍回忆说:“‘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这个大运动我是个旁观者。”(2)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原载1935年10月1日《宇宙风》第二期)),《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67-168页。“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3)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原载1935年10月1日《宇宙风》第二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67-168页。老舍委婉地解释了自己对世事幽默态度的经验立场,与其说这是自谦,倒不如说正是这种生活经验使他保持了对时代思潮的审视角度。老舍的平民视角使他并不抱“文学救国”的宏愿,基层教育界的经历和认识显然赋予他更客观的现实认知。反观新文学那些述及 “教育救国”论者最终因为现实的黑暗或挫折而逃离教育一职的情节发展,从另一侧面折射出新青年怀抱着主观理想主义,缺乏面对现实的理性,更无从谈及改造现实的实践力。“有的人急于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谓技巧,哪叫控制。”(4)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一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64页。这实际上是作者的谦逊,强调初期的实验尝试色彩,但也从侧面说明老舍对写作功用的朴素看法。老舍的平民立场,使他与激进的新文化立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形成了他对新文化,以及对时代思潮审视的视角,作为新文学独特的部分,其意义与价值值得重视。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化的社会传播并非单元的,而是分层的。文化向社会的传播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新文化传播的第一个层级,其接受对象为身处教育界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大多是当时的大学生或中学生通过教育或新文化刊物获得信息,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介入了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层级,则是从校园到社会,波及到社会世俗层面的新文化传播。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层级的传播大多是正向的,知识青年们接受现代知识教育有利于启蒙文化的传播。而在第二个层级,这种传播是复杂的,受众驳杂,大多是缺乏现代知识教育且处于保守文化氛围中的受众,他们相对保守的文化立场与世俗经验使其对新文化或启蒙更多地持隔膜,甚至反对的态度。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传播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来说,生存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新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的追求或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方式,但对于平民阶层来说显然是有距离的,甚至遥不可及的,其生存境遇与保守的文化影响影响决定了这一阶层与新文化的隔膜与疏离,这种疏离与隔膜是造成新文化以扭曲的方式被他们接受的原因。《老张的哲学》中平民子弟王德和李应虽然对新文化的自由恋爱心向往之,但平民的生活境遇——首先需要工作维持生存,使他们的爱情最终败给了现实的生存选择;对自由恋爱有较理性理解的李静,则被旧文化和旧势力裹挟;浸染于旧文化且利用新旧文化追求金钱利益的恶棍老张,则在功利的层面利用文化为自己谋利,新旧文化的精神价值完全被舍弃。
又如《二马》。老舍对小说中旧派人物老马的塑造是满意的,他比较熟悉老马这一类旧式人物,但他指出自己对小马这一类新人是比较隔膜的。老舍在创作谈中格外强调他在异域时对国内大革命热潮的隔膜,但这些创作谈写于回国后的1935年,与创作时期有一段距离,加之回到国内的老舍已经跻身新文坛,也颇有声誉,他对新思潮的认同颇有“后见之明”的情形,并不能真实反映写作时期的情形。因此,老舍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则是更重要的原因。《赵子曰》中记述的各类新潮青年,如狡猾谄媚工于心计的欧阳天风、功利的武端、头脑简单的赵子曰和反应迟钝的莫大年。这些人物形象在非常浅薄世俗的层面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完全缺乏理性的立场,他们殴打校长,追逐女学生。唯有心地纯正、具备理性与行动力的李景纯是优秀的新青年的典范,而他也显然不同于主流“新文学”的典范。主流“新文学”中的“新青年”大多是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如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他”,或蒋光慈小说中集浪漫主义与革命激情于一身的小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子曰》显然对新文化世俗社会的一面进行了讽刺性的揭示。
老舍基于平民知识分子立场的社会审视,从世俗社会的层面剥开了现实光怪陆离的面向,并成为老舍创作自觉的追求。老舍回国后意欲构思一篇以“五三”惨案为背景的小说《大明湖》,打算以爱情为主线表现两个双胞胎兄弟在学问和爱情之间的选择。虽然这篇小说后来因“一二八”事变毁于战火而未能完整面世,但小说依旧保持了自觉的平民立场。老舍对自己的平民立场这样解释道:“读书的青年男女好说自己如何苦闷,如何因失恋而想自杀,好像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而只有他们自己的委屈很值钱似的。所以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5)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原载1935年11月16日《宇宙风》第五期),《老舍全集》第1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因此,平民经验使老舍同情平民的生存境遇,知识分子又赋予了他审视现实社会的理性视角,并对平民生活深处的污秽的现实进行批判与讽刺;同时,老舍描摹时代思潮与新青年,呈现出独特的反思性:老舍小说中的各色新旧人物,以及社会生活中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使他的创作从更为深广的层面再现了新思潮在世俗社会与文化的三棱镜中折射出的各种色调,其审视性与反思性显然独具意义与价值。
二、异域经验与写作
1924年夏至1930年期间的异域生存经验,是老舍写作的缘起。1924年7月,老舍在牧师伊文思的推荐和伦敦传教会的帮助下,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聘请为该院的中文讲师。老舍在东方学院讲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在上课之余,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开始试笔写作。“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觉得寂寞,也就常常想家。此处的‘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的一切。……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6)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一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62页。人习惯于在熟悉的环境与文化中生活,生活的惯习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面对陌生的环境与文化而产生陌生感甚至不适感﹑不安全感都会对个体带来极大的生存与精神困扰。异国陌生的环境与文化对老舍是直接的经验刺激:初到异地且是异国,从环境到语言都是困扰,陌生环境带来的孤独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加之英国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来自被殖民帝国侵扰之国的老舍,在殖民帝国的本土,作为东方他者的身份格外得到凸显。孤独感与他者感,对老舍写作具有发生学的影响。
1925年,老舍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因此,可以说老舍开始小说创作始于异域生活的刺激,虽然此前他在国内也写过新诗或小说,但那时的创作环境显然与此时直接地对西方文学进行原文阅读,以及异域切身的生活经验和语言环境不同。这一方面,客观上造成老舍对国内流行思潮与生活经验的客观;另一方面,异域生活与文化体验也为老舍提供了直观的反思现代性与西方文化的经验积累:老舍并非仅从翻译传播的角度获取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切身的伦敦生活经验与在异域本土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感受,从生活体验到文化体验的异域经验是老舍初期写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老舍在英国的生存经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他者感受是无所不在的。殖民帝国的本质,霸权主义的政治压迫,以及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无知与偏见、刻板印象等,老舍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不乏真切的体验都在其小说中将之具象化,足见这种他者感受对老舍的深刻影响。《二马》对此有明显的表现。小说中的伊文思牧师傲慢自大,自认为中国应成为英国的属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信仰基督教,将自己视为东方的拯救者的心理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老舍以讽刺的语调嘲讽这种谬论:“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7)老舍 :《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事实上,伊文思牧师是有现实原型的。老舍在国内时就已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在艾温士牧师的推荐下获得伦敦大学的教职,应该说,老舍对艾温士牧师是怀有一定感激之情的;但在伦敦的生存体验使老舍有了近距离聚焦审视西方文化的机会,使他意识到传播西方宗教及文化的传教士作为帝国隐秘的文化代理人,其政治工具的性质是隐秘的。老舍在英国本土的他者感,使他敏感地发现了帝国文化传播隐秘的逻辑,给予了老舍反殖民与审视西方文化的视角。老舍悲愤地在文中表达:“二十世纪的‘人’与‘国家’是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人呢?狗!”(8)老舍 :《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392页。温都太太在没见到马家父子前,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杀人放火、吃老鼠和抽鸦片的;温都姑娘则相信中国人都是挨打的而且不会生气,中国人会用毒药害人;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都是留着长辫子五官丑陋等。这些无知的偏见来自于西方文化的歪曲塑造与传播,老舍在文中格外指出这些来自于英国小说或英国电影中的东方形象,如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折射出普通英国人对于东方的无知与偏狭。
普通英国人无意识地歧视其他种族的偏见、个体的孤独与被歧视感,唯有思乡才能慰籍异域的旅居者老舍;更加之作为普通教员的老舍所得薪资也只够维持简单生活的窘境;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影响等多重的因素使老舍的写作获取了独特的视角。他的英国经验为他提供了对中西(英)文化、两国民族性比较的充足依据。作为新文学阵营的一员,老舍与主流的疏离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的空间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其多重文化经验的影响,使其与新文学保持了一定的疏离,这些因素是并存的。
对于老舍来说,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认知除了书本,还来自于他的伦敦生活经验,使之具有了从真实体验或现实感受的层面了解西方文化的视角。在个人切身的真实经验层面,老舍对英国社会与文化的感受与认识,使其超越了将西方文化看作理性的知识或文化的单一视角;老舍在这种现实的刺激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种族歧视有敏锐的感受,他的伦敦生存经验显然是这种感受的触发器。需要指出的是,老舍在英国在经济上相对窘迫的生存经验,平民主义的立场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老舍不同于徐志摩等其他家境优裕的中国留学者,后者与属于西方社会上层人士的精英知识分子交往更多,且他们的留学生活与现实利益并无太多冲突,无功利的人际显然更为舒缓与温情,因此,他们更认同英式的自由主义;或者毋宁说老舍生存的窘迫使他更接近于西方文化的世俗层面,从女佣到房东、牧师等,这些英国小市民身上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恰恰折射了西方中心主义无意识的渗透。老舍的异域生存经验不仅使他对殖民主义有了敏感性,同时也有助于他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有了自觉的审视,他在吸收英国文学营养的同时,也对其中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辨别。这种理性思辨力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源于西方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现代性与殖民主义构成了其不可分割的成分;另一方面,伦敦生存经验作为直观的经验因素无疑是主要动因,作为外因的生存经验刺激着感情与情绪,使理性的反思作为内因,形成了老舍独特的反思性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并未狭隘地从殖民帝国的角度简单地宣泄义愤,他在揭示英国文化或现代文化殖民性压迫这一面的同时,也理性地正视英国文化及英国人现代文明和进步的另一面。老舍在英国时,1925年结识了失业教员克里蒙特·艾支顿,两人在伦敦西部合租了一层楼,后者提供伙食,前者负责房租,同时两人互相教对方外语。老舍协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还在这段时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无疑,两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对双方都是颇有益的。同时,在老舍与东方学院业务往还的信件中,如他向东方学院秘书询问合同一事,以及他向院长申请提高薪酬。在信件的往来中也足见校方的制度与文明的一面,从某个侧面也反映出英国现代制度的秩序性。又如《二马》中的凯瑟琳鼓励马威读书成才,才能与英国人竞争的细节,以及小说中的西门爵士肯定中国人有做买卖的才干和忍耐力,只是不懂新的方法,并劝勉马威学习新方法。这些人物塑造显然指向那些超越了民族偏见的英国人,也折射出有理智与见识的英国人理性的立场。
老舍在审视英国文化及其文明性的同时,也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他对老一辈中国人自矜古老文明而缺乏自审的糊涂、对“官本位”的无意识崇拜、面子文化、无是非观、缺乏理性精神等方面进行了讽刺。《二马》中的老马作为传统民族性的体现,小马则作为反思父辈传统探索道路的新一代,李子荣则代表了能反思并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务实的新一代。在《二马》中,老舍记述了老马因被亚历山大怂恿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丑化中国人的角色,引起当地爱国华人的抵制而导致古董店铺被砸的事件,对傻爱国与傻不爱国的华人都进行了批评。在短暂地旅居新加坡的几个月间,老舍却对新加坡华人学生激进的反殖民热情高度肯定,认为这里有东方的革命的希望,一改其作品常见的温和语调。老舍在返国期间游历欧洲之后,因资费用尽,只能乘坐三等舱转道新加坡,且还需赚取回国费用。在新加坡,老舍找到一份在中学教授华人学生华文的工作,在此暂居的生活体验使其体会到了华人在南洋生活的不易,同时对他们身上的民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华人开发南洋的艰辛努力,同时对新一代南洋华人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的胸襟也颇为欣赏。老舍在之前创作中流露出来的对时代疏离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似乎有了较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急变,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累积性异域经验在南洋得到了爆发。南洋华人既得不到国内同胞的理解,又受到种族压迫的现实,使身在其中的老舍感同身受,前者身上体现出的忍耐与实干精神,也正是《二马》中的李子荣所肯定的。
同时,老舍在新加坡由于教学的原因,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并获得对南洋华人生活的了解也是原因之一。华人开发建设南洋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孔飞力在其华人移民研究中指出:“作为商人、包税商、城市建设者、工匠以及农民,华人移民在东南亚殖民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9)[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1819年,英国夺得新加坡,其创建者莱佛士宣布对本地从事经商者免征税款,从而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同时莱佛士还划出商业区域,吸引了富有的福建商人入驻。1824—1827年间,一批富有的华商家庭从马六甲移居到新加坡。20世纪初,这个华人商人群体及其下一代,高踞新加坡社会的上层。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地区和海峡殖民地的行政首府,新加坡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华人的贡献。其中富有阶层对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视,而新一代的华人也在其父辈教育引导下,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追求他们的政治权利。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老舍思考殖民问题显然提供了新的思路。英国期间,老舍对英国华人的评价并不高,在对“傻爱国”与“傻不爱国”的简单归类中显然缺乏对其深层原因的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老舍对他们生活的隔膜有关。老舍的东方他者的感受在对南洋华人的体认中得到了答案:幼稚却朝气的南洋新一代华人蓬勃的革命热情代表着民族的希望。
三、英国文学的启示
老舍的异域写作离不开英国文学对他的影响,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以本土经验与语言文化的形式,对老舍的影响既是语言自身的,也是与其英国经验相关的。换言之,老舍并非抽象地获取英国文学的经验。在英国的生活经验赋予了老舍对语言与文学现实性的在地性体验,即他是在对英国自然地理及人事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了解英国文学的,并非来自间接性的翻译文学。因此,老舍对英国文学的汲取是直接的、完全的,没有翻译文学可能产生的误读和误解。老舍通过真情实感获得对小说中的人物氛围、事件的理解,英国人的性格、民族性对于老舍来说是具体可感的,而非想象的。因此,这种在异域本土对其文化与文学的体验与感知给予了老舍不同于一般的比较文化视角,其感性与理性、现实性与理念性的兼容,也不同于新文化传播者通过翻译进行西方文化传播的状态。
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观念通过翻译在中国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可以说,翻译文学功不可没。因此,新文学在形式和理念上深受西方现代启蒙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老舍则不同,他是在异域阅读英语获得直接的文学经验与积累,与翻译文本有明显的差异。新文学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翻译介绍虽然也非常多元,但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作品的译介。另外,基于文学倾向的不同,不同文学团体或个人在译介选择上也有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创造社偏向于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则偏向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介绍。即便对于这些流派的介绍,译介者也是有所选择的;同时,由于译介者外文掌握程度和翻译方法的不同,如有直译和意译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由于译介者对外文的习俗与文化语境的把握程度不同,从而对翻译的准确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加之有些作品的翻译是通过二次转译完成的,如俄国文学通过日文或英文转译等,这种情况对于原初文本的改变就更为复杂。
从翻译理论来说,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认为:“各语言和各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或哲学意义上的可能性,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构成了翻译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也是有一定限度的。”(10)许均、袁筱一等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页。因此,无论翻译,还是转译,都非原初西方文学的本色,翻译或多或少地都有其局限性,有时甚至可能造成巨大的误解或误读。翻译理论家斯坦纳指出:“不能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翻译的”,“不是任何东西现在都可以翻译。”(11)[美]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北京: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1987年,第43-44页。翻译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交流唯一的方式,但翻译总是有限度的,也说明被翻译语言的文化与个性是不能通过翻译得到完全实现的,正如于埃所说:“最好的译文也只能经过不断地修改,逐渐接近原作的要求。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12)[美]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第58页。斯坦纳还特别指出:“在翻译过程中,会在不同程度上丧失内在的含义”。(13)[美]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第65页。可见,翻译是有限度的,很难达到完美的程度,因此,斯坦纳说:“自从修建通天塔以来,百分之九十的译文是不能充分表达原意的,今后的翻译也必然如此。”(14)[美]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第115页。翻译是对不能以外语阅读原文的必要补偿,但翻译是有缺憾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舍通过直接阅读与体验而受到的英语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更为本真和原初的。英语文学语言的表达效果与对英国文化氛围的真实可感的获得,都为老舍的文学写作提供了特别的文学性影响,这不仅是形式与内容,更是具体可感的立体的形式与内容。正如老舍对英国人民族性的了解并非仅仅通过书本知识,更是通过现实的交往与实际的观察等方式,即体验与知识构成了更立体的认知途径。
如果说老舍的异域写作源于思念熟悉的家园的初衷,那么写作的形式则源于异域文学资源的影响:“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Nickleby和PickwickPapers等杂乱无章的作品,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15)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原载1935年9月16日《宇宙风》第一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62页。老舍解释了其域外文学阅读和域外创作的关系:初始时由于阅读积累比较匮乏,他根据当时的阅读有意识地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模仿,随着阅读积累日益丰富,他对形式风格的自觉性也随之提高。在老舍关于自己写作经历的记述和说明中,他时常提及的英国作家,如狄更斯和威尔· 萨克雷﹑沃波尔·哈代﹑康拉德﹑劳伦斯﹑布莱克伍德﹑爱伦·坡、斯威夫特等。老舍写作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时正在阅读狄更斯的《匹克威尔外传》《尼古拉斯尼古贝》等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直接启发了他的写作构思。狄更斯小说中刻画的英国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甚至狄更斯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都颇合老舍的平民立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受狄更斯影响最深的作家首推老舍。在艺术形式、创作风格和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可以从老舍的小说中看到狄更斯的影响。”(16)童真:《狄更斯与中国》,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老舍记述他从写作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后来写作《二马》,特意强调写作《二马》时,在“作”与“读”的方面都有了积累,他因阅读了英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于是将他们小说中的心理分析和工细描写吸纳到他同时期的《二马》中。因此,几乎可以说,异域阅读经验对老舍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老张的哲学》以王德和李应两个少年的视角,以老张为核心,编织出了北京社会世俗的景象——从教育到社会自治的新名头,以及各色人物:投机教育的恶棍老张、旧式乡绅孙守备、旧式军人龙树古、普通市民、青年学生等构成的新旧混杂的北京社会的众生相。《老张的哲学》在主题、情节设置和人物模式上,混合了狄更斯两部小说的特点:在主题上,《尼古拉斯尼古贝》(NicholasNickleby)揭示了平民教育的谋利性质、社会的不平等、下层生活的不幸。主人公尼古贝被放高利贷的叔叔要挟去帮工,并利用美貌的妹妹为自己谋利的情节;在人物模式上,《尼古拉斯尼古贝》中唯利是图的高利贷叔叔,《匹克威尔外传》(PickwickPapers)中慈善仁爱的绅士匹克威克和仆人山姆·维勒与流氓金格尔斗争的情节冲突,以上与《老张的哲学》中正直善良的孙守备和行侠仗义的车夫赵四与老张斗争的情节设置相似。这些都可见狄更期这两部小说对老舍有着显著的相互交织的影响。老舍在《景物的描写》《人物的描写》《言语与风格》等文中用以解释的例证绝大多数都是西方文学,也间接说明这些文学作品对老舍产生的影响。
在英国生存经验的积累与康拉德的影响是老舍写作《二马》的直接原因。《二马》比较了中英两国人的国民性,不能不说这里不仅有老舍异域生活经验的直接刺激,也有其当时阅读的康拉德小说殖民视角的刺激。老舍谈到《二马》时说:“在材料方面,不用说,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可是像故事中的那些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情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因为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都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17)老舍:《我怎样写〈二马〉》(原载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三期),《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老舍当时正在阅读英国当代小说,其注重心理分析和细致描写的特点对老舍写作《二马》颇有启发,他开始“求细”:“我不仅打算细写,而且要非常的细,要像康拉德那样把故事看成一个球,从任何地方起始它都会滚动的。”(18)老舍:《我怎样写〈二马〉》(原载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三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0页。老舍指出《二马》的结构设置——以结局作为小说开端的设置直接来自当时的阅读启示。小说中的小马是新青年的类型,崇尚国家利益,舍弃爱情或家族利益等。老舍表示写作《二马》时正值国内国民革命期间,他正在国外,对实际情形颇多隔膜,但心系祖国,这种爱国的情绪驱使他虚构了马威﹑李子荣这类他并不熟悉的时代青年的形象;同时异域生活经验激发了老舍的爱国主义,他通过作品表达反殖民主义的情绪与思考。他在《二马》中自觉地对中英文化进行比较,尤其是对西方文化中的殖民主义成分、种族歧视的偏见进行反驳,小说中塑造的英国人形象,也颇能反映出老舍的这种愤激情绪——伊牧师的自大、温顿太太的偏狭、亚历山大的偏执等都颇有代表性。老舍在创作谈中谈及这类人物塑造的缺陷:“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成分。”(19)老舍:《我怎样写〈二马〉》(原载1935年10月16日《宇宙风》第三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3页。老舍在《二马》中偏重于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表达表现出其小说有自觉和理性的立意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异域生活经验中的他者感受,以及老舍对英国文学的殖民主义的敏感为其对民族性的比较提供了情感刺激与理性审视的可能性。
老舍在结束海外教学返国之路上,途径新加坡稍有逗留,此地殖民色彩浓郁的种族生存状态,对老舍的刺激更大,他决定写作一部反殖民主义的小说,并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康拉德小说中对南洋的描述使老舍很感兴趣,他意欲寻找那些材料,这里潜藏着老舍反驳康拉德殖民视角的理性意识——老舍想寻找那些让白人殖民者恐惧的南洋世界孕育的生命力。“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吗?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的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们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20)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原载1935年11月1日《宇宙风》第四期),《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老舍对华侨在海外的冒险生活与取得的成就颇为激赏,为国内舆论对华侨的批评颇为不平,对华侨在南洋创业的艰辛充满了同情。老舍对华侨的情感与态度无疑基于他异域生活的经验,感同身受的体验使他对华侨的遭遇颇多感触,他创作了《小坡的生日》这一直接反殖民主义的作品。老舍在《关于〈小坡的生日〉》一文中列举国内人士对于南洋华侨的各种不同说法后,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回击,指出:“说这些现成话的人是只看见了华侨的短处,而忘了国家对这些在海外冒险的人可曾有过帮助与指导没有。华侨的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无论怎样吧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即使仅能写成了罗曼司,南洋的颜色也正是艳丽无比的”,“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是我决定赶快回国看看了。”(21)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原载1935年11月1日《宇宙风》第四期),《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0页。康拉德小说的现代主义技法对于老舍颇有启发性,另一方面前者的殖民色彩又刺激了老舍的反殖民写作,这种复杂性也正是老舍对英国文化的复杂态度,他肯定其文明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殖民的成分,而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老舍异域生活经验赋予他审视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如何理性审视西方文化依然有其启示意义。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老舍讽刺或幽默风格的形成也有着英国文学的影响因素。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与老舍都具有平民立场,前者小说的讽刺风格直接影响了后者,同时后者还吸收了前者小说展示社会世相,尤其是对下层社会悲惨境况的描绘。当然,也不可忽视中国文化——北平市民文化中的幽默﹑讽刺或机智等是老舍吸纳西方讽刺文学的文化基础,加上老舍温和的个人性格等因素也是这一风格形成的原因。文化基础与个人性格使老舍具有对人物与事件的同情性理解,经由他的写作经历被强化和自觉化。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开设中国文学和古代小说的课程,也无疑有助于他对传统的重温与思考。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化约中,以及内外因的合力使老舍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幽默与讽刺风格。
老舍早期异域写作对新文学的反思性是对后者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增益;同时,这种反思性又是建立在异域经验和真正的比较文学和文化视野上的。平民立场与文化反思成为老舍个人风格的自觉追求,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名作《骆驼祥子》,抗战时期的辉煌巨著《四世同堂》依旧保持着这种鲜明的个人风格。因此,可以说异域经验与文学积累发生学的影响对老舍个人风格的形成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