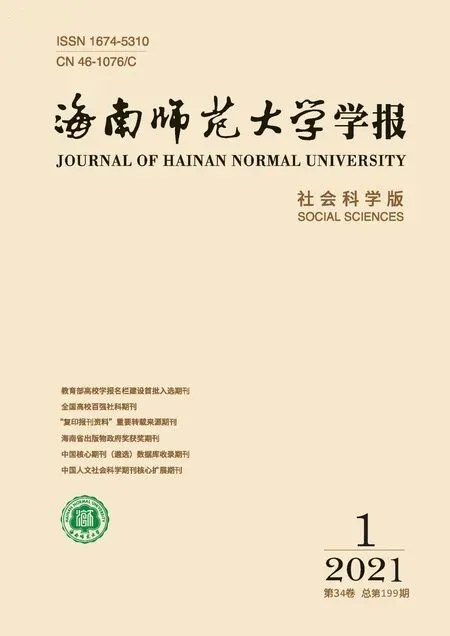思想如何成为变革现实的力量
——伊藤虎丸“鲁迅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意识
王永祥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对于日本鲁迅研究,出色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基于研究者自身深刻的现实体验。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竹内好的《鲁迅》是这样的,其后继者丸山升、伊藤虎丸等人也是如此。相对于他们的研究结论,理清楚他们在鲁迅研究中贯穿了怎样的问题意识则更为重要。一是让我们能够在有别于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看到鲁迅原创性思想所具有的巨大辐射力;同时也启发我们在本土与域外的对比阐释视野中去重新理解鲁迅,从而在承续性的历史阐释中让鲁迅成为参与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活的存在。
一
伊藤虎丸的学术研究,首先是基于对自己参与的政治运动和大学改革的深刻反思。他一方面从鲁迅那儿寻找精神文化资源来解决自己的困惑,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思考,也加深了对鲁迅的认识。伊藤虎丸在他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的序言中,曾这样定位这部著作:“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我以一个大学教师的身份去应对一九六八、六九年以来的‘大学斗争’的副产品”(1)[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过去在大学改革运动中,也可以说是在实践中的所论、所主张、所感重新带回到研究之场来,去重新加以严密的品味和验证。”(2)[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页。伊藤虎丸是在他认为的战后民主运动失败的结局上,来反思自己曾经全身心投入的大学改革运动。他之所以转向鲁迅研究,就要是通过对鲁迅的研究和学习,从自身经验入手,反思日本的现代化。在伊藤虎丸的整个鲁迅研究中,通过不断地和鲁迅对话,来咀嚼自我的现实体验,并将对自我经验的反思,延伸到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反思集中在两个方面:从个人角度而言,新思想如何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而言,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受西方冲击而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日本最后成了侵略者而导致惨败,而中国又是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这两个问题连结为整体,就是如何通过个体的新生而获得整个民族国家甚至亚洲的新生。这是伊藤虎丸从自身经验开始,又超越自身经验而要实现的终极学术关怀。
伊藤虎丸认为无论是他自己参加的战后民主运动,还是始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近代化,其问题最大的症结在于,新思想没能经过主体性的转化而变成自己的东西,思想和理念没有真正变成改变现实的力量。出生于1927年的伊藤虎丸,在回溯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认为他们是“因战败后知道‘民主主义’理念的一代”,并“把‘民主主义’理解为从议会制民主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政党的排列也对应基于‘进化论?’(‘发展阶段说?’)的‘进步’阶段,其顺序是自民党、民社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觉得从社会党往下都是左翼‘同伴’,这些‘同伴’现在虽是少数。但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这一代是否赶得上无所谓,在下一代或更下一代)必定会取得胜利。做如是之想并无什么根据,只是漫然相信比自己年轻的一代总是我们的‘同伴’,因此‘同伴’数量会自然增多。”(3)[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9页。可以说,伊藤虎丸这一代乐观地认为基于战后反思的民主主义思想会在日本扎根,并随着信奉民主主义的一代代人的增多,民主主义在日本必然取得胜利,并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的基础。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民主化运动的失败,伊藤虎丸的这一乐观信念彻底被击碎。“令我感到痛心的是,这种以战败的经验为契机,立足于对战前学问以及高等教育方式进行深刻反省之上的战后改革的理想,结果竟一次都没实现,岂止如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由此所看到的不是惨淡的倒退和只有少许内容被制度化了的惨不忍睹的形骸化过程吗?这当然是历代政府教育行政的责任,但不更是我们大学教师自己的责任吗?我们不仅没能组织起来为实现理想而战斗,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安坐在所谓‘教授会自治’之上怠慢自己的思考。”(4)[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8页。可以看到,民主主义思想并未随着制度建设和学运斗争实现,反而只剩下一些被制度化了的残骸,而且负有思考责任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安居于形式化了的“教授会自治”而丧失了思考力量。在伊藤虎丸看来,“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并未在日本获得实现。这和伊藤虎丸对“战后民主主义”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民主主义”不是说“它作为理念,作为制度的实际状态,作为实体,可以像回答考题那样,用画圈或打叉来表示它正存在着或曾经存在过”(5)[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23页。。“战后民主主义”不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制度,也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是处在各种可能性和力量关系中(恐怕从一开始就是一少部分人的)一种主张,一种希求,一种运动,一种目的和一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战后民主主义”是作为一种思想和伦理意志体现在人的主体性中,是在同各种现实关系的搏斗中的一种持续改造现实的力量。但是新的一代,并不是这样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的,新一代把握事物的方式不再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去把握,而是一种被伊藤虎丸称之为“实体论式”的方式,即“不是作为自己应去主动实现的Werden,而是已经存在的Sein”(6)[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24页。。思想不是经过具有主体性的人去主动实现的能动力量,而成为单纯理解和把握的实体性客观存在。新一代的学生只是按照理念标准去验证现实中是否存在民主主义,而不是将“民主主义”当成行动和实践中的一种可能性实现目标。由此,伊藤虎丸发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后民主化运动”中,思想越来越空洞,不但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和共识,而且在思想分化中形成无谓的对立。一方面是负有思考责任的教授越来越在知识上成为权威,另一方面则是以“实体论式”把握思想的学生来“追捕”运动的领导者。作为思想的“民主主义”成为形式化的制度遗骸,最终的结果就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空洞化”。由此形成日本学生运动的三种势力:居于教授会这一类组织的权威主义者和相对应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而居于中间的则是如伊藤这一类同情学生的教师群体。几方势力形成无望的角力,深处其中的伊藤倍感无力而疲惫不堪。知识化的权威主义不必说,而作为新生力量的学生,“对‘理念与实体之乖离’的愤怒,也在两三年内迅速变为‘反正就那么回事’的无力感(是否可以叫做‘事不关己’?)和冲动性的暴力。只是我说的‘实体论’式的思考,不论‘民青’、‘全共斗’还是‘普通学生’都没有两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伊藤虎丸甚至有了似曾相识的历史感觉,认为当时这种混杂而无力是思想局面,和战前法西斯兴起的局面非常相似。“人们逐渐不再有心思去认真对待学生的‘问题提起’和‘各种要求’,我也逐渐有了危惧感,以为那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前夜的征候”(7)[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25页。。伊藤虎丸感受到思想逐渐空洞化,不但不是变革现实的力量,反而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这样的个人与时代的危机感,引发了伊藤虎丸对鲁迅的重新思考,从对鲁迅的研究中,探索鲁迅是如何学习西方,并将新思想转化自己一生不竭的行动力量。
二
在伊藤虎丸的思想史视野中,新思想显然是来自于欧美,我们该如何对待既是学习对象又是压迫亚洲国家的欧美世界。借助丸山真男、竹内好等人的研究,伊藤虎丸区分出作为思想结果的欧洲和作为精神原理的欧洲。在他的仔细审视中,日本时期的鲁迅把握了精神原理的欧洲,这是一种在整体性中的把握,并转化为自己的主体建构,而作为结果的欧洲只是缺乏整体性的知识、零件。
伊藤虎丸认为战后民主主义为什么没有实现,而且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仅是在战后,在战前三木清等人的倡导中,也没有实现。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复的历史结果呢,伊藤虎丸认可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等思想家的判断。竹内好基于“回心”的概念,认为日本在学习西方时缺乏思想上的“抵抗”,不像鲁迅那样通过“精神”的“抵抗”,将欧洲异质精神变成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日本近代因‘精神的虚位’(缺乏‘抵抗’)而容易接纳西洋近代,急速实现‘近代化’,但反过来说,也就并没有经历过与西洋近代真正交锋所产生的‘回心’,而不过是‘转向’,不过是由‘奴隶’变成了‘奴隶主’”。(8)[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3页。这种因“精神虚位”而来的无抵抗性,就在于日本(或整个东亚)缺乏像欧洲那样基于传统的“思想的坐标轴”。“思想并没有在交锋和积淀的基础上被历史性地构筑起来的‘传统’”,新思想必须是在一种构造化的整体性中被接受,“赋予思想一种构造,一种整合,这在竹内,就叫做精神,在丸山就叫做‘像欧洲基督教那种意义的传统’”。(9)[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5页。
在“精神虚位”的情况下,接受新思想就缺乏“抵抗”,不可能有产生新思想的“回心”,外来的欧洲新思想就会被作为既成品接受。“近代日本对制度或‘机制’(mechanism)的接受,不是从作为其创造源泉的精神——自由主体在严密的方法自觉的基础上,将对象整理为概念,并通过不断检证而使其重新构成的精神——当中来接受,而是将其作为既成品来接受。与之相并行,被抽象化了的结果,也就往往比来自现实的抽象化作用更加被重视。以此而建构的理论和观念因丧失了虚构的意义而反倒转化为一种现实。”(10)[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6页显然,这样的思想接受方式,最重要的症结是接受者主体性的丧失。欧洲思想要变成一种力量,不能将其作为结果或既成品来接受,而是要从其形成的机制入手去把握。
对西方的学习,不是说思想内容或作为体系的思想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学习到欧洲思想结果背后的“神髓”。这里的关键必须是理解欧洲思想生产的机制,而支撑这一机制的,就是对人的理解。人不是被镶嵌到“作为被直接赋予的现实”中,“把自己从‘作为被直接赋予的现实’中一旦‘隔离’开来——即与某个外在超越者相遇,并以此为契机经验‘回心’,通过这一过程把自己从一切中间权威中解放出来,即把自己从作为身边社会(例如家族、国家)和自然(例如性)某一部分的状态中,转移到‘自由精神’(‘人格’)的状态——作为‘认识主体’,反过来把‘被赋予的现实’作为一个交给自身处理(‘合理化’,‘对象化’)的‘对象’来重新把握,并通过逻辑性重构这一媒介对其实行变革。这种‘自由精神’的成立,只在欧洲才有成为‘社会规模’的可能。”(11)[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7页。通过抵抗和挣扎,将自我从被赋予的现实中抽离出来,然后以思想、观念实行对现实的改造,在这其中是思想观念与人格意志的同时诞生,如此,人是一个具有精神自由的人,而不是被所处现实固化了的人。
可以说,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等人的思想判断为伊藤虎丸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这个基于对日本近代化反思的分析框架,最为关键的地方,是人如何获得主体性。在伊藤虎丸的分析中,人的主体性是和终极超越者相遇之下产生的,伊藤虎丸将这种运思方式称之为“终末论”的思考方式。将自己从被赋予的现实(无论社会还是自然)中隔离开来,在获得自由精神的同时,通过“回心”而形成意志和伦理的精神。有了这样的主体性,现实被主体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改造。作为改变现实的思想资源,不论是政治、文学还是科学等学科,都不是从欧洲拿来的零部件,从创造根柢上来讲,是人的主体性的显现,在人的自由精神的创造上具有内在的整体性。
在综合自身的现实体验和竹内好、丸山真男等人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伊藤虎丸并非简单在将鲁迅作为研究对象来检验这一分析框架,如果这样的话,伊藤虎丸只是将他所批判的那种将思想作为结论来应用的转向者,并不会有他所期盼的主体性之诞生;同时鲁迅作为研究对象,充其量不过是印证竹内好、丸山真男等人分析框架的一个工具或注脚。在伊藤虎丸的整个研究过程中,鲁迅被作为一个思想生成范例而被追踪。他在将竹内好、丸山真男等人的“假说的框架”“一个一个地放回到鲁迅的作品中来检对,以使自己能够按照自己所能重新接受的方式来理解,并把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即‘经验’化)”(12)[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49-50页。。他是希望借助鲁迅让自己在思想与经验中生成面对战后民主主义空洞化的精神资源。解读鲁迅,对伊藤虎丸来讲,与其说是得出研究结论,不如说是在进入他所建构的鲁迅世界中进行一次精神的生成。因此在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充满着一种追问的紧张感,这种紧张的背后,就是他想把鲁迅做一个行动的思想资源来看待。
三
可以说,伊藤虎丸正是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刺激和促发之下进入到了鲁迅的世界。重新阐释了留日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进化论以及得之于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意志,并阐释了作为“原鲁迅”的精神生成机制。
在伊藤虎丸看来,鲁迅是从欧洲精神的根柢处来把握欧洲思想文化的,这让鲁迅对作为异质性的欧洲思想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意味着他那时并不是把这些‘偏至’结果的各种‘主义’作为随意更换的‘部件’来把握,而是在其整体性中(不是以文学、科学和政治等等分裂形态)对孕育出这些主义的欧洲近代来加以把握。而且,这也不能不理所当然地反弹到他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来”(13)[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56页。。鲁迅从根柢上整体把握住欧洲精神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意味着对中国文化在整体性认识上的深化和完成。在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背后,是作为精神意志的人以思想方法改造现实,生产文化。鲁迅正是通过“个性”和“精神”的形式,“从他留学时期所接触的进化论、自然科学以及十九世纪文艺当中采摘了这个意义上的欧洲近代的人的观念,并且从中发现了其‘越度前古,凌驾东亚’的新的‘人’”(14)[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61页。。在这样的“人”的观念支撑下,欧洲的文明并不是部分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是奠基于人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整体。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所欠缺的就是这种有着自由精神的人。在中国,因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15)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在民族文化内部发生着“某种根本性精神衰弱和崩溃”(16)[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65页。,缺乏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而只有交织在等级结构中的“奴隶主”和“奴隶”。变革中国的根本,在鲁迅那里,就是通过重新“立人”,打破“奴隶主”和“奴隶”循环。
在伊藤虎丸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败北,但是在败北中也一步步深化着对西方的认识。这种认识到了鲁迅这儿到达了顶点。“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和‘文艺’(即后面将要接触到的作为整合文明之物的语言)使他西欧认识又深化了一步。我以为,这一点意味深长。虽然仅仅是一步,但这一步既意味着中国的‘决定’败北(达到一种整体性认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站在了一个走向新的过程的起点上,那就是朝着‘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迈进。”(17)[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68页。因此,鲁迅在中国思想史视野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从鲁迅开始,意味着旧文化的结束和新文化的开始,这样,鲁迅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从现代革命的主体性形成方面来讲,鲁迅是毛泽东所称赞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精神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竹内好所说的,鲁迅将孙文媒介给毛泽东。另一方面。作为媒介的鲁迅,必须把他所领悟到的欧洲文化精髓,即以个性主义彰显出来的自由精神,意志伦理等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异质性新文化精神传递给具有“白心”的劳苦大众。把他们从“奴隶=奴隶主”的结构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奴隶变成真正的人。那么这样的精神变革如何实现呢。在鲁迅看来,就是能反映心声的文艺,这样的文艺以新的语言通过天才和反抗的心声,破除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污浊之和平,让他们在精神的内面发生改变,变为获得真正有自由精神的人。
可以说,伊藤虎丸对留日时期的鲁迅,是作为预言者形象来生成和建构的。所谓预言者,显然是借用了基督教的思想模式来把握鲁迅。这一宗教式的把握鲁迅的方式,起自于竹内好:
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我还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述。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鲁迅在人们一般所说的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上,不是宗教的,相反倒是相当非宗教的。……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18)[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页。
在这段广为人知的竹内好的论断中,他以宗教的形式来把握鲁迅的精神思想,其论断非常直接,认为鲁迅的思考内容是非宗教的,但是思考形式却是相当宗教化的。应该说,竹内好以直觉的方式抓住了鲁迅思想的特点,而这种宗教化的思想方式,在伊藤虎丸这儿,就是以预言者的文学、“终末论”的思考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鲁迅对欧洲的把握,是以人文学的角度从根柢和整体上来领会欧洲的精神文化。人文学是语言之学,鲁迅对欧洲思想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从“语言的外在性(或超越性)”来接受和理解的。何谓外在性?首先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欧洲思想文化在鲁迅那儿是被当做完全异质性的思想文化来接受。在中国传统中,作为“心声”的诗已经消亡,“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19)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页。的状况中,中国需要异质性的语言(声音)来打破“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而且只有承认这种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异质性,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和欧洲,才能在“抵抗”和“挣扎”中有“心声”和“内曜”产生。代表预言者文学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内发性,和发出这样语言的“人格”密切相关,“这种语言一旦发生,就是针对状况的外在的自立之物,就像以‘春雷’(《破恶声论》)所表述的那样,其本身具有突破现实状况的黑暗、创造新的现实的力量(例如,就像《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是关于‘摩罗诗’的‘力’之说)。”(20)[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88页。可以说,以这种异质性和内发性所领悟的语言,就显示出鲁迅最初的文学运动,“其本身便具有这种堪称‘预言者的文学’的性格”,伊藤虎丸借用浅野顺一的分析,指出与“法规”和“智慧文学”并称旧约文学“三大支柱”之一的“预言者文学”,其性格特点是“它与某种宗教中的通过山林密室的冥思而被给予的个人的神秘体验不同,是和民族命运相关的通过历史和社会的现实讲述给人的神的声音,而且神以此来干涉人的历史,即当它降临时,人便要被迫做出决断,从而改变历史”(21)[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88-89页。。显然这样的预言者文学,和中国传统的作为教化和怡情遣兴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外在之‘力’,是‘动’,它垂降于这个世界,切断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循环’,迫使‘改悔’(自我变革),令人心产生‘恐惧’”(22)[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70页。,“瞿然者,向上之权舆已”(23)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6页。。而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人,就是“精神界之战士”。
四
显然,留日时期的鲁迅所形成的这种预言者文学,以及他所心仪的“精神界之战士”,相对于历史而言,还只是出于“独醒者”的阶段,对于变革历史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真正意义上能够不懈地持续“交锋”和“挣扎”的现实主义文学者鲁迅还没有生成。是在体验了辛亥革命败北的第二次回心发生之后,完成了《狂人日记》的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现实主义文学者鲁迅。是将鲁迅从“独醒者”状态中破却出来,再次拉回现实,由“预言者的文学”变为“赎罪者的文学”,或“现实主义的文学”。
伊藤虎丸对《狂人日记》的分析,紧紧抓住“狂人”的“发疯”状态——其实是觉醒状态,深入分析“狂人”如何由觉醒后的悬浮状态而再次回到现实的过程。伊藤虎丸将《狂人日记》看作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意味着是将“狂人”和鲁迅当作重合的分析对象。“狂人”和代表超越性的“月光”相遇,在他身上,从“作为被赋予的现实”(24)[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60页。中超离出来,伊藤虎丸准确地分析了“独醒者”一旦和熟悉的世界隔离出来之后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从安住的熟悉世界中抽离出来的恐怖和不安感,但要克服这种恐怖和不安,特别是将感性的、本能的“恐怖”和“不安”变为意志和伦理性的“恐怖”和“不安”,有待于对曾经熟悉了的对象化世界的深层次认识和回心式的自觉。
觉醒了的“狂人”,对自己曾经熟悉的世界,进行了对象化的研究。而分析评判的依据,就是留日时期鲁迅形成的“进化论”的伦理观和人的观念。经过对“狂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吃与被吃的世界,是奴隶和奴隶主构成的世界,通过研究那些重重疑虑的“眼睛”,认为这是一个“进化”停滞了世界,是缺乏“精神”(人)的世界。正如伊藤虎丸分析的那样,鲁迅接受的是赫胥黎所阐释的“进化论”,而不是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进化论”。鲁迅虽然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而接受了“进化论”,但鲁迅并不认可人必然遵从天演定律。人是有自己的伦理意志,相对严复关注的如何由“弱者”变为“强者”,鲁迅更关心的人如何由“奴隶”变为“人”,进化序列是“奴隶—野兽—人”,而不是强调“兽性的爱国”所追求的如何由“弱者”变为“强者”。在这样的“伦理化过程”中的“进化”,激发出的人的精神和意志力。“鲁迅极为本源性地接受了赫胥黎思想中所具有的这种基督教式的思考类型,即以‘伦理化过程’对置于‘宇宙过程’,虽是受进化论法则支配的自然的一部分,却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前者,而是在与前者主动进行战斗,去变革前者的过程中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亦在那里,面对代替上帝而出现的自然,去寻求人之尊严的根据。”(25)[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52页。这就是伊藤虎丸根据鲁迅留日时期所接受的进化论而阐释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呼吁的“真的人”。
在“狂人”以进化论的伦理观和人的观念下所构筑的心像世界中,人吃人的奴隶社会终会被打破,终会被“真的人”的世界所取代。但这样的意识只是一种预言式的认识,作为发出预言的“狂人”只是把自己从曾经固化和熟悉的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已。随着“狂人”的认识和反思逐步深入,“狂人”终于在“死”的自觉中,完成了第二次觉醒。由预言者变为赎罪者,在这种转变中,现实主义的“文学鲁迅”才真正诞生。
关于鲁迅的“罪的自觉”意识,竹内好已经做了直观式的说明。但在伊藤虎丸这儿,通过对“狂人”心理意识变化的分析,让鲁迅的“罪的意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框架。伊藤虎丸层层分析了“狂人”心理变化所蕴含的思想潜能。“狂人”由开始出于本能和感觉的“恐怖”,逐步变为被吃的死的恐怖;进一步由自己被吃的“死”,反思到“四千年吃人”的认识,再到最后成为“我也吃了人”。这个时候“死”的意识,再次回到个体,但此时个体意义上的“死”,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的“死”。这样的“死”,“不单纯是终结生命的生物意义上的死,而是出色的社会和人格意义上的死。死的恐怖亦随着作品的展开而从单纯本能的恐怖转变为伦理和人格的恐怖。作品中主人公的自觉,也伴随着对这种死的恐怖的深化而深化,终于达到了罪的自觉”。(26)[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63页。在这种“罪的自觉”中,“不是死在生中被理解,而倒是生在死中被自觉”。“死,是作为与现在的生本身不发生剥离的、迫切的事实来处理的”,这是终末论意义上的“死”,由此在“罪的意识”中而有了深刻的伦理自觉,这种自觉“来自‘吃过人的人’及其世界已经‘无法在自身内部保持其存在的根据’这样一种‘背负死的罪人’的自觉。因为只有经历这种来自‘死’的根本上的‘自我否定’,人才会意识到,才能、勇气、思想、世界观、社会、国家,要而言之,那些一切中间权威都不构成自己存在的根据,而只有在超越这一切,断绝这一切,否定这一切的假定者(即比‘死’更为强有力的东西)面前寻求自己存在的根据,人才会在此时真正获得作为人格的和社会性个体的自觉,即紧张与责任意识”(27)[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78页。。因此,伊藤虎丸看到《狂人日记》的另一面,“看似以‘觉醒了的狂人’的眼睛来彻底暴露黑暗社会的《狂人日记》,如果从反面来看,也并非不能看成是一个被害妄想狂的治愈经过,即作者摆脱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在这种第二次的觉醒中,“他(狂人)在此第一次做到了以自己来承纳自身,他第一次获得了自我,获得了主体性”。
显然,伊藤虎丸在鲁迅身上所建构出来的新主体,并非仅仅是鲁迅自身的思想生成,其中包含着伊藤虎丸自己曾经的现实经验,他是在完成鲁迅形象建构的同时,痛彻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困惑。在伊藤虎丸看来,经过第二次回心,新主体在“狂人”身上诞生的同时,也意味着鲁迅的文学由“预言文学”走向了“赎罪文学”,同时也宣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于:“预言者文学”只是在以新思想来对象化旧世界,将自己从旧世界中隔离出来,但依然是身在局外,还没有在世界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经过“罪的自觉”,在自我内部实现意志和伦理的觉醒,在复归世界的过程中,自己成为自己,不是未来希望和新思想权威的占有者。而是深刻把握住“现在”,并能将各种思想变成体现自己主体能动的时候,现实主义才能成为可能。“从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态度,不仅拒绝以往的依赖于既成‘主义’、‘体系’和‘蓝图’,并要把自己委身于其中的心情,同时也拒绝把自己委身于油然而生的‘自然’的激情与冲动。这是一种既不依赖于过去(既成的主义、体系和体制)也不依赖于未来的一切(程序、蓝图以及‘黄金世界’的心像)的态度,他只面对由死当中所自觉到的现在。”(28)[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82-183页。一旦回到这样的“现在”,也就意味着这是真正有自由精神的个体。把思想、文学收归个人,并能用严密的科学方法重构现实,由此开启了鲁迅现实主义的文学之路,《狂人日记》之后的文学创作才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呐喊》的各篇作品是有自觉意图的产物:‘狂人’在‘摆脱自我’中获得了的‘自由精神’,这使他‘把自我从作为被赋予的现实当中一时隔离出来,并在严密方法意识的基础上重构自我’(‘虚构处理’),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作为‘变革现实的杠杆’(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正可以说这是对‘作为现实批判的方法的近代现实主义’(《风俗小说论》)的完全正统的接受吗?”(29)[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81-182页。
从鲁迅早期在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到回国后创作出《狂人日记》,伊藤虎丸以终末论的思想构造方式,分析出作为作家的鲁迅是如何一步步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汲取鲁迅思想以解决自己在现实中的困惑,另一个方面也呈现出他所心仪的现代个体应该具有怎样的主体性和精神内涵。
五
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从纵的方面来看,是“竹内好鲁迅”的延伸。竹内好所提出的文学者鲁迅、赎罪的意识、无、回心等概念,依然是伊藤虎丸用来把握鲁迅的基本参照。竹内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从“现象鲁迅”(政治的、启蒙、论争的等鲁迅形象)中,分析出一个“本源的鲁迅”,即所谓的“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伊藤虎丸从竹内好这种本源和现象的划分中跳出来,并将自己的研究放在这种划分的延长线上。他以终末论的构造方式,并未去追寻那个“本源鲁迅”是什么,而是从“现象鲁迅”的演变中,把“竹内好鲁迅”构造成可分析的结构。因此,他不同意竹内好所认为的鲁迅的文学创作的是有直观而无构造,恰恰认为科学者鲁迅掌握了最为纯正的西方思想构造方法,在完成《狂人日记》后的鲁迅,能够用体现科学精神的方法,构造出作品世界,从而掌握了真正意义上现实主义方法。因此相比竹内好的直观式的把握鲁迅,伊藤虎丸更侧重于鲁迅思想模式的演变以及构造方法,从而在“竹内好鲁迅”的延长线上,更为具体的生成了鲁迅的形象,并借助竹内好和鲁迅,阐释了他的“个”的思想。
如果把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和比他稍早的丸山升的鲁迅论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伊藤虎丸鲁迅论的这种偏重于思想构造的特点。丸山升的鲁迅论和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应该同是“竹内的鲁迅”的延伸和深化。作为共产党员的丸山升,同时一直纠缠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和身为大学教师的伊藤虎丸不同。丸山升更看重作为行动的鲁迅,因此他提炼出“革命人”的鲁迅。“革命”在丸山升的思想中,类似于一个统合了本源和现象的概念,“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30)[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文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革命”是一种融合思想与行动的状态,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体系,因为相比完成了的终极目标,丸山升更为看重的是连接思想与终极目标之间的行动,“思想为了推动现实、转化成现实的话,不仅需要具有终极目标,而且应该具备联结目标和现实间的无数的中间项。如果缺少了中间项,思想就无法推动现实。因此实际上,比起终极目标,思想更是以中间项的方式得以体现并被尝试的。”(31)[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文俊译,第62页。因此,丸山升更看重鲁迅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他是以极端的实证方式从鲁迅式的“革命人”的活动中体会精神和思想,“鲁迅在与我们不同的状况中所把握并施行的对于‘革命’的态度——如果稍微跳跃式地加以断定,也就是将“革命”视为确实具体地变革现实的事业——和扎根于这种态度的对于‘革命’的现实的认识,才正是我从这个时期的鲁迅身上最希望学习、吸收到的东西。”(3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文俊译,第48页。
可以看到,如果说伊藤虎丸是从思想的构造方法中学习鲁迅如何把握思想并形成主体性,那么丸山升则是在鲁迅的行动中仔细辨析作为革命的精神和意志。两者都是通过鲁迅来回答自己问题,并生成自己的鲁迅形象,可以说都是切合自己的精神需要和实践历程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而言,伊藤虎丸并没有用现代性、全球化等时髦理论来搭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毋宁说还是很传统的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变体。在这一变体之下,就是内含的亚洲视野。那么伊藤在这一视野下所反思的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日本,如无根柢的思想杂居性,思想如何在个体上发生,而个体又如何投身现实,真正将思想变成现实存在的力量,特别是从“终末论”的构造方式上所阐释的“个”的意义及鲁迅思想。这是一种真正统合了个人性和社会历史性的深刻而宏观的对话。如此生成和建构的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思想生产性的鲁迅。
经过激烈的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战后日本的战争反思和高速经济增长合为一体,经历了战争惨痛的日本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样的历史不能不让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进行深刻反思。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的经验进行反思,特别是以人文角度进行的反思,核心问题是聚焦于受西方影响之下人的观念的演变。如何把受到权力异化的人重新变成真正的“人”,成为追问近代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由此联动起对近代以来的政治、科学、文学等的深刻反思。在伊藤虎丸等人的视野中,“鲁迅”的诞生意味中国新主体、新文化的产生,由此将中国近现代史做了和新民主主义论大致相近的划分。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文化发生的指导性纲领,反封建反帝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和文化创造中内含着一种主体性的诉求。如何剥离包裹在这种诉求之外的日渐僵硬的政治外壳而留下有价值的思想启示,并在近现代的整体性视野上重新审视鲁迅的意义,这就是伊藤虎丸在终末论意义上重新阐释个人主义、个性、“个”等有关“人”的概念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伊藤虎丸等人统合了战后反思和时代新需要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有别于西方的东亚语境下的“个”的意义上的“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回溯中国近现代史,对近现代文化以鲁迅为核心进行重新阐释,重新疏通历史的脉络并激活历史探索的可能性,这是伊藤虎丸等学者的鲁迅研究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