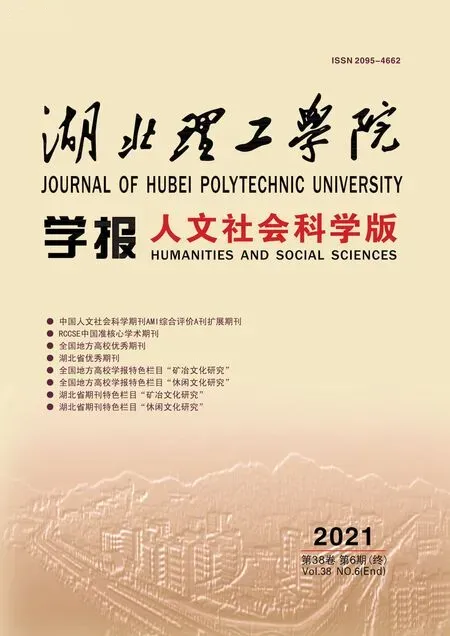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大学思政教学技术改革的启示及反思*——以“学习通”平台为例
张耀天 刘秀莲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技术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词汇以前所未有的烈度渗透到“互联网+”时代。它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空突破效应——某种程度上腾挪了人类现实生存的环境,呈现赛博空间的新生存境遇[1]。智慧课堂的出现,是迎合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发展潮流、大学教学实践环境呈现的新现象。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大学教学环境、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在线学习、混合学习、翻转学习、移动学习、智慧学习等新兴学习模式给传统大学思政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强势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涌入大学课堂,成为颠覆传统课堂的主导性力量;从教学理念出发,人工智能的高仿真导向,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师生教学的精准总结与预判,真正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主导方向;在教学模式中,传统大学教学的师生互动模式,逐渐转变为教师、学生和人工智能之间的三元互动[2]。人工智能对大学教学实践的革命性改造,既保留了传统教学实践中的相对优势,又借助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把技术力量融入到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业已成为当前大学思政教育改革的主流方式[3]。
2017年开始,我国政府主导将人工智能的研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把人工智能学习、机器学习等关键技术作为推动新时代大学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社会资本大量涌入大学教育智能改革的浪潮中,无论是国际品牌IBM、沃森等,或是国内科大讯飞、中国知网、超星等企业,纷纷抢滩市场,推动大学教育教学大数据化、智能化的发展[4]。以笔者所在的湖北师范大学为例,2017年起,在大学思政教学改革的领域内明确信息技术改革的方向,加之疫情期间在线学习模式的有力助推,目前全校2万多名在校大学生均通过超星公司开发的“学习通”软件,实现混合式教学的新模式[5]。“学习通”等智慧教学软件的课堂导入,实现了教学管理、考试管理、学习管理、教务管理等环节的数据管理和智慧分析,把教师从传统繁琐的教学管理中解放出来,也通过智能推送、智慧学习等方式有效地提升大学生学习效率[6]。但深层的问题在于,“学习通”等学习平台理应成为教学实践的工具,在传统课堂教学环境中仅能起到教鞭的作用,而在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反向地引导着教学实践的展开,以强势的工具理性反噬着师生主体价值的实现。由此,对“学习通”等智慧教学软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在探索大数据时代大学思政教育改革实践的发展路径,也能够以智慧教学、智慧教育、智慧课堂为研究的切口,管窥大数据时代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数据时代人的技术化生存境地问题。
一、创新和冲突:教鞭的革命和技术的赋能
大数据技术所实现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主流趋势,也成为大学思政教学改革的主要模式。它主要是指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支撑背景的环境下,把互联网的相关要素、大数据的相关理念、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有效融入到大学思政课堂教学展开的各个环节,以实现技术改革和教学创新两者深度融合为目的,共同服务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大学思政教学新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介入大学思政教学实践过程实现着技术的赋能,同时引发着教鞭的革命。在教学技术创新上,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智慧课堂主要是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教学形式创新。智慧课堂完成了从实体教学到虚拟教学、从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的整体性腾挪。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以实体教学、线下教学为主,师生在固定的教学场所进行面对面的场景授课,受到时间、地域、空间的局限。智慧课堂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创造性地生成了在线学习、混合学习、翻转学习、移动学习、智慧学习等多样化新兴学习模式,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丰富了课堂教学活动形式[7]。
以“学习通”平台为例,在大学思政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利用学习平台展开教学活动,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给学生发送学习课程、学习任务;学生可通过平台与老师同步、异步进行学习,教师不仅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授课,还可以通过点播、线上答疑等形式展开课后辅导。“学习通”打造的线上教学、虚拟教学,灵活性强,且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线上教学比线下教学更加具有开放性、反馈及时性等优势,具有传统教学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当前大学思政教学技术革命的主流形式[8]。
二是,教学素材创新。在“学习通”等智慧课堂的教学平台内,教学素材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从单一的读本到电子书单,从素材匮乏到海量信息,教学素材的创新在吸引大学生眼球、满足求知欲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的教学生态。在传统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常以课本教材作为主要授课资料,课本教材更新周期长、知识内容陈旧、理论内容居多,教师的教学素材匮乏,课程资源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但在“学习通”等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中,海量性、互通性、开放性的互联网信息丰富着教学资源,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视频等资源,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学习资源。同时,各种慕课、在线课程、金课资源等互联网资源,推动着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教师不再单纯依靠传统读本作为授课素材,可以通过“学习通”快速获得大量相关的素材,满足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之需[9]。
三是,教学管理创新。在智慧课堂的环境内,整个教学管理环节,全部能通过线上管理实现。以超星“学习通”平台为例,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实现020教学环境的全程动态监控:教师在课前,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向学生发“一键签到”指令,系统自动对学生进行实时考勤统计;在课中,可以通过系统实现课堂交流、资料共享、课程任务发布、弹幕评论等,实现教学行为的数据可视化,方便教师全程管理;在课后,可以通过平台进行课后学习管理,定向向学生发布课程任务,实现在线考试,并利用系统检查学生学习进度和作业完成情况。“学习通”具有强大的数据统计管理功能,直接与学校教务处的后台实现无缝链接,实现统一的信息数据管理、成绩管理,优化了教学管理模式[10]。
由此可见,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教学技术的传滚,增强了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的互动性,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学生参与度,实现了以教学为中心的虚拟教学场景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都被大数据技术赋予新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时空赋能。智慧课堂教学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有效实现了碎片化时间教与学。传统课堂往往需要学生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场地进行课堂教学;智慧课堂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在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技术综合打造的智慧课堂平台内,全程的教学活动可以在线上进行,进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实体教学、线下教学腾挪到线上、虚拟空间内[11]。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活动,均是在各类教学平台内实现,进而也加速了互联网教学的普及程度。传统教学实践无法突破的时空限制,在智慧课堂搭建的“赛博空间”内成为司空见惯的教学常态。
二是,魅力赋能。在传统教学场景内,教师的教学素材匮乏、教学模式单一,在授课方式上或是在教学管理上,基本都沿袭着统一的板式化教学。传统教学模式,不仅难以做到因材施教、难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也很难通过教辅工作,实现教师个人的魅力展现。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内,教师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剪辑视频、电子读本、信息资讯等素材辅助课堂教学,通过海量信息丰富和完善教育内容,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激发课堂学习的活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教师将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有利于释放课堂教学活力,体现新时代教师的教学魅力。教学的教育智能化、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已然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方向,教师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学活动中,既能为现代教育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也有利于推动大学思政教育与新生代“数字原住民”大学生的融合[12]。
三是,整体赋能。根本上实现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随着网络教育的发展,教师要对自身职业角色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位,提高自身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能力,更好发挥智慧课堂的优势,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水平。以“学习通”平台为代表的智慧课堂,从整体上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促进了教师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和各种教学媒体能力的提高。实现课堂教学控制,教师必须能够根据各种条件变化,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选取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教师也可以将先进新媒体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如抖音视频教学、VR体验教学等,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生动直观,实现活跃课堂氛围、提升课堂效率的整体效果[13]。
由此可见,“学习通”等智慧课堂教学软件的介入,活跃了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学氛围,契合了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和思维活跃度,大数据技术为师生教学增加了科技赋能,提升了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形象诊断式教学。形象诊断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对着装、仪容、表情、体态、举止等内容学习后,教师现场组织形象诊断活动,包括自我诊断、相互诊断、集体诊断。其中相互诊断、集体诊断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点评,通过学生对所学礼仪规范的掌握,进行诊查判断。最终达到学生对警察礼仪理论知识的掌握。这种方法适合在一个完整章节完成之后进行。
二、异化和同化:技术的反噬和算法的“共谋”
人工智能技术和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技术不同,它具有高仿真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除包含着大数据技术容量大、种类多、速度快、价值高等优势,与传统的信息技术相比,它在先天的技术优势上被赋予更高的天赋,能够通过算法逻辑高度模仿人类的思维。从这个角度出发,依托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理念所构建的智慧课堂教学体系,把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内化为技术范式,并作用于教学实践。和传统信息教学技术相比,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课堂软件,拥有整体化处理教学管理流程的能力,在采集师生学习的数据信息的同时,把相关数据纳入到课堂管理的分析系统,把老师从繁琐的教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洞悉课堂管理生态的基础上,依靠大数据的分析系统实现教育管理智能化。问题在于,在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课堂教学体系中,强势的人工智能技术反噬教师的主体价值,在逻辑算法挟持下,成为凌驾于传统教学实践之上的新主体。技术创新的代价在于,新的教学模式提升师生的教与学实践能力,但深层的伦理危机在于未来人机协同成为现实,人成为被大数据技术异化的符号,教师遭遇空前的能力危机和主体危机[14]:
一是,学生学习能力增强,出现学生在信息技术领域“反哺”教师的现象,教师的话语权被削弱[15]。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结合的双边活动,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教学的主导作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中,强势渗透的信息技术打破了教师对信息、知识的垄断地位,与之对应的是学生能够游刃有余于互联网教学,消解了传统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主体地位[16]。以笔者所在的院校为例,不少中老年教师因技术隔阂而被“数据鸿沟”疏远智慧课堂教学,他们反而向大学生“求助”以便熟悉某些教学程序。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课堂的出现,转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既是接受教育的客体,又是认识和学习活动的主体,其学习能力增强,主体意识不断提高,事实上解构了传统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的师生关系,教师的主体话语权也被实际地削弱。
二是,强势的大数据技术理性冲击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大数据时代强势的工具理性以追求最大功利为目的,过度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而非价值的实现,体现在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忽视教育价值目标、过分强调炫目的技术。在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许多教师对新媒体技术运用不够娴熟,无法真正驾驭新的教学技术;面对海量的信息、教育素材、教育资源,部分教师缺乏辨别和筛选的能力,通过网络上收集的教学素材没有进行有效整合,而生搬硬套、生硬启发的现象比比皆是;再有就是,部分教师在使用“学习通”的过程中,过度重视新媒体展示课程内容,却根本上忽视了教学的内在本质。在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极易失衡,教师逐渐弱化主体的目的意识和批判能力,极有可能沦为大数据技术的“奴隶”[17]。
三是,在智慧课堂教学环境中,师生二元互动模式被技术演绎为师生和人工智能的三元融合过程,人机协同教学成为主流模式,教师的主体地位呈现式微的态势。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大学思政教学,将传统的师、生二元互动模式转变为师、生、智能的三元互动的模式,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占据的权威地位,以及绝对优势的主体性地位[18]。
由此可见,智慧课堂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具有技术“双刃剑”的两面性,既能推动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技术异化的现象。人工智能技术赋权大学思政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在实现信息自由传递、资源共享的同时,出现技术理性的扩张性发展,导致师生对信息技术的过度依赖,人逐渐成为智能技术的“俘虏”[19]。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技术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弱化师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学习通”平台为例,智慧课堂只是作为教学实践的技术化工具,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并不是被动接受学习,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具有自主选择性和主观能动性。然而在技术的强势渗透下,师生过分依赖技术,逐渐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和自主性,教学的价值理性也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弭。
其三,抑制创新性思维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强烈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模式,大数据以其海量性、信息更新周期短的特征,使人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智慧课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提供知识和资料内容本身的同时也规定内在的思考思路和思考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师生的创新型思维发展。
三、沉沦和救赎:主体的消解和价值的重整
以“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课堂教学技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教师的教学强度及教学管理的繁琐,但技术创新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某种程度上讲,强势的技术成为反噬主体价值实现的主要原因。大数据技术所衍生的工具理性,及在算法逻辑基础上实现的技术倾轧,侵占了原本属于人的主体价值实现领地。问题在于,大学思政教学的底色是人文教育、价值教育和反思教育,强势的技术性教学极易导致教学实践丧失文科教学反思批判的能力,人成为被机器符号、数据符号管控的“傀儡”[20]。大数据实现智慧教学能力的过程,也恰好是师生教学实践被工具化的过程;人在享受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被异化为数据符号,人成为自己实现自由过程中所创造工具的“奴隶”——大学思政教学实践的改变、“学习通”的教学场景,仅是整个世界被强势技术支配的一个缩影。这也意味着,在技术倾轧、主体沉沦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实现价值的救赎,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21]。
如前文所言,必须警惕技术反噬主体的现象。传统的大学思政教学过程中,师生通过正常的教学场景的交流、人文情感的交流和信仰知识的交流,完成意识形态的灌输和人文精神的传递。而在“学习通”的教学环境下,数据平台直接把师生交往的情景腾挪到“赛博空间”中,以大数据环境集成虚拟的教师形象,引导大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教师的主体危机业已呈现。“学习通”被强烈赋权为师生交流的唯一“中介”。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被异化为数据的符号,更重要的隐患在于可能彻底丧失了主体价值[22]。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交往主体间性的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教学实践,不仅强调传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强调多个主体之间的交流。在“学习通”的教学环境中,业已实现了从师生二元主导的教学交流实践,转变为师生和“学习通”等智慧课堂教学软件之间的三元互动新模式:既可以把“学习通”的教学实践理解为双主体的教学实践的展开,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主体间性关照下的“新主体”。在新教学环境中,大学生、教师和“学习通”等教学元素,都是积极参与大学思政教学“主体要素”,以这种观点来反思大数据教学实践,既能够客观公允地对技术教学进行评价,也可以以这种视角彰显和巩固主体的价值。如仅把大数据技术视为师生异化的罪魁祸首,则既不能有效地对大数据带来的正面积极影响展开公允的评价,也不利于大学思政教学技术改革的落实。从主体间性理论出发,超越了传统的教学主客体二元认知结构,实现了最大程度的主体和谐和“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23]以主体间性理论对该现象展开反思,既能有效规避大数据技术的强势反噬,也能理性推动师生双元互动的学习实践的展开。
四、展望与未来:主体的同情和理性的可能
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下,技术的异化是经典的哲学问题,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在如此背景之下,教学主体的概念发生了新的改变,海量的教学信息和教学经验涌入的传统大学思政课堂教学的环境中,大数据技术、智慧课堂已经内化为传统教师的主要替代品。教师的权力、权威和教学魅力被无情地消解,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成为人类教育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意味着传统的教学实践发生了改变,在此基础上人作为传统的教学实践的主体,招致了颠覆性的解构,问题在于数据智慧课堂所构建的数据权力凌驾于课堂权力之上。教学权力的赋予者不再是传统的知识读本,而是来自于虚拟世界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所构建的新的教学生态,是建立于信息技术、算法逻辑的基础之上,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中,大数据技术可以清晰地记载每一个师生的搜索轨迹、学习动态和整个学习实践的学习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人被数据技术凝化为跳跃的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人引导数据技术为传统的教学实践服务,相反的是人的思想、教师的主体作用,唯有归顺于数据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的解放,数据拥有了同化思想的新权利[20]。
智慧课堂是大数据技术发展的现实成果,某种意义上讲,它充分实现了当代科学技术至上的理念,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数据技术不仅对整个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同时通过算法逻辑、算法价值等数据理念构建起全方位渗透的课堂管理方式[24]。隐藏在智慧课堂背后的大数据掌控着可以轻易地操纵管窥师生的个人信息,师生无处逃匿、无处隐身,个体的价值被资本的力量所绑架[25]。数据的力量牢牢地掌控着课堂管理的高地,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课堂生态的统治者,传统教学实践被腾挪于线上,成为虚拟化的“赛博空间”,传统课堂师生的互动也成为虚拟课堂环境下跳跃字符之间的碰撞。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学思政教学以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权威为主导所构建的课堂实践活动被彻底的消解,这些都意味着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也意味着要重新反思和警惕数据技术带来的种种隐患。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主客一体、道器一元,这与西方侧重于主客体二分思维的倾向截然不同[26]。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体的争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主体间性的理论,强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外,以交往理性的方式来解决技术异化对人主体价值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向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致敬,也提供了理解大数据技术历史发展语境下、理性看待大学思政教学技术改革现象的新视角。“学习通”为代表的智慧教学平台,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把教师从繁琐的教学实践中解放出来,但强势的技术理性反噬主体价值呈现,也成为大数据实践主体危机的一个缩影。对它的批判和反思,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待技术应有的理性态度:唯有明确重塑人文价值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地实现技术与社会环境的技术变革与未来冲击的融合。正如托福勒在《未来的冲击》所言:“这才是社会未来主义的最高目标:不仅要求超越技术中心主义,还要以符合人性的、更具远见的、更民主的计划来取代,更要求将一切进化过程置于人类自觉的控制之下,因为此刻,人类不是征服变革的过程,便是被变革的过程所吞没;不是成为进化的牺牲品,便是成为它的主人,这是人类历史性的转折点。”[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