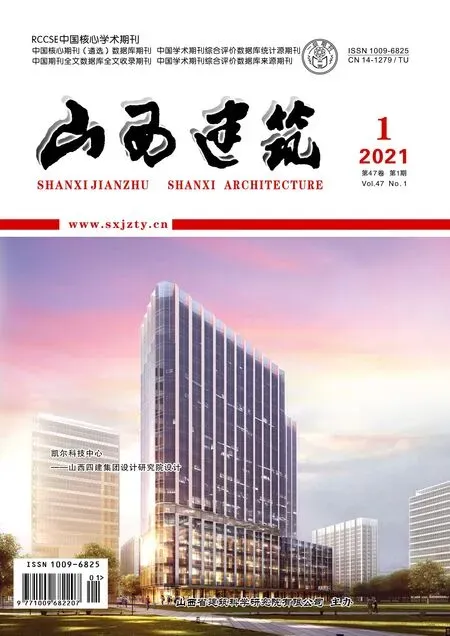淡水环境中微塑料及其污染物去除
王金鑫 刘振中 江 文 吴 阳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0 引言
粒径一般低于0.5 cm的塑料颗粒在学术上习惯称为微塑料,是人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污染物,它在慢慢降解的环节中会不断排出人工助剂。因为其尺寸不大、疏水能力高,极易依附在有机污染物中,与微生物生成综合性污染物,在被水生动植物吸收后,其毒性将在食物链中传达与聚集,并对水生系统乃至人类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这些年来日益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塑料已经在海洋、淡水和陆地生态系统中随处可见,甚至包括赤道和极地。现代社会对海洋环境的分析基本成熟,对淡水环境内微塑料的分析相对比较落后[1]。国内外的分析也在含青海湖、洞庭湖、鄱阳湖、莱茵河等相关内陆水系内找到了微塑料,部分淡水环境内的微塑料含量较多地超过了海洋系统。而太湖表层水体样中发现的微塑料丰度最高为6.8×106个/km2,为全球淡水湖泊中已找到的最高浓度[2]。淡水环境的微塑料污染与海洋环境相比,研究程度较浅。尽管研究有限,但在偏远地区的淡水环境中同样发现微塑料污染,这表明在淡水环境中微塑料遍布世界。淡水环境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十分关键,还是陆地环境和海洋环境中微塑料转移的渠道。W.D.Jean-Pierre等[3]研究后表明,海洋中的各种微塑料均是源于淡水环境。更可怕的事实是,利用显微拉曼光谱分析,在饮用水样品中都检测出纤维占主导的微塑料。由此可见淡水环境中的微塑料污染的严重性。
就微塑料展开的分析最开始重点聚集于海洋内微塑料的划分、检查与毒理学分析方面。因为对微塑料问题分析的持续推进,许多研究人士开始注重淡水内、污水处理厂内的微塑料状况,所探究微塑料的尺寸也从毫米级往微米级乃至更小的粒径发展。另外,微塑料在转移时也许会有污染物附着在上面,并与其一起在环境内转移与排出。微塑料对污染物(含对金属元素、有机污染物等)的吸收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毒性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微塑料对污染物的吸收会让之前干净的微塑料与污染物一起,提升了直接吸收微塑料生物的污染物暴露风险。
1 淡水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特征
1.1 淡水中微塑料的来源
进入到淡水中的微塑料有干净的与化妆品内的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分子,其以排放生活污水的方式进入到水生生物内。其他微塑料含塑料树脂粉或使用在喷射颗粒的工业用途上,以及使用在生产塑料制品的原料上。常见的雨水蓄水池在微塑料从陆地向水生环境的运输中发挥作用。污水处理厂也是微塑料进入到水生系统中的一种主要方式,此类工厂在沉积、凝聚等作业后,超过98%的微塑料被处理掉,虽然处理率十分高,其出水内每天也包括6.5千万个微塑料[4]。也有研究获得了与上述结论十分接近的结论,生活污水在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后,就一条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的河流分析了解到,污水口上方的微塑料浓度应远远小于出水口下方微塑料的浓度。污水厂能解决众多的塑料微珠,然而由于污水处理量相对较大,因此始终会有较小量的塑料微珠被排出。对塑料加工,尤其是废弃塑料再次利用导致的二次污染[5],需要我们额外留意。
进入淡水系统内的次生微塑料对比其原生来源更多。没有经过科学处理的塑料垃圾会进入到淡水系统内,在太阳的照射与风化作用下形成了尺寸更小的微塑料,如随意丢在湖泊中或溪水中的渔网,在降解后会形成各种纤维类微塑料。用过后的塑料扔入水体内降解后将产生微塑料污染。另外,陆地系统内的塑料产品,在裂解后有一些也会进入到淡水系统,例如,废旧的塑料棚,塑料在土壤中降解时因为动力干预,小塑料颗粒会与雨水一起融入到地下水中。扔在地面上的塑料如果没有及时降解,也会由于风力作用而进入到溪流等水体中。在大气中的微塑料也会由于空气作用而进入到地表水内[6]。
1.2 淡水中微塑料的污染状况和分布
在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淡水中均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7]。部分研究表明,微塑料的种类和人类活动空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微塑料的出处一般能够以微塑料原料的属性等来判断。例如,在多瑙河找到了一种占比多塑料,而该河的周围就有该塑料的制造厂。在工业区与人口聚集的工业湖内,树脂颗粒与微珠最多,而在人口不多的山区湖泊的初级颗粒不多,却拥有众多的次生碎片,说明了初生塑料的断裂,与水流、地下河迁移而一起累积。这些年来,我国淡水中微塑料的污染调查事务也纷纷开始进行,在三峡大坝、太湖、鄱阳湖水系附近等地发现了微塑料,这说明微塑料污染在我国的淡水环境中也是十分普遍的。同时有些分析表明,此类水体的微塑料含量基本处于较高的水平。
在对我国内陆淡水微塑料污染的分析中,湖泊中的微塑料丰度在区域上存在极大的变化,和离城市中央的距离之间为反比例关系,这表明了人为要素在微塑料划分方面的地位[8]。
2 淡水环境中微塑料影响
2.1 微塑料吸附释放有机污染物
微塑料拥有相对较大的比表面积与较好的疏水性能,所以对有机污染物有相对不错的吸附效果,就水体内微塑料展开的调查了解到,微塑料中有各种有机污染物被测出。微塑料对有机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还会因微塑料材料而有所影响。
微塑料对多环芳烃(PAHs)、多氯联苯(PCBs)等污染物都反映出了较高的吸附水平,另外,离子类化合物与重金属元素也有相应的吸附水平。柔软(玻璃化温度Tg不高,链段性能活跃)的塑料如PP,PE等对有机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较强,同时吸附等温线基本上为线性,理由是PE与PP的玻璃化温度基本不高,室温下为软橡胶形,有机污染物更多地是以分配效果的形式进入到微塑料中,所以吸附等温线为线性,同时反映出了相对不错的吸附性能;硬质塑料如PS等也可吸收一些PCBs,由于PCBs可以和PS表面的结构产生π-π电子反应[9]。此外,经由上述分析可知,表面官能团也许会协助微塑料吸收污染物。
2.2 微塑料释放有机污染物
微塑料从水系统内吸附有机污染物的情况下,还会在水系统内排出污染物。塑料产品在制造环节中通常会加入众多的阻燃剂、塑化剂等,让进入到水系统的微塑料中包括此类添加剂。风化作用则会协助此类物质慢慢地进入至系统,比如说,Staniszewska等[10]就某固定流域进行分析后了解到,塑料添加剂的排出是造成该流域中双酚类成分与壬基酚类成分增加的缘由。微塑料还会向系统内排出其含有的其他有害物,如系统内剩下众多的用含铅化合物当做稳定剂而制造的PVC产品,因为老化的推进,其中的铅将会慢慢地排出到自然界中;不仅如此,制造塑料的单体与原料在塑料中也有一定的量,此类物质也将慢慢进入到生态环境中,如PVC内有一定的HCl,聚苯乙烯内具有苯乙烯的单体与低聚体,此类物质均会因为聚氯乙烯与聚苯乙烯的老化而慢慢排出到自然界中[11]。
2.3 淡水环境中微塑料危害
现阶段,微塑料类有机污染物因为尺寸细小、数量巨大,极易被水生生物摄取,在自然环境下,有许多生物能吸收微塑料,如鱼类、龟类、鸟类等动植物。海鸟、贻贝等将其当成食物而摄入,可能造成肠道阻塞、消化不良、生长速率降低,甚至造成死亡。微塑料可以抑制藻类在淡水中的光合作用。目前对微塑料的生态毒理作用的研究主要针对已有海洋生物,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生态环境带来潜在影响和危害已得到大量研究成果的证实。因为人类生活与淡水密切,所以潜在的污染危害在淡水环境中可能会比在海洋中更高。据研究,微塑料的作用发生在不同的层面:基因,细胞,组织,植物和动物。
因为微塑料的降解几率较小,只要被水生生物吸收后便增加了在生物体肠道内的滞留时间,而造成水生生物的饮食量下滑,从而造成机体的炎症反应,让其吸收和储存能量的实力下滑[12]。尺寸大些的微塑料较多地聚集于水生生物的腮、肝脏、肠道与淋巴系统内,进而作用于生物体,并使其肠道功能受损。微塑料粒径越小,危害也越大,纳米微塑料可以穿过细胞膜,造成细胞水平的影响。
食物链的污染物富集使微塑料对自然造成的危害更大。鸟类在捕捉一些水生生物的情况下,其中的微塑料也许会迁至鸟的身体内,或是湖水内,底泥内的微塑料被鸟类误食,而被鸟类吸收的微塑料会与食物链一起从低营养程度流往高营养程度,最终将会被人类吸收。2018年召开的欧洲肠胃病学会中,有学者指出,第一次在人体排泄物中发现了好几种微塑料。
3 对微塑料控制
3.1 政策方案控制
通过公众教育促进对微塑料的关注,一些国家已经发布了相关的研究策略,2015年,美国颁布了《无微珠水域法案》,其中规定,化妆品中不得含有塑料珠将于2017年7月1日开始实施;英国被迫到2017年年底消除含有塑料珠的化妆品;韩国在2018年7月禁止销售化妆品装有塑料珠;加拿大关于化妆品中塑料珠的法规于2018年1月1日生效。
因为微塑料属于一种新型污染物,因此就此类污染物,我国尚未颁布较多的微塑料污染控制方针[13]。我国对塑料的不合理使用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将免费应用塑料袋改为付费应用塑料袋,然而效果却不太好。因为个人洗护用品为微塑料污染的核心出处,因此需管理好微塑料微珠在洗护用品中的应用。在塑料垃圾进入到自然界后,应及时予以垃圾阻拦、处理,规避裂解,防止生成更小的微塑料。相关法规的颁布和法规的发布,以及对公共教育项目的普及,将从源头控制减少微塑料进入水体引发污染问题。
3.2 处理技术控制
微塑料进入淡水环境后,污水处理厂处理微塑料也是比较可行的方法。现阶段与我国污水处理厂微塑料污染的分析资料基本不多。白濛雨等[14]在分析上海某污水处理厂后,了解到进、出水中的微塑料数量分别为117个/L与52个/L,微塑料的处理率约56%。这表明,我国污水处理厂的进、出水中的微塑料数量基本都较高,污水处理技术对微塑料的处理率不高,大量的微塑料是仍然排入环境。
根据文献,迄今为止,动态膜(DM)和膜生物反应器(MBR)是最有效的工艺去除废水中的微塑料,实现微塑料的去除值高达99.9%。而快速的砂滤和溶解气浮可以去除分别为97%和95%的微塑料。主要的MBR的缺点是超滤膜和微滤膜成本,能源需求,结垢控制和低通量。相比之下,动态膜的价格更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过滤器很容易堵塞。尽管如此,膜生物反应器在其实施并进行可用的修改,以使它们在初次使用后更加节能,防污并且运行成本更低。
不仅如此,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与出水中微塑料浓度不仅会因进水中的微塑料浓度而受到影响,还和污水处理技术相关。有分析表明,格栅等一级处置可高效阻截较多的微塑料;而在二级生物处理技术内,A/O技术中的微塑料浓度比氧化沟与SBR技术污泥中的更高,其核心理由为氧化沟与SBR技术拥有较长的水力或污泥滞留时间,微生物能够更多地使用外酶功能来降解微塑料。
污泥处理技术也将影响微塑料浓度。LI等[15]经分析后了解到,在现阶段使用次数最多的污泥脱水技术中,板框压滤得到的污泥微塑料基本浓度最少,其次为离心法;而离心法与带式压滤法处理后污泥中的微塑料基本浓度相比又更少,原因在于污泥在离心时,一些浓度较小的微塑料被再次排入水内,进而造成离心脱水污泥中的微塑料浓度相对不高。Mahon等[16]分析厌氧吸收、热干化等污泥处理方法对污泥微塑料浓度的影响时了解到,厌氧消化能够高效减少污泥内的微塑料成分,而热干化处理技术是会让微塑料发泡,而石灰稳定化处理则会让微塑料被剪裂得更小。
4 展望
微塑料属于一种新污染物,在给我们的日常提供方便的情况下也对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现在,微塑料污染问题已变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应获得我们的高度关注。就现调查的水域河流不足,还有许多水域河流未调查研究,因此淡水中微塑料研究还不够完善。基于现有微塑料及处理工艺的相关研究,应该着手于微塑料在复杂水体中研究。当今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藻类过量增长,导致水体中既含有藻类藻毒素同时含有微塑料的自然水体增多,不再只单独去除微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