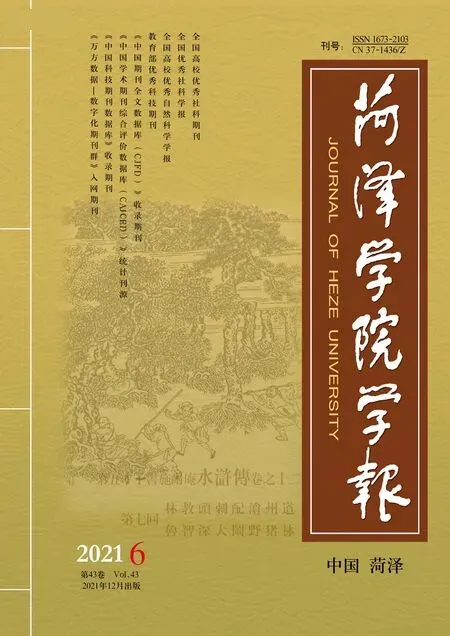“自由”与“存在”
——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时代女性形象探析
陈 颖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000)
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曾提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概念,即“众所周知的通俗小说,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发射性,同时又悖论式地主张拥有历史事件和真实的人物”[1]。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娴熟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使得小说充满不确定性,交织着多重意蕴,具有哈琴所说的“元小说”的典型特征。它刻画出一个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却塑造出一个活在19世纪的20世纪女人形象萨拉——“一个放荡的女性,一个诱惑者,一个癔症患者,一个精神病人,一个以自由为生命的新女性,一个人性进化的实践者、探索者、牺牲者”[2],并穿插、杂糅了当代物件造成一种时空混乱的效果。这一复杂的叙事张力在改编为电影时得到另一种形式的保留,即加入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安娜和迈克的“婚外情”的故事,以“戏中戏”的形式让两个时代互为观照、对比,从而保留并加深了小说对女性精神的时代探究。在电影中,通过对不同时代女性形象的对比呈现,使得“萨拉是谁”的问题得到更为深入的阐释。
一、对比: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保守”与“反叛”
影片起始将镜头定格在了阴冷灰蒙的防波堤、熙攘的莱姆镇街头和装饰繁复考究的富商家宅,还有男女人物之间拘谨的礼节对话,以道德风气保守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眼前。那个站在大堤尽头,被海浪拍打着的黑衣女人萨拉显得尤为突出、神秘,与周围大环境格格不入。这样一种镜头并置呈现出强烈的对比效果,影片的主人公莎拉以“异类”的形象出场。围绕着对女性精神的探究,影片刻画了一系列维多利亚时代女人的形象,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保守”与“反叛”两类。
首先是以富家女欧内斯蒂娜、波尔蒂尼夫人为代表的“保守者”,她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假道学”风气的维护者。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期待是道德至上,保持贞洁,在经济和人格上都要依赖于丈夫,努力成为“家庭天使”(angle in the house)。家庭是妇女们活动的核心场所,所以,尽管欧内斯蒂娜倾心于贵族男子查理,却仍维持一个淑女的矜持与故作姿态,与镇上的其他人一样,将莎拉视为“荡妇”。她想通过嫁给贵族来提升自己作为布商女儿的社会地位,当查理要求与其解除婚约时,就暴跳如雷逼迫查理签署侮辱人格的“认罪书”,相当于直接剥夺了查理的贵族身份和地位。看似温柔可人的少女,实则浅薄、虚伪,自私无比。波尔蒂尼夫人虽每日以读《圣经》为务过着简朴的生活,然而对待下人极其苛刻,禁止侍女莎拉去海边,认为人们只能在教堂聚会。她们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并自觉去维护,谈性色变,鼓吹婚姻神圣,崇尚上帝,但却极力打压异己,完全将自己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3],她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风气的产物。尤为讽刺的是,讲究道德的维多利亚时代黄色书报出版空前绝后,而且“在伦敦,每六十户房屋中就有一家妓院”[4]。一边是女性的极度约束与规训,另一边又是对女性的肆意玩弄,表面上的正经、秩序与纯洁掩盖不住早已败坏的社会道德。这种分裂的情况也造就了“英国这个主要依赖自我调节的社会依赖于自发的组织——教会、公谊团体和巨大的慈善组织网络——来对付精神和物质的沦丧”[5]。
其次是以莎拉为代表的“反叛者”。福尔斯表示他想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6]。莎拉就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却出身贫贱的下层女子,她同时被自己的阶层与上层社会所抛弃,又因爱上一个有家室、逢场作戏的法国中尉而被冠上“法国中尉的娼妓”的恶毒称呼,终日戴着自己的“红字”游荡在不受人待见的小镇。莎拉的反叛性不仅在于她不顾当时的道德禁忌,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更在于她全然接受了镇上的人对她的谴责,甚至故意活在“娼妓”的称呼中并将其作为蔑视与反抗整个社会道德的方式。这种反抗是令人震惊又匪夷所思的,正如查理与莎拉发生性关系后竟然发现她仍是处子之身一样。
在维多利亚文学中,“反叛”的女性不止莎拉一个,像简·爱、苔丝、蓓基、麦琪等都表现出抗拒宗教、向往自由、追求平等等特点,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却并未真正脱离于当时社会伦理的框架,甚至还有着不同程度地回归主流话语的倾向。而莎拉的“反叛”是最为深刻又超越于时代的,她的极为强烈的神秘性、自主性、个人意识使她在看似弱势的地位中却掌握了主动权。无论是选择充当卫道者口中的“妓女”,引诱查理靠近,还是选择在激情过后远离查理,不愿意屈从婚姻,都显示她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从未有一丝的妥协,像是在19世纪的躯壳中活出了20世纪的灵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过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说,如果说莎拉代表着“本我”,那么蒂娜就代表着“自我”,前者是受本能与欲望驱动,后者按照社会伦理与现实原则来行事。当带着原始冲动与本我意识的莎拉走出来必然会“得罪”社会,以至于被当地人认为是患了忧郁症、精神病,应该被关进疯人院。实际上,她是“诞生于19世纪理性文化中的非理性文化代表”[7],是彻底的离经叛道者。
二、互文:现代女性的“自由”与“存在”
鲁迅谈及《娜拉走后怎样》时指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8]。然而,同是作为“娜拉”符号的莎拉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她悄无声息地离开旅馆,查理遍寻不到,三年后两人再次相见,莎拉在前拉斐尔派画家罗蒂家中既是孩子的家庭教师,又进行艺术创作,俨然成为有着独立经济基础与精神意识的现代女性。小说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的现代女性精神探究在电影中通过加入莎拉的扮演者安娜的爱情故事来衬托,可以说,虽有着时空的跨越,但莎拉所体现的现代女性意识与20世纪的演员安娜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精神是一致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参照关系。
在电影中,莎拉与查理“相遇-相知-相恋”的发展过程是与两人的扮演者安娜和迈克的“婚外情”线索并进的,这既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对女性、对不伦恋的容忍程度,又给莎拉的身份与形象增添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能够让观众自觉地站在现代立场上去审视评价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精神。比如,安娜与迈克以现代人的身份讨论维多利亚时期妓院林立、嫖娼盛行的腐朽社会风气就应和了小说中福尔斯对于虚伪道德的批判,由此使得“‘当代’和‘历史’成为相互对照的两面镜子,用现代意识批判、消解历史意识”[9],而非毫无态度的古典历史影片。
莎拉与安娜两位女性是整部片子的灵魂人物,也是互为镜像的时代女性形象。影片故意营造出时空错乱感,不断推进交错并置的镜头来回闪现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社会,都在诉诸于同一个主题,即女性的“自由”与“存在”。萨特的哲学指出“存在主义即是一种行动和卷入的伦理学”[10],戏中的莎拉与戏外的安娜都在通过持续的行动与不断的选择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从一开始莎拉就卷入法国中尉的情妇的丑闻风波,她任由流言发酵,名声败坏,经常到海崖边散步来享受心灵慰藉。在几次“偶然”(其实是她有意为之)遇到查理之后,开始慢慢获得查理的同情、理解,编造自己的风流史,给查理递送小纸条等,使得两人的感情不断增进。波伏娃认为“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11],莎拉实则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在对立中确认自我的主体性,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她“有时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什么侮辱,什么责难,都触动不了我。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12]。而之后她的两次选择更是体现了存在主义精神,一次是发生关系后离开查理,将查理置于她所遭遇的境地,一次是三年后两人再相见后仍不轻易接受婚姻的许诺。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即自由”,莎拉的存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她渴望的女性力量不在某个人或某种道德观上,而在于她内心所秉持的自由信念,更在于以行动抵达存在的毅力。
相较于莎拉,安娜显得更为自信、有力,本质上可以说是莎拉精神的延续与发展。她与迈克半遮半掩的恋情在剧组得到某种程度的曝光,但并未遭到别人的指指点点。正像莎拉其实一直在引诱着查理一样,安娜在两人关系中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迈克将对戏中莎拉的迷恋投射到安娜身上,安娜自如地保持着拍摄期间的恋爱关系,在拍摄结束后选择离开迈克。从始至终,安娜都保持着高度的个人自由意识,对于婚外情有着随意坦然的态度,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如果说莎拉提供了在毫无自由的社会如何自由的可能性,那么安娜则展现出在风气开放的现代社会,独立女性追随自由的现实性,这无疑是莎拉在现代社会的翻版。无论是莎拉还是安娜,实际上都打破了外在的束缚,颠覆了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她们将个人意识作为行动的核心,把男性置于被看、被投射的欲望的客体地位,在行动中实现了对自我自由的确指。
三、不确定性:萨拉是谁?
当我们试图用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原型分析等话语进入莎拉的人物形象剖析时,我们对莎拉的理解仍未能趋向于一种确定性,恰恰相反,“萨拉是谁”的问题反而更变得扑朔迷离了。在小说中,作者也介入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萨拉是谁?她是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的?我也不知道。”[13]可以说,萨拉“迷惑了每一个人,包括作者本人,她拒绝她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拒绝按照常规生活,她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14]。
福尔斯在小说中给出的三种结局在影片中虽只出现一种,却仍是以萨拉与查理坐在摇晃的小船上朝着不知去向的水面驶去结束,暗示着两人关系的无限开放性。而安娜与迈克在最后的分离之时,安娜独自驾车离去,迈克在窗户上大喊了一句“萨拉”也颇为意味深长,将小说中的那种不确定性再次精彩地呈现在大屏幕上。迈克爱的是安娜,但他最后喊的是萨拉,他把安娜当作萨拉来爱,然而独立自主的安娜永远不可能是戏中人物的影子,而是独一无二的安娜。影片中安娜与迈克在一起的场景也多次暗示其实迈克并不懂安娜,安娜在海边的发呆出神表明两人并没有真正心意相通。其实,查理也不过是被萨拉的气质所吸引,他对萨拉的援助乃至于产生的爱恋之情都不能掩盖他不理解萨拉的事实。甚至于,他一直都是在萨拉的“圈套”中,直到他知晓了萨拉的谎言并选择承担责任,抛弃贵族身份,在经历萨拉的遭遇后才开始慢慢觉醒,但是萨拉对于他来说依然是个神秘莫测、谜一般的女子。所以,萨拉与查理、安娜与迈克两段恋情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安娜和迈克的婚外情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萨拉和查理关系的现代解读,可以被看作为试图固定化或者说确定化萨拉形象的一种手段。不过,现代语境下的安娜仅仅表现出萨拉形象的一个侧面:属于女性的进退自如,然而仍显得单薄,甚至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萨拉”已经变成一种符号,萨拉的形象在特殊的维多利亚时代才有着更为广阔的意义。萨拉是维多利亚时代“堕落的”女人,也是追求智力平等的先驱者;萨拉是对男人投怀送抱,引诱查理的不洁者,也是查理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萨拉是莱姆镇上众人指责的“婊子”,也是虚伪道德社会的替罪羊;萨拉是被时代抛弃的无助者,也是以自由选择获得重生的新女性,萨拉身上依次体现着夏娃原型、撒旦原型、替罪羊原型和再生原型等意义。“萨拉”的不确定性、分散性、矛盾性使得她充满无限的可读性,也让她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符号性人物,并呼应着现代社会的女性困境、女性重塑等多重命题。萨拉到底是谁?这一命题永远没有完结,有待于女性去探索、去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化反思电影”的背景下,可以说,影片对萨拉的时代女人形象刻画显示出深刻的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