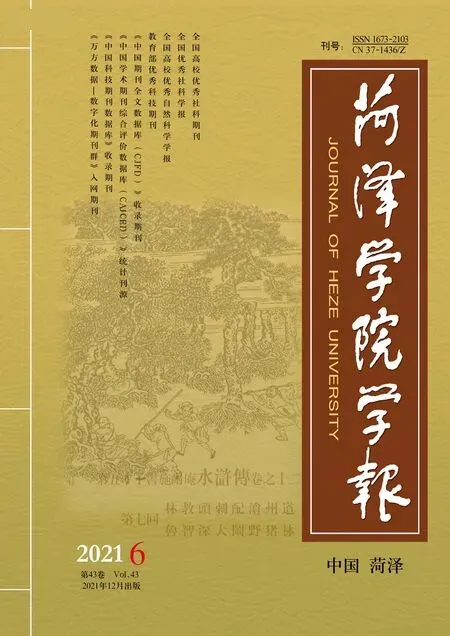近代小说中的武汉印象简论
韩 晓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领域亦随势而动,成绩突出。近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由古典韵味走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城市描写亦是小说中的重要内容。关于近代小说的城市书写,研究的目光多集中在上海、广州、苏杭等地,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却较少被提及,这或许是因为描写武汉或武汉之武昌、汉阳、汉口三地的小说作品较之描写上海等地者影响并不瞩目。尽管如此,搜检清末民初的小说可知,笔涉鄂汉之地的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仔细品赏亦有滋味。限于学识及篇幅,姑简论一二。
武汉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部分组合而成,因此有“武汉三镇”之称。武昌、汉口、汉阳各有其发展沿革,其中,武昌、汉阳均是历史悠久的重要古城,汉口则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才逐步从汉阳分出。因为“武汉”之名出现较晚,明清以来的小说中出现“武汉”一词的频率较少,而作品中出现武昌、汉口或汉阳之名,实已涉及武汉城市之书写。近代小说中的武汉印象亦是由三镇影像组构而成。简而言之,近代小说中的武汉兼具强烈的政治色彩、浓郁的商业气息和悠长的人文情怀;相较于其他二地,武昌更多地显露出政治色彩与战争痕迹,灯红酒绿的汉口商业气氛更为稠密,汉阳则更显得浪漫典雅古韵悠长。
一、武昌:强烈的政治色彩
武昌在汉代属荆州江夏郡沙羡县,三国时期属吴国,已经逐渐凭借其交通便利成为军事要地和商贸繁盛之所。今天武昌的大部分地区在孙权时期则被称为夏口,隋代改称江夏县,明清两代则为武昌府治所在。
明清以来的许多小说都曾写到武昌。第一部历史演义题材的长篇章回巨著《三国演义》中就多次写到夏口,也就是后来的武昌。按照小说的故事叙述,夏口本属荆州江夏郡,刘表派部将黄祖把守,后来落入孙权手中。尽管夏口在《三国演义》中频频出现,作者却无意细致描画其景观风貌与百姓生活,而仅仅只是将之作为征伐掠夺的军事目标和故事叙说的地理节点。有时,城市会被抽象成一个空间符号。有时,小说只对城市的某些局部场景加以点染或凸显,比如城楼、城门之类,因为这里是杀敌御寇的前沿阵地,往往是战争火力最为集中的地方,作家需要借助这一空间把格斗厮杀与勾心斗角展示得稍微具体一些,久而久之,城门或城楼就成为了城市形象的抽象表达。这种写意的书写手法,颇得中国美学的神韵与智慧,在绘画与戏曲中也常常能领略到。
除了写意式的点染,详细描绘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的长篇小说《文明小史》从湖南永顺的洋人开矿开始写起,紧接着就写到了湖北武昌。
不多几日,到得武昌。武昌乃是湖广总督驻节之地,总督统辖两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正合着古节度使的体制。隔江便是汉口。近数十年来万国通商,汉口地方亦就开作各国租界,凡在长江一带行走的火轮船,下水以上海为尽头,上水即以汉口为尽头,从此汉口地方,遂成为南北各省大道……至于武昌地面,因这位总督大人很讲求新法,颇思为民兴利,从他到任,七八年,纺纱局也有了,枪炮厂也有了,讲洋务的讲洋务,讲农功的讲农功,文有文学堂,武有武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陆军有陆军学堂,以至编书的、做报的,大大小小事情,他老人家真是干得不少。[1]
这位武昌总督政事勤勉,做了几十年的官,依然是两袖清风,经济上运转不来,又不愿贪污或挪用公款,只得把太太的嫁妆抬了八大箱去质当。说是当当,他又不肯让人看货估价,因为心想自己总是要赎回的,不过就是抵押借款罢了,把几个箱子还一一亲笔写了封条,才叫一个差官带人抬去当铺。差官跑了好几个当铺,店里的朝奉都说要开箱验货估价才能给钱。后来又去了一家离制台衙门比较远的店铺,朝奉仍是如此说,甚至流露怀疑之意。跑累了的差官不肯再跑,强要当当,仗着人多势众,便把这一家当铺的朝奉拖出柜台殴打,于是双方便扭打起来。当铺管事的听见说是制台来当衣服,便道:“制台是皇上家的官,焉有不知王法,可以任性压制小民的道理?为今之计,无论他是真是假,事情已经闹得如此,只好拉了去见官。我们开当典的,这两年也捐苦了,横一捐,竖一捐,不晓得拿我们当作如何发财,现在还来硬啃我们。我们同了他去见官,见官讲的明白便罢,讲不明白索性关照东家,大家关起门来不做生意。”接下来,作者按空间顺序叙述了两方人马的行进路线,“出了当铺,转弯抹角,走了好几条街,惹得满街的人,都停了脚,在两旁瞧热闹;还有些人跟在后面一路走的。这座当铺,离制台衙门较远,离武昌府知府衙门却很近。霎时走到武昌府照壁前面,不提防这当铺里的人抢前一步,赶进头门,一路喊冤枉喊了进去。”武昌知府弄清事情原委,感到比较棘手,既觉得制台清廉有心相帮,又不愿让当铺为难,于是就去找藩台商议。知府和藩台商议后让官差将东西抬回制台衙门,当铺也不必当这些东西了,受伤的各自回去养伤,知府则从藩台处支取银两亲自去总督府借给总督。这段故事的空间场景转换多次,从总督府而当铺而知府衙门而藩台衙门,最后又回到总督府,但是关于武昌的城市空间,小说仍没有特别具体地去写街道布局以及各类建筑,作家的笔触只是聚焦活跃在城市中的人物,而这里的人物又往往与知府衙门、总督府之类带有权力象征意味的地方息息相关,而知府衙门、总督府之类也就成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客观来说,描写政治军事的小说也会涉及汉阳、汉口,武汉三镇虽被长江、汉水分割为三,然一衣带水,实为一体。不过,比较而言,武昌的政治气息当然最为浓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武昌首义等很多大事件都与武昌关系密切,这些历史事件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近代小说之中,武昌的频频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即便是仅仅作为叙事背景出现,亦能勾画出政治色彩浓厚的武昌形象。将近代的武昌城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借此构筑宏大的叙事背景而展开各类青年男女的悲喜人生,是小说家们擅长的构思,也容易成就混合着缠绵感伤与激越悲壮的故事情节。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不独白话小说,文言小说亦是如此。譬如,徐枕亚的《玉梨魂》描写家庭教师何梦霞与青年寡妇白梨娘的爱情悲剧,梨娘抑郁而终,受此打击远走他乡的梦霞则在武昌起义中捐躯报国;张海沤的《珠树重行录》描写两对青年男女相爱于欧美留学、游历的过程中,武昌起义爆发,四人相继回国,两位男青年均在战火中受伤住院,又有一番奇遇,最后四人遵从父母之命缔结婚姻,却恰恰互换了对象。著名作家周痩鹃早在清末民初已开始创作发表小说,他的文言小说《中华民国之魂》于1914年12月发表于《礼拜六》周刊第26期。作品讲述了同为高等学校高材生的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美人倩云,然倩云心属其弟。正值时局混乱,黄鹤楼下,清军与义军之战不可避免。在倩云爱国之心的全力支持和鼓舞下,两兄弟都参加了辛亥革命为国效力。
二、汉口:浓郁的商业气息
“汉口”之得名主要源于其地理位置处于汉水汇入长江的入水口。明成化年间,汉水从原先经龟山南注入长江改为从龟山北注入长江,并使汉阳分离开来一片荒洲,此即今汉口的发源。依靠水运交通的便利,汉口发展迅速,明代中叶为汉阳县汉口镇,已是全国有名的船码头,清代初期汉口镇已经和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
虽然在“武汉三镇”中兴起最晚,汉口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是最快的,延及近代,更吸引了来自日本、美国等各色人等关注的目光。法国人加勒利和伊凡曾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一书中转述了他们一位爱旅行的朋友眼中的汉口:“汉水流入扬子江的交叉点,本地人称为汉口,中国人认为这地方是国内最大的商埠。汉口距海有两千余里,但是江流全程可以航行最大的船只。”[2]曾任日本驻汉口领事的水野幸吉在《中国中部事情:汉口》一书中写道:“汉口年贸易额达1亿3000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现今已成为清国第二要港,几欲摩上海之垒。鉴于此,机敏的视察者言:汉口乃东方芝加哥。”[3]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各行各业的发达,茶楼、酒肆、戏院、妓馆,数不胜数。在汉口的江汉路、花楼街一带,还出现专门以刊载坊间名妓的趣事奇闻的消遣类小报报社,如1906年的《现世报》、1910年的《繁花报》等等。街知巷闻的“花报”《繁华报》以高谈风月之小品,介绍妓女之广告为主要内容,间或以幽默笔调调侃讥讽时事。这既是近代武汉报刊业发达的缩影,也折射出汉口乃至“武汉三镇”已成为公认的烟柳繁盛之地。
商贾云集商业繁荣的汉口也成了不少人发迹变泰的冒险乐园。在安徽桐城人许奉恩所撰的笔记小说集《里乘》卷六中就有两篇作品写到了外地人在汉口经商的遭遇。前一篇《父子同日合卺》描写蜀地某生大悲大喜的人生,汉口正是其悲喜转折的幸运之城。某生本从塾师读书,因偶与舅舅的女儿一妹有私情,又惧怕为舅舅所察,于是逃亡在外,竟沦为乞丐,一路要饭要到汉口。一家典当行的老板见某生的相貌举止并不像乞丐之流,便收留某生还教其商贾之道。后来某生靠着自己的勤勉节俭,攒下万余两银子,已能自立门户与人合伙开布店,乃敢回蜀中老家省亲。回乡当天恰逢乡中一青年迎亲,仔细打听才知道这便是自己与一妹的儿子。故事的结局是某生就在回乡当日与一妹完婚、与儿子相认,父子二人同一天完婚也算一段风流佳话。而在后一篇《毛甲》中,江西九江的赵某与同乡李某到汉口做小生意,就远不如《父子同日合卺》中的四川人某生幸运,不仅生意连年亏损,赵某更因染病而客死汉口。李某在安葬了赵某之后私吞余财,回到家乡仍不免被赵某索命而亡,竟然投胎到赵家所养的母猪腹中,方悟到必须变成畜生偿还了宿债才可再世为人。转世为猪的李某忍受了屠宰、切割、售卖等诸般苦楚,又一次转世为人,只是左手依旧是猪蹄的模样,这便是故事的主人公颍州人毛甲。毛甲每每顾其左手,想起前尘往事,不免恐惧万分。《毛甲》的故事表明纵然城市经济发达,发家致富机会多多,汉口也并非遍地都是黄金,行商坐贾也并非人人都能一本万利。而私吞他人钱财便会堕为畜类的情节设置虽显荒诞,却指向了讲诚信、戒贪婪等商业道德,仍然是汉口商业繁盛以及强调商人职业操守的反映。
周旋在商贾间的还有一群青楼女性,特殊的职业背景造就了她们的悲喜,也被记录在许多小说作品之中。近代著名报人、小说家王韬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淞滨琐话》的卷七“谈艳中”记录沪上烟花之地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妓女,来自不同地域的妓女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王韬在此详细展示了鄂汉女子的高雅才情,“又其次曰湖北帮。神女解佩,来自汉皋;洛妃赠枕,渡从江浒。”[4]王韬笔下的汉皋多指汉口,他在此还特别提到金香和玉香两位十五六岁的姑娘,不仅青春貌美,而且才情出众。只是,这些沦落风尘的神女是否会拥有如意的人生呢?俞樾的小说集《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录了一位汉皋妓女短暂的人生,故事悲怆,令人动容。
李玉桂者,妓也。故蜀产,不知其姓氏,流转至汉皋,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颇有声北里间。有李孝廉者,长沙人也,计偕北上,道出汉皋,为友人拉作狭邪游,遂与妓相遇。妓屡目之。友曰:“若爱李郎乎?是固将买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于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赀如干,当出以佐君,为脱籍费。”李感其意,诺之,而请俟之礼闱捷后。已而春风失意,旅食京华,遂失前约。妓偃蹇风尘中,未尝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艳其色,强委千金于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药死。嗟乎!节烈如是,此女不妓矣。[5]
原籍四川的女子玉桂流落汉皋,无奈堕入风尘。她怀着一腔真情等待李郎践约赎身,却既被科场失意的李郎失约相负,又遭残暴蛮横的富商劫夺威逼。玉桂的惨烈而死,究竟是出于节烈还是因为对社会人生的绝望?对于很多沦落风尘的女子而言,早日从良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她们的理想归宿,然而从良之路却荆棘遍布。长篇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汉口妓女爱珠因为姿容平平,没有多少客人光顾,好不容易有个官位不高的瞿老爷有意纳她为妾,却也活得十分艰难。既要竭尽全力讨好瞿老爷,又要面对瞿太太上门吵闹辱骂,嫁入瞿家为人妾室的目标终究还是不了了之。从良之路固然心酸异常,即便是从良之后,又有几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有时候,风尘女子习惯了青楼的放纵生活,耐不住家庭生活的单调寂寞,即便从良也依旧延续着从前的一切,辛酸屈辱也只有自己品尝。《风流太保》中的汉口富商之子柳伯义娶了暗娼玉蝶儿,衣食无忧的玉蝶儿却不安于室,又看上了开照相馆的花中时。玉蝶儿与花中时的奸情被柳伯义的朋友甄筱仁得知,甄筱仁遂勾结衙门里包揽讼词的贵忠等人怂恿柳伯义捉奸,导致花中时堕楼身亡。为了平息官司纷争,柳伯义花了大笔银钱。面对花中时之死,玉蝶儿也谈不上有多伤心,依旧靠着献媚讨好他人来继续自己的享乐人生。作者借这样一桩风流公案表达了对社会风气堕落的批判。比之于李玉桂,玉蝶儿不再为任何男人而活,有着属于个人的欲望与追求,但是这种被金钱意识与享乐主义所左右的欲望,吞噬了玉蝶儿的真诚与情义,留下空虚的躯壳游走在尔虞我诈纸醉金迷的世间。
商人形象和妓女形象在讲述汉口故事的近代小说作品中频频出现,汉口是他们追逐金钱财富的角斗场,也是他们展现爱与哀愁的舞台。这些以商人或妓女为题材的作品,主要呈现出两种创作倾向:一种是向传统经典致敬,于俗世沧桑中找寻高雅情调,寄予对真善美的人生理想的褒扬或追求;一种则是迎合市民的猎奇或窥探趣味,暴露社会问题和人性阴暗面,表达对假丑恶的谴责与嘲讽。
三、汉阳:悠长的人文情怀
“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相传大禹治水曾至此,春秋时俞伯牙、钟子期亦在此以琴结友。汉阳在汉代属江夏郡,隋代始名汉阳县,唐代则将县治迁至鲁山,即今龟山,并筑汉阳城。元代设汉阳府,境域属汉阳府汉阳县。由明至清,基本格局大致相同,汉阳与隔江对峙的武昌并称两府重镇,后因汉口在清代迅速崛起,遂成三城鼎足之势。
或许明清以来的小说家们对武汉的描绘远不如对上海、南京、扬州、杭州等城市那样热衷与细致,即便如此,关于这座城市影像书写的浮泛与粗疏并不妨碍其城市形象自带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原因之一就是这座城市具有充足的不曾断裂的文化底蕴。在那些描写汉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悠长的人文情怀。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开篇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讲述了发生在汉阳的千古流传的知音故事。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奉晋主之命,出使楚国。事毕乘船而返,途经汉江口,因操琴遣兴,引得樵夫钟子期在岸上伫听。俞伯牙请钟子期上船畅谈,二人谈得投契,结为兄弟,并相约明年仲秋再会。伯牙践约前来,却不见钟子期,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故。临终时,钟子期遗言葬在江边,以便和俞伯牙相会。俞伯牙到坟前挥泪弹琴,奏毕,割断琴弦,摔碎瑶琴,以谢知音。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本事出自《荀子》《列子》《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等书,经过冯梦龙的演绎,不仅传达出穿越等级无关名利的友情观和信守承诺至死不渝的道德观,更洋溢着高雅脱俗的审美旨趣与人生追求。以琴可交心,以棋亦可会友。1865 年秋,当时的棋坛领袖、44岁的浙江海宁棋手陈子仙应浙籍汉口富商程寅谷之邀来汉与“上江第一高手”、年逾六旬的湖北沔阳籍棋手徐文耀在汉阳晴川阁会弈,吸引了大批好棋之士争往观摩,轰动一时。时人绘《汉江对弈图》以纪其盛,合编刊印《晴川会弈偶存》棋谱,撰写纪事诗文[6]。这样的风流往事,显示出武汉虽因地理位置便于商贸交通而弥散着浓浓的商业气息,但是在这座城市言商谈利的骨骼深处依旧回荡着一种掩藏不住的风雅从容。而历史悠久的古琴台、晴川阁、归元禅寺等人文景观,也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小说中也可能处于十分醒目的位置。例如,八宝王郎王浚卿所著的谴责小说《冷眼观》一共三十回,该书以第一人称细致描绘了清末社会的荒诞与病态,其中第二十回的标题便是“晴川阁两次宴嘉宾 黄花涝一番谈骗术”。
除了现实主义的作品,浪漫的志怪类作品也有不少涉及到汉阳。《汉书·地理志》载楚国“信巫鬼,重淫祀”,江汉流域的荆楚大地迷信神鬼之说或较中原地区尤甚,及至近代,有增无减,有些甚至见诸报端。前文提及的《右台仙馆笔记》,共十六卷,专门收录当时的轶闻异事。该书第七卷中一连记载了两则发生在汉阳的灵异故事,生动曲折,亦不乏诙谐。第一则故事刻画了一个有趣的狐仙。贪恋情欲蛊惑女子的狐精曾遭雷神追击,避过雷击之劫后便改过自新,修炼二百年终于成仙,自称明五先生。可是这成仙的狐狸性子依旧不够清静,屡屡降临扶乩之坛,然而又不肯为人指点吉凶休咎,只是空谈诗文古事而已。有人问这降临乩坛的狐仙:“先生何不以狐为讳?”答曰:“由狐而仙,譬如白屋中出公卿,方以为荣,何讳之有!”故事虽虚实难辨,多少也透露出导人向善的积极意义。比之第一则故事的高蹈飘渺,第二则故事似乎更为言之凿凿。病死的金某附身自家丫鬟的身上向母亲传话,说自己阳寿未尽却死于庸医耳,在阴间必置之枉死城中,阴风冷雾,惨不可言,希望母亲替自己多焚纸钱,庶可买他鬼替代。死去的人竟然能借他人之口传话给自己的母亲,令人匪夷所思,而被附身的女子事后对自己为鬼魂传话之事茫然无知,反而要令读者相信确有其事。死于庸医之手的金某与任由鬼魂附身而无法控制的女奴都有着作为小人物无法自主的悲哀,世事无常,人事苍凉,故而神鬼也愈加活跃。文中“冥中亦有洋钱乎”的反问,加强了故事的讽刺意味,遂令忧伤之外又添了几许诙谐。据俞樾所言,这两则故事乃由其门人汉阳人邬梅仙亲口道出,并非凭空杜撰,而俞樾将其加以记述意味着时人眼中的汉阳亦是充满神秘的所在。好为扶乩之戏的邬家人、由狐而仙的明五先生、被鬼魂附身的金家女奴……让近代小说中的汉阳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迷幻色彩。
描写汉阳精魅的故事,不独晚清,明代早有佳作。《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即为经典,相类似的故事又见于明代文言小说《广艳异编》卷三十《兽部五》“蒋生”条、《情史类略》之《大别狐》等。浙江商人蒋生行贾汉阳下榻马家旅店,见店主之东家马少卿女儿马小姐美貌而心生爱慕。大别山狐精趁机假冒马小姐前来与之欢会,蒋生身体日渐憔悴,同伴们也渐渐起疑。朋友夏良策教蒋生送一袋芝麻给“马小姐”,通过粗麻布袋漏出的芝麻粒儿查探出她的行踪与身份。狐精见身份泄露,索性坦诚相告,并帮助蒋生达成心愿,与真正的马小姐缔结姻缘。作品塑造了一个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狐精形象,传达出“万物皆有情,不论妖与鬼”的主题。这样清奇脱俗的高尚旨趣,显示了汉阳灵怪故事的文化底蕴。即使晚清时候的武汉三镇世俗气息十分浓厚,汉阳故事的浪漫色彩也没有被完全湮灭或消解,时而迸发出新的火花。著名的南社诗人、新闻报人叶楚伧的白话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书中的女主人名为甄洛神,父亲甄楚玉在汉阳兴办实业,家境不俗。在一次由青年志士所组织的鹦鹉洲集会中,甄洛神认识了年轻人无疆,其父甄楚玉也有意择之为婿,但洛神母亲对无疆并无好感,二人的婚事遂搁置。无疆后来与另一汉阳女子罗蝶云相好,洛神勘破儿女私情,决心效仿女英雄秋瑾有所作为,几番遭际后结庐墓侧,永伴秋魂。小说细腻展示了甄洛神思想性格的转变,甄洛神这一人物的名字带着浓厚的神话浪漫气息,但是她本人却不再是封建社会男性心目中爱与欲望的化身,已从封建社会的 “洛神”奔向革命时代的“秋魂”,由儿女之情的抑郁走向英雄之道的坦荡,种种新意,振奋人心。告别过去,走向新生,走向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为汉阳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的寓言。
近代小说对武汉的城市生活进行了较为丰富、生动的描写,以一种有别于史书传记与地理方志的文化视角,为读者展呈了明清时期武汉的风土人情与独特魅力。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说:“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7]了解武汉这座城市在近代这个特定时段的文学作品中的影像或许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内容之丰富,意蕴之深厚已足以让人应接不暇。本文所论,只是一些粗浅的见解,要更透彻和准确地去触摸和领悟“大武汉”,应该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