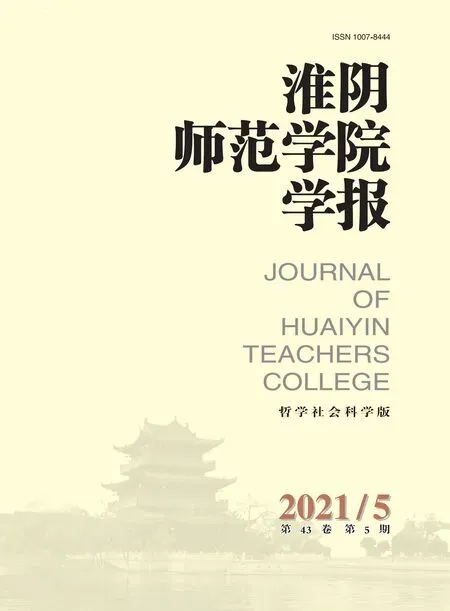论王尔德戏剧中的社会问题及其独特艺术表现
赵 峻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一、王尔德在戏剧中表现社会问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简析
(一)唯美主义本就产生于与社会问题的纠缠
美学思想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伴生物;美学范畴的扩大及审美方法的更新,是与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及对自由的追求同步发展的。唯美主义思潮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不尽一致在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实质上,无论是“生活模仿艺术”还是“艺术自律”,意图都是建立独立于政治、生活和道德的审美乌托邦,这恰恰反过来说明唯美主义与社会问题的纠缠。
首先,就美学的发展史来说,从古希腊开始,美(审美)就在试图超越生活与无法摆脱现实的焦虑中摇摆,而这正是美学产生的母体。这一焦虑可以抽象地理解为人面对神(永恒)时的局限性。柏拉图认为:“只有神拥有把多种事物合成为一、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多的知识和能力,但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两样工作中的任何一样,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1]它在实际生活中演绎为理念与现实世界、理性(灵魂)与感性(肉体)之二元对立。柏拉图一方面认为灵感是为缪斯女神所选中的纯洁心灵呈现的迷狂状态;另一方面认为必须对诗人进行监督,禁止他们在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形象。可见,审美的内涵从原初就是与它的社会愿景不可分割的。
中世纪,上帝至高无上的威权曾置其他一切智力活动于宗教的羽翼之下。文艺复兴以后,人一步步夺取上帝的权柄。近现代西方,康德一方面强调良知的先验性;另一方面却以三大批判的范畴设置把上帝(先验)的问题悬置起来,打开了通往人的实践理性和审美力的大门。他提出的艺术品“没有目的的目的性”,成为后康德时代美学理论的基石。席勒是审美乌托邦最早的营造者之一,他把美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的前提,认为唯有审美教育和艺术创造活动(游戏)才能弥合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分裂,“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2]。在席勒这里,审美与个人自由及政治清明是一致的。美填补了缺席的神的位置,恰恰是席勒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开出的药方。席勒之后,经过标举心灵主观性的浪漫主义至戈蒂耶、波德莱尔,审美对凡俗生活的超拔及艺术自律的法则逐渐风行。
其次,从唯美主义产生的英国社会背景来看,维多利亚中后期英国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印刷术发展、图书馆开放,公众对“鉴赏力”和“高雅趣味”纷至沓来,为唯美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例如,佩特《文艺复兴》初版后,他在结论部分所宣扬的,通过享受稍纵即逝的瞬间把握生命力、享受生命精彩的思想,立即受到像王尔德这样的青年人的追捧,以至佩特为了避免承担误导青年的名声,再版时不得不先删除了结论部分,并公开对之作出符合道德的解释后才再次收录。然而青年们并不在意佩特的顾虑和声明,王尔德直接把这本书称为“我的金书”。为什么当时的青年对佩特的这个结论如此着迷?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其答案在于,佩特感知了当时审美活动的新风貌,并在青年中得到呼应:“对才智和丰富的想象自身的热爱,对以更自由、更美好的方式设计生活的渴望,已然被感知到。”[3]这种新风貌的直接产物就是唯美主义运动。
综上所述,唯美主义从来就没能摆脱社会问题的纠缠,或者说它的产生恰恰是面对社会问题的艺术反应。因之,唯美主义创作实践中包含社会问题,并因此与其创作主张既对应又错位[4],则是必然的。
(二)王尔德的出身和个人学养的影响
王尔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父亲后来受封为威廉·王尔德爵士,是当时有名的耳部外科与眼科专家,同时他还爱好考古,著有关于爱尔兰民间故事的书籍十余本。母亲珍·法兰西斯卡是爱尔兰著名的才女,年轻时积极参与爱尔兰反抗运动,曾以笔名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与诗篇。父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培养了王尔德的善感与机智,他的童话、小说和戏剧中都有对时代生活精准的再现。
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学习时,深深吸引王尔德的师长主要有马哈菲牧师、纽曼红衣主教、罗斯金和佩特等人。马哈菲和佩特教会王尔德艺术地看待生活,另两位对王尔德的影响则在于对高贵正直精神的追求。
王尔德对勃朗宁夫人的赞赏可以作为一个例证。1876年7月26日,在致威廉·沃德的信中,22岁的王尔德向他推荐了勃朗宁夫人的《奥罗拉·李》(1)诗体小说,描绘了社会等级的不公、两性真爱寻觅的曲折及女性的自我成长。一书,赞叹其诚恳、自然、伟大不逊于《哈姆雷特》。12年之后,1888年,在《英国的女诗人们》一文中,王尔德再次盛赞勃朗宁夫人“使英国为小人物而流泪……对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怀有热忱,对一切受苦受难的人都心存怜悯……”[5]136-137王尔德的轻浮举止部分地是他精心设计出来的一种“表演性”的面具(因他直觉地意识到可据此攻占文化资本市场高地),终其一生他都表现出对被剥夺者的同情和怜悯。这一点在王尔德的文学创作和文论中都有据可查。
王尔德的思想和艺术观是随着他的学习和阅读不停发展的,早年他曾倾心于自然和高尚的艺术(艺术观形成后他越来越推崇爱伦·坡、波德莱尔、福楼拜以及于斯曼这类作家),关注社会问题并在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他自叙他的童话“欲以远离生活的形式来反映现实”[6]404,正如唯美主义也产生于对抗功利现实的艺术高蹈。
综上所述,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王尔德有关注社会问题的兴趣、思想和能力,这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是有所表现的。
二、不同创作时期的王尔德戏剧中的社会问题
除了两个片段《佛罗伦萨悲剧》和《圣妓或珠光宝气的女人》以外,王尔德还著有7部戏剧。以《莎乐美》(1893)为分期,早期创作了《民意党人维拉》(1880)和《帕多瓦公爵夫人》(1883)两部悲剧,后期是通常被称为社会喜剧或风俗喜剧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3)、《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4)、《一个理想的丈夫》(1895)和《认真的重要》(1895)。前5个是出版时间,后两个是上演时间,由于1895年王尔德受审,后两部戏剧至1899年才出版。
(一)早期悲剧中的社会问题
《民意党人维拉》写于1880年初,是王尔德的第一部剧本。剧本中的社会问题是多重的,至少包含以下具体内涵:(1)沙皇专制政府与被统治的人民,尤其是民意党人这样的反抗者的政治冲突。(2)政治信仰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冲突:子女相继成为民意党人后,老父亲彼得不能理解且担惊受怕,很快痛苦离世。(3)组织纪律和个人内心的天性相悖:民意党人宣誓不爱,也不怜悯,没有恐惧,要扼杀一切天性去忍受和去复仇;但实际上他们会有爱,也会有恐惧。剧中女主人公维拉与化名参加民意党人活动的沙皇长子亚历克斯相爱了,违背了民意党人的组织原则。(4)贵族中父辈和子辈的思想鸿沟:皇太子同情人民疾苦,力图改变俄国社会现状,极力与对百姓施行高压政策的沙皇及其臣僚作斗争。
《帕多瓦公爵夫人》的剧情发生在17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帕多瓦城。剧中的社会问题和《民意党人维拉》中一样纷繁尖锐。不同的是,主人公吉多鲜明地表示:“为爱而罪,罪而无罪。”王尔德式的悖论初露端倪。
需要指出的是,王尔德早期戏剧的艺术表现不够成熟。一方面,种种社会问题层叠交错,组成了颇具压力的信息团,让读者的神经不能放松;但情节的现实基础却并不坚实,或者说王尔德的笔力分散到一些更深层的着力点。比如在善恶之间、在仁慈的天性与复仇的使命之间,何去何从,这是两部戏的主人公共同面临的困惑,也可以说是戏剧内在的核心焦点。遗憾的是,王尔德早期剧作中现实社会问题与人物内在冲突对接得不够自然合理,作者想用前者的分量突出后者的分量,却用力过猛,恰如他自己对勃朗宁夫人《奥罗拉·李》的评价:“雕琢樱桃核,却动用了重锤。”[6]33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王尔德早期剧作中看到众多先贤的影子,但丁(比阿特丽斯)、多恩(死亡也不能损伤的至爱)、雨果(密室、匕首、毒药),更多的是莎士比亚(华美的台词,为爱赴死的青年男女,人性的善变,善恶的模糊)……古典主义悲剧的影响是总体性的:上述两部剧作反映了个人情感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与古典主义个人情感服从国家利益的法则截然不同的是,王尔德确立了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中心:对爱与美的膜拜可以逾越一切,为了自己的情感和欲求可以罔顾责任和规范;这一新锐价值观及对其合法性的质疑,是王尔德式悖论的实质性根源,贯穿了他整个的戏剧创作,虽然他一直在探索更好的表现方式。
(二)《莎乐美》中的社会问题
1882年王尔德赴美演讲后有了一笔收入,1883年他就去了巴黎。此后,法国文学对王尔德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1885年,他发表了评论《面具的真理》,他自己的文艺观开始确立。在1886年给报刊的阅读建议中,他强调了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重要性。他也盛赞过福楼拜。1889年,发表《谎言的衰朽》。1891年写作的《莎乐美》与早期戏剧有了较大的不同。
《莎乐美》对《圣经》原典中的故事进行了改写。《圣经》原文中的故事在王尔德的《莎乐美》中发生了偏移,主要人物由莎乐美的母亲转换为莎乐美,主要冲突由王后和先知之间的(道德)冲突,一变为莎乐美对爱的追求和现实对她的阻碍之间的冲突。这种改写和偏移的实质是什么?在戏剧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写作《莎乐美》之前,王尔德已经出版了他的短篇故事集《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1888),1891年还出版了《石榴之家》。在这些短篇故事中,王尔德运用套层叙述和小插曲以及铺散(即把注意力均匀地分散到整个领域的所有局部细节上去)[7]68的艺术手法逐步成熟,并运用到《莎乐美》的创作中。
当这部戏剧的中心迁移到莎乐美这里,乔卡南对希罗底的指斥和希罗底对乔卡南的报复,就后移为插曲,后移为戏剧的历史层面的声音,使得这一在时间上本来是这部戏近前史的情节在阅读心理中移位至类乎于远前史;而莎乐美对乔卡南的追求这个情节主干又是套层在这些被后移的历史叙述之中;彼此形成的张力支撑了作品的结构,也支撑了莎乐美对乔卡南大段大段“铺散”的台词。反过来说,当莎乐美对乔卡南大段的溢美与黑化的台词铺散开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对读者的“震惊”,又使得乔卡南与希罗底的道德之争,希律王对莎乐美的觊觎之心,以及王尔德附加的年轻的叙利亚人迷恋莎乐美并自杀的情节,这些外在的社会问题(历史现实层面)得以被反观。
“在诗歌尝试铺散时,有多少异质的意义涌进了诗歌。”[7]68在王尔德的戏剧中也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套层与铺散,给戏剧情节和结局添加了新的意味,使得观众发现这部戏对《圣经》原典的改写,其本质在于,戏剧家对内在的社会问题(心理冲突)的重视被推到了舞台上的主要位置。这也就是《莎乐美》被称为静态剧,被认为是王尔德唯美主义戏剧的代表作的原因。而当戏剧试图从社会问题中脱身出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恰恰构建了内与外的彼此观照。
“我们对历史应承担的唯一责任就是改写它。”[5]404“新世界的大门上将写上‘做你自己’。”[5]296王尔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探讨并实践人如何成为他自己。经过他的改写,戏剧《莎乐美》中的人物,从莎乐美到先知乔卡南、希律王和王后,包括年轻的叙利亚人,都不遗余力地完成了“成为自己”这件事情。至于先知乔卡南,是否真的美丽或丑陋?我们无从判断,因为陈述这个事实的莎乐美的语言是前后矛盾的。而不论他是美是丑,都是由长篇大论的莎乐美的语言构建的。也就是说,是言(先于事)生产了事,而不是言(后于事)去描述事。语言在戏剧中的重要性被提升,甚至超过了情节、性格这些传统元素。《莎乐美》这部极具王尔德风格的佳作,即便没有被禁演,对于当时英国的剧场和观众来说,陌生化的程度也比较大。
(三)“风俗喜剧”中的社会问题
密切关注伦敦戏剧商演的王尔德调整了写作的策略。与早期戏剧多方面表现社会问题不同,他后期创作的喜剧基本上不正面角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事件,戏剧的场景基本就是贵族家庭的客厅,通过人物的对话揭示出上流社会大人物们不为人知的肮脏历史和无聊空虚的宴会社交。《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和《一个理想的丈夫》两部戏可谓对位赋格,分别以一个有秘密的女人和一个有秘密的男人为中心。与这两部戏中人物道德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显著关联不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特别是《认真的重要》,相对更轻巧一些。
从表现形式方面来说,除了《认真的重要》,其他三部戏都大体采用了闭锁式结构,即戏剧中使用回溯法,以揭开人物关系中的一个秘密为全剧的枢纽,通过突转、发现,以过去的故事作为推动现在剧情发展的动力的戏剧结构。而《认真的重要》则以铺展式结构为主,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剧情。这部戏与他的前三个喜剧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有过去”的主人公,甚至也没有一个“王尔德式”的花花公子,剧情竟几乎全由主人公的话语完美连缀成篇。这是一个新的台阶,按照这个趋势,王尔德似乎可以走得更远。
那么是否可以推断,王尔德后期创作的几部喜剧,以缩减对社会问题的表现来赢得观众的舒适和满意呢?并非如此。其中关窍还要从语言方面去解锁。
传统闭锁式结构要求时间、地点、事件高度整一。备受瞩目的王尔德喜剧中的机智俏皮的语言,却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事件的整一,抵消了古典戏剧集中整饬的艺术效果。戏剧中出现在上流社会客厅里的男男女女的长长短短的对话,其中跟情节无关的部分似乎都在致力于再现现实中贵族社交的场景,跟情节有关的部分则通过悬念和惊奇满足了观众对戏剧冲突的心理需求。前者似乎在把观众往外拉,后者又把观众拉回到情节线上来。王尔德的长处在于能把二者结合得十分和谐。
语言即思想。王尔德喜剧中机智俏皮的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他擅长的技巧,也不仅仅是为了再现和模拟现实。大量“说话”的成分,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剧场幻觉,拉开了观众和剧中人的心理距离。正是通过相当数量漂移在情节之外的“说话”,王尔德喜剧呈现出风俗喜剧外表下潜在的亚文本。在连篇的俏皮话中,不仅有对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反讽观照,还有对人生本相和人性复杂的思考。与其说王尔德后期喜剧创作中对社会问题关注力不足,不如说他把关注的重心悄悄作了位移,那些俏皮话,考量的恰恰是人生和人性。
以《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为例。一位母亲为了挽救女儿的名誉而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但女儿始终都不知道她是自己的母亲。除了以这一主干情节为线索展开的对上流社会社交活动和家庭关系的讽刺以外,人物的对话特别是俏皮话,引领着有心的观众去发现剧本中层次丰富的亚文本。比如,剧中男女主人公对厄林太太这一人物的评价始终大相径庭,而他们的判断都是以诚挚的感情和严肃的道德标准为出发点的。人生有时难辨真假是非。当温德米尔夫人认识到厄林太太为了救她不惜选择让自己当众出丑后说:“这两件事包含着辛辣的讽刺,是对我们议论正派女人和坏女人的那套看法的辛辣讽刺……”[8]138《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副标题是“关于一个好女人的剧”[9],联想到哈代给《德伯家的苔丝》所加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和之后哈代因小说所受到的攻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现状:保守思想留给作家正常文学创作的自由是多么的少,对人的道德品格的要求多么严苛虚伪;也就能更深地理解王尔德通过标新立异所渴求建立的,能够摆脱道德意义捆绑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先进性。
剧中达林顿批评好人会把坏事看得太重,并认为把人们区分成好的或坏的是很荒谬的事,看似俏皮话,其实很真实。因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只有同一个世界;善与恶,罪过与无辜,携手同行在这个世界上。闭眼不看生活的一半,以为这样可以过太平日子,这好比遮断自己的视线,以为这样在绝壁与深渊之间走路可以安全一些”[8]151。这段话隐藏的亚文本,使这出戏剧不只是提出关于什么是好女人和好人,以及什么是幸福人生等问题,而是甚至将观众带到质疑理性判断力的悬崖边上。提出并试图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真?这正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写实的剧本中套层丰富的亚文本,后者的重点在于对人的内心和对真理认知的新思辨,并不是对社会问题的忽视,而是王尔德自觉的选择。因此若只把他的戏剧概况为风俗喜剧是不充分的。
三、王尔德戏剧社会问题表达的独特性及其艺术价值
1889年,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否定了艺术表现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宣称艺术除了表现自己外,从不表现任何东西。然而,王尔德也曾说过,戏剧是艺术与生活交汇之处。无疑,虽然我们通常视王尔德为唯美主义代表作家,但他本人的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显然并不囿于唯美主义的信条。通过以上对王尔德三个时期戏剧创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戏剧一直在反映社会问题,但是为什么观众对这一点的感知却不够鲜明?特别是相对他晚期的戏剧创作而言。这跟王尔德非常有自觉意识的艺术方法密切相关,他戏剧中社会问题的表达方式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后期剧作中这种独特方式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
首先,王尔德独创了一种可称之为“多重隔断并置”的结构方式。即在创作之前,他已经在戏剧中预设了一种本质性的断裂。从鲜明的一种戏剧风格开始,中途改变路线,戏剧被另一个显著不同的风格特征侵入。这种转变往往不是一次,而是多重的。在对人物的塑造方面亦如此,反转套层着反转。“‘意义’在王尔德的戏剧中乃由这些断裂、风格转换、挑战性的错位来决定,它们这样一来就引导机敏的观众触摸到潜层的文本。”[10]
其次,王尔德在艺术创作中有极强的平衡能力。博尔赫斯曾对此大加赞扬。有评论家将王尔德称为“遵奉习俗的叛逆者”。在新旧交替时代,艺术家的思想具有两重性并不少见。难得的是,王尔德在艺术创作中精妙地维持了两者的平衡:“艺术的真理便是其反论也是真的。”[5]486将思想的先锋性隐藏在花团锦簇的戏剧语言之中;将社会问题向内转,并把人性的复杂、认知的危机和对英国文化的反讽等亚文本隐藏在风俗喜剧的表层之下,这就是王尔德的方式。王尔德戏剧中机智的俏皮话正是他平衡天才的表现,也是他艺术魅力的长久与深邃所在。
再次,王尔德语言天赋过人,并且学习勤奋。王尔德自诩:“戏剧,这本是最为客观的艺术形式,在我手里却成为像抒情诗或十四行诗那样抒个人情怀的表达方式,同时范围更为开阔,人物更为丰富。”[11]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凭借天赋,也与他勤奋阅读和学习是分不开的。他不仅留心保持虚构性叙述与经验性叙述之间的平衡,而且和莎士比亚一样对于语言微妙的多义性有着天生敏锐的感觉。“莎士比亚……似乎还在每一个词语周围听到它所有的弦外之音、内涵和回声。……每一个语词……周围都是复杂的能量场。”[12]王尔德相当出色地承继了莎士比亚的天分。他戏剧中的语言之精妙含混令人叹为观止,“双关、双声、对仗、用典、夸张、反讽、翻案,和频频出现的矛盾语法(或称反常合道),令人应接不暇”[13]。
简而言之,王尔德自己给自己戏剧创作中关涉的社会问题戴上了面具,通过独特的结构、精妙的平衡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一方面将自己所表达的社会问题可能带给观众的冲击尽量淡化,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把它们藏在亚文本之中,等待读者咀嚼其滋味。
这些社会问题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再现和嘲讽。比如,读者可以将《理想丈夫》对当时政局的描摹和《认真的重要》闹剧般的欢喜对照着琢磨,思忖王尔德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现状。
其二,他所塑造的新观念的人和与之并行的他自己的新的戏剧观。诗人“必须相信并预先拥有我们共同的经验、共同的感觉和共同的道德意识”[14]。王尔德戏剧中所表达的这种新的共同经验,包括对人性本身、对人的理性和认知的复杂性和局限性的体察;欲望和对欲望的逃避;人与自我和他人的交流及其有效性等问题,是与现代思潮、现代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当时那些卓越的现代戏剧先驱所关心的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王尔德晚期戏剧不仅仅是风俗喜剧,而且是戏剧现代性改革的一部分。虽然他在表述自己的艺术观时也常常似是而非,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他诘问了现代和维多利亚价值观在个人的个性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二难困境;这种诘问不是为了以善恶的混淆去动摇传统的伦理学,而是为了在戏剧中以表现人为中心,以对人的自由表达为戏剧创作的根本。他戏剧观的先锋性为“戏剧性”这一概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三,王尔德对人类的理性、真理甚至人的认知能力都提出了质疑。就戏剧而言,写实传统有两个要求:戏剧的叙事性因素要与社会生活相一致;剧场性因素要与叙事性因素相一致。王尔德以出色的对话、悬念、节奏达成了第一种一致;又以更出色的自相矛盾的多义的对话,破坏了第二种一致。为了不吓跑观众,他给自己的新思想戴上面具。如果说人文主义传统在文学中揭穿表面的假象去反映现实,王尔德则试着让我们认识到,那表面的假象后面并没有什么坚固不变的真实。
人类对“真实”的心理需求关系着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基础。“不断增长的对真实生活的关心,……不仅只是为了家居伦常,它还是一种崭新的或被重新发现的精神经验的土壤。”[15]对传统中真实的质疑和重新审视是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艺术作品最能够生动地体现现代人在关于真实、关于自我,关于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那充满反讽和疏离的感受。
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斯特林堡、梅特林克、易卜生和契诃夫这些现代戏剧先驱共同提出的新问题,只是他们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何王尔德的戏剧和萧伯纳的戏剧共同缔造了英国戏剧的复兴,以及唯美主义和王尔德戏剧又为何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可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相提并论。王尔德戏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看起来不像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那样激烈强劲,因为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严肃的思索藏在笑剧般的俏皮话中。
“我们称之为戏剧的叛逆者、异端或是革新者的几个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克雷、科波、阿尔托、布莱希特和格洛托夫斯基,其实,他们是戏剧发展某个阶段的缔造者。他们的作品和观点打破了我们看戏和演戏的方式,迫使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意识反思过去和现在。”[16]这个行列中应该加上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语言即思想。俏皮话是戏剧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具,是障眼法。王尔德的戏剧能够抓住人心,因为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都是现代的,甚至是指向后现代的。虽然他戏剧的结构和叙事看起来是古典的。
从自我指涉的语言、权宜虚构的真理、作为“创造性”写作形式的批评等方面,伊格尔顿曾将王尔德比作爱尔兰的罗兰·巴特。必须指出的是,王尔德天赋的平衡能力,使他又异于后现代的解构与虚无。他对旧传统的敲打,至少部分地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真正的真实的认真追求相一致的,这真诚藏在浪荡子的俏皮话后面。他的戏剧让我们一面认识到人的渺小和理性认知的局限性,一面又向往不妨像那些剧中人一样努力地活出些尊严和乐趣。
综上所述,王尔德不仅仅是唯美主义的代言人,而且超越了唯美主义的局限性。人们这样评价他:“19世纪英国三个最伟大的美学教师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社会批评家: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17]他的戏剧创作个性鲜明、层次多重,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表现充满前瞻的现代性,而又潜藏在轻松的喜剧外壳之内。王尔德足以跻身于现代戏剧先驱的行列。他的戏剧创作是门槛时代现代戏剧改革的一部分。他奇异的平衡能力一方面多少遮蔽了他戏剧的先锋性,很大程度地吸引了当时的观众;另一方面,那些一边被生活冲击着趋向旧思想的瓦解,一边还在寻求真正的美好的人物,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逼近在困惑中寻求意义的凡俗尘世中的我们的生存本相,这使他的戏剧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仍旧充满了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