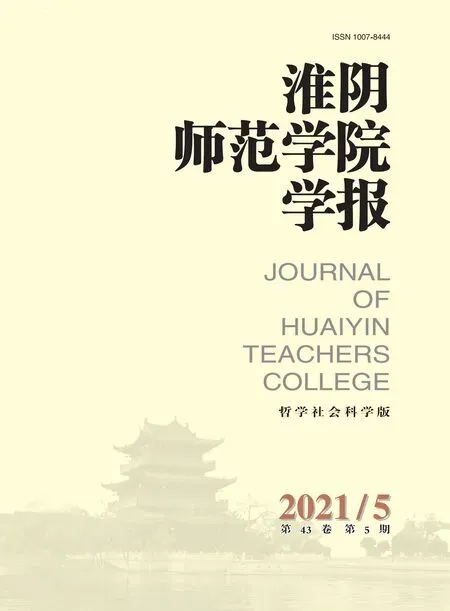从二元到三元:新符号学运动中基础理论的流变
赵星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新符号学运动中的理论变迁
符号学从20世纪初索绪尔与皮尔斯分别创立自己的学说算起,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符号学模式的奠定,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大潮的形成。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符号学逐渐摆脱结构主义的桎梏,进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萌芽、21世纪初兴盛,至今依然蓬勃展开的“新符号学运动”。
符号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已持续近30年,理论发展脉络逐渐清晰。其最大的特征是理论与流派的融合:“整合各种模式为一种新的运动。”[1]15这种融合越出符号学学科范畴,走向跨学科的发展历程。例如,符号学与生物学、生命科学整合形成“生物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整合形成“认知符号学”,与社会科学整合形成“社会符号学”,与传播学整合形成“传播符号学”,等等。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建构与拓展,这是根本。回顾当今符号学研究的新局面就会发现,新符号学运动在基础理论方面,总体上从索绪尔二元符号学转向皮尔斯三元符号学。关于这一问题,赵毅衡曾指出:自后结构主义起,“‘重新发现’皮尔斯开放的符号学,就成了符号学再生之路。从那时起,所有做出了成绩的符号学,无不重新回到皮尔斯所画下的蓝图之上”[2]。
这种皮尔斯转向,在当今符号学新流派中非常普遍。以当下最活跃的几个符号学范式为例:生物符号学学者认为该学科最准确的表述应当为“后皮尔斯生物符号学”(post-Peircean biosemiotics),因为是对皮尔斯广义符号学框架的具体落实[3]。北欧认知符号学派奠基者索内松(Goran Sonneson)认为认知符号学的核心就是皮尔斯符号学现象学[4]。延森(Klaus Jensen)则认为皮尔斯符号学是传播符号学探究新媒介社群与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把新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总结为“皮尔斯+”模式(1)关于这一模式,本人已在Peircean Semiotics in China Today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参见:Zhao Xingzhi,Peircean Semiotics in China Today,in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eircean Semiotics,Tony Jappy ed.,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9,pp.73—100.,即在皮尔斯三元开放的符号学体系基础上,再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融入其他符号学理论或跨学科理论。如“皮尔斯+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夫人”“皮尔斯+洛特曼”,再如“皮尔斯+生物学(于克斯库尔)”“皮尔斯+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路径表明:符号的阐释、交流与互动,取代符号文本的结构分析,成为当今的符号学主流。而在其中,西比奥克提出的整体符号学模式为新世纪符号学的这一多元、开放和融合的新取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二元与三元符号学的形成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新符号学运动出现上述基础理论转向的历史及其深层动因。本文的下半部分将回到符号学学术史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梳理。
符号学自20世纪初创立之时,便存在着二元与三元两种基础模式。前者以索绪尔为代表,后者以皮尔斯为代表。二者彼此不认识,这导致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两套并列的且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索绪尔以语言学为基础,将符号学称为“sémiologie”,而皮尔斯则以逻辑学与现象学为根基,将其称为“Semiotics”。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二元体,而皮尔斯则认为符号与对象、解释项组成三元表意关系。
还需指出的是,三元符号学只有皮尔斯一个源头,而被称为“符号学之母”的英国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 Welby),也几乎同时创立以意义三分为基础的“表意学”(signfics),并与皮尔斯展开长达9年的学术互动,他们共同奠定了三元符号学的基础[5]。
关于符号学的任务,索绪尔与皮尔斯之间也差异甚大。索绪尔认为符号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因此他的研究集中在人类语言和文化领域。皮尔斯的研究则包含非语言符号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是因为他认为“整个宇宙都充满着符号”(CP 5.448(2)CP 5.448,即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文献》第5卷第448段。本报告参照国际皮尔斯研究引文规则,对皮尔斯手稿文献的引用,采取如此缩写格式,下同。)。特别是,皮尔斯强调 “准心灵”(quasi-mind)、“准符号”(quasi-sing)的存在,这为探究非人类的符号活动打开了大门。
二元符号学与三元符号学在20世纪命运迥异。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二元符号学几乎垄断了20世纪符号学研究。该模式在20世纪前半叶,由已形成规模的布拉格学派与语言符号学派推进率先发展成为体系。从50年代起,他的思想又得到如雅格布森(Roman Jacobsen)、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巴尔特(Roland Barthe)、格雷马斯(A.J.Greimas)、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等人的大力推进,最后发展成为对当时西方整个人文学界都有重要影响的“结构主义”大潮。这使结构主义一度成为符号学的代名词,后来学者为去掉这一标签,付出了巨大努力。
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在20世纪前半叶,尽管影响力甚微,但依然有所推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皮尔斯与维尔比之间对意义三分论的奠基性工作。二者通过书信往来,共同致力于以认知与解释为基础的广义意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同时,维尔比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奥格登(C.K.Ogden),则在综合维尔比与皮尔斯的意义理论观点、推进意义理论整合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奥格登经由维尔比的介绍,细读了皮尔斯的大量信件和期刊文章,在当时就非常熟悉其符号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表意三分概念的解读。维尔比曾写信给皮尔斯,说自己为皮尔斯在剑桥找到了一位学生,那就是奥格登:
我非常激动地写这张明信片是想告诉您,我可能为您在剑桥找到了一位学生。他认真细致地研读了我给他的所有您有关存在图的信件和文章,他非常期待盼望阅读您和司陶特教授发表在文集上的大作,希望不久就能收到。您的这位新生(the recruit)名叫奥格登,他在麦格达伦学院(Magdalene College)。同时,他也对探索表意学充满了激情。[6]
在奥格登与瑞恰兹合作的《意义的意义》(TheMeaningofMeaning,1923)一书中,他们不仅讨论了当时默默无闻的索绪尔,也非常熟练地使用并讨论了皮尔斯一系列复杂的术语,且用十多页附录介绍皮尔斯思想体系以及他与维尔比的通信附件。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提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符号学理论:“意义,这个所有的语言理论的核心术语,如果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符号理论,是无法处理的。”因此,“我们的一生几乎从生到死,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7]。从奥格登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维尔比与皮尔斯的影子:符号表意之目的在于解释,获致得体的意义。符号学就是意义学。[1]47而处理这个核心问题的基本框架,就是意义解释的三分关系。
从皮尔斯到维尔比,再到奥格登与瑞恰兹,符号学作为意义学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晰。无论是皮尔斯的解释项三分,维尔比的意义三分,还是奥格登的意义三角,核心问题都是从符号意义的解释与传播出发,探寻符号表意的动态三分结构。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索绪尔的二元结构模式影响巨大,而皮尔斯影响力微乎其微。
同样在20世纪上半叶,在皮尔斯的故乡美国,莫里斯(Charles Morris)则坚持三元模式论。莫里斯是符号互动学派代表人物米德的学生,曾在皮尔斯的母校哈佛大学任教。也正是在此期间,莫里斯最先接触到皮尔斯的完整手稿。1914年,皮尔斯去世后,其十多万多页手稿及8 000多本的图书收藏,在其好友、哈佛大学教授罗伊斯(Josiah Royce)安排下,由哈佛大学哲学系购买并收藏[8]。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将其手稿组织整理出版。根据皮尔斯文献权威费许(Max Fisch)教授考据,莫里斯在1938年出版其名著《符号学理论》(TheoryofSigns)[9]之前,一直在帮助哈佛大学出版社编撰《皮尔斯文选》(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第一至四卷,因此他是最早参与整理并且系统阅读皮尔斯手稿的学者。
20世纪前半叶,以“符号学”为名的理论专著寥寥,其中较为系统的即为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在书中采用大量皮尔斯手稿中的术语,并且延续皮尔斯符号学第三项“解释项”,系统建构以符号接收者为中心的符号学新路径。许多当时并不了解皮尔斯学说的学者,均可在其专著中了解到皮尔斯符号学的概貌。并且,莫里斯还在皮尔斯符号学“三学科”(trivium)学说启发下,把符号学分为“符型学”(syntax)、“符义学”(semantics)以及“符用学”(pragmatism)三个分支,至今依然是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界所公认的标准分类法。特别是第三分支符用学,莫里斯说自己直接借用了皮尔斯的术语“pragmaticism”,认为该分支就是探讨符号意义与使用者之关系的学说,由此开始当代语用/符用学研究大潮。
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皮尔斯的三元模式有奥格登、莫里斯等人的推进,但其思想在符号学界真正获得重要影响力,要到20世纪中晚期,符号学运动进一步打开自身,重访皮尔斯,以三元动态符号观取代二元结构文本观。这首先得益于皮尔斯手稿开掘与整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正如学界了解索绪尔的思想是通过其学生整理出版的课题讲稿《语言学教程》,真正了解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也必须回到他自己撰写的手稿中。只是这一整理过程工作量浩大:哈佛八卷本皮尔斯手稿选集于1958年全部出版完毕,而皮尔斯手稿更加系统的编辑工作即《皮尔斯作品编年合集》[10]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启动,学界终于有机会看到皮尔斯三元符号学系统的细致脉络。与此同时,他与另一位三元符号学模式的创立者维尔比夫人的通信集也于1977年出版,符号的三元分类原则以及意义互动基础在该书中得以清晰呈现。
三、三元符号学的“再发现”
20世纪中后期经由结构主义运动之后,二元符号学开始式微。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模式主要依靠封闭的系统与结构,无法处理当今文化中越发多元、动态的符号表意活动。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即符号与其意义的结合方式可能无须论证,他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本质的第一原则”[11]61。他强调任意性原则是对任何符号都普遍适用的,因此他所要建立的符号学,其对象就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11]65。所以,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中,任意性作为一种根本原则,指导着包含语言符号在内的所有符号体系。换言之,符号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与对象的连接关系,而是取决于社群文化的约定俗成(convention)。
任意性原则引发的一系列重要结果,最关键的就是系统性问题。索绪尔指出“符号学主要着眼点,是立足于符号的任意性基础上的整个系统集团”[12]。这意味着符号必须依靠系统来确定意义。一个系统是各个成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但它不是各个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系统大于各个成分之和。因此,一旦进入系统,各个成分除了各自的功能,还获得了相应的系统功能。在结构主义者们看来,分析单个文化现象、单个语言单位,并无实质意义,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这个语言或文本背后所存在的表意形态,以及这一分析单位在系统中的结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随着符号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结构主义学者开始无法赞同符号系统的自足性与封闭性。例如,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曾为有机论作出最有力的辩护,但巴尔特也于20世纪70年代超越结构主义,正是感到了有机论存在的危机:“巴尔特之所以最后放弃了用形式主义方法确立底本/述本的语言/言语关系的努力,正是因为害怕即使成功了,也会复活旧有的特定作品与特定结构这种有机论神化。这样,我们想打开的作品又重新关闭,重新拥有一个所指的秘密。”[13]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至此开始式微。
进入20世纪晚期,索绪尔二元与皮尔斯三元这两组基础理论模式此消彼长的趋势变得愈加明显。甚至有学者提出,20世纪的符号学者主要把索绪尔理论作为整个学科的基础,是犯了“以偏概全”(Pars Pro Toto Fallacy)的错误[14]46。相应地,皮尔斯模式作为基础理论,或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理论联合,作为新世纪符号学理论基础,成为普遍共识。这一趋势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新世纪符号学以“整体性”(globality)作为出发点,它关注的是作为符号动物的人与其他有符号意识的动物、生物之间的整体性关系[14]30。而以文本与结构为中心的索绪尔模式,显然已无法在这一趋势上提供更多的理论动力。
正是在上述语境下,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符号学模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以大规模“重访”。而这种理论重访的背后,根本是符号学理论界冲破封闭的结构系统观,拥抱多元动态的意义解释观。回顾20世纪中后期的这一理论模式转向,有三位符号学家起到了尤为重要的推进作用。
首先,是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他作为莫斯科语言小组领袖,最早一批在俄罗斯接受到索绪尔符号学,二战后定居美国,开始接触皮尔斯的思想,便在推进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方面做了极为重要的奠基性贡献。他曾非常精准地指出皮尔斯符号学是“表意现象的整体多样性”,而非对语言结构与意义生发问题的研究,这从本质上抓住了广义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雅柯布森随后的系列研究中,他着重从符号三元构成(1967)、三元论与索绪尔的二元论直接的区别与联系(1975)、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等方面引入皮尔斯的相关理论,逐渐扭转符号学界能指/所指二元论一家独大的局面。特别是,他对皮尔斯基础三分法即像似符、指示符与规约符号学的引介,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学界了解皮尔斯符号三分思想的指南。的确,雅柯布森在不少论述中简化了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论,也试图通过一种简化的方式,即所谓的所指二分法——建构皮尔斯与索绪尔思想的联系。这些努力的确对当时的语言学界与符号学界起到了重要影响,至少在结构主义纷纷突破到后结构主义的当时,学者们借助雅柯布森的论著,重新发现了这种区别于二元论的“新”符号学理论体系。正如现任国际符号学会主席科布利(Paul Cobley)所评价:“由于雅柯布森的影响力,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这种三分法,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讨论新符号学范式(与索绪尔比)的一种标准程式。”[15]
其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皮尔斯三元符号学模式推进到世界符号学运动中心,意大利符号学家埃柯(Umberto Eco)功不可没。埃柯在小说、文化与文学理论方面著作等身,其符号学理论则一直处于大众文化研究与小说创作的核心地位。埃柯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皮尔斯三元符号学模式。如果说奥格登、瑞恰兹与莫里斯是三元模式的第一代继承者,他们主要关注意义三角模式的建构;那么埃柯作为第二代拓展者,则进一步激活了三元模式中的“动力因素”,即从解释项与意义生产的关系,说明符号意义生产、解释与传播的互动基础,彻底把符号学从文本与结构中解放出来。
这正如皮尔斯自己所言:“任何事物,只要它能被解释为符号,它就是符号”(CP 2.208),并且“符号过程是三种事物——即符号、对象与解释项——之间的一种合力”(CP 5.484)。这意味着符号意义的产生并不是结构或系统,而是解释者通过符号,对其所指对象之意义的解释。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解释项”这一概念,将当今符号学从文本中心论,转向解释与交流中心论。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符号学诸流派所共同关心的几个核心概念,如“符号活动/过程”(semiosis)、“解释项”(interpretant)、“对象”(object)、“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等,都源自皮尔斯符号学。
特别是,埃柯在其符号学名著《符号学理论》(TheoryofSemiotics)里,把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的生发与传播过程总结为“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清晰地指出了因为有解释项的存在,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便是一个无限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为当今符号学重新找到了动力因素。皮尔斯仅在手稿中阐明了这一机制,并未用该术语进行归纳。因此,正是埃柯对皮尔斯符号学核心思想的再提炼,让更多学者看到了三元动态模式的优越性,对符号学从解码符号学转向解释符号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埃柯对当代符号学运动的推进,还体现在把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从语言与文学领域进一步拓宽到更加广义的文化与传播领域。而他借助的也正是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正如他在《符号原理》第四章开篇所指出:本书“致力于‘符号类型学’的讨论,它缘起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规约符、指示符与像似符)。我将讨论这些符号类型如何覆盖更为细致的符号功能领域以及清晰的‘符号意义生产’活动,进而推出一个更加综合的有关符号生产的诸模式的符号N分法”[16]。因此,符号在不同传播过程中的意义生成方式成为其符号理论的核心,而在这一议题的讨论过程中,埃柯还进一步引入个别符/型符、符码、存在图、试推法(abduction)等皮尔斯符号论一系列核心概念,进一步拓宽了当代符号学运动的锋面。
最后,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在拓展皮尔斯三元模式的全球影响力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在下节详述他在此方面的贡献。
四、三元模式的进一步拓宽:总体符号学模式的崛起
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把皮尔斯的三元模式推进到21世纪。只是这次他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通过吸收与融合诸家符号学的理论,奠定了新世纪符号学“皮尔斯+”的多元融合模式。西比奥克是莫里斯的学生,也是国际符号学权威杂志《符号学》(Semiotica)的创始主编,被认为是“跨世纪的符号学家”[14]30,也是整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与生物符号学这两种主导符号学模式的奠基人。可以说,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比奥克是符号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西比奥克对新符号学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是他拓展了符号学研究的边界。按照西比奥克所设想的框架,符号学不仅是索绪尔所谓根据社会生活对符号生活进行研究的科学,而且是对所有符号交流活动所进行的广义研究。换言之,任何具有符号使用能力的生命体,均被西比奥克纳入到他的整体符号学框架之内。
显然,索绪尔以及后继者以人类语言符号为中心的符号学模式,并不能满足西比奥克的这一理论设想。在他看来,符号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就应当是打开人类符号活动这一边界,思考整个符号域中其他生命体与人类符号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理论出发点,他开始对皮尔斯提出的“符号活动”(semiosis)这一概念进行拓展。
皮尔斯认为符号解释者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具有符号使用能力的“准解释者”。因此,符号活动,也可以是具有符号解释能力的其他生命体之间的符号交流过程。例如,细胞或基因的应答性解释,是一种“准符号活动”。在西比奥克看来,符号活动关系到生命。而这就是西比奥克整体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把符号活动扩展以与生命活动相一致[17]158。
基于皮尔斯的广义三元符号学体系,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为研究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提供了一个交汇所在和观察点。按照他的设想,除了人类符号活动以外,整体符号学还应当包括“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其次,整体符号学也关照“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这一微观层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构想并不是一种泛符号学论(pan-semiotics),它昭示的不仅是符号学彻底打开自身的决心,更是符号学的范式与研究视域在21世纪的转向。唯有通过从“他者”的角度关照其他生命符号活动的构成及其基本特性,我们才可以获得一种全局的视域,探究人类符号活动与整个自然、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当今符号学诸流派的共同出发点。
西比奥克把符号活动扩展至生命活动边界,对近30年来的符号学新思潮、新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符号学理论史家迪利所指出:“自二十一世纪起,二十世纪发展而来的符号学开始走向整体。而引导这一显著的转向特征的学者,自1963年开始至今,既不是索绪尔也不是皮尔斯,而是托马斯·西比奥克。”[14]30又正如当今国际知名符号学者佩特里利所述:“正因为有了西比奥克,现代符号学将其理论视野扩展到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符号学所研究的范围。”[17]155
当然,正是西比奥克发起的这场意义深远的符号学范式革新运动,也使得皮尔斯广义三元模式成为当今符号学界的共识。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之下,欧美符号学在近30年来形成的三个显著转向,即生物转向、伦理转向以及认知转向,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思想的影响。而这一体系的核心,便是对皮尔斯“符号活动”这一概念的扩容。
总体观之,21世纪新符号学运动整体转向皮尔斯三元模式,皮尔斯符号学建构在现象学“三性原则”之上,认为任何符号关系均是由符号、对象与解释项所组成的、不可拆分的动态表意关系。这一原则让解释项成为连接符号与对象的媒介,变成符号意义生成的最关键一环;并且解释项自身又可以进行无限的衍义与发展,这将符号表意过程从能指与所指的封闭系统中解放出来,并把当代符号学的重心转向动态的、开放的意义与互动产生过程。从其学科体系来看,皮尔斯把他的符号学第三分支即“普遍修辞学”定位于处理“符号与解释项之关系”的学说,这已经把符号的解释与传播问题内置于其符号学框架之中了。这就从根本上打开了文本的封闭性结构,使符号学走向开放。具体来说,皮尔斯模式在新世纪的复兴,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开放的理论体系,更适合社会日益多元动态的符号表意现象。皮尔斯建构符号学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寻找一种探索所有符号表意之形式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以“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与“第三性”(thirdness)为核心的现象学三性原则。任何符号活动,均普遍包含着三性:符号构成可以分为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符号本身又可以分为指示符、像似符与规约符;解释项也可以分为直接解释项、动力解释项与最终解释项,等等;并且任何符号现象必然经历从第一性到第三性的动态转换过程。这种分析框架,充分体现符号所具有的、可无限延伸与发展的动态表意本质。符号解释与传播方式进而取代符号的文本结构分析,成为符号学的重点,这也就自然走出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
其次,理论的抽象性与概括性,与新符号运动的理论建构模式更契合。许多学者对皮尔斯手稿中复杂抽象的表述望而却步,但这恰好是其理论的一大优越性。他拒绝过分简化符号的定义[18],是因为他希望这一概念能足够抽象,以至于概括所有的符号活动类型。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准”(quasi-)概念(CP 4.551),如准心灵(quasi-minds)、准发送者(quasi-utter)、准解释(quasi-interpreter)等,旨在把符号表意扩展到人类活动以外的其他地方:任何生命体(或准心灵)只要能借助符号表意,皆为符号学所关照的对象。这就为更加广义的生物符号学模式在21世纪的兴起,敞开了理论之门。于是可以看到,以塔尔图—布鲁明顿—哥本哈根生物符号学派为代表,该学派代表学者在基础理论建设过程中,都回到皮尔斯的手稿之中,试图在生物学与符号学的交叉领域,找到其立论的基础。
不仅如此,皮尔斯对符号表意与传播过程的概括与抽象,同样启发着学者在新世纪对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理论的深入开掘与拓展。而皮尔斯符号学所预示的传播符号学路径,不仅是对传播符号文本的解构与分析,更重要的是,它关注符号传播背后的关系意义及其认知规律。这为我们研究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社群关系、认知传播方式、媒介与表意模式更替等重大前沿问题指明了方向。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就清楚地认识到皮尔斯符号学这一重大优越性,并指出“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人工智能的运演,或者基因密码的机能模式”[19]。
第三,皮尔斯符号学思想所内嵌的跨学科特性,更适合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皮尔斯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符号学,但其学科基础则多元包容。根据统计,皮尔斯的符号学至少包含如下几种面向:逻辑学、现象学、形而上学、修辞学、心理学乃至化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这与他自身是逻辑学家和化学家的学术背景不无关联。但他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符号学基础理论所发表的独到见解,为当今符号理论的跨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