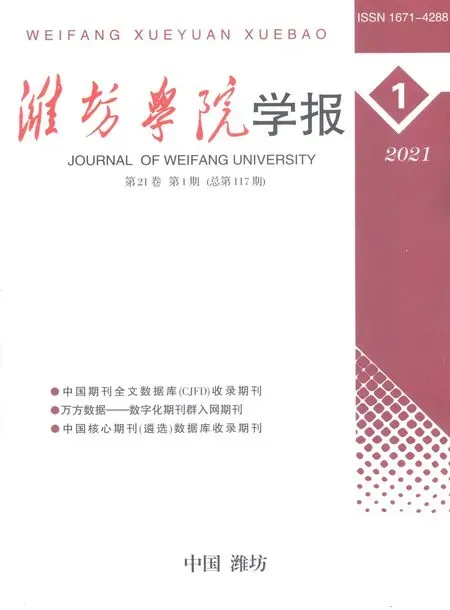程朱陆王如何看待学问与政治之关系
孙延波,董 伟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中共潍坊市委党校,山东 昌乐 262406)
程朱陆王对于学问与政治之关系的看法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他们的创见,而他们是在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释中展开讨论的。
一、学问提供治道
理学与心学认可“学以致用”,这个“用”,就包括用之于政治。程子引孔子的话,道:“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二程遗书》卷四。下简称《遗书》)对于“学”如何用于政治,程朱陆王有自己的见解。
首先,他们都很关注学风与世运的关系。世道兴衰与学风有密切关系,这在学问、学术作为人类的一项独有活动出现以后就成了常态。学问的普及影响一般人知识的量、质及其判断能力与对世界的态度,朱子曾以《国语》与《周礼》文风的比较,认为:“《国语》辞多理寡,乃衰世之书,支离蔓衍,大不及《左传》。看此时文章若此,如何会兴起国家!”(《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下简称《语类》)而学风端正的人可以转移世风,《二程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中曾引司马光举荐程颐的上疏:“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
而学问对于政治最主要的价值是提供治道。
治道,有从根本上说的,在理学,这就是义理。朱子道:“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语类》卷十三)在王阳明看来,根本的治道在于良知,“(仆)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传习录》中。以下简称《传》)
治道的细目,首先就是《大学》中指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朱子道:“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语类》卷一百零八)又说:“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语类》卷七)程朱陆王不相信那些有政治话语权的人不先去正心、修身就能治理天下。朱子道:“心才不正,其终必至于败国亡家。”(《语类》卷十五)有人问陆九渊:“荆门(陆九渊曾任荆门军知军)之政何先?”陆九渊回答:“必也正人心乎!”(《象山语录》上。下简称《象山》)
“三纲领”和“八条目”,分别言是十一事,合言只是一事,所以理学不主张独善其身。朱子道:“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语类》卷十四)一个人有了学问,就需要把学问发扬出去,“明”此明德,以至使民日新。
其次,程朱陆王认为“治道”要从儒家典籍特别是四书五经中寻找。程子所谓《诗》可以达政、专对,又讲:《诗》中的《二南》(《周南》、《召南》)言后妃之德,是圣人教人家齐而后国治。(《遗书》卷四)陆九渊认为《易》之道在于化俗成德,“《易》道既著,则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象山》上)朱子更认为天下之理皆备于《易》,“《易》须错综看,天下甚么事,无一不出于此。如善恶是非得失,以至于屈伸消长盛衰,看是甚事,都出于此。”(《语类》卷三十四)关于《尚书》,陆九渊认为,“《尚书》一部,只是说德。”(《象山》下)朱子则认为《尚书·洪范》详说九畴(九种治理天下的法则),所以是“治道最紧要处”。(《语类》卷七十九)对于《春秋》,朱子则说:“《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语类》卷八十三)
后人在资治中看重的史学,朱子认为只具有次一等的价值。在议评《史记》时,朱子道:“如司马迁亦是个英雄,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只是他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议论!……这国家许多命脉,固自有所属,不直截以圣人为标准,却要理会第二三著,这事煞利害,千万细思之!”(《语类》卷一百零八)因为,看似是身外事务的政治,其实始于“为己”,终于“为己”,这只有圣贤书才能了此目的,史学难以比肩,“若见不透,路头错了,则读书虽多,为文日工,终做事不得。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来说甚盛衰兴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语类》卷一百一十四)
再次,在经世之法中,程朱还特别重视礼的意义。在儒家,礼与乐是社会秩序的根源,朱子道:“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语类》卷八十三)朱子晚年仍带着迫切的心情编辑礼书,说:“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语类》卷八十四)朱子又特重《周礼》,认为周公以之致太平,且竭力赞赏《周礼》中设官的整齐,“看他所立法极是齐整。”(《语类》卷八十六)礼,还是一种专门之学,礼学者是政事与人事的顾问,“古者礼学是专门名家……凡欲行礼有疑者,辄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庶乡党典礼,各各分明。”(《语类》卷八十四)
第四,为让人明治道知典籍,就要兴教化。在儒学看来,学、政是一理所发,本为一体。朱子道:“古人学校、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伐、师旅、田猎,皆只是一项事,皆一理也。”(《语类》卷一百零九)讲学乃政治清明之希望,“天下人不成尽废之,使不得从政。只当讲学,庶得人渐有好者,庶有可以为天下之理。”(《语类》卷一百零八)因此,程朱陆王皆注意学校讲授甚至于创立学校、书院,如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扩建岳麓书院,创建竹林精舍(考亭书院);王阳明创立龙岗书院、阳明书院,兴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
第五,要培养学人的治世能力,并且需要花长时间涵养。程子想象的教育是这样:“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遗书》卷十五)政府要保证在学之人衣食无忧,这样经过长期训练,40 岁左右的人学问、德行、心志已定,这时才可允许入仕,官僚队伍素质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最后,宋明儒家仍与先辈一样特别关注君主的学问。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对君王的教育制度,在他们还没有执政之前有王(皇)家私塾教育,在其中的某人成为帝王之后,又有经筵制度,专门给帝王讲学。程颐、朱子都做过经筵讲官。儒家认为治天下的一件大事就是格(正)君心。朱子曾道:“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语类》卷一百零八)朱子认为,经筵进讲,要有开悟启发之功,又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变成纯学术讲座,“若告人主,须有反覆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盖人主不比学者,可以令他去思量。”(《语类》卷一百零一)
程朱虽有尊君之论,如朱子道:“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语类》卷十三)但理学家又有师道尊严的意思,希望君王尊重学术,程颐曾当面批评宋哲宗随意折柳,又曾要求讲官坐讲,(事皆见《二程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朱子也道:“天子自有尊师重道之意……天子入学,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齿(年纪)不臣之也。”(《语类》卷八十七)
二、学问对政治的消极影响
宋明儒家并不认为所有学问都对政治有正面影响。后世儒家看中国历史,认为周代之后无善治,原因即在于孔孟所讲的真学问没有得到坚持与发扬。就政治家而论,秦之后理学只认可两人:张良与诸葛亮。但就是他们二人,虽然被认为“有儒者气象”,他们的学术背景却是非儒家的,“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语类》卷一百三十六)所以程颐评孔明道:“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遗书》卷二十四)
许多想有作为的官僚臣子最终不足以成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不端正。即如程朱陆王在人品上认可在政治上反对的王安石,他的变法被认为败坏当时遗祸后人,依朱子的意见,因为他“本原不正,义理不明,其终必至于是耳。”(《语类》卷五十五)
但王安石学问虽有不正,议论却高妙,与之争辩的司马光辈学问虽端正,然见识却短浅,议论不免粗疏,“(司马光辈)只是胡乱讨得一二浮辞引证,便将来立议论,抵当他人。似此样议论,如何当得王介甫!”(《语类》卷一百零七)
道术不纯的还有一辈文章之士,他们一旦为官,亦非必定是奸恶之徒,但举止轻浮,观点摇摆,对政治甚有游戏之心。典型的如苏东坡。朱子称他的政论文只是逞其意气,“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欲其说之必行。”(《语类》卷一百三十)所以,“东坡只管骂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同上)
道术不纯之外,程朱陆王认为学术异端对政治危害最甚,王阳明称其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传》中)
异端中的道家善为术数。后世史学喜欢称赞汉初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国,但在朱子看来,老氏之学全是退步占奸,表面的无为掩盖背后的术数,所以,“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朱子因此重新评价西汉初年历史,道:“黄老之术,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让别人,宁可我杀了你,定不容你杀了我。他术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犹善用之,如南越反,则卑词厚礼以诱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等事。这退一著,都是术数……看文景许多慈祥岂弟处,都只是术数。”(《语类》卷三十九)
老子之学非光明正大,佛学则是自私。佛学说空,无了是非,那些作恶多端的奸臣往往也要谈禅说道,“则此一种学,在世上乃乱臣贼子之三窟耳!”(《语类》卷一百二十四)
和朱子同时,与朱子展开王霸义利之辩的永康学派,被朱子称为“只要理会得许多做劫盗底道理……可畏!可畏!”(《语类》卷一百二十三)对于讲究事功的永嘉学派,朱子认为是在三纲五常之外另讲一番道理,只是“乱道”,“他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不自知。”(同上)
至于法家,朱子认为,他也是要致富强,但“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语类》卷五十六)
陆九渊则不喜欢兵家。他认为如果杀伐是以正伐邪,何用诡道?“兵书邪说。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须别邪正。”(《象山》下)
三、政治如何影响学问
虽然政治最终肯定了程朱陆王之学,理学还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但就他们本人来说,则更看到了政治对学术的消极影响。
首先,政府史书的编写常有偏向性。古代中央政府有专门编史机关,朱子认为其中的机构设置“略无统纪”,史官们分别书写,不去做讨论汇总。更重要的是,写作中又往往根据君主或者势力大臣意愿改来改去,“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其次,科举取士更是他们一致批评的对象。陆九渊称:“大率人多为举业所坏。”(《象山》下)陆子的理由是“取人当先行义,考试当先理致,”这些目的科举都无法做到。对此,朱子甚是同意,在朱子看来,科举使学子们不再系统的读书,读书也不再是为明理修己,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士子们言行分离,“专做时文(指科举文章)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语类》卷十三)但他们也非一概否定科举,因为这是在古代最合理公平的取士方式,“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同上)他们只是认为举业夺人心志,防碍人更高的追求,程子道:“若(以此)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遗书》卷十八)
再次,政府管理的学校也弊窦丛生。即如太学,每次补试名额有限,但参试学子动辄一二万人,朱子认为,“要得不冗,将太学解额减损,分布于诸州军解额少处。如此,则人皆只就本州军试,又何苦就补试也!”(《语类》卷一百零九)又如学校中的教官,在朱子看来有两个问题,一是失之年轻化,二是需自乞。朱子道:“某尝经历诸州,教官都是许多小儿子,未生髭须;入学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须是立个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同上)又说:“教官,人之师表……今皆是陈乞,然不陈乞,朝廷又不为检举。朝廷为检举方是,亦可以养士大夫廉耻。”(《语类》卷一百三十二)
还有更恶劣的,如禁书。宋太祖不想让老百姓读《易》,原因在于,经筵讲官讲到《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太祖遽云:“此书岂可令凡民见之!”朱子指出,这是明显错解《周易》所致。(《语类》卷六十六)朱子又说王安石行其新经义时禁了史书(这个并无史事证据),特别是不让皇上检览史书,“此非独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见兴衰治乱之端耳。”(《语类》卷十)程朱之书也一度被本朝所禁。
再者,朱子以史书为例,指责一些当权者要杀掉乱说乱道的文人。东汉末王允在杀蔡邕之前,道:“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西汉杨恽坐上书怨谤,腰斩,朱子观其书,认为,“谓之怨则有之,何谤之有?”(同上)又如,朱子说,黄巢入长安,夜中有人作诗贴到三省门上骂黄巢,“次日(黄巢)尽搜京师,识字者一切杀之。”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记载:“凡杀三千余人。”((《语类》卷一百四十)
四、检讨与反思
程朱陆王关于学问与政治之关系的各种说法,今天我们如何理解?
首先,这种关注的迫切心情值得同情。政治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学问不离不弃,程朱陆王从正面来肯定学问对于政治的价值,他们的许多提法在今天仍然值得珍视。
其次,程朱陆王把学问作为从事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却也存在标举义理过高,绳人太严的问题。例如,对于后人推崇的唐太宗,因其弑兄逼父,程子道:“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流毒至于君不君,臣不臣,造成安史动乱,藩镇割据。(《遗书》卷十八)上文讲到秦代之后他们只勉强认可张良与诸葛亮两个政治家,还都学术不纯。如此议论,虽是高尚,代价则是失去同志与支持者。
再次,对于治道,他们提倡的过于抽象,没有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治理原则与方法。如程子,认为天下事只是区别义与利,“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遗书》卷十一)又说:“得此义理在此,甚事不尽?更有甚事出得?视世之功名事业,甚譬如闲……天来大事,处以此理,又曾何足论?若知得这个义理,便有进处。”(《遗书》卷二上)上文已举朱子所谓明义理就能泛应曲当,王阳明说得更为疏阔,他既认心即理,理即心,则但于“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传》下)这至少在理论上否认了政治问题的复杂性。面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他们提供的办法常常显得迂腐又囿于常识。例如,朱子做地方官也会思考民生问题,就如他对救灾的讨论,有两条建议,一是感召和气,二是储备粮食,(《语类》卷一百零六)却不去考虑革新技术、组织生产以提高产量。
还有,对于一些具体政治原则也缺乏辨析,例如对于作为“治本”的八条目。程子讲,“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遗书》卷四)朱子道:“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语类》卷一百零八)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是逻辑与现实的必然吗?大概很难这样说。因为,其一,八条目的前后件之间很多只是盖然关系,缺乏必然性,就如由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前件作为后件的必要条件逻辑强度都极弱,更不用说非充分条件;即使不管它属于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都假定它是成立的,还是需要一个前提——身、家、国有同构关系,组织结构必须相同,这样才能把治身的方法横移去治家,治家的方法横移去治国,但这更是不可能的。其二,就实事讲,儒家最敬仰的孔孟二圣都没有很好地齐家,二人都是离过婚的(孔子出妻见《礼记·檀弓上》,孟子离婚见《荀子·解蔽》),但程朱陆王不会否定孔孟最能治国平天下。其三,那些被认作最能治国平天下的远古圣王却可能没有齐好家,就如尧舜,他们的儿子都顽劣不堪,舜称尧帝的儿子丹朱,“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尚书·皋陶谟》)孟子也说:“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孟子·万章上》)但尧舜不能齐家却能治国。
最后,对于治道,他们只认可他们继承的圣贤之说,外此皆是非正统或是异端,甚至理学者与心学者也互相指对方为不合正道。在意识形态领域程朱陆王有高度的警觉,不允许自由地发表主张,如王阳明明确反对人著书立说,道:“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传》上)王阳明似乎忘记了他何尝没有立说!
当然,我们这样检讨是以现代人的理论来苛求古人,但这种苛求是必要的,至少,它表明在借鉴古代圣贤理论的同时不能忘记还要秉持批判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