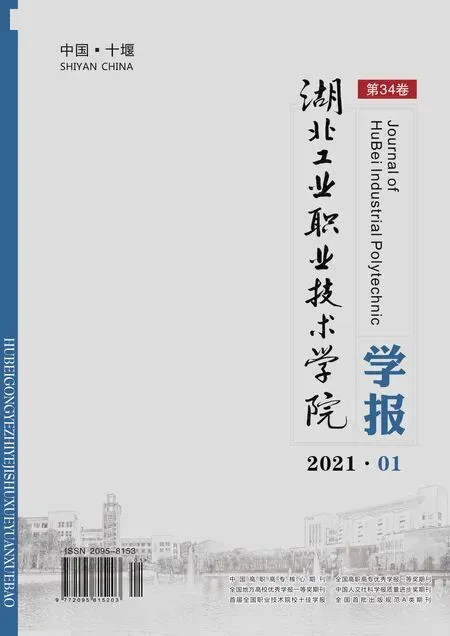《南方车站的聚会》:多元碰撞创造艺术特色
李 想,马 晨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作为“社会解剖家”与“电影类型探索者”,刁亦男的电影作品独具一格,无论是表现风格还是内涵思想都绝不单一化,既有文艺气息又充满黑色电影的晦暗、悲观与绝望,并将其个性化的社会认知与人生体验融入电影中,深刻剖析人性并反映社会问题。《南方车站的聚会》是刁亦男继《白日焰火》后的又一部力作,影片充斥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聚会”,这些元素“聚会”带来的碰撞与交融成为影片的亮点并展现了影片独有的艺术特色。在人物行为、言语的真假碰撞中,影片采用多样化叙事手法并设置情节的反转、突变;在人物内心善恶的复合交织中,影片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复杂与善变;在影视画面的美丑融合交汇中,影片展现出充满个性的黑色美学与暴力奇观。
一、真与假的“聚会”营造个性化叙事模式
刁亦男曾在访谈中说:“我的电影是一种沙盘演绎,我不仅想给观众一个骨架和线性的情节,我还想给观众人物周围的世界,人物的根茎还能带出来一些周围世界的泥土,而不能只是人物关系、铺垫、矛盾、转折、戏剧性的解决。”[1]因此,刁亦男绝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叙事,而要通过人物之间真假难辨的言语和行为自然而然地创造叙事手法的灵活、多变与情节的反转、突变,形成个性化叙事模式。也正因为以“人物的根茎”带出一些“周围世界的泥土”,影片情节的安排都紧紧贴合人物内心与社会现实,无论叙事的方式还是情节的反转、突变,都给人一种真实感、可靠感,彰显出合理性、必然性,充满张力,令人回味。
首先,真与假的“聚会”推动叙事手法的多样化。影片开头是周泽农和刘爱爱在南方车站的会面,此时两人对彼此身份的真假都有怀疑,只有通过述说经历获取信任,这便推动影片开头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故事发生的背景。两人讲述完毕后,影片采用顺叙的方式演绎之后的剧情,但由于片中人物受利益驱使,行为和言语都难辨真假,甚至有着由忠诚到背叛的转变,为将错综复杂的剧情展现得眉目清楚,影片在顺叙整个剧情的过程中又采用分叙的方式传递人物行为真假的信息,例如华华由真心变假意先通过常朝被抓片段暗示,后通过他与东哥对话片段明示;杨淑俊由信任警察、出卖丈夫到欺骗警察、帮助丈夫的转变通过警察到她家搜查的片段表现出来。人物是影片叙事的核心,影响影片叙事的方式,正是人物行为和言语的真假难辨与不断转换推动《南方车站的聚会》采用倒叙、分叙、顺叙穿插结合的多样化叙事手法,而多种叙事手法的混合运用也使影片曲折波澜又有条不紊、引人入胜。
其次,真与假的“聚会”推动情节的反转、突变并体现其必然性。情节的反转、突现不仅使故事变得丰富饱满,还可以设置悬念,激发和捕捞观众的好奇心。影片中刘爱爱和华华一直在真假之间摇摆不定,华华一开始真心帮助周泽农但很快就出卖他,刘爱爱两次出卖周泽农最终却选择真心帮助,他们对周泽农真心假意的变化在关键处推动情节的反转、突变。这些反转、突变看似偶然却有一定的必然性。华华的身份是组织陪泳女卖淫的黑社会,他和周是发小又一起混黑道,因此存在一定的情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一开始冒着巨大风险帮助周,但道义只是江湖的“面具”,利益的追逐和血雨腥风才是本质,也是刁亦男力图表现的重点,因此华华面对猫眼的威胁和赏金的诱惑必然要背叛周。刘爱爱的身份是陪泳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她只是男人的玩物,无力反抗命运更无法追求幸福。她第一次背叛是在和周湖中缠绵后对周明显产生爱慕之情时发生的,看似意外实则合理,作为陪泳女的她受尽冷眼与玩弄,内心早已冰冷,只求苟活于世,此时的她没有勇气搭救周也并不认为舍命搭救是值得的。之后刘爱爱遭受闫哥欺负被周搭救,她随即出卖周,却将三十万赏金分给杨淑俊,这是因为周给了他在社会中得不到的尊重、温情和安全感,此时她对周充满了仰慕与感激之情,而将赏金分给杨只是金钱上的损失并不会危及生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刘为求内心上的安宁必然会这样做。人物行为的必然性来源于现实,影片中人物“真心”、“假意”变化的必然性正体现了导演刁亦男对于现实中社会、生活与人的深刻观察与体悟,这些必然的反转深刻揭示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更深层本质,使观众形成一种深入灵魂的审美感悟,充满艺术感染力。
多样化叙事手法的运用和充满悬念的情节反转、突变是《南方车站的聚会》叙事模式的重要特点。这种相对松散、复杂的叙事模式能使人物存在主义式的心理迷宫得以更为有效和彻底地呈现,从而揭露人物在“真心”、“假意”之间的心理博弈,并深化人物行为必然性所带来的感染力。导演刁亦男善于制造人物行为的不确定性,对于人物叙事的艺术追求帮助他合理驾驭悬念以及电影情节的松弛度,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并且让其成为叙述的动力,带动各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形成个性化叙事模式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善与恶的“聚会”塑造复杂人物形象
黑色电影主要指好莱坞以暴力为题材,具有德国表现主义摄影风格与法国存在主义人文思想特征,影像风格阴郁、悲观,充满愤世嫉俗和人性危机的犯罪与侦探片[2]。黑色电影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于人性危机的揭露,多表现人物内心阴暗、扭曲的一面,借助晦暗、诡异的影像塑造一个悲观阴冷的世界。显然,《南方车站的聚会》符合黑色电影的这些特征,但该影片并非是常规的黑色电影,其中存在的“反黑色成分”是导演刁亦男对黑色电影在中国在地化实践的一次创新,在不影响黑色电影整体基调的前提下,深刻揭露复杂人性,形成独特风格。“反黑色成分”的重要表现是人物内心的善意,在善与恶的聚会中“黑色”与“反黑色”的对立与交融实现风格化,影片中所有人物都是复杂人性的代表,没有完全善的人物,也没有完全恶的人物,都是善恶交织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
首先,影片中“恶人”心存善意。周泽农及所有的黑帮分子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他们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然而周泽农在失手杀掉警察后想到的不是逃亡,而是让妻子举报他以领取赏金。剧中刘爱爱和周泽农有这么一段对话:“你没想过跑吗?”“往哪里跑?”“往南啊,一直往南。”“我哪里都不去,找你报案就是把赏金留给屋里。”,可见在南方车站周泽农面临生死抉择,他有生的机会,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却毅然选择了死,虽然在穷凶极恶的罪行面前这点善意显得微不足道,但依然能彰显为人夫、为人父的担当。其余黑帮分子也都如此,常朝和杨志烈虽然作恶多端但为失势大哥不惜出生入死的义气令人敬佩;猫眼穷凶极恶对弟弟猫耳却非常好;华华在影片前半段也为了兄弟情义甘冒风险,这些“恶人”形象并非固化于一恶到底的单一模式,而是被赋予复杂的性格与思想,都被鲜活地立了起来。
其次,影片中“善人”心存恶意。常规认知中,代表正义的一方的警察应该都是善良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却利用细节彰显出警察的恶。影片中警察对生命消逝展现出可怕的冷漠感,面对亲手终结的生命,他们并不悲悯反而沾沾自喜。击毙杨志烈后,一名警察大叫:“死了、死了”,语气中有如释重负感但更多的是喜悦与激动,击毙周泽农后几个警察更是欢喜得与尸体合影。将穷凶极恶的罪犯绳之以法固然可喜,但对死者为大的漠视仍让人不寒而栗。另外,影片的一次抓捕行动中,刘队批评了一个队员,那位队员穿着花哨,竟和古惑仔有几分相似,这是在暗示警察心中也有黑帮分子的恶。人性面前一切外衣都将被撕破,即使警察也食人间烟火,也有着杀戮的快感与作恶的欲望,在这里警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正义化身,而是被还原成了最真实的人。其他人物如刘爱爱和杨淑俊,也都在善恶之间徘徊。刘将赏金分给杨是一件善行,但出卖周泽农却是恶的。杨在影片最后和刘并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赏金,并紧紧抱住刘的手臂似乎担心她会跑掉,对金钱的贪欲在这些细节中显而易见,但当路旁洗车人将水喷到她脸上时,她似乎如梦初醒,将手放开并和刘相视一笑,此时杨内心也经历了善恶徘徊的过程。可见,影片中即使是刘、杨这样的弱小者也绝不平面化、脸谱化,内心也有复杂的善恶博弈。
艺术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本质的人,这就决定了艺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必定是丰蕴的、复杂的。在黑色电影对人性危机深刻的揭露面前,善意虽然微不足道,却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失去那一丝善意便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南方车站的聚会》关于人物塑造的整体风格可以概括为:文本因内在矛盾形成特殊张力,一方面指向外在世界,更主要的是朝向艺术家内心,通过犯罪爱情文艺的外观,含蓄地表达个性化的社会认知与人生体悟——世界残酷,生存不易,人性天然地追逐良知与温情,小人物身上不乏闪光点,坏人也有值得肯定的方面,糟糕的人生未必全无价值[3]。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并非遵循当代艺术传统,严格区分善恶,而是追寻现实主义原则,从生活出发塑造人物形象,突破人物形象片面化、单一化,展现出人物的立体性与真实性,吻合观众的人性理念,使得主要人物形象立得住,因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特色。
三、美与丑的“聚会”创造黑色美学与暴力奇观
黑色电影无不风格晦暗、情绪悲观,情节与人性危机紧密相关,主人公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体现出一种黑色、残酷的美学特征,形成黑色美学。在黑色美学中,美好的面纱往往被残忍地撕开,而世界阴暗、绝望的一面则被展示出来,但这种展示一般是严肃且 “哀而不伤”的,这也是“黑色美学”与“审丑”之间的区别[4]。可以说单纯有“黑色”而无美感并不能称为黑色美学,黑色美学往往是在美与丑的“聚会”中以丑压倒美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南方车站的聚会》黑色美学的视觉呈现集中体现在男女主人公湖上相会的片段。漆黑的夜色里,周泽农与刘爱爱在水塘的小船上相会,小船安静地飘着,四周只有水波荡漾的声音,两人亲热之后静静地抽烟,在晦暗阴冷的环境中透露出浪漫气息,情感的“美”与情境的“丑”在这一刻完美交融。之后二人下船走到河边,刘望向远处漆黑的豆芽山,黑暗中突然现出一点亮光,紧接着多个亮光闪烁起来,在漆黑夜空中点点亮光翩翩起舞,周和刘望向远方互相交谈,这一刻静谧、浪漫、美好。但那亮光是警察的摩托车灯光,亮光的背后是紧追不舍和亡命天涯,对应的画面就是周横尸臭水沟,光亮越来越多,给人的压迫感也就越来越大,眼前的美与背后的丑形成巨大的反差,再美又能怎么样,最终都要面对死亡的丑陋,因而给人一种悲观幻灭的绝望之感。对于绝望感的营造是黑色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南方车站的聚会》对这一点的处理非常独到,影片采用了“反衬”和“对比”的手法,在绝境处总能展现出携带些许温情的希望与美好,但这些东西转瞬即逝,紧随而来的是美丑对比带来的悲凉与凄怆,从而深化黑色宿命所带来的绝望感,将黑色电影的黑色美学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影片中暴力的表达,不同于吴宇森充满令人荡气回肠的江湖道义和兄弟友情的暴力美学,刁亦男力图营造的是暴力奇观的仪式感。《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暴力奇观设计遵循真实与血腥的思路,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呈现某种现实和梦之间的影像,并通过硬朗的剪辑,尽量让其具有一种形式感,甚至是一种美感[1]。该影片中的暴力极度写实且贴近日常生活,力图在血腥中表现出浪漫化的强悍,呈现给观众美与丑交融的视觉盛宴。
影片暴力奇观的呈现有两个代表性的片段。第一个在影片开头,猫眼用叉车将黄毛杀死,在死亡的一瞬间,黄毛的头旋转飞向高空,身体喷着鲜血随电瓶车倒下,项链挂在货叉上摇晃着滴血。一系列镜头设计给人巨大的震撼感,充满美与丑结合产生的张力。身体与头颅的瞬间分离充满爆发力,却是死亡的明喻;旋转飞向高空的姿态甚是优美,却以丑陋的人头为对象;摇晃的项链带来梦幻感,却沾满了罪恶的鲜血。这一突如其来的暴力片段满足了观众的震惊体验,也凸显了死亡的仪式感和美学意味。第二个片段是在居民楼里,周泽农用一把白色的雨伞捅进了猫耳的肚子,他将伞撑开的一瞬间,鲜红的热血喷涌在白色的伞面上,形成一朵“血花”,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使其在惊愕的同时已经难辨美丑。单从视觉的角度看,色彩的强烈对比与画面瞬间成形的爆发力会带来极佳视觉体验,从而产生美感与愉悦感;但是透过表面利用理性分析这一系列画面的成因就会发现,这一充满美感画面的背后是杀戮的丑陋,色彩中的红色由鲜血构成,而白色雨伞是杀戮的工具并象征着死亡。这一片段里视觉上的“美”与意识中的“丑”在画面中完美融合,正是美与丑的融合形成暴力奇观,对观众产生视觉和心灵上的巨大冲击,带来极佳审美体验。
《南方车站的聚会》是一部根植于现实且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黑色电影,致力于表现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性欲望的自我膨胀。片中人物受制于野蛮残酷的生存环境和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或许向往“真善美”,却只能在“假恶丑”里寻找出路。导演刁亦男的优秀之处在于合理驾驭这些对立交织的元素进行剧本创作和视听设计,通过多样化叙事、人物细节刻画、仪式感营造等方法,摆脱类型电影的束缚,大胆对黑色电影进行本土化创新,追求震撼灵魂的审美效果和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最终形成了个性化叙事模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美学与暴力奇观,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这对今后中国电影摒弃模式化、浅显化、媚俗化,增强思考性、艺术性、观赏性,形成中国特色,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