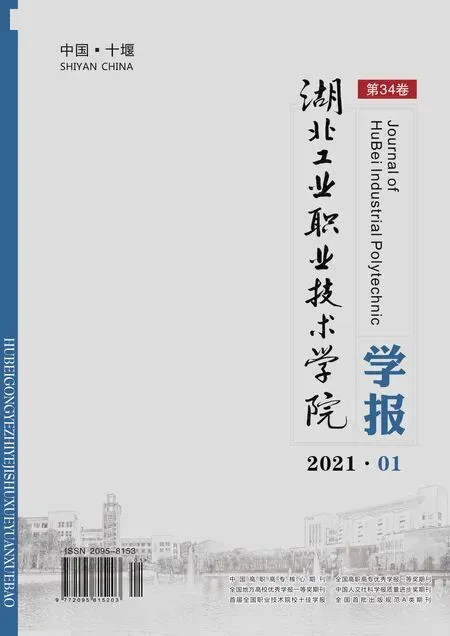媒介转化视域下的《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研究
吴岸杨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北京 100081)
2009年,河南作家刘震云推出了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以“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1)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授奖词。,在呈现一幅乡土中国浮世绘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人际关系中难以言喻又深入骨髓的孤独。2016年,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同名影片,原作者刘震云担任编剧,其女儿刘雨霖执导。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全篇36万字,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大大小小出场人物达百余个。由于篇幅和体量的限制,电影只能选取部分内容进行改编。影片《一句顶一万句》片头字幕显示:根据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部分章节改编。实际上,它主要取材于小说下部第一章和第六章至第九章的部分内容。从情节线索来看,影片以牛爱国的婚姻作为主线、牛爱国姐姐牛爱香的婚姻作为副线,原作中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改心/巧玲,牛爱国的小学同学冯文修等人物则被“合并”或略去(2)小说里的杜青海、李克智和冯文修三个角色,“合并”成电影里杜青海的形象。参见刘雨霖、刘震云、李迅:《质朴地拍一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编剧、导演访谈》,《当代电影》2017年第2期。。
从主要人物、情节线索、思想内涵等方面来看,影片《一句顶一万句》与原作都大相径庭,后者被改动得可谓面目全非。传统的改编研究可能就此得出结论:影片不太忠实于原著。但实际上,小说和电影原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媒介,它们有各自的表现优长和传播规律。故此,忠实与否不应成为评价文学改编影片的唯一准绳。本文基于媒介转化的视角,对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及其改编影片展开比较分析。
一、从小说到电影:两种不同媒介
对信息表现形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内容,所以关于任何媒介产品的文本分析都很难脱离其媒介特征而单独存在[1]。小说是语言艺术,通过语言、文字来讲述和抒情;电影是视听艺术,借助影像、声音来叙事和表意。从媒介转化的角度来看,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语言媒介和视听媒介的不同。
为了事无巨细地呈现中国人的“百年孤独”,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不厌其烦地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具体来看,在用词方面,全篇里“说话”一词共出现316 次,“说得着”出现33次,这本身就是对主题的暗示。在情节方面,大量鸡毛蒜皮、生活琐屑的反复出现,强化了“说得着”的重要性及其稀有性。比如,小说下部的牛书道和冯世伦因为一个馒头不欢而散;他们的下一代牛爱国和冯文修又为了十斤猪肉分道扬镳。相似情节的一再重现,无形之中建构起读者对“知己难寻”的理解和认同[2]。甚至下部主人公牛爱国的遭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上部主人公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命运的一种重复——两个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先后离开和走回延津。
在句式方面,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还大量使用“不是A,而是B”句式。就具体运用而言,这种句式又有“不是A,不是B,而是C”“不是A,而是B;不是B,而是C”“不是A,当然也是A;还不是A,而是B”和“不是A,而是B;不是C,而是D”等几种变体。因篇幅有限,这里仅举几处和牛爱国有关的例子。
牛爱国也觉得自己不容易,但他的不容易不是庞丽娜说的不容易,而是说话办事,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3]275。
牛爱国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庞丽娜和小蒋的事发,他就差一点杀人。没有杀人不是小蒋和庞丽娜不该杀,当时连杀小蒋儿子的心都有,而是因为牛爱国有一个女儿叫百慧……[3]309
爱国提出要去当兵时,她的姐姐牛爱香说:知你为啥要当兵,不为当兵,是烦这个家;也不是烦这个家,是烦咱爸妈[3]215。
据统计,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类似这种“不是A,而是B”句式共出现208次。这种拧巴的句式不仅营造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节奏感,更通过其反复出现,展示了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拧巴关系,由此深化了作品对“孤独”主题的表达[4]。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或者说,表达的重复和拧巴,既是小说的语言特点,也成为它传达主旨的落点。
这种语言修辞自然无法被电影照搬。小说通过时间的流淌来讲述故事,电影则通过空间的铺陈来还原现实。牛爱国的职业在小说里是汽车司机,在电影里则被改成了修鞋匠。由动到静的转变,使主人公的主要活动场所被固定在狭小的空间,这暗合了人物不自由的命运和困窘的生存状态。对牛爱国在家里储物间的两处俯拍,同样显示出他被逼仄的环境所包围,人物压抑、隐忍的心境由此得到呈现。而牛爱国拒绝离婚以后,九曲回肠的河流则成了庞丽娜忧愁、苦闷的形象化表达。但综观全片,它始终未能像原作小说那样,建立起贯穿始终而自成一脉的视听风格。
二、孤独如何言说:叙述者的职能
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在故事(tale)之外,还需要一个叙述者(tell)[5]。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孤独”是叙事的重要内容。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对于孤独的描写和展现,渗透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电影则将其聚焦于爱情,这主要是电影时长所限。而就表现爱人之间隔阂、冷漠而言,小说和电影也有很大的区别。
作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作者使用的叙事工具,叙述者可以起到提供信息、评论和概括等作用。因为都需要用语言进行交流,小说里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本质上也可看作“人”[6]。所以,运用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可以在情节发展、环境描写、人物塑造之外,随时自由地跳出来评论、解释或说明。比如小说对牛爱国和庞丽娜婚姻的描写:
牛爱国不爱说话,庞丽娜也不爱说话,大家觉得他俩对脾气;他俩在一起相处两个月,也觉得对脾气;半年之后,两人结了婚。结婚头两年,两人过得还和顺,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百慧;两年之后,两人产生了隔阂。说是隔阂,但隔阂并不具体,只是两人见面没有话说。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但它们的区别外人看不出来,看他们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大家仍觉得他俩对脾气;只有他俩自己心里知道,两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3]219。
短短两百多个字,就清楚地交代了牛爱国和庞丽娜结婚两年以后的情感变化过程。在这里,叙述者的讲述故事职能和解释、说明职能浑然一体。因为它们都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读者可以很轻松地接受,也就能理解两人的“说不着”以及由此而生的孤独。这段文字篇幅虽短,却是牛爱国夫妇情感关系的如实写照和婚姻危机的重要基础。
就电影叙事而言,因为影像具有无人称、无时态、无语态、无语式的特点,所以电影的表现模式更倾向于“演示”而非“叙述。[7]”也就是说,电影的叙述者是一个系统,因此它在评论、解释或说明等方面就不能像小说那样简单、直接。对于上述小说内容,改编影片是怎么转化的?庞丽娜和牛爱国从一开始“话还没说,就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啥”到“没话”,转变的原因何在?电影直接用“十年后”的字幕把这个过程跳过了。
如此重要的内容被省略,势必导致影片叙事根基的动摇和主旨表达的游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力有不逮。电影当然也可以精妙地呈现夫妻感情变化过程,《公民凯恩》里著名的“餐桌段落”就作了堪称完美的示范。问题在于,小说里的这段文字,并不只是在说感情变化,更剖明了其背后的原因——没话说。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未能触及牛爱国夫妇没话说的根源,它对孤独的言说也就只能隔靴搔痒。
从叙述者职能的角度来看,小说在讲述故事或发表评论、补充说明时,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媒介,因此可以方便、自如地进行职能转换。而电影的叙述者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涉及摄影、表演、服装、化妆、道具、声音、剪辑等诸多要素,因此在这方面就不如小说游刃有余。这是由媒介特性,或者说是由小说和电影叙述者的不同性质决定的。
所以,小说里有的人擅长“码事儿”,有的人能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有的人能把一件事说成四件事。这些都是叙述者在直接告诉读者,有时穿插在情节中,有时则直接解释或说明。电影为了阐明牛爱国夫妇的“说得着”,也借婚姻登记员之口问道“具体点儿”,这同样是叙述者在起作用(涉及剧作、表演等元素)。但由于电影的叙述者本身相当庞杂,所以无论这里说得如何具体,也终究难以传达出小说里“有的话无人可说,有的人无话可说”的苦楚与无奈。从牛爱国和章楚红在夜市摊上的深情对视,也不难看出导演试图把“说得着”可视化的努力,但并不成功。至于宋解放说他和百慧“说得着”,就更突如其来而莫名其妙了。
三、节选·置换·移植:电影的大众性
如果说前述对小说内核阐释的肤浅,受到媒介叙述者和创作者能力的双重制约;那么对原作素材的节选及对其主题进行的置换,则更多是编导有意为之。
从媒介演进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人类艺术分为传统艺术和传媒艺术两大族群。所谓传媒艺术,是指机械复制时代以来,借助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发展起来的各种艺术形式,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以及经过现代传媒改造的传统艺术形式等。因为要参与到现代传媒的谱系当中,所以传媒艺术的创作者在构思时,就必须考虑到大众需求和作品的大众意义,以及它将在在大众传播中产生的效果[8]。
就一般商业电影而言,其创作旨趣必须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趣味。《一句顶一万句》的改编电影同样如此。原作小说人物繁芜丛杂,为何选择了牛爱香和牛爱国姐弟俩?无法交心的孤独和悲凉固然深刻,但结婚、离婚的家长里短无疑更是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通过对原作内容的选取,影片已经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影片后半部分围绕“看女儿”产生的矛盾,以及加入的女儿百慧生病的情节,更使影片具有了家庭伦理剧的色彩。
更进一步来看,如果小说探讨的是形而上的孤独与隔阂,那么电影表现的就是形而下的婚姻和生活。小说里,牛爱国曾劝庞丽娜回心转意,后者则答道:“本来就没有心和意,哪儿来的回和转?”这句台词在电影里被改为“本来就没有的事,哪儿来的回心转意?”这样的改动,在暗示他们存在和好可能性的同时,也使牛爱国夫妇的“说不着”显得更像是一场“婚变”。
如前所述,影片并未展现牛爱国和庞丽娜从“说得着”到“说不着”的转变过程。不仅如此,它还添加了庞丽娜想去欧洲旅游的情节。去欧洲必然花费不菲,在消费能力方面,摆摊修鞋的牛爱国和开照相馆的蒋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出轨和经济能力、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它还仅仅只是因为“说得着”吗?
如果说小说里的“说不着话”,像是先天的、化学的反应,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与人间烟火、柴米油盐无关;那么电影里的“说不着话”,则像是后天的、物理的变化,它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并和物质条件、经济基础有关。就此而言,牛爱国夫妇之间,已不单单是“说得着”,而是混杂着嫌贫爱富的复杂心理。以这样的形式,知音难觅的孤独心境被置换成了围城内外的一地鸡毛。
电影并非无法透彻表现人生的孤独,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大师的作品即是明证。但如果拍成那样的艺术电影,势必会流失大量的潜在观众。影片主创有意或无意地把主题从“孤独”换成“生活”,应该也是出于大众化的考虑。刘震云为影片提出的宣传语是“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这样的宣传既以简洁的用词点名了影片内核,又通过引人的噱头道出了商业诉求。
此外,影片在删减小说人物的同时,又对其中一些经典桥段进行了“移植。”比如,影片结尾牛爱国偶遇庞丽娜却终于释怀并“放下屠刀”,就是对小说上部结尾吴摩西相关情节的移植。又如,同样是劝慰牛爱国的话,“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和“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两句至理名言,也从曹青娥的话语变成章楚红的台词。而小说里塾师老汪对“有朋自远方来”的独到见解则成了相亲人士(由小说作者/影片编剧刘震云客串)夸夸其谈的谈资,这多少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但无论如何,通过这些劝人向善的情节和发人深省的台词,影片在情感态度和思想理念上获得了当代观众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四、结语
本文从媒介转化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及其改编影片进行了个案分析。实际上,作为两种不同的媒介形态,改编影片之于原作小说,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会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9]因此,小说和电影,只有诞生先后的区别,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时候也只能是“事后诸葛亮”。毕竟,是“人们对媒体的使用决定了媒介的哪个方面和艺术相关,而不是媒介的某个特性决定了媒体的合理使用。”[10]也就是说,将文学改编成电影,或者说任何跨越媒介形态的创作,其实都存在无数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相关的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才值得进一步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