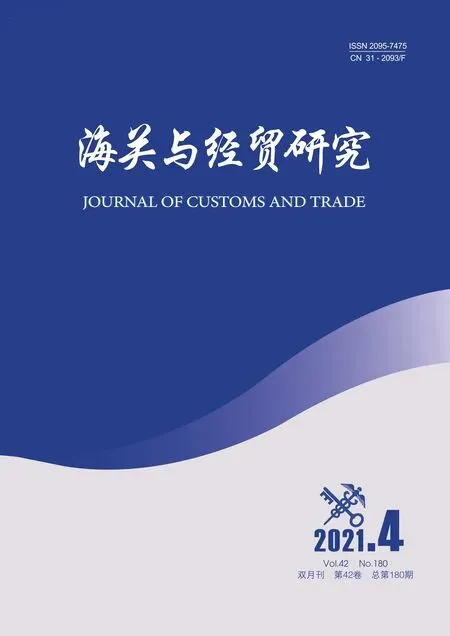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之再审视
——兼论阻断法之困境与利用
邹璞韬 胡城军
2020年6月20日,调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提出,要“强化对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阻断、反制‘长臂管辖’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1)罗沙:《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人民网2020年6月2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0022420426053498&wfr=spider&for=pc.至此,阻断法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2021年1月9日,商务部颁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被认为是我国阻断立法工作的初步实践。本文试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分析其在具体案件中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阐述该《办法》与该原则的联系。
一、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历史沿革
外国主权强制原则(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 Doctrine),是指倘若当事人因本国的主权强制行为不能履行美国法律义务时可以免责。该原则于1970年的“Interamerican Refining Corp.v.Texaco Maracaibo,Inc.”一案中被美国法院首次认可。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国家行为原则(Act of State Doctrine)的概念延伸与推导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作为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抗辩理由,其成立条件近年来呈逐渐严苛化趋势。
(一)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起源:国家行为原则
1.国家行为原则的概念与法理基础
国家行为原则在“Underhill v.Hernandez”一案中首次提出:“任何主权国家都应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独立性,一国法院不能对他国在其领土内做出的行为进行审判。因这些行为引发的申诉应当通过国家主权之间可以进行的方式加以解决。”(2)Underhill v.Hernandez,65 F.577,583 (2d Cir.1895).本案中,原告是一名美国公民,其根据合同为委内瑞拉政府提供城市供水服务。由于委内瑞拉境内爆发武装革命,原告向被告申请离开城市的护照遭到被告拒绝。滞留于城市期间,原告遭受了被告手下军队的拘留与骚扰,其据此在美国法院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随后经过一系列司法实践,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依据于“Banco Nacional de Cuba v.Sabbatino”一案中得到了最终明晰:国家行为原则源自对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尊重。(3)Banco Nacional de Cuba v.Sabbatino,376 U.S.398(1964).本案涉及古巴对美国公司在其境内资产的国有化。一家美国公司在古巴境内的资产遭到国有化后,委托被告从古巴政府手中回购古巴境内的一船货物。被告虽完成了其委托业务,但古巴政府将货物提单交给了作为船运代理人的原告。原告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依据提单给付货物。对国家主权之尊重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自不必多言,而法院之所以出于三权分立原则从而肯定国家行为原则作为当事人抗辩免责的理由,其原因在于当行政权代表全体国民处理各项外交事务时,必将对另一国的国家行为做出回应。此时,只能凭借个案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司法权力倘若宣告另一国的国家行为之合法性,势必将侵犯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行政外交权的行使,这将严重违反三权分立这一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根基原则。可见,对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尊重成为了国家行为原则的法理基础。当事人倘若想要以国家行为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必须向法院证明:法院对当事人的行为追责建立在法院宣告外国主权行为无效的基础之上,即当事人的行为是一种国家行为。如此一来,对该行为的审判宣告无效将严重损害外国国家主权,同时也扩大了司法权的审查范围从而对美国行政权形成了不正当的干预。此时国家行为原则便能够免除当事人在案件中面临的法律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主权豁免与国家行为原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前者而言,国家主权豁免是一种管辖权上的豁免,美国法院在涉及主权国家的行为或财产时不得对相关案件进行管辖;就后者而言,国家行为原则是指由于被告的行为是一主权国家行为,美国法院对被告行为之合法性的宣判势必将导致对该国家行为合法性的宣告。出于对他国主权以及本国行政权力的尊重,法院此时应当放弃管辖权。换言之,国家主权豁免提供的是一项管辖权的例外或排除事由,而国家行为原则的内容更侧重于要求司法权力在相关情形下弃权,体现了法院对相关行为的审视程度。
2.国家行为原则的发展:外国主权强制原则
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与国家行为原则息息相关,当私人纠纷中的当事人行为若为其本国政府强制,则该行为亦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延续,故而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与国家行为原则往往被相提并论。(4)参见彭岳:《论美国跨境反垄断诉讼中的主权抗辩——从“维生素C案”谈起》,《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第24页。然而,两者仍然在适用主体与构成要件两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就适用主体而言,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被诉行为多为独立主权国家行为,故而适用主体多为拥有外国政府身份或授权的机构组织。以最早确立国家行为原则的“Underhill v.Hernandez”一案为例,被告是拥有委内瑞拉政府军人身份的主体,其行为被认为是国家行为的体现从而被免于法律责任。但就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而言,相关案件的被告行为更多被视为是国家行为的延续,即作为私人主体的当事人被本国当局强制从事相关行为。以著名的“维生素C案”为例,我国多家企业在该案中提出的抗辩便是其行为是对“预核签章”这一中国出口制度的遵守,存在适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可能性。(5)In ReVitamin C Antitrust Litigation,810 F.Supp.2d 522 (E.D.N.Y 2011).
就构成要件而言,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要求被告行为必须达到为其国家当局“强制”实施的程度。然而,国家行为原则由于适用主体多为拥有外国政府身份或授权的机构组织,其行为只要被界定为国家行为便存在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可能性。在著名的“Midcal”案中,法院总结国家行为原则的构成要件包括两项:第一,相关行为必须能够肯定且清晰地被表述为一项国家政策;第二,该项政策必须被国家积极监督执行。(6)California Retail Liquor Dealers Ass’nv.Midcal Aluminum,Inc.,445 U.S.97 (1980).换言之,国家行为原则并不要求当事人行为达到被“强制”的程度,只需要认定它是一种国家行为,且该行为被国家积极监督执行即可。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相比,国家行为原则在构成要件上对于“强制”的要求明显不同。可见,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虽然是在国家行为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在适用主体与构成要件方面相较于国家行为原则存在差异。归根到底,国家行为原则解决的是纯粹国家政策的执行在美国遇到的法律责任问题,而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提供的则是那些受国家行为强制而实施的私人行为在美国法院上的抗辩理由,针对的是国家行为支配下的一种私人延续行为。
(二)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发展动向:“强制”标准认定的严苛化
在1970年,最早确立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Interamerican Refining Corp.v.Texaco Maracaibo,Inc.”一案(以下简称“Texaco Maracaibo案”)中,被告作为一家委内瑞拉原油开采公司停止了对原告的原油供应,致使原告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被告以该行为“受委内瑞拉政府强制”作为抗辩免责理由并最终为法院采纳:“当一国实施了贸易强制手段且涉案企业只能选择遵守,商业行为变成了有效的主权行为,美国谢尔曼法并未赋予法院对外国主权行为的管辖权。”(7)Interamerican Refining Corp.v.Texaco Maracaibo,Inc.,307 F.Supp.1291 (D.Del.1970).这一论述也印证了前文观点:外国主权强制原则适用的行为是私人行为,只不过由于国家的强制手段从而变成了国家主权行为,其本身不能与国家行为原则中的“国家行为”相等同。
尽管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于美国判例法中提出,但其成立条件至今在美国判例法中无法得到精确统一。就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法理基础而言,当事人因本国当局的强制手段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本质原因除了作为概念来源的国家行为原则以外,还包括了“礼让(Comity)”与“公平(Fairness)”两项要素。(8)The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Operations (1995),68 Antitrust & Trade Reg.Rep.(BNA) No.1707,§3.32.对于礼让要素,司法实践与学界对其并无过多争议,即美国法院在一般情况下承认外国主权者的命令和法律在美国的效力,除非这种承认损害美国国民利益。就公平要素而言,在存在外国主权强制的情况下,外国主体势必将陷入美国法律义务和本国强制手段相冲突的两难境地,即外国主体要么违反美国法义务,要么违反本国强制义务,因此出于公平要素的考虑应当避免对外国主体施加法律责任。
然而,美国法院对于这种“公平”的标准在实践中认定并不统一。具体而言,如何判断外国政府的这种手段达到了“强制”的标准成为美国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主要审查的问题。倘若外国的这种政策手段未达到能够“强制当事人违反美国法律义务”的程度,则基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提出的抗辩不能成立。纵观美国诸多判例,可以发现,对于这种“强制”标准的认定趋向严苛化,美国法院往往在案件中认定当事人主张“强制”无法成立。这一点大致可从“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形式”以及“当事人对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态度”两方面体现。
1.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形式
在“Texaco Maracaibo案”中,委内瑞拉政府要求被告停止原油供应行为并非任何成文的特别法令或行政命令,相反,只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做出。(9)Interamerican Refining Corp.v.Texaco Maracaibo,Inc.,307 F.Supp.1291 (D.Del.1970).在此情况下,法院仍然认定了此项国家主权行为达到了对被告的强制效果,从而宣告了被告抗辩理由的成立。在“Mannington”案中,法院认为外国主权实体对当事人的强制行为只需在当事人不履行有关义务时承受相应负面影响,即可达到“强制”标准。(10)Mannington Mills,Inc.v.Congoleum Corp.,595 F.2d 1287 (3rd Cir.1979).本案原告声称被告的外国专利证书是依靠欺诈取得的,从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相应不正当竞争责任。然而,《第三次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以下简称“《重述》”)对于该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外国主权强制必须以“规定了严格惩罚制裁措施的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形式呈现,仅仅是“未来交易机会的损失”等负面影响并不构成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中的“强制”标准。(11)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1987,§441.换言之,《重述》对于强制行为的形式要件采取了严格的法定主义,即这种强制行为只能以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成文法呈现。这一观点也为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95年联合发布的《反垄断执行的国际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所采纳。《指南》明确:外国主权强制行为必须体现为当事人若不服从这种强制,则会受到相应制裁。(12)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1995),68 Antitrust & Trade Reg.Rep.(BNA) No.1707,§3.32.而在多数案例中,相关主权国家往往并无配套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对相应制裁予以落实。即便规定了相应制裁,多数国家也没有真正做到落实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法院往往不会认定相关主权行为构成对当事人的“强制”,因而当事人的抗辩理由无法成立。
2.当事人对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态度
在“Mannington”案中,法院认为外国主权行为所达成的“强制”效果必须是当事人违反美国法律的“根本原因(fundamental force)”,而这种“根本原因”的标准并未杜绝当事人参与相关主权行为落实的情形。(13)American Law Institute,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1987,§441.换言之,“Mannington”案对“强制”的认定侧重于从强制行为的客观效果出发,即只要国家的主权行为是当事人违反美国法律义务的根本原因(并非唯一原因),则“强制”标准便得以达成,而无问当事人在这种国家行为做出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然而,这种客观效果标准并未被美国的司法实践广泛接受。早在“Sisal”案中,美国法院便指出当事人如果请求政府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从而迫使当事人在内的私人主体达成不正当竞争协议,外国主权强制的抗辩就无法在案件中适用。(14)United States v.Sisal Sales Corporation (Sisal),274 U.S.268 (1927).同样在“瑞士钟表制造商”一案中,法院也指出即便瑞士政府确实拥有相应明文法规,但相关不正当协议仅能被视为是私人协议,而不能看作瑞士政府的强制行为的延续。(15)United States v.Watchmakers of Switzerland Information Center,Inc.,1965 Trade Cases (CCH) 71,352 (S.D.N.Y.1965).这一点在著名的“维生素C案”中得以体现,美国法院通过中国多家企业的会议新闻、记录等作为证据,认定涉案中国企业实施的涉嫌垄断之行为是当事人努力促进达成的,并非中国政府的主权强制行为所致,从而判定我国企业败诉。可见,美国法院在考察外国主权行为是否真的达到的“强制”标准时,对当事人在行为形成的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会严加审视。倘若相关主权行为的落实过程中仍然体现了当事人的主观促进该行为的意思,以及其实现该行为的努力,那么相关主权行为难以被视作“强制”被告违反美国法律义务的理由。
总而言之,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经过美国判例法的一系列实践,被告行为构成该原则从而利用该原则成功有效抗辩的条件愈发困难。这种“强制”标准成立条件的严苛化也为美国当局以官方文件加以记述。在2017年,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指南》进行了更新。该份指南对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该原则的构成要件总结如下:(1)必须存在外国政府的强制行为,而这种强制行为的表现体现于倘若当事人不服从这种“强制”,则会受到相应国家制裁;(2)这种强制行为只有在本国领土内发生才可抗辩生效,如果是在美国境内发生,则抗辩不成立(例如,外国政府要求本国企业的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签订卡特尔协议);(3)这种强制只能来源于外国政府行为,“商业例外”不包含在内。(16)The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Operations (2017),68 Antitrust & Trade Reg.Rep.(BNA) No.1707,§ 4.4.2.可见,美国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的发展,对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构建了一套完整明确的适用规则,我国企业在面对美国反垄断等领域的诉讼时同样也曾意图将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并面临了诸多困难与挑战。
二、外国主权强制原则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即便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经过美国判例法的一系列实践,其当事人有效抗辩理由的条件越来越难,但该原则对于我国企业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过往案例中,中国企业以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应对美国反垄断之诉的案例极多。对其中代表性案例的梳理不仅能将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抽象宏观概念落实于具体案件之中,同时也能理解《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维生素C”案
2005年1月,美国“维生素C”药品的购买者向药品制造商——六家中国企业提起了一系列的集体诉讼,声称相关中国企业共谋控制药品维生素C的价格与产品供应。2008年,作为被告的中国企业提出如下抗辩:第一,“维生素C”生产商的出口价格垄断行为是在中国政府的强制下做出;第二,该价格垄断行为是中国的国家主权行为;第三,法院应当遵从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当局强制执行价格垄断的行为。(17)In re Vitamin C Antitrust Litig.,584 F.Supp.2d 546,(E.D.N.Y.2008).
同时,我国商务部史无前例地作为该案的法庭之友向美国法院提供了意见书以及两份陈述。这些文件均表明中国政府承认其设立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从而控制“维生素C”药品出口价格与供应量的国家行为,同时也向法院阐述了“预核签章”作为中国出口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及重要性。所谓“预核签章”制度,是指由中国特定行业建立起来的商会进行协调,要求商会内的会员企业协商出口的统一最低限价,即“同行协议价格”。协商完毕后,商会需会员企业进行监督,要求企业遵循该“同行协议价格”。在商品出口时,经商会审核并签章后才能被海关放行。该项制度常常使得中国企业面临反垄断调查,所谓的“同行协议价格”也常常被外国法院认为是一种变相的卡特尔协议。(18)参见金美蓉:《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法学家》2020年第2期,第161页。
在“维生素C”案中,商务部向法院阐明了该制度作为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国家主权属性并被2002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调整出口商品海关审价目录的通知》明文记载,可见其与涉案企业均意图加强该案与外国主权强制之间的联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然拒绝宣告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成立。法院认为,相关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被告施加如被告和中国商务部所声称的“强制”。这些证据主要是中国企业出口前举行的会议新闻或纪要,表明虽然存在“预核签章”等法律制度,但被告当事人仍然拥有履行美国法律义务的选择空间。同时,法院认为我国商务部对中国法律的阐述完全是出于袒护被告的辩护角度,不足以为法院采信,相关中国法律制度无法对被告施加足够的“强制”。(19)In re Vitamin C Antitrust Litig.,810 F.Supp.2d 522 (E.D.N.Y.2011).
总而言之,在“维生素C”案中,法院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审视,认定被告企业的卡特尔协议行为系被告自愿做出,并非中国政府强制所致,从而判定中国企业败诉。虽然在2016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基于国际礼让原则推翻了一审判决,但该案在2018年依旧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全票通过判决中国企业败诉。
(二)“铝土矿”案
美国宾夕法尼亚西区地方法院在2006年受理了著名的“铝土矿”案,其涉及的是我国的铝土矿出口贸易问题。在该案中,法院做出了与“维生素C”案的一审判决完全不同的认定:通过对案件证据的审视,法院承认了中国政府在本案涉嫌控制出口的行为做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认定被告中国企业并未触犯《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的密谋操纵价格与产品供应。(20)Resco Products,Inc.v.Bosai Minerals Grp.,2016 WL 308863(W.D.Pa.Jan.25,2016).
2006年2月,美国雷斯科产品公司等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密谋操纵铝土矿的出口价格和产品供应,违反《谢尔曼法》应当承受相应法律责任。该案被告博赛矿业公司等几家中国企业是铝土矿的生产商,并且是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会员。原告声称,据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会议记录显示,被告企业曾联合诸多铝土矿生产商协商并投票决定出口价格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辩称其行为系依据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法律规定,由中国商务部强制实施,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同样是政府设立的实施相关出口贸易制度的实体。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相关会议记录显示了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员企业对于铝土矿出口限额的讨论可被视作提供给中国商务部的政策建议,体现了被告企业对相关出口控制行为的参与程度。然而,法院认为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缺乏足够的权力使得该出口协议无效,相反,自2001年起该项权力便被作为中国政府有权机构的商务部所掌控,中国商务部拥有调整出口配额与价格的政府权力,故法院认为被告涉嫌违反《谢尔曼法》第一条的出口行为事实上为中国政府所强制,本案被告的抗辩应当生效。
需要注意的是,在“铝土矿”一案中,法院的判决逻辑在于首先承认了被告当事人对于相关出口行为的参与程度,随即以“中国商务部掌握出口配额与价格调整的权力”为由认定被告与其他企业通过商会这一无权组织实施的协商事实上为中国政府强制达成,从而宣告被告的抗辩成立,其对于“强制”标准达成的认定条件显然与前文所述的《指南》之立法规定,以及“维生素C”等案件中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所体现的严格法定主义不尽相同。笔者认为,法院做出如此判决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当时美国在WTO框架下对中国提起的贸易诉讼有关。美国在当时提出中国的一系列进出口管制制度和中国2001年入世时做出的承诺协议相违背,从而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中国在进出口贸易制度层面做出改变。WTO作为促进世界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其制度框架下处理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换言之,从美国在WTO层面的起诉行为来看,美国当局已认定中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行为在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实施,不具有中国企业的私人行为属性。倘若法院因中国企业参与相关出口价格和产品供应的协议认定相关行为不属于中国主权行为下的“强制”,那么美国(至少是行政当局)在WTO层面的起诉将与之产生矛盾。故我国的主权强制行为在美国法庭上的认定是否会与WTO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认定相冲突,同样值得学界予以相应关注和思考。
(三)“菱镁矿”案
“菱镁矿”案的案情与“维生素C”案、“铝土矿”案相类似,原告指控被告中国企业违反《谢尔曼法》实施对稀有金属菱镁矿的出口价格控制。如前所述,“维生素C”案与“铝土矿”案分别对被告中国企业提出的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理由持不同态度:前者在中国商务部作为法庭之友的情况下,认为我国商务部的声明完全基于被告辩护立场,因而拒绝承认我国商务部的声明以及被告的抗辩成立;后者则基于对案件证据的审视以及中国商务部的法庭声明肯定了被诉行为的国家属性,认定被告抗辩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菱镁矿”案的审理法院对我国商务部在本案中提交的文件认定采取了更为明晰的审查标准。
在“菱镁矿”案中,法院认为:外国主权对其法律强制的承认往往是具有极高效力甚至近乎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抗辩理由,即便这种被该国承认的法律强制在美国的法律科学看来是一种不成文法。(21)Animal Sci.Products,Inc.v.China Nat.Metals & Minerals Imp.& Exp.Corp.,702 F.Supp.2d 320,426 (D.N.J.2010).换言之,法庭在此对“强制行为”的形式认定采取了与“Texaco Maracaibo”案、“Mannington”案相同或近似的认定标准,即对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认定无需严格的法定主义,只需该行为在客观效果上达到“强制”标准即可。因此,法院对于我国商务部提交的声明文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认定方法:第一,本案证据与中国商务部提交的声明文件是否存在不一致性,且这种不一致性是否被查明;第二,倘若这种不一致性存在且被查明,该不一致性是否对认定中国商务部提交的声明文件不可靠具有根本或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法院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审视,认可了我国商务部提供的法律声明文件中对我国出口法律制度的阐述,从而认定被告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成立。令人遗憾的是,法院于2011年推翻了上述观点并在2014年做出了不利于被告中国企业的判决。(22)Animal Sci.Products.,Inc.v.China Minmetals Corp.,34 F.Supp.3d 465 (D.N.J.2014).
上述三项案例都体现了我国企业在反垄断领域以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作为抗辩理由的实践。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不同地方法院对于我国企业提出这一抗辩理由的态度很难寻得统一规律。然而,三项案例均展示了美国法院在涉及我国企业提出“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抗辩事项时,都对相关案件中的证据以及我国商务部在个案中帮助我国企业提交的法律声明文件的认定问题进行了审视。这种“商务部个案随时出击”的抗辩策略,笔者认为存在两项主要问题:第一,由于商务部本身的行政权力属性,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阐述会受到美国法院的合法性质疑。正如在“维生素C”案中,法院认为我国商务部提交的声明文件有“袒护被告”的立场存在,故而不予认定。第二,仅依靠商务部对于出口管理的操作性制度规定,难以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适用严苛化的背景下构成能够为法院承认的主权“强制”标准。缺乏系统性的法律制定,仅凭个案中的证据以及我国商务部提交的不同声明文件,难以形成统一、完善的“强制”标准体系。基于此,我国企业在美国法庭上提出的“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难以为法院采纳。随着《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颁布,我国的阻断立法工作得到了初步实践,其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结合将为我国当事人在面对美国法院诉讼时提供强有力的抗辩武器。然而,世界各国阻断法由于其执行和适用原因,在诉讼中仍然难以为本国当事人利用。
三、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下的阻断法困境
(一)基于阻断法产生的外国主权强制行为
我国商务部于2021年1月9日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是我国阻断立法工作的初步实践。所谓阻断法(Blocking Statute),是指禁止外国特定法律以及依据这些特定法律做出的行为在一国境内产生效力的法律统称。世界各国于20世纪开始便陆续着手制定本国阻断法以应对美国不断扩张的域外管辖(如法国的“68-678号法案”)。
这些阻断法的共同特点是禁止美国特定法律或基于特定法律实施的各项措施在本国境内得到承认、执行或遵守。以欧盟的《免受第三国立法及由此产生行动之域外适用影响的保护法案》(以下简称“《阻断法案》”)为例,其于附件中列举了一系列美国特定法律,并于第四条规定:“(外国)法院或仲裁庭的裁判以及外国行政当局的决定,若直接或间接地使(附件中的)法律或依据这些法律做出的行为有效,则不得以任何方式被承认或执行。”同时,对于遵守了附件所列法律的私主体,《阻断法案》第九条赋予了欧盟各成员国对这些私主体实施“有效的”(effective)、“成比例的”(proportional)且“劝诫性的”(dissuasive)制裁。对此,我国商务部颁发的《办法》第七条规定,由商务部确认存在不当域外适用的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得被承认、执行或遵守。倘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遵守这些特定外国法律,则将面临《办法》第十三条与第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可见,作为阻断法的《办法》在内容上与世界各国立法一样,均宣告了外国特定法律在本国境内无效,同时对于遵守这些特定法律从而履行义务的本国私主体,国家将对其实施公权力惩戒。可以看到,这种通过阻断法禁止本国私主体遵守外国特定法律的行为已然构成了前文所述的“外国主权强制行为”,即以立法形式强制要求当事人违反美国法律。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维生素C”案等一系列典型案例中,中国当事人在提出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这一抗辩理由时,都会配套提供中国商务部的文件声明甚至是中国商务部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出庭阐述中国相关法律制度。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商务部个案随时出击”的抗辩策略不仅由于商务部本身行政权力属性而难以为法院采信,同时个案证据以及案情的不同难以形成我国当事人在美国法庭上有效适用的成熟体系化抗辩。从这一角度看,《办法》借鉴了世界各国阻断法的立法经验,加强了我国当事人在未来对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适用效果,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纵观美国法院对相关案件的裁判,阻断法通过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达到抗辩目的的效果由于其执行问题逐渐难以实现。
(二)“强制”标准难以成立之原因分析:本国当事人的“两难困境”
在著名的“法国航空公司”案中,被告当事人基于同样是阻断法的法国第68-678号法令拒绝美国法庭的证据信息披露的请求。对此,美国法院通过审视第68-678号法令的执行历史,发现在当时法国对该法令并无执行历史,故认为法国的阻断法立法行为并未达到“强制”标准,因此被告抗辩不成立。(23)SociétéNationaleIndustrielleAérospatialev.U.S.,482 U.S.522 (1987).事实上,这也是世界各国阻断法面临的尴尬窘境。一方面,各国阻断法希望通过禁止本国当事人履行美国法律义务从而达到“阻断美国法律效力”的效果。另一方面,本国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只能面临两项选择:要么遵守本国阻断法,违反美国法律义务从而受到美国法律制裁;要么遵守美国法律,违反本国阻断法义务,从而受到本国法律制裁。从这一角度来看,阻断法无疑是在“强人所难”,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了一种法律义务履行上的“两难困境”。因此,世界各国制定阻断法后往往难以真正落实与执行,因为一旦落实执行无疑会给本国当事人造成难以避免的权益损失,从而受到本国舆论的极大质疑。这也使得阻断法制定各国同样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要么避免执行阻断法,使当事人只承担美国法律义务;要么坚定阻断法的适用与执行信心,通过对本国当事人处以制裁维护阻断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但无疑将牺牲个案当事人合法权益并面临国内舆论压力。这种“两难境地”阻碍了各国阻断法的适用,因此也难以构成美国法院所要求的外国主权强制标准。
令人欣喜的是,从《办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商务部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这种困境因素。因此,《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禁令,未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并因此受到重大损失的,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支持。”该规定中的“必要支持”可以理解为商务部在制定《办法》时对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平衡考量。诚然,阻断法的落实与执行势必会令本国私主体陷入法律义务履行上的“两难困境”,但这并不代表阻断法在制定完成后就注定会沦为束之高阁的宣誓性立法。相反,我国行政当局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维护阻断法规范权威、使当事人关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抗辩成立的同时,亦兼顾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种“行政便民”的积极思维应当予以肯定。进一步而言,笔者认为,此处“必要支持”在未来可以通过具体细则予以更加明确的落实,包括对私主体在美国法庭上的诉讼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补偿,均可以纳入这种支持的范围内。然而,需要考虑的是,这种“支持”会否违反WTO关于“专向性补贴”的禁止性规定?立法者在未来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对此问题做出较为妥善的安排。
四、我国阻断法如何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
如前文所言,阻断法的执行势必会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两国法律义务履行上的“两难困境”,这一点致使许多国家在完成阻断法制定后都缺乏对阻断法予以适用与执行的决心,使阻断法成为束之高阁的“宣誓性立法”。正因如此,当本国当事人以“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为由在美国法庭上进行抗辩时,法院往往因为相关阻断法并无执行历史认定外国的阻断立法行为不足以达到“强制”标准,从而对当事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鉴于此,未来我国阻断法在修订完善以及执行适用两方面均应参考我国当事人已有的司法实践,并结合域外阻断法发展经验,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维护我国私主体的合法权益。
(一)对《办法》规定予以完善细化
正如前文在对“维生素C”案中的分析所指出的问题一样,由于商务部行政权力的属性,其声明文件会被美国法院认为有“袒护被告”的立场,从而认定“强制”不成立。虽然《办法》作为我国商务部颁布的行政规章,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法律强制效力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该办法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定位不明,其规定也多为宏观层面的指导,许多方面有待未来进一步完善细化。
首先,《办法》作为行政规章于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判决、裁定致使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可以看到,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因相关主体遵守外国特定法律而产生的民事争议的解决方法。然而,《办法》作为商务部颁发的行政规章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这种由政府公权力出于阻断外国域外管辖需要而制定的行政规章能否介入平等主体间的法律纠纷,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中需要进一步明确规范。
其次,《办法》对商务部的职权界定问题。《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作机制评估,确认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的,可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这一条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办法》作为商务部自身颁布的行政规章,在法律、法规对于阻断法问题没有相关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能否实现对商务部发布禁令的自我授权?第二,这种禁令针对的是禁止外国法律在我国境内的承认、执行与遵守,具有普遍效力,其性质是否为商务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当事人不服商务部对其实施的制裁措施时,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是否需要对商务部的禁令进行合法性审查?笔者认为,《办法》作为我国阻断立法的初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化的国际局势之紧急应对需要,在未来应当通过法律、法规等位阶更高的规范实现我国阻断法的体系化构建。
最后,兼顾企业利益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言,阻断法的执行与适用势必会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两国法律义务履行的“两难困境”,因此如何于立法层面在实现对外国特定法律的阻断效果之时,亦能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是立法者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对此,现行《办法》在此方面分别在第八条的“豁免程序”,以及第十一条的“必要支持”两项条文表述上做出了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就“豁免程序”而言,商务部在审查当事人申请时应当注意程序细则的完善,必要时需要举办相应听证会并对社会公开;就《办法》执行过程中“给予企业必要支持”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应当对这种支持措施通过具体细则予以落实,如税收优惠亦或是高科技产业补贴等。但需要注意与WTO关于“专向性补贴”规则的衔接问题。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在执行《办法》过程中加强与企业的信息沟通,坚定企业应对美国域外管辖下的困境之决心。只有将企业利益平衡到位,阻断法的执行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抗辩理由在未来才有得到美国法院采纳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第二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并未如欧盟《阻断法案》一样,将特定国家的特定法律列为禁止效力之对象。《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情形。”有学者指出,《办法》如此立法方式旨在减少其自身的对抗色彩,同时防止未来我国阻断立法受到其他国家法律的变迁与影响。(24)参见廖诗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属事适用范围》,《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2期,第51页。
总而言之,《办法》作为我国阻断立法的初步实践,从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视角出发,可以看见其作为立法形式的国家主权强制行为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积极意义,即通过系统化立法规定为我国当事人在未来面对美国司法诉讼时,能够更为有效地适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同时,其执行时如何兼顾我国企业利益以及其法律位阶层级问题均有待进一步落实。
(二)对未来我国阻断法适用的建议:构建成熟的阻断体系
如前文所述,《办法》作为我国阻断立法工作的初步实践,由于其执行势必会使本国私主体陷入法律义务的“两难困境”,如何兼顾私主体利益成为各国阻断立法均需思考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以反制报复的思维进行立法工作。相反,应注重阻断立法工作完成后,推动商事司法的发展以及国内市场、出口监管等领域制度的完善,从而构建我国成熟的法律域外规制体系。(25)商舒:《中国域外规制体系的建构挑战与架构重点——〈兼论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2期,第80页。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对于阻断法的适用与理解不能仅停留于法律文本或司法程序层面。更重要的是从法律与政治角度同时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阻断体系。
所谓阻断体系,笔者将其定义为:“以阻断法为核心,能够实现阻断效果的一系列法律、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措施的总称。”需要指出的是,阻断法只是阻断体系中的一部分,成熟的阻断体系并非仅停留于法律层面的立法实践,相反,是以阻断法为核心在法律、政治等多元维度展开的实现阻断效果的措施总称。以欧盟为例,其在法律与政治层面构建阻断体系的措施大致如下:
第一,在法律层面加强对阻断法的执行与解释。自1996年欧盟的《阻断法案》出台后,欧盟针对《阻断法案》的执行与解释出台了诸多配套法律制度。首先,为了加强欧盟境内对《阻断法案》的执行,欧盟同时出台了《联合行动》(26)Joint Action,96/443/JHA.与《执行条例》(27)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No.2018/1101.作为对《阻断法案》执行工作的协调补充。《阻断法案》虽然在第九条允许各成员国对违反《阻断法案》的本国当事人予以公权力惩戒,但《联合行动》同时基于欧盟的“一致性原则”(即欧盟各成员国整体对外行动的一致性)赋予了欧盟理事会统一执行的权力。《执行条例》则为了更好兼顾本国当事人利益,对豁免程序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其次,为了进一步正确适用《阻断法案》,欧盟在2018年对《阻断法案》的附录进行更新的同时,出台了《指导文件》(28)Guidance Note Questions and Answers:adoption of update of the Blocking Statute,2018/C 277 I/03.对《阻断法案》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说明。《指导文件》列举了23项《阻断法案》适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答复,给欧盟成员国的司法机关提供了统一、完善的适用法律标准。
第二,在政治层面积极运用《阻断法案》完成谈判、斡旋与施压。美国对他国进行制裁的手段可分为“初级制裁”与“次级制裁”两类:前者针对的是与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但受美国管辖的主体;后者则禁止第三国主体与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影响的主体多为第三国私主体。(29)参见叶研:《欧盟〈阻断法案〉述评与启示》,《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3期,第51页。《阻断法案》附录中所列举的美国单边制裁法案,其内容多为影响欧盟私主体贸易活动的美国次级制裁措施。在次级制裁的情况下,涉案当事国包括了美国、受制裁国与欧盟三个国际法主体。在《阻断法案》出台后,欧盟以《阻断法案》为核心,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层面均展开了积极活动。国内政治方面,2007年奥地利银行BAWAG因遵守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而关闭了古巴用户的账户,直接违反了《阻断法案》的规定。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Ursula Plassnik在同年4月27日宣布将以《阻断法案》为依据对该银行提起诉讼。随后,BAWAG银行立即恢复了之前关闭的古巴用户账户;(30)Beatrix Immenkamp,Updating the Blocking Regulation:the EU’s Answer to US 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European Union (Sept.29,2020),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BRI(2018)623535.国际政治方面,1996年欧共体积极开展美国与古巴关系缓和的外交工作,并于199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制裁,最终使得美国与欧共体达成了和解与豁免协议。
总而言之,立法者除了需要通过法律、法规以及具体细则对《办法》现存的争议问题进行回应和落实以外,还需借鉴域外阻断体系构建的成熟经验。在法律层面,应当对执行以及阻断法的解释出台配套成体系的司法解释,同时通过相关国际协定实现与他国在阻断法案件上的判决承认与执行合作;更重要的是,我国不能在阻断立法工作完成后忽视政治层面的阻断法运用。事实上,由于阻断法的适用和执行势必会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不同国家法律义务的“两难困境”,各国对于阻断法的执行往往缺乏决心,致使外国主权强制原则视野下的各国阻断立法行为无法在法律层面达成“强制”标准,各国对于阻断法的运用往往集中于政治层面的谈判、斡旋与磋商。阻断法制定的目的也常被认为是“迫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31)Erica M.Davila,International E-Discovery:Navigating the Maze,Pittsburgh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olicy,2007(34):8-44.故我国同样于政治层面应当积极运用阻断法,通过谈判、斡旋与磋商等方式实现争议问题的解决。笔者坚信,只有一方面在《办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完善我国阻断法法律文本的制定工作,兼顾我国企业合法权益,坚定阻断法的适用决心;另一方面通过多维度的措施手段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成熟阻断法体系,才能突破阻断法困境,实现阻断法的有效适用与执行。如此才能帮助我国私人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实现在美国法庭上的成功抗辩。
五、结论
首先,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是美国判例法上的概念,由国家行为原则发展起来,但其与国家行为原则存在着适用主体与构成要件上的区别。在适用主体方面,前者往往为从事经贸活动的私主体,后者则多为带有政府身份或授权的官员或机构组织;在具体构成要件方面,前者要求被告行为必须达到其国家当局“强制”实施的程度,后者则由于适用主体多为拥有外国政府身份或授权的官员或机构组织,其行为只要被界定为国家行为便存在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可能性。同时,美国法院对于被告以“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抗辩的采纳程度愈发趋向严苛化,尤其体现在对外国主权强制行为的形式以及当事人对于该强制行为的态度两方面。
其次,我国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诉讼时以“外国主权强制原则”为由进行抗辩时,往往会配套我国商务部向美国法院递交的我国法律制度作为主权强制行为的文件说明,但效果往往不佳。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由于商务部本身的行政权力属性,其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阐述会受到美国法院的合法性质疑,即法院认为相关声明文件有“袒护被告”的立场存在;第二,缺乏系统性的法律制定,仅凭个案中的证据以及我国商务部提交的不同声明文件,难以形成统一、完善的“强制”标准体系。在此情况下,我国商务部于2021年1月9日颁布的《办法》以明确的行政立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企业体系化适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的效果。然而,《办法》作为阻断立法,由于其执行会使本国当事人陷入两国家不同法律义务履行的“两难困境”,世界各国在完成阻断法制定后缺乏对其执行与适用的决心,致使美国法院认定“强制”标准不成立。
最后,为了使我国私主体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维护合法权益,可以在立法层面以及法律适用层面借鉴域外经验加以完善:第一,对《办法》的规定进行发展完善。包括明确《办法》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商务部的职权定位,以及依靠豁免程序与对企业的各项支持使《办法》能够更好实现阻断效果的同时,兼顾企业利益;第二,在阻断法适用层面构建更为成熟的阻断体系,即依靠法律与政治层面的多维度手段积极运用阻断法,更好利用外国主权强制原则实现传统阻断法的困境突破,对美国扩张的域外管辖做出更为成熟的中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