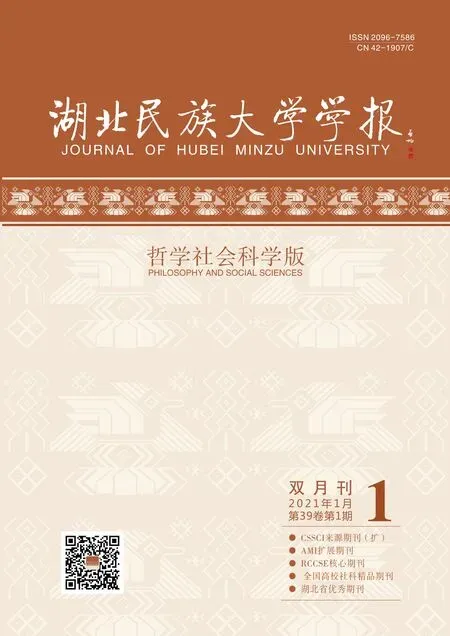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生的中国教育研究路径与话语构建
吕光斌
民国时期,一批留美生从社会重建和学术的角度出发,进行中国教育研究探索。他们撰写有102部教育类博士论文,其中有关中国教育议题的论文60余部,其内容涵盖面广,涉及学科门类多。目前,对于民国留美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宏观式的考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拓展。(1)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创建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留学生群体与民国时期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丁钢:《20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份博士名单的见证》,《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林晓雯:《1902-1928中国留美学生学位论文选题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吕光斌:《美国学术场域中的中国教育研究——基于民国时期留美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刘蔚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博士生“教育基础理论”领域论文的历史意义分析》,《教育学报》2014年第5期。以上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考察了留美生学位论文的基本概貌,或分析了留美生对新式教育、学科创建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在探讨留美生中国教育研究的路径、话语构建问题上还有待拓展。博士论文是留美生在吸收西方理论后进行的早期学术实践研究,考察这批教育学留美生博士论文的研究路径与话语构建,可以探究中国教育研究的早期学术发展脉络,以及留美生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努力。这批留美博士学成归国后,绝大多数从事教育事业,逐渐成长为近代中国接受过系统化专业学术训练的教育学者和教育界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国教育研究的发展和话语构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起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3)朱立元:《美学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424页。民国留美博士生从事的中国教育学术研究,一方面以西方教育学术话语进行问题阐释,另一方面则是在海外中国学勃兴的刺激下,根植于中国学人关于学术自立的反思,力图以丰富多样的研究题材和阐释话语,以“四个维度”与“一种策略”尝试构建中国教育研究话语,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一、中国学兴起背景下的中国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勃兴与中国学人学术自立意识的觉醒。“欧洲的中国学,亦即所谓的‘汉学’。”(4)许倬云:《北美中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和走向》,朱政惠、崔丕:《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72、74页。在“二战”以前,欧洲汉学界形成了巴黎学派,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形成了以京都帝大为首的汉学研究中心,汉学成为一门热门学问。美国的中国研究,起初是裨治文等传教士带动下的非专业化介绍式考察,逐步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了以太平洋关系学会和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专业化研究,“因基于美国人寻求了解中国现状的急切需求”,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史语文为主的范围”。(5)许倬云:《北美中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和走向》,朱政惠、崔丕:《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72、74页。二战后,以费正清、恒慕义为代表的远东问题专家们,主攻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和欧洲传统汉学不一样,美国的中国学相对受现实的牵制和影响更大”。(6)朱政惠:《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进程、特点和研究方法的若干思》,朱政惠、崔丕:《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二战前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表现出截然两分的特点:“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7)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同时,一批中国学人前往美国留学或执教,如洪业、杨联陞、萧公权、邓嗣禹、陈友松、张敷荣等,他们一面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搜集整理文献,一面从事相关研究,推动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展。
在20世纪前叶的国际学术舞台上,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成为研究者争相竞逐的领域。外国研究者大量占领中国学研究领地,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学人和留学生,引起了他们的民族情怀与忧患意识。中国学人普遍表示要积极进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承担学术自立责任。蔡元培指出“我们应该赶快整理固有的文明,贡献于外人,要是让外人先来开拓,那实在是件可耻的事。”(8)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27年,第31页。潘光旦也认为:“一是外国研究中国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绩一天精似一天;同时中国人自己做这种研究的人并不多见”,并告诫:“将来我们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学问则已,否则怎样能不就教于外国的支那通先生们呢?”(9)潘光旦:《中国人与国故学》,《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第55-56页。曾留美的教育家孟宪承在1934年更是大声疾呼:“为什么我国的学术要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为什么我要外国人寻出路来我们去跟着它走?”(10)孟宪承、虞斌麟:《欧洲之汉学》,《国学界(创刊号)》1937年5月15日。号召知识分子要有学术担当。中国学人在学术领域的这种忧患感,既体现了一种民族情感,也说明了中国学人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他们已然意识到学术自立与抢占学术话语阵地的重要性。
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时人指出他们的优点在于“科学实证法之采用”“辅助学科之发达”“特殊资料之保存搜集”“冷僻资料之注意”“公开合作之精神”“研究机构之确立”“印刷出版之便利”。(11)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再建旬刊》1940年第8期。就中国教育研究的情况而言,其优点则突出表现在“科学实证法之采用”“辅助学科之发达”,如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麦柯尔主张的教育调查测量思想,都给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方法。外国人的中国研究亦有其缺陷。留德生王光祈批评一些西方研究者们,“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代寻引证,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尝为之。”(12)王光祈:《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新中华》1933年第17期。因是“他山之石”的取巧之法,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何况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对中国文化内理的认识上,掣肘于重现实轻语言典籍的研究范式。中国学研究代表人物拉铁摩尔也颇为清醒地批评道:“在欧洲和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13)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42页。指出了国外的中国学存在的问题,而属于海外中国学一分子的中国教育研究,亦不排除上述研究之弊。
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上,中国学人对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批评。陈训慈认为:“浅率西人,至有置之原始文化至西方文化之过渡”“孟罗教育史,论中国教育谬误甚多,而其视东方文化为过渡为尤甚。”(14)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922年第2期。缪凤林也提出:“如蒙罗之教育史(Paul Menroe: 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第二章东方之教育,即专论中国教育以示例”,认为有关中国古代教育的教材(四书五经)、中国考试制度、中国教育目的等方面的话语阐释,存有诸多谬误和偏颇。他批评道:“蒙氏书全章仅三十余页,就余所知,类此之谬误,已不下数十”,认为“其出之盲目而不自知,亦以在彼土无正确之史料”,进而对留学生提出批评:“即此若干留学生,平素以沟通中西文化自任,既不能介绍吾中国正确之历史,又不能正其谬而匡其失,顾乃窃其谬论,奉为圭臬,且以自诩渊博也。”(15)缪凤林:《中国史之宣传》,《史地学报》1922 年第2期。因此,纠正西人认识中国教育的偏见和谬误,分析中国教育问题,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留学生既有的责任和义务。
事实上,留美博士生在中国教育研究上做出了颇多贡献。民国时期留美生共撰写有关教育研究议题的博士论文102篇,其中有关中国教育研究的博士论文有63篇,占同期教育类博士论文的61.8%,其数量远超同期其它学科中国问题研究的论文。可见,民国留美博士生在海外中国学勃兴的国际大背景下,在学习新知救国图强的爱国意识与学术自立意识的双重驱动下,将学术志业与教育救国结合起来,大量选择研究中国教育问题。这些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众多教育学科门类及前沿问题,主要有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实验测量、教育经济学、教育行政与管理、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及课程教学。从学制分类看,其研究领域包含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女子教育等。其他还有以文化适应、师资问题研究的专题论文。囿于语言隔阂与文化差异,西方学者的中国教育研究虽然理论视角多样,但不免有隔雾看花之嫌。民国留美博士生则力图以自身的文化优势,通过接受专门的学术训练,以西式理论方法,选择丰富多样的中国教育研究题材,探讨中国教育问题与中国教育重建方案,展现了他们独特的研究路径,并为中国社会发展谋求新出路。
二、留美博士生的中国教育研究路径分析
教育话语的构成,“按照谢弗勒(Scheffeler)的分析,主要由三种形式构成:(1)教育术语;(2)教育口号;(3)教育隐喻。”(16)但昭彬:《话语权与教育宗旨之共变》,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第23页。郑杭生认为:学术话语权“就是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17)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7日,第B02版。留美生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价值观念、论证逻辑和理论范式等要素的阐释,表达他们在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上的说话权利和资格,并用学术研究实践的形式展现出来,体现了留美生在美国学术场域背景下进行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独特路径。考析民国时期留美生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路径表现为“四个维度”和“一个策略”的特点。
其一,在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上,留美生以博士论文的形式,积极参与并选取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争取教育研究的话语资格与权利。研究议题决定了研究所触及的领域,也反映了研究的重要程度。考察留美生博士论文的选题,可以发现他们尤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社会改造类和方案类的论文十分流行,以“重组”(reorganization)、“重建”(reconstruction)、“改进”(improvement)、“建议”(suggestion)、“计划/方案”(plan/program/proposed)、“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为题目核心词汇的论文比较常见,共有26篇之多。傅葆琛为回应国内乡村教育改革的需要,选择中国乡村小学课程重建作为论文的研究主题,他提出:“它不是要与城市课程相同,而是应建立在根据乡村需要和乡村人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任务为现今中国教育者提出了一项重大的挑战”,(18)Paul C. Fugh,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to Meet Rural Needs in China: Abstract of a Thesis,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1924, p.3.开辟了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新领域。在民众教育研究上,陈维纶从教育的功能理论出发,选取了民众教育研究,“有关中国民众教育问题及其发展已经写了很多,而在他们的历史与世界的联系的相关民众问题,或以社会目的与成人教育功能的相关民众问题,却很少或没有”。(19)Wei-Lun Chen, A Sociological Foundation of Adult Education i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0, Preface.蒋梦麟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对教育原理和思想进行了整理,尤其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哲学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20)Monlin Chiang,(A)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刘湛恩的博士论文《非语言智力测验在中国的应用》对教育测量学的开辟和适应中国儿童的智力测量量表进行了设计,(21)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刘湛恩文集(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些都是他们开拓的新领域、新论题。留美生对中国教育研究新论题、新领域的探讨与开辟,是他们在美国学术场域中争取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资格与阵地,展现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权利意识与在场理念。
其二,在博士论文中,留美生以自身母国文化优势,借鉴西方学理梳理并阐释中国教育,争取中国教育研究的意义赋予。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考察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分期并结合中国教育自身的发展特点,使用教育统计法和比较研究法,梳理了中国自上古至论文撰写时的“公共教育制度”,重点关注了民国成立前后的教育热点问题,试图“提出一项能够在中国教育制度的长期发展中有关它的相关解释,给出一个历朝历代有关古代和传统教育制度兴衰的透彻看法”“它代表了向英语世界的公众梳理中国教育复杂历史的首次认真的尝试”。(22)Ping Wen Kuo,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T. C. Columbia University, 1914, preface, v.蒋梦麟则利用西式的论证逻辑与理论范式,尤其是系统化的教育研究法整理中国教育材料,建立起中国学人对教育原理的初步解释,诚如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所述,“主要是对中国教育原理的开拓性研究,且是第一个试图揭示中国众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教育思想,用更清晰的语言去解释这多多少少含糊的观点,并试图将这些零散的思想整合成一个相关的整体”;他也承认“本书使用的资料来自中国原始文献,而组织和系统化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却或多或少是西方的”。(23)Monlin Chiang, (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iii.改编自钟鲁斋博士论文的《中国近代民治教育发达史》,主要考察了从癸卯学制建立至1933年间的中国现代教育中的民主趋势,这些民主趋势体现在教育管理制度、组织制度、义务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以及教会教育等方面,他期望对“近年来在中国混乱的政治社会环境下趋向民主的教育运动”(24)Lu-Dzai Djung, A 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p.17.给予一番综合阐释。庄泽宣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民治的趋势》选择中国教育民治的趋势作为研究主题,“这是因为很少西方人完全成功地理解中国的事实,也因为很少的中国人成功地将中国介绍给他的西方朋友的这样事实”。(25)Chai-Hsuan Chuang. Tendencies toward a Democratic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2, iii-iv.这些留美博士生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以“表白”中国文化为己任,为西方世界呈现了中国教育的丰富面相,初步建立了中国教育研究的意义赋予和阐释。诚如叶崇高博士论文《美国大学中国研究生的适应问题》所指:“中国研究生应体会到在美国代表中国的责任,并向美国阐明中国的理念与态度”。(26)Tsung-Kao Yieh, The Adjust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Private Edition, 1934, p. 122.在留美生看来,就民族情感和文化优势而言,他们才是最有资格对中国教育研究进行意义赋予和阐释的群体。
其三,在西方人主导的美国学术场域中,留美生仍积极地寻求学术对话,争取中国教育研究的鉴定评判与指引导向的权利。留美博士生试图拨正中国教育研究被“发明”的言说,探讨被遮蔽的问题,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如在华人华侨的教育问题研究上,张敷荣就积极争取华人华侨教育研究的评判和指引导向,发出中国的声音,在其博士论文《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市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中提出:“好像华人只是默默等待更加激进的日本人于1906年去打响反对教育领域种族歧视的第一仗,这是真的吗?”(27)靳玉乐、沈小碚:《张敷荣教育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31、276-277页。他基于事实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华人在反对教育领域种族歧视和争取公平权利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驳斥了两名教育学院研究生吹捧美国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的政策,驳斥了他们认为的中国侨民对隔离政策和措施的‘默认’和‘欢迎’”。⑥曾昭森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试图打破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霸权,通过实证分析和研究,对被曲解的中国学校教育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探讨,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中,他指出由于西方世界错误的信息、毫无根据的阐释,直至日本侵华之前,“中国学校教育被构建为不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是否好像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确实已经达到了一点,而这造成了充满敌意批评家的谴责或我们朋友的警告?”(28)Chiu-Sam Tsang, 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Printed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1933, foreword.曾昭森根据整体分析以及中日外交关系的经验做出了判断,认为西方世界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主义研究中,曾作忠在博士论文《现代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中国后革命时代情况为中心》中,向西方世界展示并评析了中国学校教育的民族主义特征,是“为生活而文化,而非为文化而生活”。(29)James F. Abe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9, No. 4, Oct., 1939, pp. 385-387.留美生利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纠正“他者”研究的“我者”形象,以争取中国教育研究的鉴定评判与指引导向的权利,自是为了在“他者”场域中如何确立“自我”。
其四,在博士论文中,留美生还通过对教育研究术语的容受与规训,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学术概念,进一步丰富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如对“民主化”“民主趋势”“公共教育制度”“政治伦理”“公共教育财政”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运用。教育民主化是民国时期时人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留美博士生关注的主要论题。钟鲁斋在改编自博士论文的《中国近代民治教育发达史》书中,就以教育“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民主趋势”(democratic tendencies)为核心概念,从政治的民主、经济的民主、教育管理的民主、教学的民主、教育观念的民主、教育机会的民主以及科学方法来构建其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在他看来,自新学制以来,中国教育民主的趋势显现在“更加民主的管理和组织制度的发展中,义务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及女子教育的发展中,以及教会教育的革新中”“真正的教育是进步的,一个面向真实和美好的运动。民主、科学和教育都是共同的”。(30)Lu-Dzai Djung, A 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Preface,p.11.张汇兰在博士论文《中国体育的合理课程结构的事实与规律》中,则提出民主教育的基本原则为:“教育必须认识到个体需要;教育必须认识到个体差异;教育必须认识到永恒的社会变革;教育必须认识到个体的整体人格的融合;教育必须认识到经验的连续性与相互作用;教育必须认识到个体对其环境的关系”。(31)Hwei Lan Chang, A Colligation of Facts and Principles Basic to Sou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1944, p.3.不过在傅葆琛看来,若从教育机会平等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民主,中国需要的教育不仅要通用,而且要行之有效并实用。”(32)Paul C. Fugh,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to Meet Rural Needs in China: Abstract of a Thesis, p.3.以上论者皆从不同研究视角,发挥并界定了教育“民主化”的概念。
郭秉文运用了“公共教育制度”(Public Educational System)的学术概念,进行中国教育制度的系统整理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认为:“所谓公共教育制度者,乃指国家所维持与管理之学校,所以为人民教育者。狭义而言,则不能括登庸考试制度。”(33)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绪言。蒋梦麟在论证中国古代教育文化思想特点时,提出了“政治伦理”(politico-ethical)这一概念,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指出:“儒家学派的中心问题可称为政治伦理问题”,进而建议“不必让政治伦理问题占据所有的知识领域。必须唤起对自然的强烈热情,必须引介调查研究的系统方法。我们必须融进科学的精神”。(34)Monlin Chiang,(A)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pp.75-77.在教育财政学领域,陈友松首度将“财政”与“教育”联结起来,确立“公共教育财政”(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这一基本学术概念,并使用“应计经济费用”(accrued economic charge)来分析教育的经常费用。傅葆琛则以美国中等教育家亚历山大·J. 英格利斯的“社会公民目标”“经济职业目标”“个人修养目标”三个教育基本目标为理论源泉,并结合中国乡村教育建设实际,从教育的有效性出发,构建中国乡村小学教育的初步目标体系,提出了“体能效率”“职业效率”“社会效率”“公民道德效率”“修养效率”“心理效率”。(35)Paul C. Fugh,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to meet Rural Needs in China,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5, IX, No.2, pp.331-332.赵冕则从中国的时代背景出发,依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解,对民众教育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和阐释,他认为:“‘民众教育’(people education)、‘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社会教育’(social education)都是同义词”,“民众教育”(people education)在当时来说 “是一场社会运动,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一种教育实践”。(36)Pu Hsia Frederick Chao, 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Report of a Type C Project, Columbia University, 1946, pp.231-232.赵冕对民众教育的界定和阐释,丰富了教育研究话语,起到了规范教育术语建设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理解。
留美博士生对中国教育研究术语的界定和规范,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留美博士生的教育术语界定和规范首先来自于对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容受。第二,留美博士生对中国教育研究术语的界定和规范,紧密联系中国教育发展现实,侧重于与当时教育热点的结合。第三,留美博士生对中国教育研究术语的界定和规范,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和文化背景,对教育术语的内涵和范围进行了拓展,体现了创新意识。
总而言之,留美博士生对教育核心概念的容受和规训,融入了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丰富了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内涵,促进了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构建。
三、留美博士生中国教育研究的研究策略与海外影响
在中国教育研究的策略上,留美生在博士论文中普遍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证分析与系统整理为方法,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底色,建构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性。
朱君毅在博士论文《中国留美生:与其成功相关的质量》中设置了“什么应当被认为是一位留美生的成功?一些与之相关的质量是什么?”等六大问题,(37)Jennings Pinkwei Chu,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Success, New York: T. C. Columbia University, 1922, p.1.分析了留美生的学问与领导能力、英语知识及中文知识等因素及其相关性,考察他们的选拔与成败。王凤岗在博士论文《1895-1911年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中考察中日教育关系时,以“引起日本影响中国教育改革的知识背景和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改革在日本人身上产生的结果,相同的教育改革在中国人身上却没有产生一样的结果?”等十四个问题来架构论文,(38)Feng-Gang Wang, Japanes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from 1895 to 1911, Peiping: Authors Book Store, 1933, i-ii.试图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建议。陈友松在博士论文《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中,设置了“关于现行教育方案的经费现状,事实上是怎样的?一个合理可行的普及教育方案所需的经费,可能是多少?现行教育方案是如何维持的?”等五大问题,(39)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方辉盛、何光荣:《陈友松教育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1页。以便为中国教育的财政改革提供帮助。
以问题为导向还不足以完全展现留美生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其“科学性”还被赋予了实证分析和系统整理法以及美国盛行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前提下,朱君毅在论文《中国留美生:与其成功相关的质量》中,对中国在美37所院校的664位留学生的个人档案、英语测验、在华高中成绩和在美大学成绩等资料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并运用美国时兴的“相关评价”理论进行建模分析,提出了“可以用于管理预备和挑选赴美留学生的政策考虑上”的几点建议,“如果期望这些学生在美国于学问与领导力上取得成功的话……英语知识应置于更多强调的位置而中文知识应更少的强调”。(40)Jennings Pinkwei Chu,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Success, pp.51-53.在留美期限和留美资格上,他建议“为在一个短时期内获得高深知识,因此建议三到四年,几乎势在必行的是仅遣派那些在中国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或已有过训练的学生”。(41)Jennings Pinkwei Chu,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Success, pp.51-53.此后中国政府采纳了此种建议,显示出他的研究颇具科学性与预见性。王凤岗以历史实证主义的分析,得出了相同教育改革在日本开花结果而在中国未见成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经费的不足”“管理人员与教师的不足”“现代教科书、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不足”“良好舆论的缺乏”,(42)Feng-Gang Wang, Japanes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from 1895 to 1911, pp.91-102.回应了论文最初的设问。陈友松则运用了统计分析、事实评估、抽样调查以及采访调查等实证研究法,对中国教育经费的现状与支出、来源与负担能力以及湖北省个案进行了研究,他建议“中国至少将各级政府综合预算的25%用于教育”,(43)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方辉盛、何光荣:《陈友松教育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7页。并主张提高经费的利用效率,实行财税制度统一化和教育财政职业化、专门化,要求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上,其研究颇有见地。
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早期实践,留美博士的中国教育研究发出了中国学术的声音,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肯定评价。陈友松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被评价为“为他的英文读者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机械实施的教育扩展与发展20年计划提供了积极建议”。(44)G. W. H.,“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1912-1938), Jul. 1, 1936.约翰·杜威教授给胡适写信指出:“这是一部阐明可靠的作品,它对中国将有很高的价值”,乔治·D. 施菊野教授认为:“这项研究不仅对中国教育管理者是一种挑战而且是世界教育家们承认的一个重要贡献”。麦柯尔教授评价道“这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曾创作的最重要的博士论文之一,并且它以一种才华横溢的方式答辩”。(45)Ronald Yu Soong Cheng,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A Factual Analysis of Its Major Problems of Reconstructio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5, Introduction.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政府的决策还是教育改革中,都得到了一定的验证,又进一步证明了留美博士生中国教育研究的水平。
郭秉文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也获得了国外学界的肯定,被认为是“一项由了解同时代中国和教育的人所作的中国教育发展的相关解释”,被列入传教士必读书目,并被纳入美国大学教材,美国教育史家孟禄指出:“它为西方了解东方状况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46)R., “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 Feb. 1, 1918.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美国教育学家克伯莱对钟鲁斋的《中国现代教育中的民主趋向》,给予了高度评价,从中“学到了许多关于这个古老而新生大陆教育发展的至今我还不了解的知识”,并且“发现钟博士的故事以一种非常有趣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写作而成”。教育史家奥尔马克则评价道:“首先我们可以从中一览古老中国伟大的智慧和文化,占有一席之地而强大的文明”。(47)Djung Lu-Dzai, A 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prefac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4, xii.萧恩承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教育史》被教育学家霍恩评价为视角独特,“这里是一种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教育”。(48)Theodore E. Hsiao, 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Peip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32, Introduction, vii-viii.曾作忠博士论文《现代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中国后革命时代情况为中心》中关于中国“为生活而文化,而非为文化而生活”“很少盲目徘徊于时被称为民族精神的传统上”的观点,获得了学者阿贝尔的高度评价,通过对比,阿贝尔认为西方学者皮克(Peake)的观点“或许夸大了情况”(49)James F. Abe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 pp.385-387.。上述海外教育学者对留美生博士论文的肯定与评价,高度体现了这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彰显了留美生为中国学术发声的努力。
四、结论与启示
梁启超认为,“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而学问成绩主要在于“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原则以研究前任未经研究之现象”。(50)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学术独立不仅仅是指研究对象由域外转向本土,或者是以本土固有材料来填充外来体系或框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是要能够立足本土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建与发明。”(51)桑兵、关晓红:《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81页。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以“四个维度”和“一个策略”逐步形塑中国教育研究路径和话语,已经萌生了学术研究的自立意识,并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留美博士在进行中国教育研究时,还要面对如何考量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问题。在研究中,他们往往通过寻找与西方教育思想相应的观点或历史,以类推的形式建立起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合法性依据。如郭秉文认为孔子“举一反三”的教育法“颇合于自动主义”;孔孟之教特别注意开发人的心性,“深合近世所谓自然教育法”(52)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11、16、29页。。周代教育的长处在于“为重实验而与当时生活相接近”“阳明先生之哲学,精微而切实用”(53)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11、16、29页。,其教育宗旨类似裴斯泰洛齐派。蒋梦麟指出朱熹格物寻理体系的态度最接近现代科学方法,他赞同陆象山的观点,“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54)Monlin Chiang,(A)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pp.59-60.这种类推的方法,有利于贯通整合中外教育思想资源,但对其背后的文化心态应有清晰的认识。留美生多出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心态,以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国形象为目的,然而这种类推法,难免存在强行“调适”的风险。此外,留美博士生的中国教育研究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特点,民族性往往是把双刃剑,它在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同时,也不免将其带入“为民族而民族”的研究视野困境。
考量留美博士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实践活动,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时,要以知识分子的学术担当为己任,保有开放的学术心态与广阔的学术视野,重视各个研究论题的积极参与,尽管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有时声音是微弱的,但亦要在场;其二,进行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实践,要有着学术独立的主动自省意识;其三,中国教育研究理应从中国背景和中国需求出发,顾及中国固有哲学和民族特性,“对中国背景的清楚认知是有效满足中国当前需求的要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传递一大堆西方题材和方法上,这将是两者的结合”(55)R., “Review”,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2-1938), Feb. 1, 1918.,从而建立起学术与时代、文化、现实之间的桥梁。其四,对基本教育术语的阐释、规范,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民国时期留美生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的研究实践,根植于中国学人学术自立的内省,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虽然参差不齐,但总体上不失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亮点。无论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构建,还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学科建设,留美生博士论文皆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学术财富。重新审视留美博士在美国的学术实践活动,对当今的中国教育研究建设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