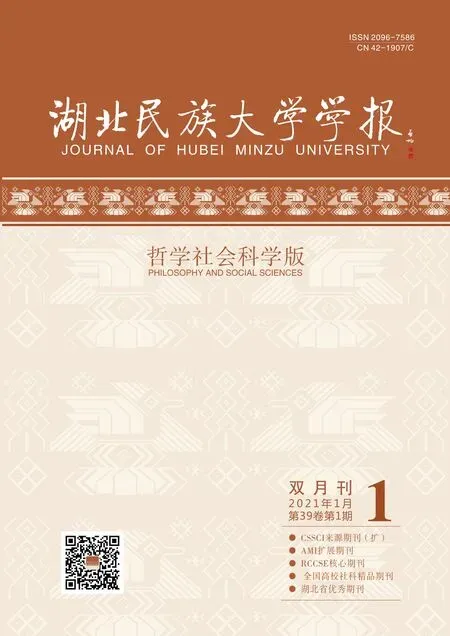民族志视野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黄建生
正式制度规范和人们的实际行为选择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叫“策略空间”。无论一个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它都不可能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影响这一“空间”的要素除了来自各种正式制度的结构性规范外,还有来自传统文化、信仰、人生观、世界观、利益考量、个人品性、当下环境条件等。反之,人们对这个空间的认知、态度和利用方式又影响着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因此,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完善各种正式制度,还需要充分理解那些参与治理的人或社会组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空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民族志研究方法假定:在一定范围内曾经发生的事、各种关联的问题、场景、环境和社会关系等要素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合集对个体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要素的合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具体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研究者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中,与研究对象建立稳固而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收集大量可视资料,以揭示那些当地人未表述出来的需求,捕捉那些日常生活中不同场景下的行为模式。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同样一个国家政策(或法令),在甲、乙、丙三个地方实施,或在不同时代实施,因执行者的认知和能力不同,当地历史、实施场景、所处环境、社会关系构成等不同而可能出现不同的执行方式和实际效果。
一、学术史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在某个社会体系内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风俗习惯和行为有机地架构起来实施管理以实现某个(或某些)共同目标的全部过程。治理理论的研究大致包括两个视角:其一是把治理理解为一个规范的概念体系;其二是将治理视为一个共同决策和实现某个(某些个)目标的实践过程。规范视角强调的是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分析,强调治理中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等原则,最终的目标是探寻实现“善治”的合理性和有效路径。从实践过程的视角来看,所谓治理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运用法律、规范、权力和语言来调整成员(社会群体)间相互关系以实现某些具体目标的复杂过程。虽然治理的核心主体仍然是国家(一般称为“元治理”),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群组织、利益团体,甚至个人也能够有机会积极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
讨论治理的实践过程不能简单地假设正式制度的完善就能实现“善治”的目标,也不能将治理的多元主体视为没有主观意识的机器零件和正式制度运行的“螺丝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既要思考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完善,也需要对多元治理主体及其能力进行深刻理解和阐释。要对这些“有血有肉”的理性(尽管有限)个体、历史、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社会组织、互动场景、社会关系、互动原则等进行民族志的“深描”、理解和阐释。
社会科学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并非只是靠王权、政治权力、经济体系或宗教神权等决定的,而是多种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社会体系、文化习俗和传统等相互作用的结果。17至18世纪,一部分欧洲启蒙思想家(如博纳尔、梅斯特等)就曾经强调,社会习俗和传统这样一些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相比不那么“正式”的社会机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马克斯·韦伯主张把研究视角从宏大的社会结构分析转移到社会行为个体,并从行为者的视角去理解他/她赋予自己行为的主观意义上来,即强调对社会行为者及其背景(环境)进行理性的“全面阐释”。(1)Mar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1958.乔特雷和斯托克认为,现代治理理论的研究者应该把治理的过程视为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分析性的、经验性的解释,而不是作为应该遵循的一份由各种规则构成的“愿望清单”来看待。(2)Chhotray Vasudha & Stoker Gerry,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9, p.6.为什么呢?因为:其一,治理首先是一种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实践活动,很难用清晰的逻辑关系来加以解释;其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其三,各主体之间在信息、能力、场景判断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有时甚至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最后,主体间的各种差异又严重影响着各自的目标设定、集体决策意愿、协商模式的偏好以及对合作关系的理解和阐释。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一书中讨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在朝廷或政府管理缺位背景下“士绅”这一民间力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3)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费孝通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即便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国度,民间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还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4)在此书中,费先生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士绅”这一民间力量在很多地方却往往逐渐演变成欺压乡邻的恶霸、“土豪劣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乡(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管理体系在城乡治理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类似“士绅”这样的民间力量被政府的管理取代,或者说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去。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思想观念、行为态度、愿望和诉求,也因此对基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一,政府管理职能和效率如何提升?其二,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及各种社会新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和诉求?其三,新形式的“士绅”可能成为基层治理的积极力量,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黑恶势力”,威胁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问题的讨论同样需要从国家和民间两个视角来思考,特别是对于那些拥有独特环境、历史、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地区。
(一)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民族地区治理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西方学术界鲜有专门讨论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文献。与中国少数民族相近的“原住民”概念在西方很少作为专门的治理对象来思考,而是常常作为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或“受害者”来看待。西方人类学家关于“原住民”(“土著”“部落”等)治理的研究与殖民主义背景息息相关。这种研究大致包括三个视野。其一,考察和探讨西方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原住民内部自我管理的社会机制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学家对前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亲属制度、家庭、联盟或部落的结构关系及社会交换、互动原则的研究,如摩尔根、(5)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马林诺夫斯基、(6)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布朗、(7)拉德克里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施特劳斯(8)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等的研究。其二,对殖民统治与原住民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原住民要么不得不顺应殖民者设立的政治统治,要么在殖民背景下随机应变地去适应殖民的管制,比如参与殖民政府的一些工作(如选举)、组织社群委员会,甚至参与某些司法审判、签订协议等,如菲德豪斯、(9)D. K. Fieldhouse,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1.斯塔夫里亚诺斯、(10)Leften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Morrow, 1981.霍布斯鲍姆、(11)Eric Hobsbawm,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1987.萨伊德(12)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等的研究。其三,研究原住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积极争取独立、反对种族歧视等,如博德利(13)Bodley J. H. ed., Tribal People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 Global Overview, Palo Alto, CA: Mayfield, 1988.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本质上把原住民视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或社会弱势群体,因此,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原住民争取平等的权利,建立一个“和谐共创的社会”。(14)参阅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章程。
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本质上与西方学者眼中的“原住民”“土著”“部落”等有巨大的区别。自21世纪初开始,国内很多学者引入西方关于地方治理的一般理论、模式,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特色以及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性和发展趋势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并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观点认为,探寻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处理上述三种关系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与中、东部地区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因此,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差异是民族地区治理成败的关键。很多学者从民族地区社区层面入手,探讨政府、社区组织、家庭和社区居民在共同管理公共事务、风险管理、社会冲突与法制(15)吴开松:《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等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他们分别从民族地区城市社区、(16)徐铜柱:《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特征、困境及对策》,《理论导刊》2007年第5期;刘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则研究——以勐海县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郑茂刚:《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贵州省锦屏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启示》,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5期;青觉:《和谐社会与地区政府能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转型时期的农村社区、(17)孙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初探》,《东方企业文化》2010年第5期。个案分析、(18)吴开松、方付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应急管理(19)朱秦:《边疆民族地区和谐治理:在应急管理框架下的考察》,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不同视角研究政府在为民族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家庭和居民个体作用的问题。同时,也积极探讨国家、社区组织、家庭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意义。
2.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与社会资本
陈小红、(20)陈小红、白赵峰:《民族传统的社会治理采纳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黄增镇(21)黄增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等认为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正是他们的独特性所在,研究者可以借用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民族地区治理的路径。这些研究者更倾向于从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分析和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通过合理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社会资本来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
3.公民参与
一些学者认为公民的有效参与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质效的提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要通过加强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充分利用本土性、强化法制管理、拓宽多元利益表述渠道、为公民提供制度平台等来建立有序的公民参与。比如青觉、(22)青觉、闫力:《共建共治共享: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3期。尤丽波、(23)尤丽波:《公民参与视域下民族地区治理路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陈玉、(24)陈玉、王胜章:《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障碍及实现途径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蒋辉:《浅论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桂海论丛》2010年第9期。李俊清(25)李俊清、陈旭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功能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在公众或社区参与民族地区社会进行了探讨。
这些研究大多从国家(或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民族地区治理,因此,在研究者眼中,民族地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比内地很多地方滞后,在文化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在资源上具有相当的对外依赖性,工作上的行政特征比较明显,在政策上往往相对滞后等。正如张继焦总结的那样:民族地区研究应注重民族特性,其中“民生问题应该成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根本;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必须高度重视民族特点;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必须注意充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必须对少小民族予以重点关注。”(26)张继焦:《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民族论坛》2015年第3期。基于这样的判断和认识,学者们认为民族地区治理首先需要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治理方面加强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促进民族地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强化民族地区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关系以及治理模式本土化的理论研究。(27)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郭春霞、潘忠宇:《我国民族地区治理研究综述》,《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总之,民族地区治理必须采取独特的参与模式和治理模式。
(二)问题的提出
虽然上述学者(包括很多这里没有提到的学者)强调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也分别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进行了案例分析和研究,但往往让人觉得一个“特殊性”就概括了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不同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地区,其“特殊性”也常常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演变。同样是民族地区,边疆与内地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所谓“特殊性”和“社会资本”的型构具有动态性,往往因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时间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从学科视域来看,很多与民族地区治理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都采用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视野,在讨论“什么是民族地区地方善治”问题时总会有意无意地从“客位”的视角去看待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应然”状态,忽略了其“实然”景观。也就是说,学者不知不觉地站在“旁观者”立场上来讨论民族地区的地方治理“应该怎么或应该是什么样”。而对于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异以及那些每天面对具体生活实践的少数民族实际碰到什么矛盾、问题,有什么样的新诉求和愿望,他们心目中的“善治”是什么样的等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土化视角
全球化和民主化是推动治理理论兴起和发展的两个主要动力。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商品生产、消费、服务、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贸易等逐渐掌控在跨国公司和相关的组织手中,形成了国际性的分工和资源、产品、信息的国际性流动。这些公司的运作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地球村由此产生,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全球化”,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扁平”、同质和一体化。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上来说,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存在或再生产也同样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紧密地相互依赖和全球的互联互通并没有完全抹去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学家罗伯特森在一个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文化”的会议上借用日本经济学家的“全球本土化”概念首次阐述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技术、信息之间的联系,并与各种地方性的特质交融、互适,形成特定的全球本土化形态,在面对那些来自全球化的生产、消费、服务及思想观念冲击的时候,人们总是善于把“全球的”与“本土的”各种特质混合起来,建构出“让自己舒服”的现代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或族群)的人对全球化过程的理解和适应方式各不相同,人们总是努力让一种全球性的产品或服务去适应某地的文化,有时候甚至采取抵制全球化浪潮的各种措施,以保护本土的历史、传统和原生文化。
因此,讨论一个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我们至少应回答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某个具体地方而言,它自身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那些代表全球化的外来冲击和表现是什么?一个地方的人(或一个族群)如何理解和适应全球化的浪潮?全球本土化在一个地方(族群)的具体演变过程是什么样的?它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出现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思考一个地方(族群)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治理体系和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治理层次,人们对上述几个问题的回答都会有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地区(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差异。比如,云南省南部的M村,2007年村旁的茶叶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很多外来的茶厂老板、茶叶经销商和一些上门女婿不仅给村里带来资金、技术和发展机遇,而且带来各种新的思想、观念。村民对传统文化、亲属关系的高度认同与政府的管理、外来商人和上门女婿的影响紧密交织在一起。日常生活中,村民对村民内部相互间的关系比较敏感,当说到某人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好像怕引起双方的矛盾,但又常常透露出相互之间暗暗较劲、利用各种资源寻找个人(或家庭)发展的机会,有时甚至表露出某些“比富”的心态。部分村民至今仍在城里打工,但大多数还是愿意在附近茶厂就业或收购和销售茶叶。外来的商人通过捐款或其他社会交换形式与村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以非官方的形式经常参与村内“公共利益”的规划和实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政府、村民、外来人员这三个治理主体,但每一个主体内部的差异仍然存在,比如虽然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法律法规是明确的,但不同地方领导的管理能力和具体实施方法等还是有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会影响到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再比如,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往往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某个商人可能与村内的某个人(某些人)关系比较密切,但另一些村民可能从来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差异有时会影响到村子的内部关系和公共决策。(28)资料来源于笔者2007至2013年在M村田野调查笔记。M村的很多新村民(如茶厂老板、商人、技术人员、上门女婿等)户口并不在村里,但他们存在又与村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虽然县、乡政府和村委会把他们作为“暂住人口”管理,但他们参与村内事务以及与村民之间的日常互动往往不在正式管理的范围之内。
地处云南省西北部的B村坐落于独龙江大峡谷中,峡谷的东西两面是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南北都是独龙族村寨,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其他民族的村寨。独龙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家族(氏族)为单位,分散居住在山坡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一直努力将他们搬迁到独龙江两岸居住,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直到2015年才真正完成搬迁(还有个别老年人不愿搬)。无论从传统文化、亲属关系还是从周边文化的影响来看,B村与M村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路径来看,M村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茶叶工业园带动的茶叶产业大发展。B村的发展则主要是因为云南省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实施的“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项目及其他政府扶持项目。这些国家主导式发展项目彻底改变了B村的交通、住宅、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引入了草果种植,大大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村民都愿意在家里,而不想到城市去打工。村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民族有高度的认同,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一些,自主发展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9)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至2017年在独龙江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笔记。在M村,村民的生活机会主要靠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较好的村民往往更有机会成为茶叶中间商、销售代理或茶厂的管理人员,从而有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在B村,不少村民常说:“听政府的”,即他们坚信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
云南省东南部的D村,坐落在偏僻的山谷里,属于多民族混杂的村寨,全村只有41户185人。在这种小规模、多元文化构成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自古就形成相互间的严重依赖。当全村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长年在外打工,不在村里生活的时候,这种传统关系和相应的社会互动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简单来说,旧的行为规范没有完全消失,新的经济行为模式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村内互动关系。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新型留守儿童”(30)所谓“新型留守儿童”是指那些父母外出打工并离异的孩子,离异的父母都不想承担抚养的责任,只能由爷爷奶奶辈来抚养。在D村,这样的孩子就有5名(4户)。及其成长和教育问题、老年人问题、婚姻问题、心理问题、村民之间关系协调问题等。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D村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管理对象却常年“不在场”(其中有些村民还是共产党员),有近四分之一的家庭甚至在乡镇、县城或其他地方建造或购买了住房。这就给村子的管理或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合作社、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这里几乎不存在,而村里的所谓“能人”基本外出务工。D村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乡村治理问题:如何治理“空心村”?这里的“空心村”不仅仅是好多村民“不在场”的问题,还涉及其他的社会问题,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离婚后把孩子留给老人、老人没人照顾等。(31)自1999年开始,笔者一直关注D村的发展演变,每年至少到D村一次。以上资料均来自笔者的参与观察。
上述三个村子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推动了村内社会秩序、生活机会、生存策略的快速转变。这一过程中,有来自市场、政府和人口流动方面的推动力,也有来自原有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当现代与传统相互碰撞的时候,他们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对人们的生活策略选择和社会治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社区组织层面上,所谓全球本土化主要表现在社区的自组织过程中。那些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上似乎比较明确的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社区层面上陡然变得模糊,因为社区成员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面临的各种实际社会问题往往说不清楚究竟是全球的还是地方的,而这些东西往往是相互依赖和联系的,中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社区成员组织起来既是为了解决本土的问题,也是为了应对全球的问题。比如,社区组织大家清理生活区内长期积压的垃圾,这既是改善小区内的生活环境,也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小部分努力。
社区内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往往是为了满足某个具体的需求、获得某种利益或者解决影响人们生活的某个共同难题等。这种组织形式特别强调对某些问题(如权力、授权、社区利益)、变化策略(如教育、直接行动、协作)和促进“包容性关系网络”的沟通策略的深层理解等。它们的目标是通过采取直接行动,将社区成员组织起来以满足社区当下的需求,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治理理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化不是绝对同质和一体的,而是有区域、国家、甚至地方和民族特性的。无论从全球治理层面或国家治理层面上来说,还是从地方治理层面上来看,要实现“善治”,人们首先必须充分了解一个国家、地方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它原有的历史、文化和资源配置。
三、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动性与善治过程
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和法律都那么完善了,生活中总还是问题迭出?这是全世界(特别的高度发达国家)很多人常问的一个问题。除了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制度本身外,我们还应该把制度放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来思考,因为正是具体的实践活动才把各种相关的因素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阐释一个制度在面临具体情况时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因此,治理是一个需要不断理解和阐释的实践过程。
作为一个实践过程,治理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又很有挑战性的维度,因为治理需要参与者不断认知自己所处地区的社会本质、经济运行特性、政治体系与实践、文化形态等。此外,治理的过程本身必须作为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分析性的和实证性的理解。(32)Vasudha Chhotray and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 2009, pp. 1-5, 36-41.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治理是以某个具体的目标(公共利益)设定开始;然后,围绕着这个目标,制定能够让不同主体参与的机制;在政府作为“元治理主体”的地位不变的条件下,共同决策、共同参与、共同协调,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从目标设定到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都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极大的相关性。比如,在我国民族识别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多民族地区的最大公共利益就是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的权利,参与国家建设,在经济上提高生产能力。这些目标的设定都是基于对当时民族地区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状况和自然环境的认知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大量流往中、东部地区。各种新思想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民族地区群众的观念,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诉求与民族地区资源缺乏、人才缺乏、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虽然民族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但是随着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个体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孤陋寡闻”的形象。正如一位基层政府公务员说的那样:“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难管了,他们用手机就可随时查阅国家的政策和规定,你要是哪里做得稍微不合规,他们就去找上级部门。”从某些方面来说,老百姓有了新觉悟是好事,这也算是全球化的后果之一,但这句简单的话语也折射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所以,治理理论认为,要解决越来越复杂和多元的世界中治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需要充分理解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地方(特别是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必须基于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具体环境下的国家治理实践及面临的挑战的全面、深刻认识。正如乔特雷和斯托克所言:“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必须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小心地实施各种正式规则,而且要注意各种规则之间的平衡。”(33)Vasudha Chhotray and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 2009, pp. 1-5, 36-41.
治理模式和实施方案的设计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同的人因其信仰和欲望不同而对世界的理解各不相同。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与实际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如何在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之间达成有效的链接是当代社会治理的最大挑战。(34)Vasudha Chhotray and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 2009, pp. 1-5, 36-41.比如纽曼就强调说,要真正理解治理,首先必须重视行为者通过对某些事物赋予(或抑制)意义,以及服从或协调各种可能意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即行为者的世界意义及秩序。(35)Janet Newman, Modernizing Governance: New Labour, Polic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2009.如果不了解人们的信仰和观念,研究者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和阐释一个地方治理的社会背景及实现善治的各种可能路径。
在民族地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往往站在纯粹经济学或者城里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一个民族村寨或乡镇的治理问题,忽略了那些基于某些未显露的价值观之上发展出来的各种不同愿望。正如李晓燕对广东省GL镇的社区营造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中揭示出的那样,每个社区都有其治理的独特性,所拥有的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也各不相同,因而其社区营造重点和路径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36)李晓燕:《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理论与案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因此,要对少数民族村寨实施有效治理,不仅要理解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治理资源,还要在治理过程中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各类参与主体的愿望、诉求和价值观产生的根源以及人们在实践中如何表达这些愿望和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理的过程应该同时是一个评估的过程,而评估必须基于当地历史、文化以及实际经济、社会状况、文化背景及人们的愿望、诉求、价值观等的民族志理解和阐释。迄今为止,在众多的国内学者关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文献中,理论和方法上的讨论不少,却很少能看到某个地方(或某个民族)探索善治路径和方法的详尽民族志“深描”。像李晓燕那样,对不同社区治理实践的描述和分析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直观印象和经验,但从民族志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描述仍然不够“深”。
四、治理网络:治理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
“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组织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增进个人和集体的安全和物质满足,并达到共同的目标或管理共同的问题?这是对治理的永恒提问。”(37)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一核多元”治理过程的第一步是作为这“一核”的政府要考虑谁来参与治理以及参与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治理网络”的建构。网络建构和治理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对治理能否顺利开展、能否取得预计的成效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前所述,即便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乡村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文化传统等与城市社区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治理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上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不仅如此,不同地区的村寨之间、城市社区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治理网络的视角来看,治理就是管理各种行为者和组织复杂混合而构成的网络及其运行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一定范围内人的整个社会生活想象成一个由各种行为者和组织之间各种复杂关系构成的网络的话,那么,所谓治理就是构建网络和协调这个网络的运行。(38)Chhotray Vasudha & Stoker Gerry,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这一协调的具体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现有网络内部各种关系的建构和协调。如政府召集相关的利益主体来协商达成某项新的合作原则,或者联合决策以达成某个共同的目标(或公共利益)。这一过程包括发现潜在的网络参与者、参与者的动力激励机制以及可能达成目标的能力。其二是网络的结构化过程,即改变成员之间关系结构、资源分配机制、改变政策倾向、吸纳新成员或者努力促成某种新的结果的过程。这一结构化的过程可能长,也可能短,主要取决于目标实现的具体实践。
在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从中央一直到乡镇的行政管理体系,各级政府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机构,另外作为村民自治机构的村委会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此之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妇联、工会等制度和组织为公民权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事实证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公众参与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正如之前所述,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愿望诉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单一管理模式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政府如何才能改变“包办一切”的管理方式,减少一些人的“等、靠、要”等思想,培养当地人的独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其次,面对那些越来越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的个体和不断扩大的社会网络或社会组织,政府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责任和义务边界,以便更有效地实施治理。
索仁森将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角色归纳为四种类型:放手自我治理模式、放手讲述故事、插手支持和提供便利、插手参与。所谓“放手自我治理”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政府只是从立法上为网络中的主体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至于这些主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则完全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再比如,政府只是采取某些激励机制去鼓励各类组织以某种方式开展合作,但不直接插手。总体来说就是,政府提供指导但不直接干预。政府想要对网络的运行施加影响并不仅仅是靠制定目标和激励机制,政府的叙事同样可以影响网络的运行。索仁森认为,讲故事可以建立起相应的价值观、区分敌友、塑造个人和群体(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与未来,从而树立起所谓“什么是恰当行为”的标杆。所以,政府不用直接插手就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影响多元自治主体的政治策略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网络内的各主体用某种观点去理解和看待他们所处的社会,从而对这个网络的整体运行进行管理。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管理者(政治家)首先必须学会新的领导技术。(39)Sorensen E.,“Metagovernance: the changing role of politicians in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choic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索仁森眼中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四种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过它说明了治理网络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政府依然是治理的重要主体,所谓“元治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有效地处理好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
斯拉蒙认为,领导者首先要学会从传统的官僚体制下的管理技术向使能技术转变,即,从居高临下的管理、控制向平等地看待各个相互依赖的主体转变,将他们凝聚起来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新的技术包括:激活、协同和调整。也就是说,在治理网络中,政府必须从管理的习惯转变成治理的思维,需要放弃管控的思想,采取平等对待不同治理参与主体,协调相互之间关系,以最终达成预计的目标。这是中国当下民族地区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长期习惯了自上而下、上传下达的管理方式,很多地方政府公务员仍然动用行政命令来完成各种目标。因此,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思维和能力转变的问题。但究竟该具体转变什么、如何转变、这些问题又与实际环境,甚至具体的个人有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从网络的角度来说,治理意味着“从基于政府决策和政府机构的管理理念向基于目标和网络的治理观念的转变……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将把公共价值最大化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千方百计配置和调整网络内部的所有资源。”(40)Goldsmith S. and Eggers W.D., Governing by Network: The New Shape of the Public Sector, Wa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 Pr., 2004, p. 181.
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制度性的变革;其二,个体行为的改变。人们一般认为制度调整、改革和完善才是从管理到治理转变的核心,而且把治理体系的变革仅仅局限于政治(或经济)、法律体系等这样一些正式制度的改变。这种理解在宏观的层面(如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等)上或许是很有道理的,但在乡村治理层面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不足。首先,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法律、亲属关系、社会交换原则、民族传统文化等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政治上或法律上的管理措施能否良好运行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些措施是否完善或实施者的能力有多强,它还与人们在亲属体系、社会交换中长期形成的习惯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价值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所谓“公共利益”“共同目标”的达成往往需要以当地人的社会文化状况和思想观念为基础。其次,从管理走向治理,从单一主体的管理转变成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最核心的是人的思想、行为的改变。俞可平认为:“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所以,善治要求有关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地同意和认可。”(4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页。
五、结论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的差异性,甚至在干部和不同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态度、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在讨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时候,应该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及全球化影响进行全面、整体性的理解和阐释。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不完全是一个来自外部的设计和规划,而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因此对不同主体的认知是善治的重要基础。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容、范畴、多元主体及参与方式的认定需要基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治理理论的民族志视角为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富有挑战性的维度,为探索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路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的地方治理应该以具体发展项目为引领,对不同的地区或群体进行项目周期的民族志评估和监测,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咨询来对当地或该群体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愿望、诉求等进行整体性的理解和阐释,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