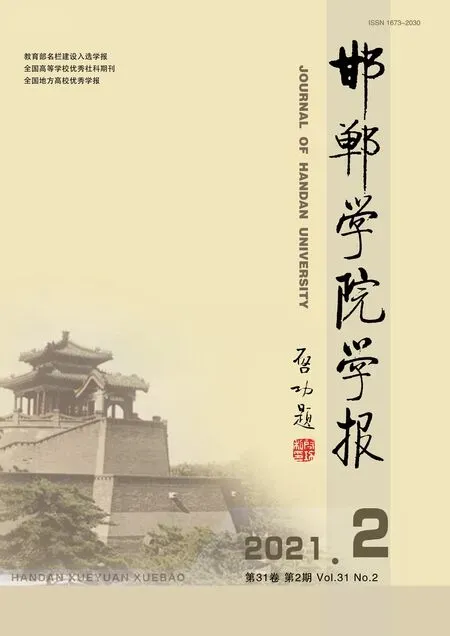论苦难题材与戏剧创作——兼谈“抗疫”戏剧
焦振文
论苦难题材与戏剧创作——兼谈“抗疫”戏剧
焦振文1,2
(1.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 河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更是一个愈挫愈勇的伟大民族。面对战争、洪水、瘟疫等天灾人祸,文学家们从未缺席,他们以诗歌、散文、小说或戏剧等形式来艺术地再现苦难,表达悲悯的人文情怀。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戏剧戏曲界更是纷纷行动,各个院团、各大剧种都纷纷创排各种长短不一的“抗疫戏剧”,然而,却难以出现能够经受时空考验的经典文本。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主体自身创作能力所限,更主要在于单纯追求短平快,急于发声表态,缺少思想与艺术的沉淀,缺少对逆行英雄发自内心的敬畏之心。
苦难题材;戏剧创作;新冠疫情;抗疫戏剧
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对文章价值的高度肯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文章与诗歌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强调。“多难兴邦”,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更是一个愈挫愈勇的民族。每逢灾难,不论天灾,还是人祸,文学家、艺术家都会以悲悯的情怀,用不朽的作品艺术地、审美地再现或表现灾难地现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真实记录了汉末建安时期战乱带给人民的巨大创伤,“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战城南)这是对乱灾难的真实记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这是汉末瘟疫肆虐在曹操眼中的真实呈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瘟疫肆虐整个北方,曹植在其《说疫气》一文中也曾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盛唐大诗人杜甫的诗歌被誉为“诗史”,就是因为他饱含深情地艺术的再现了安史之乱带给人们的巨大灾难,他的《石壕吏》以一户普通人家的遭遇由小见大,网射了千家万户;他的《兵车行》那“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宵”的悲惨场面,即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对战争的灾难不寒而栗。宋代的大文人苏轼在《与林天和长官》中对瘟疫的流行所造成的灾难悲痛的写道“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
元明已降,通俗文学尤其是戏曲的出现,瘟疫、蝗灾、洪灾、旱灾以及战争灾难常常作为背景出现在戏曲、小说的情节之中。元杂剧《陈州粜米》艺术地再现了大宋仁宗年间,陈州大旱三年,颗粒不收,人民饥至相食的惨景。与之相关,大多后世的包公戏多有陈州放粮,赈济灾荒的背景,比如《狸猫换太子•草桥遇后》就是写包公陈州放粮归来,路经草桥镇,遇到李国太鸣冤告状之事;再比如评剧《秦香莲》的背景是湖广钧州府三年大旱,饿死了陈世美的一双父母,秦香莲身背琵琶,携儿带女,千里迢迢进京寻夫。拦轿告状一折戏,也是以包公陈州放粮为背景的:“宋王爷坐江山,谗臣当道。普天下众黎民受尽煎熬,实可叹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哀鸿在道。下陈州奉旨放粮不辞辛劳……”保定老调《忠烈千秋》也有包公放粮赈济灾荒的背景,类似情形不一而足。根据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改编的河北梆子《窦娥冤•冥诉》一折戏,也通过窦天章之口再现了楚州荒旱之景:“奉圣命到楚州审囚刷案,一路上触景生情生疑团。为什么赤地千里行人断,十室九空不见人家。白骨遍野无人管,鬼哭狼嚎心胆寒”这分明是封建社会天灾人祸下百姓苍生的真实生存状态。元末明初高明的《琵琶记》也是以陈留郡三年荒旱饿死了蔡伯喈一双父母为背景展开剧情的。再比如京剧《生死恨》(又名《韩玉娘》)《凤还巢》河北梆子《南北和》等则展现了战争灾难的背景。不惟戏曲,小说《女仙外传》《三国志平话》《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也都描写了瘟疫带给人们肉体与精神上的巨大伤害。比如《水浒传》的楔子便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小说描写到:“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1]2《西游记》里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其中的“温”与“瘟”是谐音,也就是管马的小官。正是由于瘟疫的肆虐,才出现了“瘟神”的形象——中国文学对瘟疫的艺术想象。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瘟疫,毛泽东主席欣喜地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展现了从“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能奈小虫何”旧社会人们面对瘟疫横行的无奈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新社会人民战胜瘟疫的自豪之情。
晚清近代已降,中华民族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也遭遇了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瘟疫横行诸多苦难,戏剧人都用艺术的手段再现或表现了中华儿女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诸如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洪涝灾害、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乃至2020年的新冠肺炎以及南方洪灾肆虐等历次重大的灾难面前,戏剧都从未缺席,而且较之以往瘟疫等灾难作为戏曲背景处理有了很大不同,那就是直击灾难,创作出了一批批“抗疫”“抗灾”戏剧。
二
2003年“非典”疫情的肆虐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瘟疫,封城封社区,全民抗疫,白衣天使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戏剧界也纷纷行动,较有代表性的有:话剧《北街南院》《最高利益》粤剧《风云2003》京剧《非常会见》《真情颂》越剧《被隔离的春天》豫剧《花好月不圆》等。话剧《北街南院》是北京人艺委约作家王俭在“非典”肆虐期间创作的一部充满浓郁京味风格的“抗疫题材“话剧,该剧是“非典”结束后首部搬上首都舞台的艺术作品。该剧讲述了SARS病毒逞虐期间,北京城北街南院因出了一个SARS病人而被隔离。职业、经历、性格各不相同的一家人和院里的其他人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封闭境遇中,各现本性,发生碰撞,危难考验着人生,也淘洗着人心,在共同克服和战胜SARS过程中,人与人在靠拢,心与心在沟通,表现出真情和相互关爱。SARS隔离解除了,这个院里的人的精神也得到提升。京剧《非常会见》是由北京京剧院老旦名家赵葆秀与花脸演员陈俊杰联袂排演的“抗疫”题材的短剧。该戏讲述一位瞒着父母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和父母在特殊环境下见面的故事,热情讴歌了一线医护人员在疫情横行的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救死扶伤的美好心灵。越剧《被隔离的春天》是由上海越剧院赵志刚倡议领衔、汇合全院力量,在短短数天创排的“抗疫”题材现代戏。该剧以抗击“非典”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为原型,塑造了传染病专家齐春晖在危难时刻主动请缨,逆行而上,不顾妻子何静和女儿齐心的反对,最终与妻子同时在抗疫前线会面,夫妻冰释前嫌,传达出“非典”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将人们隔离了,却在心灵空间将人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的主题。
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又一次严峻考验。面对地震灾难,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谱写出了一首首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颂歌。戏剧界再次行动,排演了诸如川剧《大爱——国魂》沪剧《废墟上的爱》舞剧《托起生命》等。其中《大爱——国魂》是由四川省川剧院牵头,联合涵盖京剧、越剧、黄梅戏、二人转等多剧种的全国多位戏剧表演艺术家联袂打造的抗震救灾戏剧。该剧艺术再现了5·12汶川大地震来临时和之后的感天动地的事迹,塑造了以身殉职的教师、勇救村民的村长、累倒在救灾前线的救援人员等艺术形象,歌颂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伟大精神。沪剧《废墟上的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长宁沪剧团紧锣密鼓创排的一出抗震救灾题材的现代戏,也是当时上海文艺界推出的第一台抗震救灾大戏,该戏以一所学校为切入点,艺术地再现了了几个家庭在地震中生死离别的遭遇,塑造了临危不惧、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挽救他人生命的教师和警察艺术形象。
2020年的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比2003年的“非典”要凶猛的多,同时也涌现出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逆行的英雄,他们连同广大人民中华儿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再次谱写出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赞歌,广大文艺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戏剧工作者纷纷响应,用艺术作品来讴歌英雄,记录灾难,哀悼逝者……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上至国家级各个剧种专业院团下到基层各个剧种的协会组织几乎都创排了各式各样的抗疫作品,从北方昆剧院的《端正好•楚江吟》《担心映日护人寰》《苍生大医》到北京京剧院的《战疫情》《中国脊梁——钟南山》;从越剧《逆行者的心声》《从我做起》到沪剧《一路有你》《有风的日子》《出征之前》;从河北梆子《年关》到豫剧《打不赢这一仗不把家还》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奇怪的是,从反映抗击非典到如今反映战胜新冠肺炎的戏剧,从反映抗洪救灾到反映抗震救灾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也随着疫情或灾难的消失甚至在灾难消失之前就早已无人过问了,留下来能够与前文提及的汉乐府、杜诗中灾难叙事一并成为经典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甚至一部都没有!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些剧目思想的深刻性不足,歌功颂德的功利性过强;艺术的表现力不够,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过强;悲天悯人的情怀不足,哗众取宠的私心过重;对英雄的敬畏之心缺乏,对模范的道德绑架有余。归根到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关起门来造车,急于政治表态,背离了艺术创造的规律。清代大戏剧家李渔指出“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尤加倍焉。”[2]11
三
戏曲不同于诗歌,诗歌的个性很强,短时间即兴可以充分抒发自己的情怀,同时,汉乐府民歌也好,杜诗也罢,它们都是以揭露批判来立意的,他们的艺术创作完全不带有功利目的,不需要评价评优,不需要在媒体前表态发声,因此能够创作出既有思想深刻又有艺术水准的艺术经典,当然,更为本质的还是艺术家自身具备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从事戏剧活动,无论是创作演出,还是欣赏评论,都是一种审美活动,都需要具有一种审美的感受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诗意的感觉,有了这种感受力,人们方可将戏剧的艺术工作与其他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工作区别开来,使戏剧创作成为真正的艺术创作。”[3]49
然而,当下的抗疫题材戏剧则不然。首先,戏剧是集体创作的产物,个性的因素在某些方面就会被消弭。其次,当下的抗疫戏剧都是短平快的急就章,缺少必要的沉淀与思考,主题流于肤浅。“当然,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属于短平快性质,它们更多是文艺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应急式表现,甚至很多还会带有新闻性的那种直击现实、快速反应、广泛传播的特点。”[4]此外,大多数作品都是歌功颂德之作,当然,我们的抗疫英雄或者抗震救灾的英雄是完全应该被歌颂的,但绝不能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再用艺术作品表现他们时,一定要认清他们都是“这一个”,而非脸谱化、平面化的千篇一律;应该认识到这些英雄都是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有妻儿老小,他们也有七情六欲,而非道德化的冷血动物,可惜的是,很少有作品能够把握到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在其发表的《“抗疫”美术创作的罪与罚》一文中对于绘画界单纯以歌颂为能事的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他将“抗疫”(美术)作品分为了“恶俗的”与“平庸的”两类,进而指出:“恶俗作品,我用三句话打发:于社会有害,于道德有亏,于艺术则一文不值。而所谓平庸之作,即为按同一套路生产出来的作品。其创作方法很简单:抄照片+宣传画模式。摆拍式造型、雷同化场景、八股式图像、苍白的形象、凉薄的情感、单调的结构,将作品牢牢地捆绑在口号的水平上。”[5]其实,抗疫题材的戏剧也存在这个问题,模式上大体一致,无非是主人公医护人员或人民警察奋不顾身主动请缨去疫情前线,而后与家人产生分歧,最终取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其中的人物缺乏个性,换上张三或李四,马上就会成为另一出戏。
更有一些恶俗之作,完全是出于博人眼球,或者在互联网王炫耀演技,将严肃的抗疫或者抗震救灾当成喜剧来表演,表演时嬉皮笑脸,弄乖卖巧,斗人傻笑,这完全是打着宣传抗疫,礼赞英雄之名去亵渎民族的脊梁——人民英雄的神圣!疫情无情,肆虐苍生,这毫无疑问是民族的悲剧,人类共同的悲剧,这样的戏剧一定是悲剧的底色,悲壮的情怀,这正如张晓凌先生所言:“真正的‘抗疫’作品是扎在民族心灵上的一根尖刺,稍有异动,便痛彻心肺。如果我们意识到新冠肺炎是一场民族的灾难,那么,悲剧便是它的呈现方式与语言属性。令人惊诧的是,艺术家们对此一无感知,他们步调一致地采用了依葫芦画瓢的颂歌体。”[5]如果将抗疫题材的剧目演成了喜剧或闹剧,如果在创排这类戏剧目时不能秉持敬畏之心、悲悯之心,而只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私利,是绝对不会创作出对得起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来的。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册[M].金圣叹,李卓吾,点评.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李渔.闲情偶寄[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4]汪人元.关于当前抗疫题材戏剧作品的创作[J].中国戏剧,2020(6).
[5]张晓凌.“抗疫”美术创作的罪与罚[N].中国美术报,2020-2-5.
On the Theme of Suffering and Drama Creation——On Anti Epidemic Drama
JIAO Zhen-wen1,2
(1.Graduate School,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100029;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Baoding,071001,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nation full of disasters, and it is also a great nation with more setbacks and bravery. In the face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such as war, flood and pestilence, writers have never been absent. They artistically reproduce suffering and express their compassionate humanistic feelings in the form of poetry, prose, novel or drama. In 2020,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raged, the drama and drama circles were acting in a row. Various theatrical troupes and major dramas had created various kinds of "anti epidemic drama" with different lengths. However,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classical texts that could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and space. On the one hand, it i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reative ability of the creative subjec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simple pursuit of being short, plain and quick, the eagerness to express one's position, 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precipitation, and the lack of inner awe for the retrograde hero.
suffering theme;drama creation;COVID-19;anti epidemic drama
I207.3
A
1673-2030(2021)02-0082-04
2021-02-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档案资源协同整合机制研究”(20BTQ099)
焦振文(1983—),男,河北涿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论与地方戏研究。
(责任编辑:李俊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