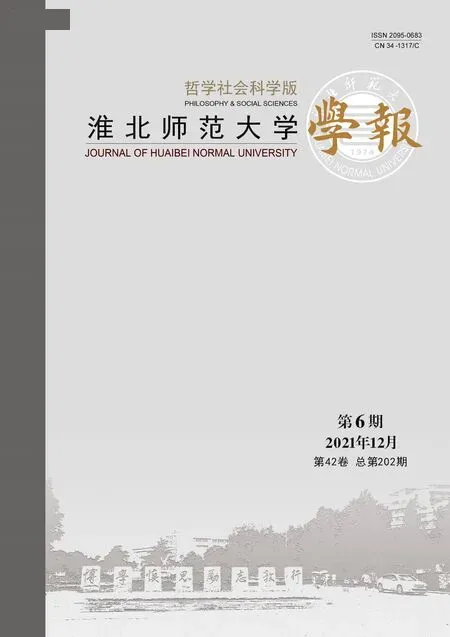笛卡尔实践理性观的四个基本维度探析
邹顺宏,杜国平
(1.琼台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1127;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英国哲学史专家柯普斯登在其多卷本著《西洋哲学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一般来说,近代哲学开始于笛卡儿,或由法兰西斯·培根开始于英国,而由笛卡儿开始于法国。”[1]作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是认识论理性主义的典范性代表。之后,对笛卡尔思想的继承发展生发出波澜壮阔的哲学研究浪潮。从科学史视角看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笛卡尔主义传统,甚至于,牛顿在自己独特的自然哲学形成之前(1665年初之前)也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其作品的成功则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世纪之末笛卡尔主义的消亡”。[2]随着近代笛卡尔主义演进为现代新笛卡尔主义、乃至后笛卡尔主义,笛卡尔理性观的影响依然占据了现代哲学的研究问题域。在其繁富斑斓的理论体系中,笛卡尔秉持了严谨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开创了革命性的新哲学体系,其理性观蕴含了面向科学实践、呼应社会发展的鲜明实用化趋向。依据科学实践的有关学理标准,我们可以将笛卡尔理性观总括性地展开为开创性、批判性、实践性与实在性等四个基本维度。
一、革命性的哲学使命:笛卡尔理性观的开创性及其历史影响
理性主义从来就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继承并发展了西方古代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将理性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说道:“事实上,笛卡尔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哲学。”[3]3但是,与柏拉图将理性神秘化与形而上学化不同,笛卡尔主义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基础上。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浪潮之后,笛卡尔将人的自我意识提升到全新的层面,其关于科学理性的探索打开了聚焦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新局面。笛卡尔认为新哲学的使命在于:探寻任何比教条式理论更确定的哲学基础。他以“我思,故我在”(ego sum,ego existo)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个论断后来成了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之一。笛卡尔认为这是他所追寻的哲学第一原理,也是“知识的出发点”[4]。笛卡尔理性观保留了感知觉及感性认识的重要定位,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经验主义的必要而基本的作用。理性建立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理性也是贯通与提升人的认知能力的直接依托。在笛卡尔的原初语境中,理性与理智、智力、心灵、精神、思想构成了近义词系。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理性主义,它强调科学研究的严谨分析方法,以此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阶段。
康德如此评价笛卡尔:如果说德谟克利特是古代的第一位哲学家,那笛卡尔则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他们都改进了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5]23当人们将现代分析哲学的渊源追溯到黑格尔和康德之时,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说,笛卡尔的分析方法显然是现代分析运动的卓越先行者。在笛卡尔看来,分析“是指导的最好和最真方法,这是我在沉思中唯一运用的方法”。[6]156笛卡尔的分析方法可以用“穷其可能、纵览全貌、一丝不苟”来形容,他如此描述:“我们先逐步将复杂和模糊的命题还原为简单命题,然后,从所有最简单的直觉开始,尝试通过相同的步骤来追溯所有其它的知识。”[7]分析不仅展现在理论思考层面,在具体科学研究中也必须做到条分缕析、步步深入。“即使在物理学中也没有满足的理由,除非它们涉及到所谓的逻辑或分析的必要性。”[8]这种严谨分析态度衍生出了后来爱因斯坦所赞美的理性精神。
笛卡尔的分析理性对现代分析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现代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接受了笛卡尔关于物质(事物世界)和思想(观念世界)之间的区别;像笛卡尔一样,他认为有必要对观念论的怀疑主义做出回应,后者主张观念之外无物存在。[9]158弗雷格之后,英国的分析运动经由罗素—维特根斯坦—赖尔等人蓬勃发展起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高度赞扬了笛卡尔认识论及批判—怀疑方法论的开创性成就,并指出,笛卡尔认识论的破坏性比其建设性有着更突显的历史意义,其思想的两面性甚至“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10]。于维特根斯坦而言,其早期思想是分析运动的理论典范,其晚期理论则发生了后实证与后现代的激进变化,并由此对笛卡尔主义展开了严厉批判。这种批判也对后来的赖尔、普特南与罗蒂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赖尔在名著《心的概念》中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做了详尽批判,将其中机械之躯与理性之心的关系讽为“笛卡尔的神话”,即“把人当作一个神秘地隐藏在一架机器里的幽灵的看法”,以此反对心理主义以及早期行为主义的机械论取向。[11]但赖尔也婉转地暗示,尽管笛卡尔二元论及其心灵实体化思想是错误的,但他对心灵概念的定位却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也有利于并有待于认知科学更深入的研究探求。
在美国实用主义思潮中,皮尔士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批判原则,认为怀疑是探究之源。在皮尔士看来,单个人不能合理地期望达到我们所追寻的终极哲学,这只能通过哲学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philosophers)来实现。[12]实用主义的初始本意在于其词源“实践主义”。随之,詹姆斯进一步将实用主义思想推向前进。詹姆斯将情感理论追溯到笛卡尔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他关于人类心灵的理论观点也受到笛卡尔的全面影响。[9]200之后,奎因—乔姆斯基—普特南—罗蒂等人的理论谱系形成了新实用主义新进路。奎因的理性观是典型的新笛卡尔主义;在他看来,“逻辑,一如任一学科,旨在对真理的追求。所谓真理乃是确定性的陈述,真之追求则是努力将真陈述与假陈述辨别开来。”[13]乔姆斯基则将笛卡尔理性观扩展到现代分析运动的语言学核心领域。他指出,笛卡尔主义语言学的中心论调是:语法结构的普遍特征贯穿了所有的语言,并反映了心灵的基本属性。[14]至于普特南与罗蒂,他们更多地在后实证主义批判立场上提出了对笛卡尔主义的深刻反思。罗蒂认为,早期分析哲学运动总体上仍受制于新笛卡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束缚,而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为开拓者的后实证主义则掀起了后分析运动的狂飙,关于认识及其知识的表象主义“自然之镜”需要被打碎,取而代之的应是面向人的社会历史实践及其生活意义的人文主义教化。[15]
值得一提的是,笛卡尔作为法国哲学先驱,其思想对西方大陆哲学也产生了同样的重要影响。胡塞尔将自己的现象学先验哲学体系直接称为新笛卡尔主义,他说:“在过去的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那样对现象学的意义产生过如此有决定性的影响。现象学必须将他作为真正的始祖来予以尊重。”[3]1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基础上创立了存在主义学派,他的存在(Dasein)概念则直接渊源于笛卡尔的存在(Being)、自我(Ego)以及物自体(self-subsis⁃tence/per se)。后来,德里达在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中对后笛卡尔主义做了激进批判。另外,笛卡尔理性观也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其直觉主义产生了相当影响,后者又直接影响了詹姆斯和怀特海等人,并间接地促进了现象学运动的发展。甚至于,在数学领域,直觉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布劳维尔将直觉原则追溯到笛卡尔在十七世纪对解析几何(analytic geometry)的发明。[16]
二、时代性的科学方法:合理的怀疑与激进的批判性
威尔逊指出:“通过将知识的批判置于哲学探究的首要前沿,笛卡尔开辟了近代时代(the mod⁃ern era),这已经是哲学史的老生常谈。”[17]194在其广泛多样的理论体系中,笛卡尔始终视批判性为其重建哲学的核心使命。他的合理怀疑与大胆批判的精神鲜明地体现了科学方法的历史时代性。
首先,笛卡尔提出了“怀疑的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在笛卡尔哲学思想中,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对概念与信念的批判性分析。[18]在笛卡尔看来,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要保持怀疑的批判态度。一方面,怀疑一切:“在经验和思想的生活中是确实可靠的每一种东西,都要对其怀疑一番,从而进行方法上的批判。”[3]40怀疑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任何能引起哪怕一丝疑虑的东西都应被视为怀疑的可行理由。这种怀疑还必须是基于理性思维的怀疑,即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广义上说,笛卡尔怀疑方法的关键在于分析方法,其中又生发出演绎主义与还原主义的双重路径,前者以数学形式的演绎推理为认识手段,后者强调基于机械论原子主义的分析—综合研究程序。因而,“通过在方法上发现存有问题的事物,分析揭示了演绎推理的正确路径。……要是忽视了那些最微小的细节,结论的必然性就没有保障。”[6]460另一方面,怀疑一切的宗旨服务于问题的解决,通过依次彻查所有相关因素、排除无关因素、把握问题本质,进而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探究,获致认识的确定性与真理性。怀疑用于释疑,批判的出发点与目的都是建设性的。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期,笛卡尔基于理性分析的怀疑原则与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可谓相辅相成,并对后者做了重大补足。
其次,笛卡尔在相当程度上反对经院神学的精神禁锢及其客观唯心主义实质。尽管其形而上学观包含了上帝创世论的基础成分,并且在得知伽利略遭受宗教审判打击之后他被迫采取了妥协式的暗度陈仓策略,但笛卡尔通过对人的心灵的客观认知定位及其理性与人性的致力宣扬,开创了主体性哲学的全新体系,将源自柏拉图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发展到新的历史形态。在将神性不断转换为理性的形而上学自然化进程中,笛卡尔不但促进了太阳中心说的社会影响,更通过自然哲学理论维护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也为牛顿力学体系的深广社会化铺垫了历史伏笔。
再次,笛卡尔对传统的哲学及科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封闭性阻滞了人们的认识,经院神学囿于上帝的创世论依据也忽视了上帝所赋予自然和人类的神圣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通过对传统、权威与宗教信条的基于科学理性的斗胆质疑,笛卡尔以科学的观察和逻辑的证明进一步宣传了新物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从各个方面对传统物理学理论发起了激烈批驳。笛卡尔沉思的最终目的在于:“六个沉思旨在发现摧毁亚里斯多德原理的物理学基础”[19]。
最后,笛卡尔的自我批判精神也直接面向科学实践。在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他勇于怀疑、甚至不惜放弃先前不成熟的观点。在早期思想中,笛卡尔重视研究对象的形式属性,煞费苦心地用各种量化或图形解释的方式来描述研究问题,甚至认为物理学也无非就是几何学;但随着观察与实验的深入,尤其是其机械力学、气象学、生理学等研究领域的拓展,他开始认识到经验与实践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决定放弃只有抽象的几何。……而这个中缘由在于,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创设一门不同类型的几何学,后者关联于自然现象的解释。”[20]这种自我批判性体现了其理论体系自身的演进步阶,更承载着笛卡尔作为哲人—科学家的实践精神。如王太庆先生所言,“笛卡尔是机械唯物论的创始人,但他不仅有创立它的功绩,也有舍弃它的勋劳。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只知作茧自缚,而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自强不息,在机械论碰了钉子的时候开动脑筋另辟途径,向辩证法靠拢。他在数学上的伟大发明解析几何,就是其中光辉的一例。”[21]
也许,笛卡尔批判性的破坏力度远大于其建设性的功劳,其机械论的决定论立场也内在地抑制了或自反于其批判性的本质;但是,对于确定性基础的不屈诉求始终构成其哲学研究事业的核心目标。二十世纪哲学中,弗雷格、罗素、胡塞尔、杜威以及维特根斯坦等大哲们对于确定性问题的探究拓展了这种生生不息的研究理路。笛卡尔思想的批判性引致了哲学旧体系的崩溃,也揭开了新体系的诞生。诚如胡塞尔所言:“现代性始于笛卡儿,因为他率先追求从理论上满足不容置疑的真理,将之置于怀疑的论据基础上。他第一个使其理论成为关于世界的普遍领域,一个预设了激进怀疑的否定性领域,并将之作为辩护的支撑,即其本身之确切认识的主体性。”[22]
三、理性的实践基础:观察实验与科学知识的实践性
笛卡尔认为理性能弥补和超越经验的内在局限性,这种理性建立在大胆怀疑、严谨分析与精确论证的方法基础上,同时也具有经验认识中观察实验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着内在的关联,一如身体与心智的有机结合促成了健全的理性。人们掌握的知识越多,经验就变得越发必要,在其研究中,“我用的都是数学的和有证据的推理,我的所有结论都由真的观察资料所确证”[23]。因而,实践性构成了笛卡尔理性观的基本特质,其中包含了他对于经验、观察实验与功利实用性等几方面的观点。
首先,在经验重要性之外,笛卡尔突出了观察与实验对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的重要性。笛卡尔不但创立了解析几何,也是折射光学与气象学的先驱。作为科学家的笛卡尔在其具体科学研究中采取了亲力亲为的观察与实验方法。他在摆动力学原理的分析中指出,空气阻力取决于其冷热、干湿、清浊以及很多其它因素,最终的摆动阻力值还因材质(铅或铁或木头)、形体(方或圆或其他形状)和其他众多因素而变化。他的光学研究除了涉及到折光原理与棱镜制作,还详细描述了眼睛、光线、视线以及属于反射光学和普通光学的所有情形。为了解释血液运动及心脏的生理功能,他反复解剖与观察各种动物的器官结构及其功能。可以说,笛卡尔秉持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精神,将科学知识建立于观察实验基础上,也将其自然哲学依托于不断发展的实验哲学。“这位法国哲学的创立者,虽在原则上,为一唯理论者,精神论者,但在实际上,却近于经验论者与唯物论。”[24]这看起来似乎很迷惑:笛卡尔既是一个认为知识来自于理智的理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视实验和观察为知识事业本质的实验主义者。这种哲学困境的相融性恰恰在于,经验诉求乃是建构演绎科学方法的本质部分。[25]234
其次,笛卡尔自觉地面对理论现状的既有问题与发展困境,将实践性置于与批判性等同的地位。笛卡尔研究的终极理想在于:反对思辨哲学、发现实践哲学,获取对人生有益的知识,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为此,笛卡尔反对套话连篇的经院逻辑,强调逻辑技能的训练及其与数学演算的结合,指出逻辑能使人正确地运用理性去发现真理。笛卡尔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与知识的效用性,但他并非处于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一方面,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笛卡尔的怀疑法与分析法都旨在建构有确实真理性、并切合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理论体系。一如康德之言:“在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实用性方面,是笛卡尔开创了这条路径。”[5]264另一方面,笛卡尔不是终结了哲学,而是寄望将本体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就需要有坚实的实验观察基础。在对古典逻辑以及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笛卡尔将其方法与理论的创新使用建立于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在笛卡尔哲学思想的语境下,哲学并非一门指导性的课程,而是一种具体的活动;相应地,除了通过深入浸润于哲学的实践活动,别无其他捷径。笛卡尔认为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基于人类的实际利益;在知识之树的分类描述中,他将道德科学树立为智慧的最终层次,科学之真归依于道德之美。以笛卡尔看来,人们必须用经验和理性来分辨善恶、认清好坏,理性为人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四、实践性的理论框架:笛卡尔的科学实在论取向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这种两极竞合困境鲜明地体现于“科学大战”中。作为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开拓者,笛卡尔理性观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总体立场上蕴含着科学实在论的浓郁取向。“无论如何可以说,笛卡尔对实在论的承诺及其包括实在论的物理科学所提供的物质概念的世界绝对概念,对他来说是根本的。”[26]笛卡尔认为,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实在性,即可依据不同的范畴标准将实在性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特色类别:物质的自我本体、感觉与心理活动的神经生理学构造、心灵的先验实体性、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等,这些都是客观实在。还存在着不同等级的实在性,如本体客观实在性与偶性的实在性、形式实在性与实质实在性,等等。
笛卡尔思想的实践性基于实在论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作为近代科学革命的急先锋,笛卡尔认为世界的客观性在经验层面终究是科学知识的直接来源。于他而言,“理性(ratiocinantis)有着实在的基础——因为没有了基础,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思想”[27]。因而,“思想”的概念包含了感知觉及其生理活动的不可缺外延成分。另一方面,在认识论总框架中,理性的确定性超越了经验的局限性。诚然,在笛卡尔看来,知识的追求在于自然之光的显现与累积,这导致了客观唯心论立场。德里达就此批判道:“为了规避不断烦扰自己的逻辑循环,笛卡尔自始至终将理性之链内嵌在自然之光的框架中,后者却源于并归于上帝。”[28]
笛卡尔可谓是科学实在论的近代先驱。“无疑,笛卡尔在关涉(传统怀疑论的)确定性问题本身之同时,也将之拓展到对反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宣扬,后者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17]7诚然,这种科学实在论立场呈现在笛卡尔的系列科学理论中,带有明显的机械论与决定论特征。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笛卡尔的科学实在取向慢慢蜕化为“形而上学”的实在性。由于对观念与理性矫枉过正式的极力强调,笛卡尔背负着唯心主义者的骂名,但他却秉持了科学实在论的唯物主义底线,他认为,观念从来没有在理智之外,所谓的“客观存在”意味着以客体总是在场的方式的理智存在。因此,布莱克恩为此鸣不平:“我不认为笛卡尔陷入了唯心主义阵营,因为在我看来,他所辩护的数学领域于他而言就是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实体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思考或认识,这种实体既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虚构的。”[29]
当然,在对待经验与理性、观念与实在等二元范畴时,笛卡尔受制于当时代宗教神学、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但是他在哲学的总体性及关键理论取向上却建立了科学理性主义实在论的开拓性成就。事实上,笛卡尔的具体科学理论中满含着实在性的基本特征。比如,感知觉、意志与情感活动等都是作为身体构造的物质功能的运动表象。虽然身心二元论包含了松果腺的机械论解释以及上帝创世论的客观唯心主义窠臼,笛卡尔也尽可能地在身—心联合体机制中作出了当时最具科学说服力的合理性审视。作为解析几何的创建者,笛卡尔的逻辑与数学思想也是科学实在论取向的。在广泛的自然哲学研究领域,笛卡尔总是将数学形式化方法运用到对各种研究对象的结构分析与自然运动的精确说明。在他看来,几何学只是关于可靠形式化及精确量化的科学体系,“数”的本质在于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因而,逻辑理性有着另外一层更精微的涵义:人类是理性动物,哪怕作为上帝的子民及其所具备的先天神圣禀赋,其本质归于实在的思维范型。笛卡尔更直接的表述则是:纯数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属性实在性”。[6]80胡塞尔就此将笛卡尔视为“贯穿整个近代哲学之心理主义的始祖”,并奉之为“超验实在论之父”。
结语
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体系所展示的开创性、批判性、实践性与实在性等基本特征都表明了其理论立场的实践化特征。他不仅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行者,也是近代实践哲学的开拓者。在笛卡尔关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经验与理性的矛盾之后,康德将问题提升到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以及判断力的更复杂综合高度,黑格尔则构建起宏大的历史理性辩证法体系。一直到马克思,理论与历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才得以真正的合理解决。显然,笛卡尔以理性主义旗帜引领了实践哲学的发展,因此开创了西方自然哲学的实践化浪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于人类理智的演进步阶与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本质而言,笛卡尔无疑是逻辑理性现代化与实践化的双重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