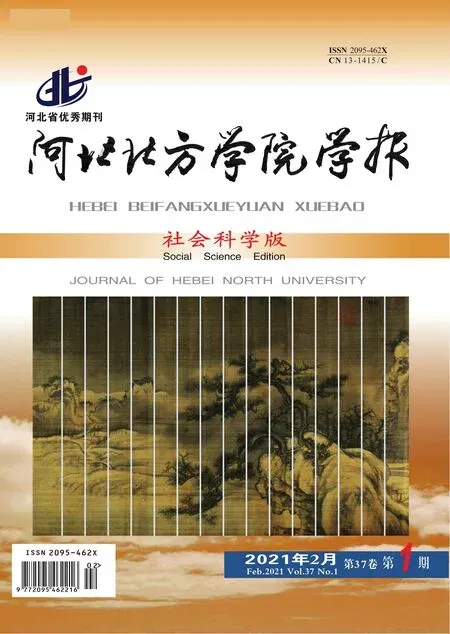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孙 阳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开展对日外交,谋求和平解决两国争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事专职外交活动,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谈判,积极寻求国际支援,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鉴于王宠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学者对他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他的宪政和法学思想方面,对其的外交思想与活动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全面考察。
一、王宠惠对日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所处时代密切相关。整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中西教育的积淀
王宠惠生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其父王煜初不仅让他接受西方教育,还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1887年,王宠惠进入圣保罗书院,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891年,王宠惠从圣保罗书院毕业后,到香港皇仁书院继续求学,学习西方文化。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来港招生,王宠惠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该校采用西方办学模式,教师以外教为主,教材与授课全用外语,对学生要求极高。在这里王宠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英文、几何、天文、物理和法律等课程,还要学习中国的汉文等课程。4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两年后,在留日风潮影响下,王宠惠进入日本高校钻研法学,在日学习1年后又留学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王宠惠又到欧洲继续深造,先后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国际公法,并在法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除西方教育外,王宠惠还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王宠惠年少时师从周松石学习国学,他不仅阅读《三字经》和《百家姓》等基础读物,还学习《论语》和《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在此过程中,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小便树立了报效祖国和挽救民族之志。多年的中西结合式教育不仅使他掌握多国语言和通晓政治法律知识,还使他坚定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立场,这为他对日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
孙中山与日本渊源深厚,对日本有独特感情,并将日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日两国关系有独特看法。在中国民主革命早期,孙中山主张中日两国相互合作,和平共处,当时他认为两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曾说过:“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存亡安危之两相关连者,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1]此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孙中山逐渐认清了日本想要彻底灭亡中国的野心,他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他对民族主义重新解释,明确主张“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2],鲜明地提出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孙中山还在遗嘱中提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3]王宠惠从6岁起就开始接受孙中山的教诲,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服膺于他的三民主义,受他影响颇深。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挽救国家民族之道被王宠惠吸收继承,并成为他日后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所言:“回忆宠惠自识总理至于其殁,垂三十年,当革命进行之始,事机危难之秋,均获追随,亲受指导,其后虽或合或离,而秉乎总理之教,行乎总理之所安,则精神所寄,盖始终如在其左右云,爰述亲所闻见,著于简端,不敢忘。”[4]
(三)国内局势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强盛后,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引下,日本一步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问题,愈趋严重,而民族之斗争,愈趋激烈,乃至敌军深入内地,迫近长江流域,谁为为之,孰为致之”[5]359。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吞并我民族,奴化我民族,消灭我民族,以实现独霸东亚之迷梦,再进而企图颠覆一切强有力国家,独自生存,以实现其统一世界之迷梦”[5]529。日本不断侵华,不仅使中华民族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促使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还严重破坏了国际和平,给世界各国都将带来巨大灾难。对此,王宠惠指出:“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人民即曾告世界,依据和平不可分割之原则,远东之和平不保,即世界安宁无日。”[5]399因此,中日战争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还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5]535。在此紧张局势影响下,王宠惠认为,不论以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为立足点,还是以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为目的,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并开展对日外交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正如他所言:“自‘九一八’以来,我国的整个国策,可以说是应付日本,我国的外交,也是以日本为中心。抗战发动以后,对日的交涉虽然停止了,但是过去一年我们的一切外交活动,仍然是对付日本,而且是更加紧的对付日本。”[5]354
二、王宠惠对日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通过政治协商和平解决中日争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规定,即“国家之领土与主权,必须保其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基础。在此原则下,循和平路线,力谋友谊之增进。凡政治的协调,经济的合作,必本两利之原则,以求相互关系之日趋于密切”[5]334。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在遵循此政策的基础上,王宠惠对日“始终是采用和平方法,寻求两国邦交的调整”[5]354。他认为,“为两国百年大计计,应谋永久亲善之道;但若不将两国间亲善之障碍,一举除去,对于亲善当然谈不到。中日一旦失和,于中国固不利,于日本亦未见有利”[5]332。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上海虹桥事件发生后,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形势变化,王宠惠仍然宣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5]354他坚持以政治解决为主的有限度的和平方针,希望“以外交途径及国际公法所允许之任何和平方法,解决纠纷”[5]354。对“七七事变”他明确表示:“我方本无扩大事态之意,仍愿用和平方法,得一解决。”[5]343针对虹桥机场事件他也表示:“我方始终主张,在和平绝望前之最后一秒钟,仍望能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吾人应认清,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将两国之地理上相邻之地位变更,故两国间一切纠纷,为将来着想,为两国民众永久福利计,总以和平解决为最善。”[5]346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国际合作
对于中国政府的和平倡议,日本帝国主义置之不理,仍不断扩大侵略事态。鉴于和平无望,王宠惠开始调整对日策略,采取“多求友,少树敌的外交方针。即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援助我国,抵抗日本”[5]383。关于实行这个方针的原因,王宠惠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首先,中国的力量太弱。他认为:“如果国际方面不予中国之援助,不予以日本制裁,则中国人民所受之痛苦,目前尚无法解除。因以中国一国之力量打倒日本,短时间内当难收效。”[6]其次,他认为中国抗战与国际局势密切相关,对各国都有影响。对于中国抗战具体的实行方法,王宠惠主张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集团制裁之推动。依据盟约,促请国联,利用集体力量,对日实施制裁。二是各国个别援助之推动。基于道义关系,促请世界各国分别予我援助,以增强抗战力量。”[5]445此外,王宠惠强调中国抗战绝对不能完全依赖外援,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抗战。他说道:“自力更生云者,只能为不倚赖外援之解释,并非拒绝外援之谓。国际间之同情与援助足以时吾人感奋,但决不可以稍存倚赖。我们惟有凭者公理正义与各邦共同努力。吾人必求其在我,尽其在我,然后外援可期。且唯有如此,才能发挥抗战之最大效能并获得最后胜利之果实。”[5]402
(三)依靠国民抗战到底
王宠惠争取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努力彻底失败后,他根据战争形势,提出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方针。他表示:“吾人抵抗日本侵略之坚强决心,始终不渝,非至日本军阀偿赎其破坏东亚和平与秩序之罪恶,吾人决不停止抗战,战争时期如何延长非所计也。”[5]380他充分认识到,中国要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全民动员,国民伟大之力量,集中于一点发挥,尤易收事半功倍之效”[5]551。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国民力量抗战,王宠惠提出了诸多方法。首先,要团结一致。他主张:“我们在抗战时期当中,最当注意的是莫过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我们大家要将全国的力量——人力、财力、物力等都用在抵抗日本的侵略。”[5]527其次,充分发挥革命精神。王宠惠认为充分发挥民众的革命精神对于抗战的胜利至关重要。他经常向国民呼吁:“要坚强团结,巩固统一,充分发挥三民主义之大无畏精神,来与我们唯一的敌人日寇军阀相搏斗,来争取我们光辉的最后胜利!”[5]535最后,进行自我检讨。王宠惠认为:“凡属国民,即应一致紧密团结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振作精神,通力合作,发挥我民族之全力,为抗战建国而尽其应尽之职责,不可稍存私见,自招毁灭。”[5]553
三、王宠惠对日外交思想的具体实践
王宠惠将其对日外交思想积极付诸实践,对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重大影响。
(一)访问日本谋求两国关系和平发展
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遭到西方国家强烈谴责,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1935年,广田弘毅上台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对外宣布“不侵略,不威胁,对华主善邻,谋与中国接近”[7]。在这种形势下,王宠惠于同年2月19日至3月5日对日本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关于此行的目的,王宠惠表示:“趁此次来日之机会,将中国方面之心理传达于日本朝野之人士,同时将日本方面之意传达中国,藉以增进两国之友谊而已。”[8]在日期间,王宠惠充分运用他的外交才能,就中日关系和平发展问题同日本军政界实权人物进行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最重要的是2月26日同广田弘毅的第二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王宠惠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的3条原则,即“第一点,中日两国关系始终应通过和平方法(或和平手段)加以处理。第二点,两国外交关系的调整应基于两国相互平等的立场。第三点,两国应在友好和睦的目标下进行交往,做到互助互让”[5]187-188。对于这3点原则,广田弘毅只赞同前两点,对第三点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这次会谈结束后,王宠惠向广田弘毅表达了离日之意,并在正式离日前对外声明:“余窃愿对于寻常外交之恢复,有所贡献,余尝为中日之关系,仅能以和平之方法,外交之途径,以平等和平之基础解决之……中日如恢复寻常关系,必能获得和洽,而使东亚和平稳固,以至永远。”[9]138
(二)交涉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宠惠立即表示:“请即派员向日本大使馆口头严重抗议,并劝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免事变扩大。”[10]263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日本表示:“日本无意扩大,并允将我方制止军事行动要求,立即电知驻屯军转洽,再嗣后情形若何,仍请随时详细电示为荷。”[10]2477月10日,王宠惠趁日本驻华大使日高访问中国外交部之机再次表示:“本部已电告冀察当局,并派专员前往接洽,冀获步趋一致,免致因应分歧”[10]249,希望日本政府同中国外交部直接交涉。7月10日下午6时,日军不顾和平协议,再次挑起军事冲突。对日军的违约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为了尽快解决事变,7月12日,王宠惠与日本驻华公使日高进行会谈,提出两种解决之法:“一是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二是双方立即停止调兵。”[10]267对此,日高坚称“北平中日双方军事当局间,已成立一种谅解,如照部长之意进行,反将使事态恶化”[10]268。王宠惠坚决反对日高的提议,并指出:“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方为有效。”[10]271此次会谈以失败告终,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此后,日本不断向中国华北增兵扩大事端,面对日军挑衅,王宠惠决定为和平解决问题作最后努力。7月20日,他发表声明:“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10]273面对中国政府最后的和平倡议,日本帝国主义仍置之不理,不断扩大侵略,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10]259
(三)积极寻求国际援助
日本侵华对欧美各国在远东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他们也“深悉非援助中国,裁制强暴,无以维世界之和平,谋人类之福利”[8]363。基于这种认识,西方各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王宠惠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涉,争取国际援助。第一是争取苏联援助。他认为中国与苏联国境毗邻,为最亲密的友邦,两国主持正义反对侵略的政策也应一致。基于此,苏联成为他的重要争取对象。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王宠惠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加快对苏谈判。经过协商,双方于1937年8月21日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规定: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他方不得对该侵略国予以任何援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国之举措。即在中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于日本,不予以任何援助。第二是争取欧美各国援助。欧美各国也是王宠惠的重要争取对象。1937年10月,他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呼吁:“第一请避免任何行动促使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受益,第二请发动全力,对于中国此次生死关头之奋斗,予以赞助,果能如此行动,则君等对于贵国传统的正义和平之国际政策所负之道义上责任,庶亦可以无憾矣。”[5]3521939年6月29日,他又通过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向欧美国家作《日本政策与列强在华利益之将来》的演讲以寻求援助,他表示日本的侵华必然会损害各国在华利益,呼吁各国“对于中国之援助,可以用各种不同之方法”[11]。
四、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评析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职业外交官,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具有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性。但受阶级出身和党派立场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局限性。
(一)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的进步性
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特色鲜明,具有很大进步性。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外交涉的原则之一为“国家之领土与主权,必须保其完整”[5]334。1937年3月,王宠惠就任外交部长时宣布严格遵循此原则,他说道:“本人此次奉命出掌外交,深感责任重大,自当一秉新旨意,依国际正义,循外交常轨,努力进行。”[5]334在此后的对日交涉中,王宠惠始终以此原则为中心,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接受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提出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4项议和条件。对于这些条件,王宠惠坚决拒绝并表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接受。”[5]3561938年12月,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后,前首相近卫文提出“东亚新秩序”之说,王宠惠坚决揭露该口号侵犯中国主权利益的本质。
2.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之分
王宠惠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受党派利益和阶级立场影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一定敌视情绪。1936年10月23日,王宠惠在与日本驻华武官代表喜多诚一会谈时,就中日关系表示:“我个人意见,如欲调整中日关系,应从根本调整,果能如此,不独可以共同防共,即军事同盟,亦有可能”[5]332,这鲜明地反映了他反共防共的立场。但中日关系和平调整失败后,王宠惠放眼国际,希望寻求国际合作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他说道:“在抗战期间,寻求友国,是我们外交上重要目的之一。其国家与我利害相同的,当与之为友。”[5]355而“苏联和我国国境毗邻,其爱好和平与反对侵略的原因,亦多与我一致”[5]355。基于此,苏联自然而然成为他争取的重要对象之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宠惠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党派偏见和意识形态分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实属难能可贵。
(二)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的局限性
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仍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性。
1.过度强调和平解决,对日妥协退让
对于中日争端,蒋介石主张通过政治方法和平解决。王宠惠十分赞同该方针,并在对日外交中付诸实施。所谓和平解决,王宠惠强调其是有限度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超越了这种和平限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经过交涉一致同意暂停所有军事行动,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争端。但日本帝国主义违背约定,不断挑起冲突。面对这种情况,王宠惠指示中国外交部对日违约行为发表声明,称:“举凡中日间一切悬案,均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250能够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固然是第一选择,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灭亡中国,同意和平谈判只是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对此,王宠惠有着清晰认识,但面对日本的多次违约行为,他仍然强调和平解决,这充分反映了他对日妥协退让的一面。
2.过分夸大美国作用,对其抱有幻想
王宠惠受多年留美经历以及阶级出身的影响,对美国具有一种强烈的信任感,他片面地认为美国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国家,对华“以维持中国独立与主权,领土完整,为其一贯之外交方针”[5]463。这种错误认识使王宠惠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和其对外交往的利益实质,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后,王宠惠强调美国此举是为了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正义,并一度认为“美国对于远东及世界其他部分之和平,均能实施其决定性的威权”[5]376。对此,王宠惠还表示:“美国素以富于正义观感著称,中国对于美国人民,尤素富有坚决不摇之信仰。”[5]376对于美国的这些行为,王宠惠只看到了表面,错误地认为美国是致力于帮助中国和维护国际和平的,过分夸大了美国对国际和平的作用。
综上,民国时期王宠惠两次出任外交总长,其一生与外交工作密不可分。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对日外交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他将自己所学与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相结合,逐渐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对日外交思想,积极开展对日外交。王宠惠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止日本侵略,但同时他的外交思想也存在对日过度妥协和过分夸大美国作用等不足之处。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名职业外交官,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促进中国外交近代化、树立中国正面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以及争取抗战胜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