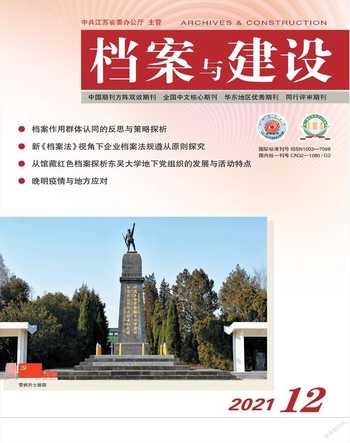档案作用群体认同的反思与策略探析
周林兴 章煜
摘 要:档案对于群体认同作用的研究已成为档案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认为档案应该从正向建构与强化群体认同、以集体记忆载体形式作用于群体认同等,但在研究中也忽略了档案强化群体认同可能带来的挤压选择空间、割裂各式认同等负面影响以及淡化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与认同效力的整体性。文章针对群体认同问题,认为档案学研究应该拓展研究视角,更加关注档案作用群体身份的消解、群体权利的确立、群体情感的凝聚、群体认同的效力等,提出要尊重群体意愿,维护成员“被遗忘权”;适当让渡职能,鼓励成员参与叙事;分享共同记忆,激发成员思想共鸣等实践策略。
关键词:群体认同;档案学研究;社会记忆;权利
分类号:G270
Reflection and Strategies Research on Archives in the Field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Zhou Linxing, Zhang Yu
(Department of Library,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Abstract:The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archives on group identity has become a hot area in archives academic circles. It is believed that archives should construct and strengthen group identity in a positive way, and act on group identity in the form of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s. However, archives are unintentionally ignored in some studies. Strengthening group identity may bring about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squeezing the choice space and fragmenting various identities, as well as dilu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archives affect group identity and the integrity of identity effectiveness.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group identity, archives researches should expand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archives, the elimina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group rights, the cohesion of group emo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identity, etc. The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group and maintain members’ right to be forgotten; appropriately transfer functions and encourage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narration; share common memories and stimulate empathy.
Key words:Group Identity; Archival Research; Social Memory; Right
伴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流动日趋便利与频繁。以血缘、地域、肤色等为纽带形成的群体认同逐渐松动,新型群体在不断碰撞与融合中孕育而生。同以往群体关系的疏远以及对未来群体身份的茫然加剧了个体不安全感,群体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档案学界基于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独特价值,对档案运用于群体认同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分析与思考现有档案与群体认同研究的基础上,在理论层面研究档案是否应作用于群体认同,在实践层面探究档案应如何作用于群体认同,为档案与群体认同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思路。
1 文献回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档案与群体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1 正向建构与强化群体认同
在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归纳的档案四个范式的引导下,档案工作者被认为应作为自觉的中介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1]档案学界受此影响,形成了群体认同是一种积极因素的思维定式,多从档案何以作用于群体认同[2][3]、档案以何作用于群体认同[4][5]、群体认同视域下档案资源开发[6-8]等正向视角思考档案在强化群体认同过程中的功能。
1.2 以集体记忆载体形式作用于群体认同
现有文献在分析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问题时,多从集体记忆视角着手。在理论层面,以“档案(工作)具有社会记忆建构性资源和建构性行为的双重属性”[9]为基点,阐述档案、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天然相连”且“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10]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提出“档案-记忆-认同”(AMI)模型”。[11]在实践层面,现有研究通过对各类型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路径的介绍与研究,阐述构筑集体记忆从而凝聚群体认同的多种方式。[12-14]
1.3 针对特定群体认同施加影响
现有档案与群体认同的研究在研究层次上着重于档案对特定群体认同的作用与影响,[15]主要集中于家庭档案[16-18]、档案专业及档案工作人员身份认同[19-21]、农民工身份认同[22][23]三方面。其大多在聚焦于某一特定类型群体的前提下,通过问卷调查、理论运用等方式,对选定群体现有认同状况进行分析。并结合群体特点,阐述档案在促进群体认同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提出针对特定群体开展档案工作的愿景与展望。
2 群体认同领域档案学研究实然分析
2.1 忽略档案强化群体认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档案学将群体认同天然视为积极因子,从正面视角建构档案赋能于群体认同机制的做法。这种研究思路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研究视角受限,分析相对片面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群体认同并非始终处于正面地位,发挥正向作用。一味加强群体认同,也可能凸显其负面影响。
(1)挤压选择空间
档案作为建构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体现了社会主流阶层的意志。“在后现代语境中,档案虽不是权力的化身,但却一直存在权力的隐喻。”[24]当权者借助档案及其所记载的信息,塑造乃至固化特定群体形象,将其符号化、使其具有象征性,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此种情况在阶层划分不合理的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印度为例,尽管贱民阶层已从法律上被废止,但种姓制度仍然困扰着该群体,个人与家庭的记录始终如影随形,向社会宣告着他们曾经的身份,阻止着这个迫切希望抛弃过去屈辱身份的群体融入更广大的社会之中。[25]档案变成了种姓制度与种姓成见的“代言人”,成为在实质上维持不公正秩序的工具。在此种情况下令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有可能催生双重困局的出现,即寻求改变者步履蹒跚,难以有效融入社会;安于现状者无动于衷,沦落为“快乐的奴隶”。档案为保证多样性而具体化身份,从而为档案对群体认同施加影响创造空间,可能会导致文化差异不可改变,消除个体、个性和群体内的选择。[26]
(2)割裂各式认同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7]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多种群体身份的集合体,部分身份之间甚至暗含矛盾。档案对特定群体意识的强化,有可能导致个体内部各式群体意识之间隐藏的对立关系激化,使其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之中。以美国犹太历史学会的建立为例,美国犹太历史学会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升和改善美国犹太人的形象。为此,学会成员通过搜集并出版各类有利于展现美国犹太人爱国虔诚、勤奋努力形象的档案资源,档案逐步成为美国犹太人身份建立的支柱,赋予其“美国人”的身份以合法性与真实性。[28]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美国犹太人认为需要强化自身作为美国人身份的理念之上,但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彻底激化了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信仰与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犹太学会的成员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通过历史学会整理出版档案以增强美国犹太人国家认同尝试的彻底失败,这代表着在危急时刻,对犹太教以及其余犹太人的忠诚会跨越国界而被优先考虑。但对有可能重建故国的诱惑,学会成员又难以完全舍弃。可见,受制于群体认同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档案对于特定群体认同的强化,有可能割裂个体的自我认知,使其丧失归属感与认同感。
2.2 淡化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
档案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记载内容具有丰富性,对其所蕴含的价值可从不同视角加以解读。现有档案学研究多从集体记忆承载物的角度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感的形式,探讨档案信息所蕴含的集体记忆对构建与强化群体认同感的意义所在。这种相对单一的研究视角,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限制研究意义
借助“集体记忆”这一媒介,探究“档案—集体记忆—群体认同”之间的运作模式,其理论依据在于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之间所具有的天然联系。集体记忆是支撑群体认同的力量源泉,而档案记录又是存储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从集体记忆维度分析档案对群体认同的影响方式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但单纯从集体记忆角度切入,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表现形式,势必需要考虑集体记忆对于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集体记忆的构筑与完善以作用于群体认同,进而使逻辑终点滑向群体认同的强化,引发研究思路的固化。同时,这种思维定式也可能导致档案在群体认同领域研究价值的单一化,难以反映档案自身功能及其作用于群体认同方式的多样性。事实上,档案不仅表现为集体记忆的承载物,也可从争取权利的工具和表达情感的渠道等层面探讨档案与群体认同之间的联系。
(2)冲击个性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群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群体认同的强化,共性的凝聚,有可能会对成员个性造成冲击,使个体“孤立、不安全感的增加,以致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命的意义产生疑虑,并因此加深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无力感与无足轻重感”。[29]具体到档案层面,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群体内部成员主动舍弃个性。在主流叙事框架的制约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为有效融入特定群体,借助档案等媒介主动抹去自身与既定群体要求不相符的特征。以期通过选择性记录的方式掩盖原有部分个性,得到群体认可,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30]此种现象在从小就在城市生活长大,有更强烈的“城市梦”,却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难以获得法定市民身份的“农二代”身上表現得尤为突出。[31]二是群体内部成员被动丧失个性。档案体现着权力的博弈,其形成包含着对信息的识别与选择。在此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自然有更多机会得到记录和描述,其内部差异与细节也更有可能得以展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其个体成员情况多被草草带过,“他者或个体差异被粗暴地排斥了。”[32]我国古代“官档多,民档少”正是对此类现象的直接反映。
2.3 忽视档案影响群体认同效力的整体性
人具有社会性,在多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下呈现出群体身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非受单一群体意识影响,这一特性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推动下体现得尤为明显。单纯研究档案对于特定群体认同感构建的影响,忽视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整体性,存在一定问题。
(1)缩小研究范围
档案学界在具体探讨档案对群体认同所起作用时,习惯于从特定职业、身份(如农民工、档案工作者)等角度切入,通过调研问卷、数据搜集等方式,對特定群体的认同感现状加以解读,并结合档案在群体认同领域所具有的价值,提出相应策略与建议。这种研究模式在论述群体认同现状时更为具体形象,易就特定群体成员认同感提出档案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但缺乏同一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和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对比与联系,可能导致研究范围的窄化。在人口交流迁移日益频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日渐没落的社会大背景下,群体关系加速演变,愈发复杂多样。单从某一角度研究档案对群体认同影响效力,难以揭示群体认同形成及变化的实质与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普遍性规律,有可能妨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利于更具科学性、有效性研究结论的提出。
(2)加剧群体对立
当今社会环境下,旧有群体认同发生松动衰退,而新型群体认同尚未完全确立。新旧交替所产生的空白易引起群体对未知的恐惧,为不同群体之间歧视与对立的滋生提供温床。对彼此认知的匮乏导致群体之间产生隔阂,并逐步演化为对立甚至敌视关系。具体到档案层面,从特定群体视角切入研究认同问题,受研究思路缺乏整体性的影响,可能出现同一举措由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表现为相反效力的情况。以农民工档案为例,创建农民工档案的举措就农民工这一群体层面进行分析,可起到保障农民工群体在子女教育、医疗设施等方面的权益,体现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进而增进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和自信心的作用。但将农民工群体置于其所生活的城市社会进行考量时,建档过程中对农民工身份的强化和凸显可能导致对该群体歧视的加剧,使档案工作的同一举措在不同维度下呈现出相反的效果。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以整体性与联系性思维看待群体认同问题,在立足于农民工这一身份特征以实现建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同时,兼顾推动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进程。
3 群体认同领域档案学研究应然选择
针对现有群体认同领域档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档案学界可适当拓展研究范围,从以下角度探讨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可能性。
3.1 转向思考档案作用群体身份的消解
考虑到正向运用档案强化群体认同感可能导致的问题,档案学研究者可转变研究思路,反向探讨档案作用于解构群体身份的可行性。
一方面,档案作用于群体成员身份消解与重塑具有现实需要。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群体对待过去可能持有不同态度。部分群体“除了偶尔一两个诗人、圣徒或传奇英雄,他们的过去一无所有,仅有屈辱。他们的屈辱同他们的起源相连。”[33]此类群体渴望抹去过去,通过既有身份的消解获取新的身份认同感,这亦与现代社会身份更具流动性与多元性的特征相适应。
另一方面,档案作用于群体成员身份消解与重塑具有实际可能。记忆与遗忘相伴相生,一体两面。受记录方式、记录篇幅等因素限制,档案无法穷尽社会记忆。故档案在作为部分集体记忆承载物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使部分集体记忆被边缘化或沉默化,这就为档案工作者参与身份的消解与重塑创造了条件。[34]档案工作者通过对档案的鉴定与销毁等方式,可有效作用于档案及其所记载集体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3.2 转向思考档案作用群体权利的确立
档案学界应意识到档案在争取群体权利,提升社会地位方面不可替代的功效,从争取与确认权利角度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可能性。
一方面,群体可通过档案证实其权利的来源及其合法性,发挥档案对其群体身份的支撑作用。档案独特的原始记录性,赋予了其在争取权利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当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受到其余信息记录载体挑战时,档案可凭借其确定性与真实性而技高一筹,更具说服力。[35]群体成员在为本群体发声呼吁、争取支持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不同声音的质疑。此时,群体成员可依托所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源,有力证明群体身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赢得社会舆论支持。
另一方面,群体对外可通过搜集档案与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相联结,[36]提升其公众形象。对内可通过档案展现群体特色,以凝聚群体意识,重塑群体信心。[37]以英国黑人文化档案馆为例,长久以来,由于英国官方缺乏有关黑人群体的真实历史记录,英国黑人群体难以全面了解群体过往,有力证明群体贡献。为改变此种局面,黑人文化档案馆在一些民间学者和活动家的组织下建立。档案馆在收集与保存反映生活在英国的非洲裔和非洲—加勒比裔历史文化档案的基础上,通过主题展览、媒介互动等形式,展现了黑人群体对于英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改善了该群体的公众形象,增强了群体成员对本群体的凝聚力和自豪感。[38]
3.3 转向思考档案作用群体情感的凝聚
档案学界应注重档案在唤醒群体意识,引导社会氛围方面的突出作用,从影响与凝聚情感角度思考档案作用于群体认同的可行性。
一方面,群体认同感作为情感的一种“高级形态”,其强烈与否和情感被有效营造与激发的程度直接相关。档案作为原始记录事实性经验,[39]是公信力的象征。档案所记载内容可有效还原历史情境,触动乃至建构受众情感。档案作为信息载体,其记录的内容包含档案形成者的自身情感,可通过激发受众思想共鸣的形式,直接作用于群体认同的塑造与巩固,实现档案从“工具性价值”到“意义追求”的转变。[40]
另一方面,群体认同感作为情感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正向与否和情感被选择与设定的方向紧密相关。通过档案信息的识别与选择以设定叙事风格,汇聚包含特定情感的内容信息,可将碎片化的情感因子整体化,传达一定情感要素。如节目《朗读者》,通过嘉宾对个人书信、文学作品等(扮演类似档案的角色)的朗读,带动受众的共同情感,以传递主流价值观念(爱国情怀、父子亲情等)。受众在通过“档案”内容获得沉浸式体验的同时,其与节目情感传递相关联的群体认同感也因归属感和自尊心的满足而得以强化。
3.4 转向思考档案作用群体认同的效力
档案学界不应单纯局限于研究档案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力,而是要以整体思维看待档案对群体认同的作用,探讨档案在此过程中的影响效力。
一方面,档案学界应注重从宏观层面把握个人档案—群体档案—泛在档案(如有关国家认同的档案)之间的总体关系,不同类型的档案划分标准不同,反映出其对群体认同效力与作用的不同。因此,构建档案对群体认同的整体解释系統,[41]既符合群体身份关系复杂、相关档案类型多样的现实情况,也适应档案学界在群体认同领域开展整体性、层次性研究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实现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层级的丰富,发挥档案对于衔接各认同层级、塑造群体宏观形象的作用。
另一方面,档案学界应注意从不同侧面辨析个人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动态联系。不同层次的认同感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有可能由于身份的冲突而表现为对立关系(如教徒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同一个体在同一层面也可能因具备多重群体身份(如籍贯地和常住地不同的状况)而呈现身份撕裂的现象。为淡化认同矛盾,避免叙事冲突,档案研究者需注重了解不同层级、不同阶段认同感对立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发掘各环节之间的共同点,以深化相关研究层次,发挥档案促进个体自我和解,群体彼此谅解的正向积极作用。
4 实践策略探析
4.1 尊重群体意愿,维护成员“被遗忘权”
在处理特定群体所形成的档案资源时,档案工作者应尊重群体“被遗忘权”,考虑群体成员对其固有群体身份的认同感与持有意愿。通过协同合作、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相关群体实际情况与留存本群体档案态度。在充分考虑群体态度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公平正义需要,确定相关档案工作的开展形式。对于不愿提及过往的群体,档案部门应在后续档案形成过程中有意剔除可能反映群体成员身份的内容,严格控制现有相关档案的开放与利用,以此消除社会对特定群体身份的歧视,破解群体成员因群体身份而形成的自卑失落心理,推动特定群体融入宏观社会生活的进程,实现迈向和解的遗忘或重塑身份的遗忘。[42]
群体认同感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形态,在社会发展水平、思想文化氛围或重大事件催化下可能发生转变。因此,档案部门要提升对社会环境、重大社会事件的敏感度,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群体认同感的问题,构建同相应群体长期联系的机制,通过定期走访、实地调查等形式,及时捕捉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对档案工作开展形式进行动态调整。以同性恋群体为例,尽管同性恋者一直存在于社会中,并且逐步开拓了属于同性恋者的社会空间,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性恋者才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少数群体,频繁打出“平权”或“权利”的旗号,并且在60年代的石墙事件后增进了群体自信心和认同感。[43]
4.2 适当让渡职能,鼓励成员参与叙事
为解决群体认同强化可能导致成员个性隐匿的问题,档案工作者应结合当前档案形成者日益泛化的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角色,下放部分档案记录权。通过由上到下的专业性指导,鼓励和协助群体成员通过文字、照片,乃至录制具有区域特色的歌曲舞蹈等方式记录个人故事,展现个体价值,共同参与群体记忆的构建。这样一方面可借助档案叙事这一话语权工具,实现档案形成者与解读者之间的互联互通;[44]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群体成员在理解群体工作生活方面更具深刻性和全面性的优势,调动成员构筑群体认同的积极性,推动档案来源与内容丰富化,凸显档案工作包容性的特点。英国诺福克郡的在线社群档案馆WISE Archive便是实践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该项目由志愿者自发组织建立,档案部门提供协助与指导,旨在记录和保存老年人的工作生活,铭记他们做出的贡献。WISE Archive也允许该地区从事衰败行业的工作者们记录其工作经历以形成档案并上传资料库,鼓励他们在故事描述过程中加入照片等素材以展现工作细节,以此为这些长期“噤声”的民众搭建发声平台,[45]体现了群体档案对多样性的尊重,增进了成员对所在群体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4.3 分享共同记忆,激发成员思想共鸣
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理解与和解,[46]档案馆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理应肩负起构筑记忆宫殿、凝聚共有认同的责任。档案部门应通过实践活动激活或动员档案记录活动,挖掘档案内容之间的共同点,出版激发共情意识的档案编研成果,促进群体的共通与和解,实现责任、良知与正义的结合与统一。如以灾难记忆为切入点,借鉴唐山市政府修建纪念墙,无偿镌刻唐山大地震中死难者姓名,为唐山大地震遇难者家属提供悼念平台,汇集个体记忆的做法,[47]收集整合不同区域承载灾难记忆的档案资源,聚焦于挖掘灾难的破坏力以及人性在面对灾难时所散发的闪光点。通过档案反映灾难带给全体人类的苦痛,展现人类抗击灾难、重建家园的决心与努力。激发档案受众共鸣,增进全体人类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的共识,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档案馆社会影响力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BTQ10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Schwartz J M, Cook T. Archives,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Archival Science,2002(1):1-19.
[2][10]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96-103.
[3][11]加小双,徐拥军.档案与身份认同:背景、内容与影响[J].档案学研究,2019(5):16-21.
[4]杜童欣.论档案在强化制度认同中的功能与路径[J].山西档案,2020(4):113-117.
[5][37]张晶,陆阳.档案的群体认同强化功能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9(1):9-14.
[6]王嫱.面向文化认同的档案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D].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9:21-25.
[7]王玉珏,洪泽文,李子林,等.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理论依据[J].档案学通讯,2018(4):52-58.
[8]王萍.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体制外档案资源建设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3(1):24-27.
[9]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通讯,2014(5):29-34.
[12]傅少玲.档案记忆理论视域下台湾地区政治档案实践探究[J].现代台湾研究,2021(1):60-67.
[13]胡莹,崔丹妮.爱国主义教育背景下南侨机工记忆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思考[J].档案学通讯,2020(3):83-91.
[14]展晓鸣,吴志杰.档案记忆观视野下的社群档案开发利用策略研究[J].山西档案,2021(1):94-99.
[15][41]陆阳,蔡之玲.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现状考察与进路展望[J].档案学通讯,2021(1):32-39.
[16]张全海.家族档案与国家认同[J].档案学通讯,2018(2):1.
[17]李云鹏.家庭档案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机制[J].山西档案,2020(3):116-122.
[18]加小双.当代身份认同中家族档案的价值[J].档案学通讯,2015(3):29-34.
[19]张衍,张奕萱.档案学本科生专业认同研究——以上海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J].档案学研究,2020(2):19-24.
[20]张洁.档案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6:32-38.
[21]赵春庄.档案工作者职业状况及职业认同度实证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4):36-42.
[22]张丽,冯惠玲,马林青.转型身份认同过程中档案的功用——以中国农民工群体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9(1):4-8.
[23]陈玉杰.农民工身份认同中档案的作用[J].浙江档案,2018(3):19-21.
[24]闫静,徐拥军.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思想实质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9(4):4-12.
[25][33]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1-172.
[26][28] Kaplan E .We Are What We Collect, We Collect What We Are: Arch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J].The American Archivist,2000(1):126-151.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
[29]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23-24.
[30][32][34]闫静,刘洋洋.档案中的认同悖论——兼论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与机理[J].档案与建设,2021(3):9-14.
[3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EB/OL].[2021-08-30].http://www.nhc.gov.cn/wjw/ 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 b0e9688.shtml.
[35]陆阳.权力的档案与档案的权力[J].档案学通讯,2008(5):19-22.
[36]王静.权力选择与身份认同: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構的两个维度[D].济南:山东大学,2017:23-24.
[38]程慧.英国社群档案参与式管理模式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20:22-23.
[39]李晶伟.档案情感价值的内涵与特征[J].北京档案,2018(11):9-12.
[40]王玉珏,张馨艺.档案情感价值的挖掘与开发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8(5):30-36.
[42]Connerton P. Seven types of forgetting[J]. Memory Studies,2008(1):59-71.
[43]徐立甫.美国石墙事件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71.
[44]乔硕功.时尚视角下社群档案的文化认同价值[J].档案学研究,2020(3):51-57.
[45]钱明辉,贾文婷.国际社群档案包容性实践模式研究与启示[J].档案学通讯,2018(4):40-44.
[46]丁华东,张燕.迈向理解:灾难记忆的力量与档案部门的责任[J].思想战线,2021(3):113-121.
[47]灾难记忆与灾后反思,如何构筑一部全球人类史[EB/OL].[2021-08-30].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63916102601302349&wfr=spider&f 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