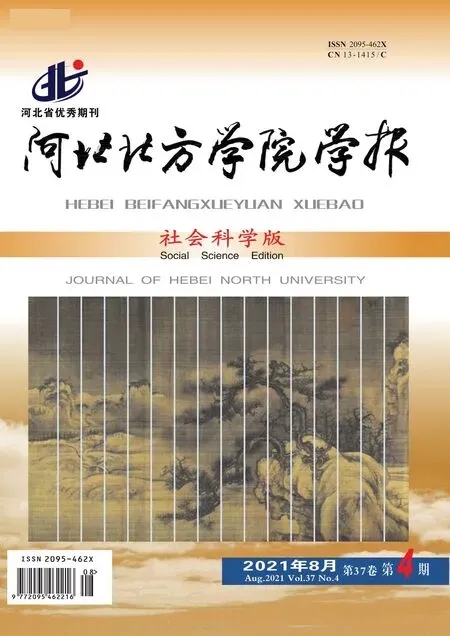连番溃败后的救赎与终结
——重读《高老夫子》
刘 方 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老夫子”形象趋于大奸大恶与至善至仁的两极,如巴金《家》中的高老爷、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遯翁以及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姚思安等,古代文学中的公孙策、贾雨村与范进等皆是如此。鲁迅则借“高老夫子”的形象来把脉一个时代的病症,挖掘时代保守顽固力量的象征性、同构性和反讽性。“高老夫子”易被简单比附为旧学究或封建卫道士等保守符号,鲜有论者对其独特的心理特征作进一步推断,更缺乏对鲁迅小说的开拓性发现。通过分析高老夫子的“巨婴症”心理,可发现启蒙思潮使浑浑噩噩的高老夫子获得了难得的觉醒,但同时也将其送入歧路,而这种觉醒暗含着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对启蒙思潮的警惕。
一、“觉醒”的“巨婴症”患者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带有些许新生希望的魏连殳、吕纬甫和涓生,还是旧式文人孔乙己、高老夫子、四铭与鲁四老爷等,均无法承担启蒙时代建构社会历史与人性道德的使命,更没有走向未来的可能。就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而言,“旧”是鲁迅笔下所有知识分子形象中的本质性特征。“高老夫子”是这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他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椹吃,但他们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树来磕破了头,又不给好好地医治,至今左边的眉棱上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他现在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可以勉强遮住了,但究竟还看见尖劈的尖,也算得一个缺点,万一给女学生发见,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他放下镜子,怨愤地吁一口气[1]76。
小说以近似滑稽剧的反讽语言,着重从人物心理上塑造了一个“巨婴症”的奇葩形象。童年是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童年的成长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走势。高老夫子如今的不快与焦虑皆源于童年因意外受伤形成的眉头上的瘢痕,但他将此归咎于父母照护不力,并长期以来对此念念不忘。这正是高老夫子人生观扭曲的表现,其思维仍停留在童年时期,指向“人的严重扭曲与压抑”[2]。如此不合情理甚至有违人伦的归罪既是心理安慰,也是为讨尚未谋面女学生的欢喜而起,其身体之老与心理之年轻以近乎变态的方式集聚在一起,也使高老夫子具备“巨婴症”①的明显心理特征。《高老夫子》讽刺语言的传神处在于鲁迅对高老夫子应聘贤良女校教员的动机分析上。对于一般社会心理与隐秘心思而言,柔弱的女学生代表了欲望的非常态发泄。高老夫子向牌友老钵夸耀“谋一个教员做,去看看女学生”[1]77,这既是他欲望发泄的表征,也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性。高老夫子的扭曲心理及有违人伦的恶德败行根本不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伦理框架。除欲望发泄外,高老夫子还保持着旧时代有钱有闲阶级的无聊生活习性及贪鄙相,如一众老者聚众“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1]77。从牌友黄三和老钵艳羡高老夫子可看女学生,到老夫子们的聚众娱乐,都呈现出一个“巨婴症”群体的可憎面相,鲁迅对这类人的批判言简意赅又深刻到位。
在空前的历史转折中,一些如高老夫子般的旧式文人借“整理国故”②获得了由幕后走上时代前台的机会,他们对时代改革的风潮与社会的必然行进几乎无所了解,即使有涉,也宁愿选择保守以待和自欺欺人。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的遽变,甚至还将自身的恶德败行以变态且滑稽的方式毫不保留地表演于历史舞台上。殊不知,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是在寓新于旧和旧中孕新的辩证中得以实现,以高老夫子为代表的旧式文人所彰显的诸种不堪是将传统有价值且有意义的人格文化全然抛弃的结果,亦从本质上断绝了他们通向未来新生的路径。进而言之,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鲁迅通过塑造高老夫子这一形象有力地回应了五四时期人性解放偏执化的问题。“顿觉地对于世事很有些不平之意了。而且这不平之意,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1]76高老夫子的“顿觉”与“从来没有”意味着“不平之意”来自于外部生存环境及思想氛围发生较大变动后的自身体验,这一改变实际上也源于启蒙思潮向人性纵深处发展的态势。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启蒙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即“人的觉醒”背景下个人主义的兴起使人的欲望得到复活,这是历次启蒙运动对人性清晰而广泛的影响。高老夫子想要看女学生的动机多显其心理扭曲和有违人伦,但也歪打正着地符合了启蒙时代强调个性解放与伸张人性的社会思潮,且他对自身形象的过于重视也源于这一思潮的影响。鲁迅对这种思想启蒙成果被滥用的现象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这促使启蒙者对偏执化甚至极端化的觉醒有所警惕与反省。
二、双重溃败后的金钱救赎
鲁迅在刻画高老夫子“巨婴症”心理的同时,又让高老夫子经历了欲望体验与逐名体验的双重溃败,展现出以高老夫子为代表的“巨婴症”患者以金钱弥补欲望的全过程,且呈现出动态、立体与日常生活化的叙事特点。小说中,高老夫子首先遭遇了欲望体验的溃败。童年时的意外受伤使其左眉棱处留下了“永不消灭”的瘢痕,“永不消灭”是一种超时空的隐痛体验,既形容瘢痕坚硬不退化,也表达出高老夫子对此无法释怀的心理。人过于注重外表是源于自身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自信心缺乏,进而会形成自卑的心理。担心因左眉的瘢痕被女生发现进而被看不起,这使高老夫子想要去看女学生的欲望体验遭遇溃败危机。而他在应聘贤良女校教员时遭遇的才学危机则再次击溃了他的逐名体验:
如果那人不将三国的事情讲完,他的豫备就决不至于这么困苦。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以及其他种种,满肚子都是,一学期也许讲不完。到唐朝,则有秦琼卖马之类,便又较为擅长了,谁料偏偏是东晋。他又怨愤地吁一口气,再拉过《了凡纲鉴》来[1]76-77。
高老夫子的教学仅停留在照本宣科阶段,教科书语焉不详处即需求助于历史启蒙通俗读物《了凡纲鉴》,预备畅讲的三国与隋唐故事也仅停留在演义的热闹娱乐层面,而非历史教学要求的意义发掘与价值判断。如此假大空的才学、缺乏现代授课技巧与心理素质极差,再叠加动机不纯,导致高老夫子“看看女学生”的计划宣告失败。当然,失败原因亦源于贤良女校的办学动机与性质。贤良女校办学的动机并非是知识习得与思想启蒙,而是借时代兴学风潮以谋利,学校因压缩成本才聘用死气沉沉的校役与不学无术的教员。办学性质上,在多少带点新潮味的女校中,挂名“贤良”招牌并将之作为教育主题,就是与启蒙思潮宣扬的科学与民主等话语的方向性对立。女学生本应承担着未来新生的希望,却在保守氛围的影响下仍专事于提升缝纫等旧式家庭对女性要求的技能,这类代表着未来希望的青年女学生也陷入了旧式生活氛围中而不自知。因此,高老夫子无论有无学识,都注定不能在此长久任教。从事保守派“整理国故”主题教育活动的高老夫子在新式教育场的浅尝辄止,再现了旧时代保守顽固力量卷土重来的企图与失败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当欲望与逐名体验失败后,心情沮丧甚至气急败坏的高老夫子仍试图借助其自身的庸俗人生重启洗刷耻辱之旅。对此,牌友黄三早已为高老夫子铺设了金钱救赎之道。由黄三不知高尔基可看出其文化程度有限,但他的言行无所顾忌,他认为高老夫子的从教行为与时兴的男女学堂为“无聊的玩意儿”[1]78,与其被“何苦去闹,犯不上”[1]78而影响情绪,“尚不如坑拐钱多人傻的后生来得痛快”。果如黄三所料,在高老夫子授课失败且处于“还不舒适,仿佛欠缺了半个灵魂”[1]84之际,金钱开始发挥万能效用。“不舒适”源于欲望与逐名体验的溃败,高老夫子的“半个灵魂”确已丢失,若要保住另半个灵魂,恐怕只能寄托于金钱的刺激。
“阿呀!久仰久仰……”满屋子的手都拱起来,膝关节和腿关节接二连三地屈折,仿佛就要蹲了下去似的[1]85。
这是长幼秩序的紊乱,是以老夫子自居的长辈向“胖到像一个汤圆”[1]85的有钱人的屈膝,是金钱万能时代里人性赤裸的呈现。与之相比,万瑶圃和高老夫子的初次见面却表现出面子上的貌似尊重与实际动作上的虚与委蛇。因为无利可图,客气与恭维仅停留在表面,两个不学无术的老夫子呈现出对损互欺之道。高老夫子“面前的筹码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1]85,金钱虽最大限度地弥救了高老夫子因欲望与逐名体验溃败后的遗憾与耻辱,却不能彻底根除高老夫子不快的复杂心理,小说便在他纠结的心绪中结束。
鲁迅在《高老夫子》中以逐层加深的讽刺力度,完整呈现了一个经历双重失败后又被金钱救赎的可怜可鄙的老夫子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革新时代里的社会渣滓形象。表面看,小说无一处是悲剧,喜剧因素及氛围呈无限扩大状,高老夫子作为“传统生活的虚伪面被严厉谴责”[3];深层看,小说却无一处不是悲剧,旧中国的保守文化氛围与“整理国故”为代表的逆历史行为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因素,这必然引发人们对一个僵死麻木的中国如何新生的思考。此时,鲁迅激昂的战斗精神“却冷得不少”[4],“情绪已转向‘彷徨’,转向波动的怀疑和烦恼的哀伤”[5]。
三、知识分子启示录
鲁迅充分考虑到晚清民初以来时代因素对旧式文人的影响,并对旧式文人源于传统文化积弊的劣根性作出了近乎尖刻的讽刺,也再现了其自身对传统文化辩证统一的认知路径。作为20世纪初文学的时代记录,《高老夫子》更是别有所寄。1923年前后,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与政界兴起了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反智识阶级”潮流。关于“智识阶级”问题的讨论在最激烈之际,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遭遇了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的全面否定:“二十年代初期,一群披上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的绅士,由于竭力维护封建思想文化,或者同封建势力完全采取妥协的态度,他们已成为五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阻力。”[6]这场“反智识阶级”的思潮几乎获得了所有五四文化及文学层面的呼应与肯定,“反智识阶级”成为当时时代的共识。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也否定了“智识阶级”的作用与地位,在鲁迅与新月派及太阳社的论战中,“反智识阶级”话语频频出现:“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7]229鲁迅看穿了这类所谓新派知识分子在西装革履下隐藏的士大夫灵魂,嘴上说着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忠实信徒,实则是端着架子且背靠旧势力的帮闲嘴脸。对于提倡尊孔复古的读经者,鲁迅则认为他们是“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狂造谣,蝇营狗苟”[8]。这一思潮反映在文学写作中,即表现为鲁迅、罗家伦与叶圣陶等作家几乎否定掉了所有新旧知识分子。具体而言,若说鲁迅对孔乙己、魏连殳、吕纬甫和子君尚持有一些同情与理解外,那么对七大人、鲁四老爷、高老夫子与四铭等旧式文人所呈现的“具体人生世相的荒谬与昏乱”[9]就给予深刻的批判与辛辣的嘲讽,他们作为一个反动的、僵死的甚至是麻木的旧世界里的遗存物被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高老夫子成为这类人物形象谱系中的典型代表,其无权无势更无丝毫人生荣耀,也没有一点旧式文人的良善道德情怀,因有违现代公序良俗且有悖现代健康人性而遭到辛辣讽刺,成为“反智识阶级”思潮背景下最先被淘汰出局者。
鲁迅对以高老夫子为代表的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就《高老夫子》所继承的一种讽刺文学传统而言,小说上承《儒林外史》对旧式文人的讽刺,高老夫子的性格行为特征是《儒林外史》中被讽刺人物的多点集中。同样,小说也下启钱锺书《围城》的反讽叙事。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围城》中有着精彩再现:“但是隔壁李梅亭的‘先秦小说史’班上,学生笑声不绝”[10],“卡片教授”李梅亭的教学效果最大程度上源于其糊弄学生的高超本领。与李梅亭相比,高老夫子缺乏随机应变能力,更显愚笨与痴拙。就此而言,高老夫子作为不学无术的旧式文人形象特征的集中展现,鲁迅对他的观察仍是基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框架,小说呈现与丰富的是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境遇中的虚无面。至于真正的知识阶层,鲁迅认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满意,所感受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7]227。
鲁迅亲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在对思想启蒙的认同与坚守过程中对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出了持久而强烈的批判。在鲁迅看来,觉醒并不为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天然具备,正是在对魏连殳、吕纬甫、高老夫子、鲁四老爷、涓生与子君等新旧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中,鲁迅发现了中国启蒙运动中存在的巨大危机,即这些知识分子放纵人性与有违道德的行为源于启蒙运动中不负责任的觉醒与解放。鲁迅在深层次上讽刺与反驳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欲望复活的无良化与泛滥化范式,其中的警醒意味尤为浓重。也正是在对包括高老夫子在内的彼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全面否定中,鲁迅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行进感到深深的绝望,这也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行进的主要脉络之一。
注 释:
① “巨婴”是一类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识,一旦出现超乎自己预期的情况就会情绪失控并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人群。从心理素养角度而言,“巨婴”具有3个主要特征:1.过度依赖,缺乏独立人格;2.自我中心,缺乏共情能力;3.自我主体认知责任缺失,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何芳.“巨婴”现象的现实表征与社会背景探讨:关于当下国民心理素养热门话题的分析与思考[J].青年发展论坛,2021(1):82.)
② 1923年,胡适创办《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并提出“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的口号,提倡以科学方法从事“国故学”,并拟定近200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对“整理国故”具有理性的反思态度,在他看来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革新,“整理国故”会使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出现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