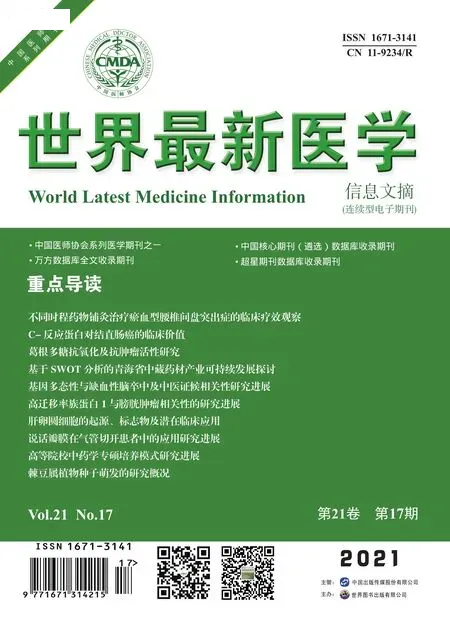中西医结合联合火针治疗痤疮的临证经验
李晓沁,冯永芳,2*
(1.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5;2.武汉市第一医院,湖北 武汉 430022)
0 引言
痤疮(acne vulgaris)归于中医学“粉刺”范畴,俗称青春痘,是一种主要累及面部的毛囊皮脂腺单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多好发于青春期,青春期患病率为86.9 %。中国人群截面统计痤疮发病率为 8.1%[1]。但另有研究发现超过 95%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痤疮发生,3%~7%痤疮患者会遗留瘢痕[2]。本病初起为粉刺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可演变为炎性丘疹、脓疮、结节、囊肿、癖痕等。本病多无自觉症状,若炎症明显时则可引起疼痛及触痛。一方面与皮脂腺分泌脂质过度,皮脂腺角化功能异常及排出不畅导致皮脂堆积,堵塞毛孔。另一方面与患者体内雄激素水平过高导致痤疮杆菌等毛囊微生物增殖,从而使面部产生炎症反应也使得获得性免疫被激活有关。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强调了遗传因素在这一疾病中的作用。不过其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1 病因病机
中医学对痤疮的认识和治疗由来已久,《素问》中“汗出见湿,乃生痤痱……郁乃痤”就是关于痤疮皮疹的最早记录。而《肘后备急方》中“年少气充,面生施疮”则进一步阐明了本病的好发人群是青少年。而关于痤疮的病因病机,则见于以下文献:其中《诸病源候论·面皰候》曰:“面皰者,谓面上有风热气生疮,头如米大,亦如谷大,白色者是也。”而《医宗金鉴》论“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每发于面鼻……色赤肿痛,破出白粉汁”。
从古至今不同医家对本病的认识各有异同,辨证纷杂繁多,从而衍生了不同的证型和治法。而归结起来,痤疮的病因病机复杂,五脏皆可致病,非仅肺胃也。由湿、热、瘀、虚等病因而成,多呈虚实夹杂。一般病因病机为肺经蕴热,外感风邪,邪热犯于肌肤,上熏头面而发;或因脾失健运,水湿内停,郁久凝结成痰,气血凝滞肌肤,或因过食肥甘。脾胃受纳运化失常,湿热内生溢于肌肤。由于部分患者在经前发疹或者皮疹加重,又与冲任不调,气血失和有关,常从肝肾论治。
2 辨证论治
2.1 辨皮损,分型论治
局部皮损辩证是临床皮肤病诊治最直接的依据,也是最直观的判断,有其自身的特点。若皮疹以粉刺,皮色或红色丘疹为主,或有痒痛。舌红,苔薄黄,脉数。属肺经风热证,临证多治以疏风宣肺,清热散结。若皮疹以红色丘疹、脓疱、结节为主,皮疹红肿疼痛,面部、胸部、背部皮肤油腻;可伴口臭口苦,纳呆,便溏,粘滞不爽或,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属湿热蕴结证,治宜清热利湿。若皮疹以结节和囊肿为主,色暗红或紫、也可见脓疱,或有疼痛,日久不愈。舌暗红,苔黄或腻,脉滑。痰瘀结聚证,治宜活血化瘀,消痰散结。若皮疹以粉刺、丘疹为主,或有结节,色暗红,或伴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平素性情急躁;月经先后不定期、血块、经前心烦易怒或皮疹加重。舌质暗或有瘀点,苔黄,脉弦或涩。治宜调和冲任、理气活血。医者应当依据患者的不同皮损情况而选择相适应的药物,同时依据不同的证型选择不同的治则。辩证论治是取得疗效,减少复发的关键。
2.2 辨整体,随证加减
皮肤病辨证论治应本于原发皮损同时结合整体辨证。皮肤病虽然种类繁多,病因复杂,但总离不开“形于外而成于内”,所以从整体出发,把握细节,四诊合参,病证合一,随证加减,从而直达病所。而从痤疮来看应注意不同的年龄阶段其辨证有所侧重。青春期痤疮,多从肺、胃论治;女性青春期后痤疮患者,多从肝、肾论治,久治不愈者,多存在本虚标实[3]。
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熬夜频繁。睡眠长期不足,久则阳气不足,阳虚则气化不行。毒无源已助其外达,故皮损多为粉刺且难发,常常色黯。而饮食方面人们大多喜食肥甘厚腻、生冷、辛辣刺激之物。其势必阻碍脾胃受纳运化,气机阻逆而化热,从而湿热内生;溢于肌肤。故皮损多有脓疱,易于反复。基于以上的情况,故应嘱咐患者(1) 规律作息,避免熬夜。(2) 清淡饮食,避免肥甘厚腻、生冷、辛辣刺激之物摄入。(3)面部护理尽量简单,尽量不用化妆品,同时注意防晒。(4)保持消化道通畅。而又因精神压力加剧,易于诱发痤疮,而肝主情志,喜条达恶抑郁,肝主疏泄,肝失疏泄则肝木克土,肝脾不和则脾失健运,从而水湿内停,上犯于肺表,溢于肌肤而发疹。故患者皮损多在下颌两侧,多为结节样丘疹,质地偏硬,伴疼痛,易于反复,同时女性患者多经前期加重,易伴月经不调、痛经、经期血块等。此时医生则应当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及时调解、减轻、消除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为患者制定更为完善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3 火针
针对痤疮患者,若皮损为粉刺、丘疹、脓疱,点刺一次即可,稍以挤压,将皮疹上的黑头粉刺或脓疱分泌物、脓血脓栓清除;若皮损为坚硬的结节,则在其中心及周围多处点刺,不需挤压;若为囊肿,刺破囊壁时有落空感,用棉签轻轻挤净内容物,消毒棉签沾干并轻按针孔使其暴露。治疗痤疮用火针,主要是借助火针穿刺之力,开门祛邪,引邪外达,从而起到穿刺引流、化腐生新、祛瘀消肿、软坚散结的作用。
4 病案举隅
患者,女,31 岁。2020 年7 月10 日初诊。面部反复起疹2 年余,再发加重半月。症状:面部可见散在丘疹、丘疱疹、结节、红斑。前额、双颊、口周及颈部可见密集分布的粟米大小的白头粉刺及炎症后色沉。手脚偏凉、心烦、易燥,睡眠差、精神稍差、食欲可、月经量少伴血块、经期伴腹痛、头疼,小便正常,大便偏干。舌暗,苔少,脉弦。既往病史:子宫多发囊肿,宫颈纳氏囊肿。方用丹栀逍遥散合桂枝茯苓丸加减:牡丹皮15g,栀子10g,柴胡12g,当归10g,白芍15g,赤芍10g,白术10g,甘草6g,桂枝10g,茯苓10g,桃仁10g,红花10g,夏枯草10g,酸枣仁30g,益母草10g,陈皮10g,黄芩10g。7 剂,水煎服,每日2 次,每次200mL 温服。嘱经期停服中药。此外外用阿达帕林及林可霉素b6,口服多西环素,结合火针治疗。2020 年7 月16 日二诊:面部结节,丘疹、丘疱疹均有减少,结节较前稍平,白头粉刺较前略有减少,无明显新发皮损。前方去夏枯草加莱菔子10g、苏子10g、白芥子10g。2020 年7 月30 日三诊:白头粉刺减少变平,结节部分消退,遗留色沉,无新发皮损,停用多西环素,以逍遥散合桂枝茯苓丸为主方加减治疗,其余治疗方案不变。一个月后,粉刺基本消退,面部仅遗留色沉。停用中药、阿达帕林、林可霉素b6 及火针,外用sod 熊果苷及维生素e 乳膏治疗。
按:桂枝茯苓丸出自《金匮要略》“妇人宿有症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症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断后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枝茯苓丸主之。”丹栀逍遥散出自明代薛己的《内科摘要》,是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加牡丹皮、栀子组成。其中柴胡、当归、白芍、夏枯草疏肝养血,牡丹皮、栀子清肝经之热,白术、茯苓以健脾养血,乃治其本;桃仁、赤芍活血化瘀,桂枝以邪外出,治其标;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共奏疏肝清热,化瘀养血之功。此患者经量少、心烦、易燥,睡眠差,脉弦辩为肝郁血虚化热,肝在志为怒,有疏泄之功。《素问·举痛论》曰“百病生于气也”。故用丹栀逍遥散以疏肝解郁清热、健脾和营;以调畅全身气机,使气血调和。亦有研究[4]证实其对抑郁情绪等具有较好的疗效。故本案用此疏肝解郁。而患者月经血块伴腹痛,手脚偏凉,舌暗考虑为血虚夹瘀,故用桂枝茯苓丸活血化瘀[5]以消留滞胞宫之淤血。此案肌腠郁热、寒邪克宫是标,而冲任壅实为本。故用二方合用以泄其壅实,壅实消则痤疮自愈。除此之外,配合火针及西药治疗来帮助患者改善油脂堵塞皮脂腺的情况及控制炎症从而减少皮疹和色沉的发生。中西医结合联合火针治疗来帮助此患者缩短病程,控制病情,疗效显著。